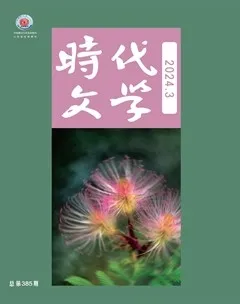山顶上的雪
太阳一沉,天很快便黑了下来。堂叔的儿子小尾巴拢了一堆火,我们围了探着头瞧,脸上一片赤红,伸了手过去,手指头也映得透明。我接过萝卜,咬上一口,低了头嚼,吞进一口甜水,抹抹嘴,递给身旁的二弟,二弟也照做,又把萝卜传给了小尾巴,说:“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做,这是我爸教给我们的。”
火苗颤抖,登时蹿起老高,像是绯红色的巨人。风刮过来,凉得紧,火被吹歪了,一疙瘩暗红,接着腾起一团火星,风落了,火又亮了起来,抻开,愈烧愈旺,噼噼啪啪地响。
堂叔打胡同口踅来,睇了眼二弟,凑过来,压着声音说:“快回家吧,你爸出事了。”二弟和小尾巴争咬着萝卜,声音脆响,带着水声。我拍拍二弟的背,硬硬地说:“好生待着,完事儿就回家。”说完碎着步子上前,跌跌撞撞地随堂叔钻进了胡同。
一
“叔,我爸怎么了?”堂叔沉了声,止了步子看我,然后哀哀地说:“刚才大队来人说的,煤气中毒,人在岗位上没了。”我顿一顿,问:“我妈知道了吗?”“知道了。”路越走越窄,黑影挡了下来,风在耳畔嘶嘶作响。
家里来了不少人,有大队里的干部,还有同氏的长辈,簇在前屋,十来口人,紧凑得很。我进里屋,母亲倚靠在炕上,不动,身子软着,凄凄地看,见到我,脸一垮,呜呜地哭,一旁是堂婶搂着三弟,都不说话。堂叔屋里屋外来来回回走动,见大队领导,忙掏烟,点上,递过去,说了些什么,然后走过来,对我说:“按村里的讲究,棺材还要回老屋停两宿,算是归魂,再下葬。”我说:“听叔的。”他又说:“你守护在旁,尽尽孝道。”我点头。
不多时,堵在外面的人全进院了,人影在眼前移来移去,然后是一口被漆得乌黑的棺材,摇摇晃晃,一耸一耸的,像一星火在暗夜里跳,摆一摆,落在我眼前的地上。堂叔推了我上前,大队领导过来,朝我说:“你得看一眼……算是确定了。”棺材盖被挪开,露出一小截,在场的人都凑了过来,极静,都瞧我。我喉咙紧了紧,看了,是父亲,衣领笔挺,像他从前一样,爱干净,好整洁。我点头,轻轻叫了声:“爸。”那一小截又盖上了。我抹了脸,硬挺挺地站着。
同氏的几个长辈每人掌握一门手艺,养家糊口,有的打铁,有的做木工,父亲给牲口瞧病。当年父亲险些被划成右派,在家农耕了一阵子,后给生产队放羊。他为人爽利,家里总来各种各样的人,各种来路,我问,他很少答话。后来他再回畜牧站是六年之后了。那天,父亲兴冲冲地进屋,啜了一口水,对母亲说:“把我的东西都收拾收拾吧。”母亲问:“做什么?”他索性坐下来,捻了烟丝和纸,在双膝间卷起来,说:“我要回畜牧站了。终于给跑下来了。”母亲问:“哪个畜牧站?”父亲这次没再说话,嘴巴紧锁着,半晌,搓一搓板正的脸面,方自说自话,声音模糊得很:“换了一个远点的站点。”我直了身子站在一旁看他忙前忙后,不打紧地问:“那地儿在哪儿?”他只说:“外乡,一个叫远村的地儿。”我又问:“骑着车去?”他说:“骑车,骑一天。”我心下明白,远村如其名字,是个遥远的地方。
夜里,水汽凝结。
堂叔叫上我,抱了一床被子,两人一前一后往老屋的方向走。老屋当年归了老爷爷的独子,此人以算卦为生,心性孤僻又不爱干净,鲜少与村里人来往。两间小矮房挤在村里最偏远落寞的犄角,屋外墙壁脱落,露出半爿土坯,满墙写着大大小小扭曲的“月朋”,是用黢黑的木炭写的。屋里有丝光亮,渗在当院,蛛网一般迷蒙。父亲的棺材就放在主屋。
堂叔说:“知道怎么守灵吗?”我说:“知道,别让蜡烛灭了。”堂叔揾了揾脸,点头,又说:“来风挡一挡,再烧些纸。里屋有炕,你累了歪一歪。”我点头。堂叔点了烟,扭身回屋,叫了我,沉吟片刻,慢慢地说:“早先,大队领导过来说了一下你父亲的情况,你也知道,是煤气中毒……但后来又说,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姓肖的人……这人是县畜牧站的,去远村畜牧站传达工作,宿在你爸那儿了,也没了。”偶尔有一两声乌鸦叫,飞不多远,止了,又叫,之后再回归静寂。
我问:“还有个人?”堂叔说:“你父亲工作的地方,山高路远,一天只通一趟车,那个姓肖的人,恐是错过了那趟车,没走成。”“那个人呢?”“运回人家那个乡了。具体是哪儿的,大队也没细说,只知道是县畜牧站的人。”话语在空气中震荡。我没再言语,心颤颤的,悲伤的同时,多了深重且无名的愧疚,这种感觉我平生第一次有。
“还说什么了?”堂叔透过烟雾看我,脸缩着,静静立了许久,方说:“怪得很,这事儿怪得很。”我问:“哪里怪?”堂叔慢慢地移眼看我,又不说了。待那支烟一点点烧光了余烬,他起身,出院门前说:“你爸还说开春要盖房,木材石料都运来了。你说这房还盖不盖?”我垂了眼,说:“叔,你做主。”夜很静,有种压迫人的力量,比剧烈的声响还让人难以承受。堂叔的喉咙嗡嗡作响,发出鼾声一般的声音:“这个主你叫我咋做?”说完掩上门走了。
我静静地琢磨堂叔的话,父亲的这场意外,还有那个姓肖的人,在木棺前坐下,捻了纸烧,顿一顿,又模糊地悲伤起来。
三天的守灵,抽筋剥骨,我像死了一遍,抑或重新活过来了一回。但我始终没和母亲提那个姓肖的人。
雾很浓。天还没亮透,陆续来了人,母亲也在,哀怨地泣着,声音细若蚊蚋,被二弟的哭声掩埋进了缝隙里。不多时,同氏的长辈也来了不少。唢呐在屋外响,声音一抖一抖的,棺材被摇摇晃晃地抬上了拖拉机,车开得极慢,几个男人扛了铁锹走在前头,女人孩子牵衣顿足跟着,队伍沉默地沿着山路走,黑色的湿树枝一般,不多时便被厚雾吞没了。落坟的地方离家不远,远远地就见有人围在那儿等着,土被刨开,像揪起了一块疤瘌,露出乌色的血水。队伍一点点凑近了,棺材从拖拉机上运了下去,一点点往墓坑里坠,有人递了纸糊的元宝进去。大寮让我拿了铁锹从四个方向各铲了一铲土入穴,男人们便一齐填了土,埋了,不多时,原地拱起一座小山包,插了孝棍,白色的纸在风里舞。一旁火堆燃着,火影跳了跳,拢起了一小片亮,刺破浓雾,舔燃了一件纸糊的衣服。
山顶上还有一层积雪,亮亮地闪着,如同凝固了的蜡油,被时间锁在了冬天。温度升了,雪一点一点地融化,露出土地的颜色,太阳照在上面,像锦缎上针脚的暗影。
我和二弟照旧读书,父亲是因公走的,我家因此多了一个进厂的名额,但我成绩一向很好,又以参军为志向,进厂当工人不是我的理想,二弟又年龄尚小,此事便不了了之。开春,劳碌而繁忙的生活消解了母亲的悲伤。县里每个月发给我们家一些抚恤金,挣工分的任务全落在母亲一人肩头。家里还有一小块自留地,整个春天,母亲都在整理土地,春天结束,夏天播麦茬玉米,秋天更是繁忙,奔波于丰收的辛劳之中。三弟有时候在堂婶那里,母亲要瞧堂婶脸色,不敢常去,再下地,就把三弟拴在炕头。
父亲老早就从大队要来了宅基地,石料木材也都运了过来,盖房子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如今他没了,房子是盖还是不盖。大寮来过几次,催问盖房的事儿。我做不了主,便去地里找母亲。
玉米堆着,被母亲塞进鼓囊囊的筐子里,齐腰立起,母亲掮了,肩头摆一摆,身子矮去一截,见我来,不自在起来,筐子也不听话,闷声砸进地里。我跑去,掀起来,揳进锁骨窝,筐子如焊在肩头。母亲叹道:“你怎么跑来了?”说完揾了揾脸,额头上水光闪闪,汗珠留下青黄色的阴影。我没说话,热风砸向脸蛋,吹得人蔫蔫怯怯的,母亲在后面托了筐子,两个人弯弯曲曲走好远。
我撂下,抹抹脸,问:“咱家的房今年盖吗?”母亲瞧我,说:“你说?”我说:“大寮又问起来着。”母亲目光短了,哀哀地眨着眼,说:“不是咱们不想盖,堂叔算是积极的,当家子没人抻茬,问了,也支吾不作声,我听你堂婶说,他们小范围开过会了,都不想帮着盖了。”风把额头的汗吹干,脸面紧了些,像是要扯破的纸,我说:“知道了,明年开春再说。”
空气里有土腥味,厚重地扎进肺里,我和母亲都没再说话。走了良久,我想起了什么,心悸起来,说:“妈知道那个事儿吗?”母亲的头发在暖风里翻滚,她用衣袖沾了沾脸上的灰,说:“什么事?”我说:“父亲出事的时候,还有一个姓肖的人,那人也没了。”母亲攥住我的胳膊,低声说:“我知道……想想就害怕,我没有一天睡踏实过。”
我问:“怕什么?”
母亲停了脚步,看着我,脸像一块牛皮纸,闪着粗糙的光泽,说:“怕那家的人找来。”
二
父亲的死已经逐渐沦为一桩无法撼动的陈年旧事,关于他的一切,哪怕只发生在几个月前、几年前的事情,都被盖上了尘埃,鲜有人再提起他。直到某一天,那个肖家的女人来了。
堂叔早早地敲门,哑了喉咙叫着我的小名,让我出去。我出了门,看见一个瘦长的身子,肩头一块灰色的包头巾,酡红的脸蛋。我知道她是谁,羞于看她,慌忙中叫女人进了院子,转身再去叫堂叔,见他已经走出去老远。再看女人,那是一张寂静的脸,碰上我的目光,嘴角挤了挤,像瓷片上的裂缝。我留她原地站着,赶紧进了屋。
妈妈正要去地里,见我慌张的样子,大概猜出了几分。我说:“那个女人来了。”母亲问:“哪个?肖家的?”我点头,母亲反倒松一口气,踅进屋舀了水,匆忙抹了脸,出屋。
女人错了错乌黑的眼珠,问:“这是不是张家?家里的男人以前是不是在远村畜牧站做兽医?”女人皮肤红黑,像是在红色的炭火中烤出的铜币,在太阳下闪着健壮的光泽,这让母亲的脸看上去更苍白,像是被熨烫过的纸。母亲没回答女人,她显出了少见的胆魄,问:“你从哪里来?”
女人眼光钝了,指指身后的山,说:“山那边。”
母亲的脸面僵得硬硬的,嘴角掀了掀,便不再问了,只戒备地看着女人。
二弟跑出来,躲在后面,抱着母亲的腿悄悄地看。
女人鼻翼翕动,嘴巴向下扯了扯,母亲便知道了什么——两个女人绝口不提男人们的死,她们在缄默中达成了共识,都不去揭开彼此身上的伤口。她们是那场灾难的孑遗,有着相通的敏感和脆弱。
成片的安静,安静得叫人难以忍受。母亲叫我去倒点水,然后径直进里屋抱了三弟出来。三弟的样子稚嫩又原始,被母亲欲掩欲遮地藏在怀里,像是锐利的暗器。女人瞧见,怯怯地说:“你家有几个娃娃?”
我听闻,不作声,看母亲。母亲说:“三个。”接着又说,“你呢?”女人说:“一个。”瞧瞧不远处的二弟,又说,“跟他差不多大。”
二弟被点了名,颇得意,又不自在,跑了出去,很快折回来,给女人拿了两块前一天捡的铁片,极圆,像铜币,但比铜币稀罕。女人接过,摊开手掌看看,又捻了放在一旁的桌角,只眯了眼冲二弟笑。二弟见状转了身子,藏于门外,细细朝屋里打量。不多时,二弟拽我,然后沉了沉气,眼珠子幽幽地闪着光,小声说:“你看她的鞋子。”
女人的两只鞋被泥水浸透了,汪着水,在地上黢出两团煤黑的影子。
母亲叫我和二弟带女人去河边清洗。河水就在堂叔家房后,深处极深。小尾巴精着身子在河里凫水,招呼二弟下水。二弟水性极好,能沿着河床一直游,远远地泅于水中,不见其踪,再露出头来,已经到了河的尽头。我胆子小,充其量横着游一个来回。二弟没耽搁,解了衣裳,跳进去。小尾巴擤擤鼻子,问:“这人是谁?”我摇摇头。小尾巴抹了脸,略略有些疑惑,没作声,只慢慢地眨了眼看。
女人在远处,脱掉鞋袜,挽了裤腿和袖口,蹚进河,静静地立在水里,水没了腿肚子。两截子粉白扎进去,她渐渐往深里走,似乎比我们还亲近这水。我瞧见,忙喊:“喂!”女人停住,我又说:“里面深。”她便不动了,摘下包头巾,蘸了水,擦起了脸,又净了脖子。小尾巴游过去,在不远处瞧,女人便拍了水花,小尾巴也照做,水花噼噼啪啪地砸了过来,他就笑,抹了脸和女人说:“我还会憋气呢。”女人说:“你能憋多久?”小尾巴不作声,只颠倒了身子,水面上露出一双脚,摆了摆,水顺着腿管子流,河面极静,女人数起了秒数,不多时,水面响了,脚没了去,原地钻出了脑袋,小尾巴拢了头发,咧嘴笑了,问:“多少?”“三十二。”小尾巴又说:“我能踩水,你瞧。”说罢便忙不迭地往深里去,教起女人来。女人乐,说:“我是旱鸭子。”然后往岸上走,捡了鞋,攥了,挤出两摊水,摆在一旁,晾晒起来。
待鞋子半干,女人趿上,整了整衣袖,原先包头的头巾就散散地坠在肩上。小尾巴立在水里,看得眼呆,我捡了石子往水里扔,搅起动静,小尾巴还是凝了神看,我知道他在瞧那女人。二弟草草穿了衣服,随着女人往家走。我问小尾巴:“你不走?”小尾巴说:“我待会儿。”我便紧了步子跟上去,不多时听后面传来小尾巴的声音——“我明天还在这儿。”
待进了家门,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叫女人坐下一起吃,女人紧了紧脸面,拘谨地坐下,捏了一双筷子,并不夹菜,只三两下就把手里的馒头啃了,然后又撂下筷子。母亲说:“多吃点。”女人不语,站起来,听见三弟在里屋哭,忙过去。我也站起来,却被母亲揪住,见她朝我摇摇头,便作罢,只静静地听,心一跳一跳的。里屋声音短了,不多时就静了下来,我悄悄起身,站在里屋门外,只见三弟在女人怀里蹬了蹬,揪扯着她的头巾,极为安静,偎着睡了。
女人临走前,母亲问我:“要不要给她一些钱或者粮食?”我说:“不用。”母亲沉默了半晌,又说:“那她是为了什么来?”我摇头。母亲说:“她来,不给些粮食不踏实。”说罢舀了两碗小米,装进袋子,给女人送了出去。
女人之后又来过,两个女人不仅找到了熟稔的话题,还有知己知彼的宿命、感同身受的境遇,以及和这种处境媾和的共同决心。像是为了打消母亲的疑虑,之后女人每次出现都不空着手,有时候拿来几枚鸡蛋,有时候捎来一把小菜,或者一袋杏子。最让人惊讶的是,女人有一次带了一件自剪自裁的小衣服,大小正合适三弟穿,母亲研究过女人的针脚,见扎实细密,继而羞赧,像是永远无法企及般地说:“这针线活做得真好。”我听闻,笑笑,不知道母亲是否和我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戒备与提防之中偶尔也在某个瞬间开始期盼起女人不定期的到访。
三
林间荡着热气,女人又来了。
我躲在树荫下制火枪,远远地听树叶响,不抬头就知道,是小尾巴。“那女人是谁?”汗淌了下来,小尾巴揩了,见我噤声,他目光短了,轻轻地说:“我见她又来了。”我把炮仗里的火药掏出来,放入枪筒,捻了枚响炮塞进枪的起火点里。小尾巴凑近,凝了神看,黑黑的手指头在枪口处略略擦了,又收回去。呼吸声逐渐平静下来,但热气依然挤在我俩中间,他又问:“她是谁?你肯定知道。”我上了弹簧和扳机,从腰里扯了绳子,扔给小尾巴一头儿,说:“系在树上。”小尾巴捡了绳子,麻利地拴起来,把火枪绑在两棵树之间。
我轻轻动一动小尾巴的肩膀,他躲到我身后。枪筒朝着稠密的树林,深不见底,看得人眼晕,这种未知感让人恐惧且着迷。我拽动扳机,扳机勾动弹簧,把那粒响炮砸碎,爆炸出的火星点燃火药,接着“砰”的一声巨响在森林里炸开。
我俩朝那片隐匿的树丛深处望去,极静,几秒钟或者更长。我不知道最精彩的部分究竟是那“砰”的一声,还是之后深不见底的寂静,或者两者皆令人沉醉。小尾巴抽动鼻子嗅着火药味,说:“问你呢,她是谁?”我垂着头,手指抹着枪筒,说:“你甭管。”小尾巴登时红了脸,目光灼灼,说:“要是你爸活着,我一准跟他说你做火枪。”
我回了家,见只有母亲和三弟,便问:“肖家婶子呢?”母亲说:“上河边了。”我说:“去那儿干吗?”母亲说:“捡了你们脱下来的脏衣裳,说是去洗。”我问:“干吗让她去洗?”母亲见我模样严肃,忙说:“她上午来的,我地里还有活儿,就叫她在屋里坐着,她偏要跟着一起上地里,人多口杂的,我没叫去,她便自己找事儿做,说洗些衣服。”听罢,我便跑了出去,沿着河找,在窄瘦的河床上远远瞧见了她,二弟跟着,在一旁跟她说些什么,远远瞧见我来,挥一挥手,朝我跑了过来,喘着气说:“哥,你咋找来了?”我说:“你怎么没拦着她?”二弟被我问愣了,说:“拦着啥?”我把气吞进肚子里,说:“没什么。”说罢走过去,咽一下,又回过头,问:“我瞧她刚才跟你说得热闹,你们都说什么了?”二弟说:“没说啥,她就问我知道衣服怎么洗吗,我说不知道,都是脱下来由母亲洗,她便教我怎么搓,怎么拧。”我又问:“没说别的?”二弟说:“说了。”我停下,轻轻地问:“还说啥了?”二弟说:“就问咱们上学的事儿,问我读几年级,认得什么字。”我顿一顿,又问:“也问我来着?”二弟说:“问了,就是问上学的事儿。”我便不再作声,只静静地听着,慢慢地走。
到了跟前,女人抬头看一看,继续忙着,我有些不安,不知道说些什么,只瞧,顿了顿,把没洗的那两件捡了,蹲在不远处自己洗起来。女人见状,便很高兴的样子,也不说话,不似刚才那般活泛,只安静地洗。
白昼渐短。
小尾巴家房后面的河冻住了,冰床像是一块巨型琥珀,乳白色的,里面生长出巨大的斑驳和纹路,光亮和暗影变成黑色的洞穴和白色的棉絮被锁在了河里,河床两岸的柳条断在冰上,湿漉漉的。远处的河道沙漏似的缩了起来,极窄,穿过木桥,桥那边又是开阔的一片,极静,冰面完好如镜,没有人在上面滑过,偌大的波浪般的水纹被冻在了河床里,像是等待着被犁垦。
我低头整理冰鞋。父亲教我的,把两根八号铅丝捆扎在木块下面,当作冰刃,再用绳子把木块和鞋子绑在一起,能在冰上滑很久。见我来,小尾巴远远地滑过来,不说话,只盯着我看,眉眼间有模模糊糊的笑模样,顿一顿,哑声说:“那女人是不是来索命的?”我一怔,抬头说:“你胡说什么?”小尾巴眼神亮了起来,说:“她丈夫被你爸牵连,你说她不来索命来做什么?”
我蓦地心中一惊,耳边嗡嗡响成一片,拉了小尾巴的胳膊和他扭打作一团。冰面极滑,我俩曲着腿在冰上打起了圈,互相摔着,又各自摔着,身旁远远近近地围了不少人,都是孩子,没人劝,反倒围着叫好。我俩都打不动了,手又冻得麻木,便前后松了手,仰面躺在冰上,长长短短地呼气,热气荡起来,蒸着脸。柳条挂在树上,如倒挂着的生锈的长钉,齐齐地扎向眼前,我俩便都被唬住,呆了似的。
一旁的孩子见没了下文,怏怏地散了。
须臾,我问小尾巴:“你听谁说的?”小尾巴瞧一瞧我,说:“你不知道?村里人都这么说,那女人时不时来,就是为了讨个公道。”我说:“不是我父亲害的。那人是死得冤,但我父亲也死得冤。”半晌,我又说,“是煤气中毒,知道不?是意外。”小尾巴又问:“那女人来到底是为啥?”我怔住,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她来这儿是为啥。”小尾巴说:“她没说过啥?”“没说过,就是因为没说过,才熬人。”小尾巴只凝了神望着我,没言语,半晌揪了一截子柳枝,说:“你说她下回啥时候来?”我不作声,坐起来,抻了衣衫。他见我要走,还躺着,搓一搓通红的脸,又说:“她下回啥时候来?来了你告诉我。”一长串雪白的热气从他嘴里跑开,我笑笑,说:“我爸从前总说,灰总比土热。”小尾巴侧过脸,急匆匆地问:“你说啥?”我说:“是夸你的话。”小尾巴把那截柳枝扔过来,脸上也露出笑模样。
母亲见我回来,问:“你上哪儿去了?”我说:“滑冰。”她说:“一直滑到现在?”我没言语。
晚上,三弟睡了。母亲搬来荆条编织的筐,比鸡笼略大一些,罩到火盆上,叫我把湿鞋脱了下来,放到上面烤,我照做,拧身上了炕,和二弟在炕上玩扑克“跑得快”。那副扑克是父亲带回来的,其中有二十多张早已丢失了,我便攒了硬纸片,比照着剩下的临摹了,画上桃心,方块,梅花,逐一补齐了54张牌。二弟总输,玩了几局失了兴致。
母亲在一旁说:“那女人也是命苦,这两次话逐渐多了些,我才知道,她从外乡来,一走走多半天,才能到咱们村。”顿一顿,母亲悄悄地说,“你说,咱们是不是该为她丈夫的死负责?”我把二弟支开,看着幽微的火光在影子里跳动,摇头说:“咱们家为什么要负责?就因为她男人死在我爸单位?”母亲说:“他要不是去看你爸,也不至于。”母亲的脸在晦暗处,停一停,又说:“奇不奇怪,你说她来,绝口不提你爸的死……来了就是帮着干活,偶尔说两句不打紧的话。”我问:“妈也觉得奇怪?”母亲点头,说:“她这一趟趟地来,不问,也不提,更是折磨人。”“妈为什么不直接问她?任由她占据主动。”母亲目光散掉,说:“还用问?她来肯定是为了那件事,不问也知道。”
须臾,我问:“咱这房还盖吗?”母亲被问住,停了半晌,说:“你堂叔怎么说?”我湿了眼眶,说:“咱们家的事总是由别人来做主。”小小的一点红映在母亲的双颊上,水一般洇开。我硬了心,说:“咱家不是有个进厂名额……过了冬天我就进厂,不读书了。”母亲细细地瞧我,问:“不50FNPYq4vpJeEufd889blA==是说等着当兵?你不是一直想当兵去?”我凝神望着从荆条里蹿出的火光,说:“不当了,让二弟当,我们俩都出去赚钱。”
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女人来过,父亲的死亡又开始频频被人提起,还有更多的猜测,仿佛那不是一件正常死亡,在特殊的年代里,人言可畏。父亲的悲剧不再是他个人的了,而是传染给我们整个孱弱的家庭,波及整个村庄。我逐渐恨起了那个女人,觉得她一次次的到访就是在折磨母亲和我们,她把对命运的不公平都怨在了我们身上,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来制裁我们,来缓解自己的痛。我也恨同氏的长辈们,他们不是陌生人,但却用陌生人的方式来待母亲和我们,这种态度远比陌生人更可怕,更残酷冰冷。我更恨堂叔,他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那个人,但他始终如一的缄默让我明白了那是一种最大程度的狡猾。我唯一不恨的就是小尾巴,因为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四
下雪那天,堂叔过来叫我从他们家牵走一只羊。
羊在圈里,都缩着脸,咩咩地叫,看见我凑近便都立了起来,噗噗地吐着气,蹄子突突地敲着,像是要把地凿开。十几只羊里,我只认识那只豁了耳朵的。那耳朵是我弄豁的。父亲熟悉牲口,又读过不少外面的书,他跟我说,生活在北极圈里的驯鹿人总是把鹿的耳朵豁开一块,叫打耳标。鹿的眼睛能记住给它打耳标的人的模样,从此那人就是它的主人了。我也照样子在羊的耳朵上豁口子,但那只羊用蹄子踢了我,它没有归顺我,反而对我多了份仇恨。后来父亲去了远村畜牧站,堂叔把放羊的活儿接了过去,也包括这只豁耳朵。
豁耳羊扭过身子,用灰色的软塌塌的屁股冲着我,它的毛在风里竖着。
堂叔说:“我还记得你爸在的时候,每年年底都给我送点儿羊肉,叫我们家上下老小能痛痛快快吃顿肉。”我说:“这些事我都不记得了。”堂叔吐了口烟,拧熄了烧得红通通的烟头,又说:“那天小尾巴说的话,勿往心里去。他傻,你还看不出来吗?”我说:“我不知道叔指的是哪件事。”堂叔弯腰,把烟头直挺挺地插进雪地里,拍拍我的后背,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豁耳羊动了起来,在圈里走过来又走过去,发出呜呜的低鸣,它身上的肉疙疙瘩瘩地攒动着,硕大的眼睛盯着我直勾勾地瞧,蹄子一点点向后挪去,积蓄起力量来。
堂叔问:“选好了吗?”我说:“选好了。”堂叔说:“那一只?”我点头。
堂叔打开门,其他羊呼啦啦浑水一般冲了出来,唯独那只豁耳羊在原地不动。堂叔上去拽,它仍不挪窝,蹄子钉在了地上。堂叔抄了铁锹又进去,扇在豁耳羊的头上,铁锹被坚硬的羊角顶了回来,又撞过去,再顶回来,来回两次,那羊便急了,倏地腾了出来,角像削木头的刀子,分毫不差地扎在堂叔身上。堂叔的手挡在前面,被钻出了个洞,血汩汩地流。我把堂叔拉了回来,叫他闪到一旁,硬着心定定地站住。见我上来,羊忽地切了方向,身体软软地砸向墙面,一下,两下,直到那灰白色的影子也渗出来一团猩红,方停了下来。我心中一颤,喉咙紧紧地缩着,喊了一声堂叔。堂叔只短促促地应着,凝了神看,半晌方说:“你看那角。”羊的角已被自己生生撞去了一截。
豁耳羊停了下来,鼻子嘶嘶地吸气,嘴里发出遥远的哀怨声。其他羊又都跑回了圈,尖利地叫着,蹄子声像壶里煮沸的水。
豁耳羊跟着我走了,被我拴在院子里,模样像溃不成军的士兵,它头上的毛浸在伤口里,冻成了一层黑色的薄薄的冰壳。我拿菜叶喂它,它只垂着头细细地叫,我又换了粮食,它依然不为所动,渐渐地我明白了,它是在绝食,想赶在这个冬天结束自己的生命。
没过两天,羊果真柴瘦了,肉紧紧箍起来,包着骨头,直耸耸地立着,像个影子。我摸了摸它耳朵上的豁口,它大的眼珠子如栗黄色的玻璃球,瞳仁宽阔齐整,我从那圆溜溜的珠子里瞧见了自己,还有父亲,我们是它的主人。
天地被冻住了似的,万物停滞。我们很快就忘记了死亡。
雪下了一天一夜,拱了起来,被绵绵无尽的山脊托着,仿佛是铅色的巨兽,呼着银色的哈气。终于出了太阳,雪停了,太阳把坚硬的山烤成了胶状的、絮状的、水状的,雪水湿润了山背,迎来了女人和她的儿子昆宝。
日头正高,山上远远的有两个黑点。母亲抱着三弟在当院里晒太阳,三弟粉色的舌头正舔着水晶一般的指甲盖。我瞧见了山上的人影,回头望望,没说话,然后跑了出去。
我朝女人挥手,女人也朝我挥起手来。我在村口瞧,女人身旁的男孩脸红红的,眼睛蛮有劲头,凝了神看我们。我们在前,女人和孩子在后面,听女人说,他叫昆宝,是她唯一的儿子。我便又扭了头瞧,昆宝这回抬了头紧紧地盯着我,嘴巴嘟囔着什么,我听不清,只觉得他气鼓鼓的,脸蛋像下面藏着活物似的扭了扭。我便不理他了。
村口有人抽着陀螺,声音响脆,在空气中裂开,细碎出锐利的回音,昆宝远远便听到了这个声音。我们凑了过去,停了会儿,抽陀螺的人甩下背上的鞭子,抽了一记更响的,咧嘴笑笑,说:“看在这个小孩儿的面儿上,我得再使劲抽一个。”
我瞪了眼那人,然后看看昆宝,他的脸像是被冻住了,板正极了,看不出表情。鞭子声又传了过来,这次是在我们的耳边,我问昆宝:“你没见过这个?”昆宝依然没说话,只盯着那只在日头下扭转出闪亮的光的硕大的陀螺。
二弟远远地跑过来,看见了女人,又看了看昆宝,极为高兴,冲我说:“妈叫你把羊宰了,中午咱们吃。”我听了走在前头,匆匆回家。
“羊死了就没法吃了。”母亲说,“趁还活着,赶紧宰了。”我知道母亲的意思,留女人和昆宝一起吃。羊在近处听着,朝我们粗暴地吐着气,两排瘦弱的骨架撑着,蹄子狠狠地扎进地里,笃笃地凿。它知道自己气数将尽,随便什么都能叫它丧命。我摸摸它,又柔顺地扯了扯它的豁耳朵,它不再哀号,也不再挣扎。
等二弟带着女人和昆宝进屋,我便准备起来。
我牵了羊,二弟帮我把绳子捆在羊的四个蹄子上,扎了结扣。这只柴瘦的羊缩着,叫个不停,费力地翻滚扭动起来。我搬起它的脑袋,放了血,血很快从盆子里溢出来,不多时,筋肉懈了下来,血凝了,不再流出来。我和二弟抬着把它吊到木桩上,剥皮,我从父亲那里学会了不少手艺,刀子翻转着。要是父亲,能一口气忙完,我中间歇了几次,直到那只羊卸下了灰色的毛,露出惨白的皮。二弟端了盆子,给羊开膛破肚,把内脏接走。我长吁了口气,拾了抹布擦去手上的油脂,看到一个红脸蛋的孩子正站在我身后。
昆宝的眼睛狠巴巴的,朝我说:“我宁愿不吃这只羊。”我说:“它活不过今天的,它病了。”昆宝问:“什么病?”我垂了眼,说:“不好说,不吃东西。”他的话像冰冷的鞭子抽了过来:“不吃东西就要被宰掉?”我说:“它太瘦了,已经奄奄一息,和死了差不多。我见过死去的羊,你见过吗?我见过,那不会是你想要的结果。”我的确见过死去的羊,那些灰色的皮肉在荒草之间腐烂,剥落,剩下的白骨宛如被石灰冲刷后定格下来。昆宝依然看我,不依不饶、直勾勾地看定了我。我干干地一笑,忙说:“只管吃吧,这是一顿好饭。”二弟挤了过来,朝昆宝说:“不要问那么多,我可饿坏了,我一年到头才吃一顿肉。”我看看二弟,又看昆宝,他眼睛里闪烁着光亮,我知道他要哭了。我又扭头看看女人,女人正在屋里和母亲做饭,无论如何我不能让昆宝哭,天知道他会胡诌些什么。我顿一顿,低低地说:“听着,这是它的命,养羊就是为了吃肉,难不成埋葬它?”二弟听了嗤嗤地笑。我不作声,心里发酸,喉咙紧了紧,咽了,只觉得干疼。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还是错,在生与死这件事上我丧失了明辨是非的本事。对父亲的死,对眼前这只羊的死,都一样,当我对死亡束手无策时,再背负上罪恶感,哪怕是一丝愧疚的念头,都会让我雪上加霜。
昆宝着实让我意外,他没有哭出来,非但没有哭,还用手背抹去泪花,一个人舀了水,擦起了地上的血水。我跟他说:“别收拾了,冻住更麻烦。”他没听进去,依然埋着脑袋抹地上那摊血水。
羊肉在烈火的炙烤下越来越蓬松,膨胀起来,像是一块海绵,厚墩墩地黏在锅上。火舌跳动,二弟用冰块喂着火,火瞬间就灭下去,冰块化了,不多时火又蹿了出来,锅子周围愈来愈热,羊肉缩成了一块块,硬得跟燧石一样,二弟在锅子上拨动,那几块形如石状的肉便滚动起来。羊骨被剔了出去,两块纤瘦的骨头在火里愈烧愈黑,炭火和羊骨逐渐融为一体,骨头被灰烬覆盖,生出黑斑状的灰渍,二弟把骨头掷进火堆里,不多时骨头便被灰埋了起来,看不见了。
我和二弟都不作声,纷纷琢磨起来刚才和昆宝的对话,二弟像失了魂,看着火里的灰发呆。羊是父亲带回来的,那时候它还小,是只羊羔,被父亲抄在腰间,雪白的屁股朝前,脑袋藏着,父亲把它递过来,它便进了我的怀抱,我捧着它像捧着一条雪白的河。白河——我还曾给这只豁耳羊起过名字,只有我和父亲知道。
我拾起了铁钳,把弟弟推向了一边,说:“别看了。”
五
我、二弟和昆宝占据了整张桌子,二弟将贪婪的舌头伸出来,舔了舔那块肉。
昆宝问我:“这只羊活着的时候都做些什么?”我说:“吃树叶,吃菜叶,在从前,后来就什么也不做。”昆宝没动筷子,继续说:“如果活得更长些,它还能在河里游泳,在山上跑,吃草,羊爱干净,不喜欢不洁净的草,爱吃柔嫩的、带咸味或苦味的草。”我从桌子前站起来,骨头里嗡嗡作响,母亲脸通红,不再说话,她按着我坐下。
二弟边咀嚼边说:“你也养羊?怎么知道这么多。“昆宝说:“我爸爸养过。”他说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爸爸”这个词一出现,饭桌上便静了下来。我不再说些什么了,因为我也是父亲教我养的羊,父亲没了,如今我把羊也杀了。二弟吐出骨头,伸手又夹了一块肉,我打了下他的胳膊,说:“别吃了。”没人再去夹锅里的肉,都呆呆地看。不多时,二弟哭起来,昆宝用黑黑的手背抹了抹脸,他脸颊上多了一块灰色的印记,像是死亡的阴影又笼罩过来。
屋里冷极了,我不再饥饿,胃里像是塞满了石头,沉沉地压着,嗓子里偶尔钻出阵阵血腥味,我感觉自己要吐出来了。
是母亲先开的口。
“那天……两人很久没见,聊得投入,肖师傅误了末班车,就宿在了畜牧站。半夜还有人去找过孩子他爸,叫他给牲畜看病,敲畜牧站的门,没人应声,那人就回去了。要是推门进去,兴许能救两个人的命。”母亲的脸像水纹一样动了动,泪水顺着她的鼻梁坠了下来。
我们等着女人说些什么,她一字一句都听了进去,然后苍白的嘴唇吐出模糊的声响,咽了下,又断断续续地说起来:“老肖死在外乡,稀里糊涂的人就没了。这些话我大概能猜出个八九,只想再听个人跟我说说,我才甘心。否则,我会想一辈子……”
那天是周五,昆宝有些发烧,从村卫生所回来便躺在床上昏睡,晚上天都黑了,她洗了脸要躺下,大队突然来人,说孩子他爸出事了,信息少得很,只知道是在远村,说是下去传达工作,煤气中毒,再问,大队的人也不知道,只是反复说着运遗体的事儿。越来越多的人聚在家里头,有出主意的,但更多的是猜测,等大队领导走了,开始有人劝她,叫她去看看,多渠道打听打听。日子久了,开始远远近近有人背着她嘀咕,说她丈夫是不是树敌了,得罪过谁,这种话多了,传到昆宝耳朵里,他也总问。她决定走出去问问。去了远村,又去了丈夫之前工作的县畜牧站,得到的都是那套官方的话。
女人说:“我去过远村,去过两次。”
母亲看向女人,问:“那儿什么样?”
“坐车坐好久,下了车找那个畜牧站,第一次还没找到,那地方人少户少,看不见几个人。后来又去了,找到乡里去问,乡里的人不多说,只说我丈夫是县畜牧站的,具体的事还要问县里。后来我又去了县畜牧站,县里说算是因公殉职,再问,也问不出其他的。问来问去,都是那么几句话。”
“那院子什么样?”
“院子空空的,大门也关着,我想是远村的人给关上的,算是体面。”
“屋子里呢?”
“屋门锁上了,透过玻璃看,里面还有东西,但不多了。”半晌,女人又说,“你们家不难找,翻过山,进了村子,沿着路一直走,左手边高处的那个房子就是。每次我回去,昆宝都在家门口等我,见我第一句话总是:‘妈妈,问了吗?’我说没有。昆宝又问:‘那是一家什么样的人?’我说:‘和咱们一样。’昆宝又说:‘人好吗?’我说:‘好人。’”
母亲双手掩面,手里埋着哭红的脸,像是悬而未决的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她嗓子里呜呜的,说:“你应该一来就说。”
女人湿着眼,说:“问不出口,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其实是怕听到的。”
我印象中,那次对话母亲和女人都很克制,没有说太多,两个女人像是把所有的悲伤都吞咽了下去,只说一些相互慰藉的话,但每个字都是仔细斟酌之后的,带着极重的分量,她们在用一种极为含蓄的方式揣摩着对方的心。多年之后我知道,这是一种本能。
我和二弟送女人和昆宝走,我们四个人沿着绵长的山脊前行,雪在山体间悬挂着,伸出铅灰色的触角,风把山体吹得轰轰作响。
地上的雪很厚,又湿又亮,踩上去,脚底下的白就成了阴影,仿佛有一部分脆弱而纯真的东西从这个世界上随之消失了。我们一路纵队,我踩着昆宝的脚印,二弟踩着我的,女人落在后面,她的脚印很孤独。
女人看了看远处,又看了看半山腰的太阳,说:“你俩回去吧,甭送了。”说完便拉了昆宝继续走,昆宝扭头看了我们一眼。二弟和我站在雪里望着,直到女人和昆宝成了两个黑点,接着我听见风的声音,还有二弟被风吹散的话:“哥,肖家婶子还会来吗?”
大队来人,把我从征兵的名单上划下来了,换成了二弟的名字,我的名字出现在了工厂招工的名单上,开春就能进工厂当工人了。坏处是,我一进厂,县里就不再给我们家发放抚恤金了;好处是,一听说我不再读书,而是要进工厂赚钱,同氏的长辈们都主动过来问盖房的事。
女人没再来过,关于父亲的死的种种猜测,也没有人再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