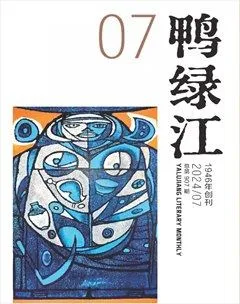汪曾祺笔下的女人是水做的吗
逐渐清晰的女性形象
李建新:
当我们谈论某位作家时,往往会听到一个笼统的说法——他很善于写女人。意思不外乎作家笔下的女人性格很突出,文字描述的女性人物心理很细腻,很“像”读者实际生活中接触过的人乃至本人。汪曾祺先生笔下,让人过目不忘的女性人物很多,像《受戒》中的小英子,《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沅,《徙》中的高冰、高雪,还有晚年几个短篇小说里的小姨娘章叔芳、小孃孃谢淑媛、薛大娘等等,形象鲜明,各有不同。
我想这次不妨从汪曾祺笔下的女性谈起,他怎么欣赏、怎么写女性的美,包括他的观察角度和小说技术问题,还有他的女性观。
汪曾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绝大部分人物有原型。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女性人物来写?是不是选择即代表了某种看法?他对女性的立场来源是什么?和西南联大的教育有没有关系?也可以通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来说明某些问题。
徐强:
汪曾祺初登文坛,1940年最早的小说之一《翠子》就开始了女性书写。小说写幼小的“我”丧母后,由父亲抚养,而父亲整日在外游荡,由丫头翠子陪伴照料。失母的孩子,依恋父亲,更依恋温柔贤惠的大丫头翠子。三十岁的父亲忘怀不了逝去的妻子,每日在妻子坟头流连。有人劝他早日续弦,但他都置之一笑。翠子照料家很细致周到,但常常发呆,以至于小主人公埋怨她总跑神儿、不给自己讲故事、不跟自己玩。十九岁的翠子有心事了,她对孩子的父亲有着隐隐的爱意,贴心照顾;记得他的生日,为他置办庆祝。“我”央求父亲叫翠子永远留在这个家,父亲却决意叫她回家,因为她要嫁给一个跛子。父亲拒绝为自己庆生,却带着儿子去上坟,纪念母亲的忌日。次日起床,“我”看见翠子红着眼睛站在床头。小说从孩童的眼睛和口吻来观察和讲述,通过翠子对于“我”的父亲的引而不发的感情,表现了少女翠子爱情的萌发。“我”与汪曾祺幼年经历非常相似,小说显然是汪曾祺自己早年生活的反映,翠子也就是汪曾祺的保姆大莲的化身。小说在题材和技法上似乎都令人想起契诃夫《厨娘出嫁》的影子。对女性感情的尊重、同情,是汪曾祺的一贯思想,这显然在幼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
另外,汪曾祺曾提到大莲对于父亲续娶的张氏有敌视态度。从常理来说,大莲作为一个情感萌动的少女,在汪曾祺的生母杨氏去世后,潜意识中以家庭女主人身份自居、对男主人产生某种爱恋心理,从而对于新进门的张氏抱有敌意,这样的推测不算离谱。那么,汪曾祺初期习作就有《翠子》这样的叙述,说明这种经验在他的心理中是很重要的,也证明幼年、童年、少年汪曾祺对于成人世界的感情关系已经有敏锐的观察。
李建新:
我大致捋一捋汪先生全部的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他“先锋时期”的小说写到女性的不是很多,徐强兄举的一个例子之外,还能想到的是《小学校的钟声》里的“初恋”女孩儿。1949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算是早期创作的总结,全部八篇小说,女性形象几乎不怎么出现,人物形象特别突出的也少,写得比较具体的也就是《落魄》中的扬州人,《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陆鸭,等等。
徐强:
总体来说,早期写作中对女性的表现的确很少,除了建新兄说的那几篇,还有1942年的《结婚》一篇,写女主人公宁宁新婚前后的心理,总体还是意识流风格,心理意义大于社会意义。在他的同乡朱奎元晚年献出的昆明时期汪曾祺写给他的一批书信中,几个女孩子的事情是汪曾祺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反映了汪曾祺当时交际状况之一斑。其中有一位女性,我认为在汪曾祺心目中地位很重要,那就是他和朱奎元在从广州去越南的轮船上结识的那位漂亮优雅、带一个女儿的广东女子。汪曾祺和朋友经常到她家去聊天,和她的女儿玩得也很好。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写小说《绿猫》,虚构了“我”去看望一位在昆明结识的有才华的、正在写一篇叫《绿猫》的小说而苦恼写不出的朋友“栢”,其中引用“栢”的一篇旧文,回忆昆明时期认识的一个新婚的广东女士,提到在她家中看到地毯上的猫的景象,并借由柏的口吻对她的丈夫表达“你真幸福”的艳羡。引文后面,作者汪曾祺补述道:“这里所说××(女子的丈夫——徐注)我也认识。”那个女主人呢,不少人暗暗地为她而写了诗。我们的栢兄大概也写过不止一首吧。想想他说“××,你真幸福”那股子傻愣劲儿,这里暗示了作为青年学生的汪曾祺和“栢”对于年长十岁左右的成熟女性的朦胧的渴慕之情。我发现《绿猫》所引用的“栢”的文字,有些就是汪曾祺本人的,例如他引用了早期散文《花园》,移植到“栢”的名下。由此我判断,《绿猫》中的“我”和“栢”是一体两面,都是汪曾祺的写照。汪曾祺晚年仍然对这个女子念念不忘,为她绘画、作诗。画跋中说:“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软缎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诗云:“四十三年一梦中,美人黄土已成空。龙钟一叟真痴绝,犹吊遗踪问晚风。”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猫》中再次描绘这一场景:“这位母亲已经过了三十岁了,人很漂亮,身材高高的,腿很长。她看人眼睛眯眯的,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她斜靠在长沙发的靠枕上,神态有点慵懒。”可见这个广东女子在汪曾祺心目中长久盘踞、不稍减退的印象。文中对陈女士不乏性感色彩的“恍恍惚惚的成熟的美”的描绘,和“犹吊遗踪问晚风”的念念不忘的“痴绝”心态,暗示出她是年轻的汪曾祺心中幻想和崇拜的对象,影响到汪曾祺对女性的认知和写作。
李建新:
汪先生的早期创作和后期差异很大,“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基本上是对自己20世纪80年代之后创作的总结。可能就是从《受戒》中的小英子开始,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形象清晰的女性人物吧。从小英子,到巧云、沈沅、高冰、高雪、薛大娘等,非常鲜活,人物性格也非常突出。
徐强:
给汪曾祺笔下的女性人物稍微分下类,大概有:以侉奶奶(《侉奶奶》)、文嫂(《鸡毛》)为代表的旧时下层劳动妇女,勤劳、善良而命运凄惨;以小英子(《受戒》)、巧云(《大淖记事》)为代表的底层少女,着力在爱情生活中表现她们健康淳朴的美;以小姨娘(《小姨娘》)、王小玉(《百蝶图》)为代表的女性突破社会偏见,追求自主爱情的形象;以孙小姐(《珠子灯》)、高雪(《徙》)、裴云锦(《合锦》)为代表的中等家族女性,这几位都受过一定教育,有新女性特征,但在惨淡没落的家庭,苦闷、抑郁而终;以沈沅(《寂寞和温暖》)、白蕤(《天鹅之死》)为代表的受迫害的知识女性形象,有社会批判意味;非正常婚姻爱情关系中的女性,如露水夫妻(《露水》)、娼妓(《八千岁》《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乱伦(《小嬢嬢》)、尼姑之爱(《仁慧》),越到后期这类大尺度的叙事越多,其中寄寓着对女性的强烈同情和对人性的肯定。在时代分布上,旧女性多于新女性,可能显示了汪曾祺对新社会女性把握不足的问题。在主题上,女性叙述也明显表现出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一自我定位。
杨早:
汪曾祺曾经回忆,他在读到沈从文的小说之前,已经读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但他很少提及后两者的作品。虽然没有证据,但我大胆推测,除了叙事手法与风格的差异,汪曾祺的阅读趣味或与几位作家笔下不同的女性观有关。巴金、郁达夫的小说里很少出现“健康的”少女之美,而汪曾祺与乃师沈从文一样,都会将审美的理想对象锁定为远离俗世纷扰、自由生长的少女。
我统计了一下汪曾祺笔下的性别称谓,发现关于职业、身份的描述,汪曾祺仍然习惯用全称来指代。比如《汪曾祺全集》提到“作家”1500多处,其中“女作家”只有47处;“工人”230余处,“女工”只有29处;“教师(教员)”计140余处,“女教师(教员)”只有两处。但是,如果以两性的泛指而论,男女的差别很大。请看这组统计数据:
“女人”331+“女的”135+“妇女”83+“女子”47+“女性”27+“女同志”23=646
“男人”91+“男子”49+“男的”43+“男性”11+“男同志”(0)=194
关于男女的描写,确乎又更集中于少女(女孩子),其中“女孩儿”174处,“少女”97处,合计271;而“男孩儿”34处,“少男”4处,合计38处。
如果从伦理关系角度考察,“女儿(闺女)”共433处,“儿子”则是344处,相差不大。“父亲”(566处)则远胜于“母亲”(266处),“祖父”(194处)“祖母”(94处)更是如此。但在更为口语化的“爸爸”(116处)、“妈妈”(181处),数目比则刚好掉转过来,似乎家庭中的女性更适合出现在口语化的场合。
以上统计,并不绝对客观科学,但看重“少女”“女儿”的趋势是很明显的,揆诸印象,最让读者记忆深刻的,确实也是小英子、巧云、高雪、王玉英、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等一系列年轻女性,在后期高邮书写与经典重写中,这种倾向也非常明显,这里不一一枚举。显然,在汪曾祺笔下,年轻女性身上寄予的审美理想与人性光辉,是别的类型不可替代的。正如汪曾祺评废名的小说云:“废名的作品有一种女性美,少女的美。他很喜欢‘摘花赌身轻’,这是一句‘女郎诗’!”(《<废名小说选集>代序》)
使女性更诗化
李建新:
汪曾祺写女性,很少用直接描写。他在创作谈一类文字中,交代过一些“技巧”。20世纪90年代,他在短文《美在众人反映中》说:“用文字来为人物画像,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中外小说里的人物肖像都不精彩。中国通俗演义的‘美人赞’都是套话。即《红楼梦》亦不能免。……一种办法是写其神情意态。……另一种办法,是不直接写本人,而写别人看到后的反应,使观者产生无边的想象。希腊史诗《伊里亚特》里的海伦皇后是一个绝世的美人,她的美貌甚至引起一场战争,但这样的绝色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荷马在叙述时没有形容她的面貌肢体,只是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看到海伦的几位老人的惊愕。”《大淖记事》中写巧云,就用了这种方法:“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分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酸疼。泰山庙唱戏,人家都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杨早:
汪曾祺擅长写女性是公认的,笔下鲜明的女性形象不知凡几。其实从整体来看,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就是偏柔美,也就传统认为比较偏女性化的。用王国维的话说,汪曾祺更偏向“优美”而非“壮美”,选择“婉约”多于“豪放”(这倒很像他的大胡子同乡秦少游)。他在《泰山片石》里说:“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又批评汉武帝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感矣!”像是“狗一样地乱叫”,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是“学洒狗血,装疯”,而汪曾祺推崇的泰山叙事如《诗经·鲁颂》里的“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都是比较写实,比较中正平和的。汪曾祺说的“抓挠”应该就是作者理解一个对象、一种现象的进路。
李建新:
柔美、婉约,是中国诗的传统风格之一。他晚年还有一篇短文《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文章首先承认文学的教化功能,但作者认为教化不是强迫的、灌输式的,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其实也和他说过的“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一致。文章中他明确总结道:“一个作品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是作家个人的事。拿出来发表,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他小说里的女性人物也是“诗化”的。后期有些更“大胆”的短篇作品,比如《窥浴》中的虞芳,她很欣赏的学生岑明偷看女职工洗澡,被剧团的电工、武戏演员群殴,虞芳上前拦了下来,把岑明叫到自己的单身宿舍里,脱了衣服让他看。说这篇小说“大胆”,是其直接写到了和性相关的内容,但写这些并不是出于猥亵、猎奇的目的,而是和美、自由相关。汪曾祺自我评价这篇小说是“一首现代抒情诗”。包括他写过两遍的薛大娘,也是诗化的女性形象,不让人觉得很污秽。
杨早:
汪曾祺晚年写薛大娘等女性人物,同时是把女性落实为“人”,有七情六欲的更真实的人。在他看来,自自然然的女性是很美的。《薛大娘》的最后两段说: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不妨再从一篇散文来谈。
同样是写泰山,汪曾祺对于民间的泰山神是碧霞元君而不是东岳大帝很感兴趣。他在《碧霞元君》里引前人笔记称“礼岱者皆祷于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岳神久矣”(福格《听雨丛谈》)。泰安百姓“终日仰对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王照《行脚山东记》)。汪曾祺认为,这是“原始社会母性崇拜的远古隐秘心理的回归”,因为母亲象征着“生”,“假如说东岳大帝是司死之神,那么,碧霞元君就是司生之神,是滋生繁衍之神。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母亲神。”所以他引用明万历八年山东巡抚何起鸣的说法:“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特别指出“这里的‘父’字可删”。也就是说,“母亲神”成为了汪曾祺理解“太大了”的泰山的抓手,进而成为他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抓手,后来汪曾祺在《<国风文丛>总序》里重提此事:“海之神是女性,顺理成章。但是山之神碧霞元君却也是女性,是很耐人寻味的。民间封神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是女权主义者。”汪曾祺显然认为,民间对女性神的认可与崇拜,其实是代表中国民间对女性、对母亲的朴素的信仰,这种信仰超越了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传统,足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因此汪曾祺在同样讨论女性神的《水母》的结尾说:“研究这种题目有什么意义,这和四个现代化有何关系?有的!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汪曾祺是一名作家,不是学者。所以他对于民间信仰,以至于神祇性别的理解,不完全是民俗学、社会学的视角,而是首先从审美出发。因此他说:
水母的塑像,据我见到过的,有两种。一种是凤冠霞帔作命妇装束的,俨然是一位“娘娘”;一种是这种小媳妇模样的。我喜欢后一种。
这是农民自己的神,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这是农民心目中的女神:一个能干善良且俊俏的小媳妇。农民对这样的水母不缺乏崇敬,但是并不畏惧。农民对她可以平视,甚至可以谈谈家常。这是他们想出来的,他们要的神,——人,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头上的一种压力。(《水母》)
这一段可以看作汪曾祺对自身作品性别观的一种阐释。
美、自由和尊严
李建新:
《红楼梦》中,作者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读者常常觉得是对女性的尊崇,其实这仍然是一种“男性视角”,“水做的骨肉”仍然是男性眼中物化的女性,所以不可避免。宝玉又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汪曾祺常常通过作品为女性争取自由,不是把女人作为附属物,而是要和男人平权。我觉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改写的民间故事和《聊斋新义》等短篇作品,更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和人性的看法。1987年改写的《螺蛳姑娘》,基本情节和民间流行的故事没有太大区别,但民间故事多是大团圆结局,“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类。汪曾祺在幸福的结尾之后又加以续写,种田人“初得温饱,不免骄惰”,对螺蛳姑娘“稍生侮慢之心”,但是螺蛳姑娘性情温淑,并不介意。后来有一天,种田人把秘藏的螺蛳壳取出来,用筷子敲着逗弄婴儿:“丁丁丁,你妈是个螺蛳精!橐橐橐,这是你妈的螺蛳壳!”螺蛳姑娘听到这个,突然就爆发了,跳回螺壳一去无踪影。这个修改的结尾代表了汪曾祺对女性尊严的看法,男人由勤劳变得骄惰,还在女性容忍的范围之内,后来把妻子的个人隐私和尊严拿来开玩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螺蛳姑娘终于忍无可忍。
我记得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的《黄英》一篇,也改了结尾。他在创作谈中说:“我把《黄英》大大简化了,删去了黄英与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我不喜欢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骄惰”“俗不可耐”的男人,在汪先生这里,配不上美丽聪明的女子。
杨早:
汪曾祺的两性观,散见于他的各种文体,比如,对于本色当行的京剧,汪曾祺也同样强调:“粗豪和妩媚是辩证的统一。男性美中必须有一点女性美。”故此他对裘盛戎被嘲笑为“妹妹花脸”鸣不平,认为裘对花脸这一传统男性粗豪符号的改造“很讲究,很细,很有韵味,很美”(《裘盛戎二三事》)。同样,汪曾祺也会用“妩媚”来形容他心目中的才子赵树理(《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进而论之,汪曾祺习惯用性别反转的手法,来呈现世界的某种被刻板印象遮蔽的本相。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几易其稿的《寂寞和温暖》。小说中沈沅的南洋出身,应该取材自汪曾祺夫人施松卿,而沈沅在农科所工作,被划成右派,则是汪曾祺自身经历的变形。那么汪曾祺为什么要将小说主人公设定为一位女性呢?我猜测因为他并不想写右派的苦难历程,像从维熙、张贤亮,他们的右派小说比较强调右派知识分子的生存绝境,同时往往用来自女性的拯救(尤其张贤亮)来喻示民众对知识分子的景仰与援助。然而沈沅不是这样,她感受到周围的恶意与温暖,但与爱情无关,她更多是作为一名有赤子之心的技术员,与她遭逢的世界达成某种和解。小说原名《寂寞》,“寂寞”本身是一个知识化的形容词(汪曾祺因此在修改《鸡鸭名家》时将养鸭人的“寂寞”替换成了人物会使用的“冷清”)。而“寂寞”对于知识分子沈沅来说,是恰如其分的。这个词来自张老对她的强调:“搞农业科学研究,是寂寞的。要安于寂寞。”沈沅是可以安于寂寞的,她也不嫌弃没有文化的女工,甚至不讨厌马夫王栓身上带着汗气的酸味儿。我认为汪曾祺将沈沅设定为女性,多半要制造这种反差感──女性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里,很难与底层民众打成一片。而具有这样难得品质的沈沅,仍然逃不过受难的命运。
只是,来自周边人群的“温暖”,让沈沅完成了从“逆来顺受”(丁玲)到“随遇而安”(汪曾祺)的转变。不需要旁人的救赎,沈沅已经获得内心的安宁。而“打仗出身”的赵所长对沈沅的看重,更像是对“革命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某种隐喻,赵所长希望推进农科所专业研究,沈沅才能获得她价值的体现。这让人想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香草美人”的借喻传统。但汪曾祺的写法,突破了“香草美人”那种哀怨的、依附的基调,女性也好,知识分子也罢,都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寂寞》越改离“惨”越远,最后直接更名为《寂寞和温暖》的缘故。
沈沅的形象,跟《受戒》里的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薛大娘》里的薛大娘,构成了呼应的关系。后面这几位农村女性,在感情方面,都是主动的、进取的、不拖泥带水的。这是知识分子沈沅需要历经磨难才能从民间习得的处世态度。汪曾祺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感觉农村的小姑娘,在思想上比城里富庶人家的女儿少一点束缚,比较爽朗,她另有一种健康的美。我的表姐表妹、女同学,都忸怩作态。农村的女孩儿没这一套。我说我要写,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发表以后人们问,你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说,就是写的人的美,人的健康的美。(陈永平采访《汪曾祺访谈录》,1995)
徐强:
相对于茅盾、张爱玲、沈从文等公认为善写女性人物的作家来说,汪曾祺的女性人物在复杂性上、深刻性上要逊色,这一点毋庸讳言。他太注重氛围,注重生活本身的叙述,消解戏剧性,就难以在矛盾情境中展开人物内在冲突。所以在写法上,比如在心理世界的描写上,他往往以抽象概括、观念宣示为统领写出人的行动,而在情绪展示、心理分析方面相对匮乏,或者说,他太倾向于比兴这样的含蓄手法,而在以铺叙为特征的“赋”法上弱了一些。其实他在早期作品中已经表现出他对于意识流那种绵密的介入式情绪书写的熟稔掌握,但在后期作品中却很少运用。我想,如果能适当地将心理介入与点到为止的比兴手法结合起来,是否在人物形象的深刻性上有更好的效果呢?不过,那样的写作,还有没有汪曾祺式的独特性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女性,是汪曾祺理解世界的抓手
李建新:
我曾经以为,汪先生在小说中表现的对女性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故乡高邮的普遍认知。去过高邮几次以后,和当地人聊天,发现不是的,普通百姓和其他地方的老百姓没有多大区别。所以他小说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是一个19岁走出故乡的青年不断学习、积累起来的,是一种慢慢生成的新观念。他对于女性的平视态度,现在看来也是很“先进”的。
就像小说《大淖记事》中,写大淖边的人家,“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显然作者对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抱着“温情和敬意”,甚至觉得他们朴素的道德观念更符合人性。
徐强:
要问汪曾祺女性立场的来源,我感到首先要追溯汪曾祺生命中的女性的影响。他早岁丧母,幼年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影响首先来自继母、祖母、姑姑们。所有这些女性,在汪曾祺笔下都是善良、温婉的正面形象。他的第一个继母(张氏娘)也是幼年丧母,跟着姑姑长大,不受外公待见,汪曾祺对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也许我和娘有缘,娘很喜欢我”。张氏娘待他如己出,像屙了裤子都是张氏娘毫不嫌弃地为他收拾,张氏娘省亲时也都带着汪曾祺,回程按习俗要给孩子拿点燃的安息香,汪曾祺“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对女性的爱、尊重和善意,从小就奠定下来。张氏娘死于肺病。在汪曾祺17岁时,父亲又娶了任氏,不久汪曾祺就离乡去昆明,中间只在1947年回家见过一次,再后来是1980年回乡小住再见,一见面就下跪。这种尊重、尊敬,既颇有古风,也是其现代女性意识的一种表现。汪曾祺的祖母更是中国封建时代传统女性的典型,她出自大户人家(邑中名士、诗人谈人格的女儿),汪曾祺记忆中的祖母最大的特点是勤劳,饭食好,针线好,本分,照顾祖父仔细,宠爱孙儿。汪曾祺谈到他所推崇的归有光《先妣事略》,说其中“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描绘的就是祖母的形象。他写《受戒》中的小英子的母亲剪花样,也是挪用了祖母形象。另外一个就是她的保姆大莲姐姐。大莲是他是生母杨氏带来的丫头,杨氏死后汪曾祺主要由大莲带大,几乎昼夜不离,汪曾祺幼时是家里的“惯宝宝”,也深得大莲宠爱,这种依恋之情对于幼年汪曾祺女性观的建立,应该十分重要。
杨早:
在汪曾祺的性别叙事里,城乡之别、男女之别、知识高低之别,都与主流成见不同。我们可以揣测,汪曾祺作为有文化的城里少爷、联大学生,也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这样的思想变化与认知重塑。联想到沈从文曾在1949年的信中说汪曾祺“像个女人,全无用处”,相比于沈从文笔下更为客体化的“像只小兽”的翠翠和夭夭,汪曾祺对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塑造,更为主体化,也更能颠覆传统的性别叙事。
单从汪曾祺性别意识的形成来考察,估计仍脱不开高邮家乡的风气、西南联大的教育氛围、张家口等中国农村的印象凝炼。他最终将“健康的美”定型于“农村的女孩儿”,本身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性别叙事的颠覆、承续与清理。“女性的发现”是“五四”的主题之一。但这个命题本身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拯救意味。鲁迅的《伤逝》可以说非常恰当地反映出这种拯救的虚无与软弱。但是,这样的叙事在其后的作品里不绝如缕,在沈从文笔下,在赵树理笔下,在张爱玲笔下,在丁玲和周立波笔下,这种主动的“健康的美”都是稀缺的。直到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投票评选时,评委们仍在为《乡音》中的陶春本该被批判的“我随你”的逆来顺受性格却赢得观众喜爱而大伤脑筋。这种审美惯性,也为当下网络小说与影视剧中的“慕强”“雌竞”等热门元素准备了丰富的土壤。以此观之,汪曾祺早早表现出小说中两性关系的“性转”,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也是对性别启蒙理念的文学化实践。
徐强:
有的作品虽然不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但仍然投射着汪曾祺的性别观念,典型的如《陈小手》。小说的最后,团长在陈小手为自己难产的夫人成功接生后,一面奉上不菲的酬谢,一面却以“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样匪夷所思的理由,从背后一枪毙了陈小手。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是对传统的男权意识的辛辣讽刺和严厉批判。
李建新:
汪曾祺晚年的小说《名士与狐仙》也可以作为一个注脚。小说里的杨渔隐不随俗流,妻子去世后,续娶了照顾自己的丫头小莲子,而且我行我素,全然不顾什么规矩。他教小莲子写诗,很快把一个小丫头调教得像模像样。小莲子也大大方方,不像一个“下人”。杨渔隐去世后,小莲子安排好后事,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她之所以被称为狐仙,也是因为不像世俗中被各种规矩束缚的女性,超出了大众的认知。汪曾祺写这个故事,我想他是对名士和狐仙的做派都颇为欣赏。聊“女性”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从一个角度,再次辨别汪先生究竟是“士大夫”还是“现代派”。他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回归现实,语言的表象更接近中国传统,又画画又写旧诗,但据此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理由是很牵强的。
作者简介>>>>
李建新,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曾任《寻根》《中学生阅读》杂志编辑,2016年参与创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分公司出版品牌“星汉文章”,现任职于河南文艺出版社。编选有《食豆饮水斋闲笔》《汪曾祺书信集》,编订有《汪曾祺集》(十种),策划《汪曾祺别集》(二十种)并担任分卷主编,为《汪曾祺全集》中后期小说、书信分卷主编。
徐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叙事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近现代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吉林省写作学会会长。从事文学理论、叙事学、新文学文献、语文教育、写作教育等领域的研究。著、译、编有《汪曾祺年谱》《小说与电影中的叙事》《故事与话语》《长向文坛瞻背影——朱自清忆念七十年》及《汪曾祺全集》(散文、诗歌、杂著诸卷)等。
杨早,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传媒时代的文学重生》《拾读汪曾祺》《民国了》《元周记》《野史记》《说史记》《城史记》《早读过了》《早生贵子》等著作,主编《话题》系列(2005—2014年)、《沈从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汪曾祺别集》、《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汪曾祺文库本》(十卷)。译著有《合肥四姊妹》。合著有《汪曾祺1000事》《墙书·中国通史》《小说现代中国》等。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