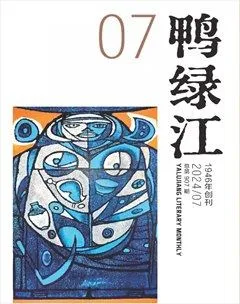布鞋里的母爱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对布鞋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那年代,村里人都穿着自家做的布鞋。农活儿再忙,母亲也总会想着法子为家人做上一双双温暖而舒适的布鞋。按乡下的说法,只要穿着娘做的鞋,心里就有了底,再远再难的路,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心灵手巧的母亲,当年是村里手艺最好的女子,每每穿着母亲新做的布鞋走出去,村里人都夸赞比店铺卖的耐看好用,我心中更是充满道不完的幸福。
当年在生产队的母亲,春耕时处于最忙碌的时节。为了多挣些工分,天还麻麻亮,母亲就赶着出工了,清晨,一串串细碎的脚步响彻山涧,划破了山峦的寂静,蜿蜒的山路拉长了母亲瘦弱的身影,细小的肩膀晃悠着倾斜的扁担。
夜深人静,母亲挑亮煤油灯,开始为我们赶制布鞋。每每我悄悄从被褥探出头,打量着她做鞋的模样,总会被母亲发现,“赶明儿还要早起上学,赶紧睡”。我深知母亲性子,只好乖乖听话,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
童年的我,时常看到月光透过轩窗,洒落在母亲清秀的脸颊,“碧天银月亘古如斯”。山里的月光色如镜,灯光下专注做鞋的母亲,无暇顾及月色皎洁,然而身心浸透月光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女儿心中一轮最美的皓月。
兴许是白天干活儿太累了,母亲的脸上分明布满了倦意,夜深了,她却依然一针一线地专注地纳着鞋底,想方设法赶在立春前为我们添置新布鞋。
母亲心思细腻,做起布鞋来有板有眼。灯光下,只见母亲将按脚的尺寸剪好的纸质鞋样置于桌面压平,再取出合适的布料,沿着鞋样裁剪出鞋面与鞋底。虽不曾用尺子笔画过,但经母亲裁剪出来的鞋型,看起来尺寸不会出半点儿偏差,光滑的底边,比机器加工出来的还精细。
母亲用事先熬制好的糨糊,铺在硬纸鞋样上,再将四五块裁剪好的鞋底,次第均匀地刷好糨糊,对着边缘整齐地码在一起,就制成了厚实的鞋底。
湖南的初春雨水多,母亲为了早日做好鞋,常将糊好的鞋底搁置在炉火上的木架子上烘干,半夜里时常要去翻边,生怕烤煳了鞋底。母亲为了家人能穿一双合适的鞋子,花费了太多心思,但辛苦二字从未见她提及。现在回想起母亲的布鞋,油灯下放大的母亲的身影,即使是寒冬,脚底也是暖烘烘的,一直温暖到了女儿的心底。
我常为做鞋的事心疼母亲。母亲笑着对我说,农村人出去干活儿,靠的就是脚上这双鞋,鞋底硬朗了,再难的路,也能坚持走到底。娃儿们走山路去学堂,更是要做得扎实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像山那头的火车,总有一天,孩子们也能走出村子,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总会低着头望着脚上的布鞋,我就会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语,让我鼓足勇气往前走。母亲说过,只有坚持走下去,脚下的路才能有希望。
一到周末,碰上雨天,母亲也出不了工。一日陪伴着母亲纳鞋底,这也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不同于平常的线,母亲纳底子用的是麻绳。母亲将三五根麻线按着条纹理顺,我则赶忙帮忙扯紧打好小结的一头,母亲则沿着中心搓叠成麻花状。母亲动作麻利,一会儿工夫,就编好了数根结实紧致的麻线。
我吵嚷着也要学着做,而麻线到了我的手中,任凭我怎么去做,真的乱成了一团找不着头绪的乱麻。母亲一边耐心地与我一起重新整着线头,一边笑着说:“多试几回就好了,静得下心来,熟悉了它的性子,绳子也就随心所欲了。”一堆乱麻,到了母亲的手里,又变成了细小的麻花辫。我捧在仔细地打量着,不舍放手,也认真地学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虽远不及母亲做得精细,想到终究拿得出手,我心中欢喜不已。
一针一线间,无不纳着母亲心中对儿女最深的爱。最后一道工序,母亲将裁好的鞋帮与鞋底用麻线缝合。母亲用木头做成鞋模,放在鞋内支撑少许日子,鞋子就变得更加硬朗而有形了。
母亲的布鞋耐穿,穿上好多年都不会坏,直到鞋码小了,穿不下去了,我们也舍不得扔弃,哥哥的鞋穿不了,我来穿,待我穿的尺码小了,会留给更小的表弟、表妹接着穿……母亲的布鞋,陪伴着我们一起走过无数条崎岖的山路,很艰难,却很幸福,我也知道,有条心路在母亲心中永远没有尽头。
来广东后,在铁路工作的我,常要走线路,母亲特意从老家寄了双自己做的布鞋给我。打开包裹后,想着母亲年龄大了,穿针都颇费力气,不敢细想母亲曾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敢细数她的手心又给扎伤了多少次……泪花子不停在我眼中转动。我仿佛看到了她那颗细腻的心跃动于娴熟的指法间,布鞋绵延着说不完的母爱。
无数个与星空相伴的夜晚,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与工友们一起忙碌在线路上,细致地检测设备,一轮皎洁的皓月倾泻在锃亮的轨道上,光影里,浮现着母亲昔日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纳鞋的情景。光阴一去不复返,母亲的布鞋留下了岁月最美的印记,留下了女儿一生都说不完的感恩与感动。
作者简介>>>>
万蕊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妇女报》《中国铁路文艺》《人民铁道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本栏目责任编辑 铁菁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