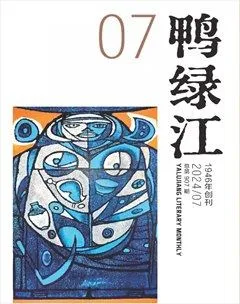书卷多情思故人
1
我的床头柜上始终放着两本书。一本已显有年份,为黄色封皮、史铁生所著的《我与地坛》。另一本展露新颜,为红黑玄幻色调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作者是矿工诗人陈年喜。两年间,床头柜上的书来了又去,换了又换,唯独这两本岿然不动。这对“CP”似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令我在睡前或是醒后反复捧起,百读不厌。
《我与地坛》是20年前街头淘书时入手的。对于作者史铁生,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他的大名,陌生是因为没有阅读过他的一部作品。《我与地坛》可谓我与这位前辈作家的缘起。
这是一部史铁生以《我与地坛》为主导篇目的作品合集。粗疏地读完,觉得无非是一篇自传,有些寡淡,没有特别的感触。彼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血气方刚,热衷于激情洋溢的文字,如是深沉内敛的作品没有激起我太多的情感共鸣。和许多沉默的书籍一样,随手拾掇进了书橱,成为“百城”中存在感不大的一分子。
二十年后,我不经意发现,《我与地坛》出现在儿子高一的语文课本里。虽列为自读篇目,且是部分节选,但当手指划过书页,目光扫过一行行似曾相识的文字,内心还是不经意温热起来。我发现,史铁生的文字竟然有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柔和中透着某种倔强的秉性。我从书橱里寻回原著,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
书读三遍,其义自见。我对该书生发出新的认知。它是史铁生瘫痪十多年与命运交手的实录,饱含着他对生与死、命与运的思考。地坛是他后半生“相看两不厌”的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园子燃起了他的生命烈焰,融入了他的生命纹理。他将缕缕心迹犁铧为一笔一画的章节,熬煮成浸染岁月包浆的脉脉书香。
我将《我与地坛》郑重置于床头柜上,这是家藏图书的最高礼遇。我有睁眼闭眼不离书的习惯。床头柜上的书籍,皆深得契味,几乎能熟谙成诵。端起《我与地坛》,曾闪过一念,这部作品面世于1991年,作者年方四十,而我读出其中真味亦在不惑之年。这是一种巧合吗?或许有些阅读,本来就需要代入年龄。
这时,文友向我推荐了一本名为《炸裂志》的诗集,我第一次注意到陈年喜的名字。这部与阎连科长篇小说同名的诗集,一度令我觉得乖张。读来却肃然不已。作者面对“炸裂人生”的坚毅和达观始终萦怀难释。这本书在我的床头柜上待了差不多两年,直至更具有“炸裂性”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到来。这是一部作者出生入死的写真集。幕景深沉,笔触隐忍,一个个具象丰满的故事,串接成一部厚重的生命史诗,悲怆炽烈的文字中喷发出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
床前翻动浸染作者心酸和血泪的书页,一字一句,一段一章,不耽于无常的生死,超脱于寂寥的灵魂,尤显幽微无言的人生参悟。我想,这样的作品,和《我与地坛》一样,属于每一个为生存而奔命、于逆境而不馁的人。
2
思绪在墨香中游走。脑海里浮现出熟悉的一对文友。他们是亲兄妹。兄长姚军,泥瓦匠人;胞妹姚林芳,残障人士。观察他们的人生辙迹,与两本书的作者竟多有相似。
和他们相识于三年前。姚军携《学艺时节》一文在家乡晚报首秀。该文回溯了因贫辍学后养家糊口的一段苦涩的经历,赢得了文友的广泛好评。不久,他的《跛脚鸭》再度引爆文友圈,文中引出了他的胞妹,长年饱受褥疮困扰无法正常行走的真人版“跛脚鸭”。由于身体缺陷,妹妹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教会她习字读书。她也喜欢用文字探知这个在她看来并不完美的世界。
该文在读者群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报社循线追踪,编发了姚林芳的文作《谁能说匍匐前行不是前行》。姚林芳在文中刻画了那双令她愁肠百结的脚,演化出一系列复杂的情感纠葛。“别人走过的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而我走过的路,很多时候留下的,是一步一个带血的脚印!”字字行行,椎心泣血。
启动搜索引擎,发现她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一家名为“老乐在线”的公益组织的公众号上,原来她是公益事业的热心参与者,也是该公众号的踊跃撰稿人。她的不少亲历和情感,都在这里分享。捋一捋这些零散的文字,可以大致还原出她的所来之路,这是一部难以想象的与褥疮几近与生俱来的缠斗史。
如果说史铁生的不幸降临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尚属不可承受之重的话,那么命运给予姚林芳的劫杀来得似乎更加残酷。“仿佛美好的开端总是稍纵即逝,只不过,我的美好戛然而止于4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那双美丽的脚的记忆。”
记事起的姚林芳的生命里也出现了一座园子,那是同样有着季节变换的家庭小菜园。离她的卧榻咫尺之遥,无须像史铁生“扶轮问路”去赶赴一场遇见。帮衬母亲的间隙,她也会和史铁生一样,“撅一杈树枝左拍右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觉得“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心头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园子烙下了她匍匐成长的年轮。渐渐地,在与园子的凝视与对话中,她不再自怨自艾,将园子变成“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不甘、痛楚和孤寂,散佚于无形。
姚林芳也曾在园子里发出史铁生的灵魂之问:“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
万幸有了书本。虽是捡拾他人过手的卷帙,且是汲取家人之“牙慧”,但姚林芳格外专注和用心。蒙学后的她手不释卷,文学的心源由此发轫。文学,成为她在这个颤颤巍巍的人间,踽踽独行的重要倚仗。
“我挑战了世俗的偏见,做常人认为不能做的事,比如工作,虽是以外包手工活儿为主,我为自己的自食其力感到欣慰。”“在加工鞋子的时候,我把泪水和汗水融进了一针一线——我是多么渴望能为自己制作一双漂亮的鞋子,看到自己穿上新鞋的样子。”
姚林芳敲下的文字片段,俨如她在文学春山奋力登攀的足印。她用文学填充心灵,也在开拓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日积月累,发微抉隐,一座诗文长廊初见端倪。《谁能说匍匐前行不是前行》便是其中熠熠闪光的一篇奇文。
未承想,该文的发表为她迎来命运的转机。读者中,有时任当地人民医院院长的朱莉女士。她被姚林芳的自励自强深深感动,当即联系了报社,并派出专家组上门探视。望闻问切后,决定对其实施免费医疗救助,终结她匍匐前行的历史。历经两次手术,褥疮治愈,继而截肢,指导康复训练,直至成功安装义肢。媒体的呐喊,白衣天使的仁心和妙手,慈善总会、残联、义肢公司、康复机构的翼助,广大文友的因缘相契,共同铺就了一条护持姚林芳涅槃重生的爱心通道。
2022年5月19日,姚林芳终生难忘的一天。她第一次穿上了亲手缝制的新鞋,开始蹒跚移步。她的站立让所有人惊叹。她成为各路媒体的焦点,收获了无数的点赞和祝福。
相比史铁生,姚林芳无疑是幸运的。她迎来了人生的柳暗花明。她将所有的感恩诉诸文字,敲下了《从匍匐到站立》系列篇什,分享在老乐在线公众号上和个人QQ空间里。这在我的家乡传为佳话。
3
姚军,姚林芳生命中的重要见证人。《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里,似乎有着他的某种投射。抑或,仿若陈年喜笔下的某个人物。
他与陈年喜同庚,却比陈年喜更早地背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标签——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一个爆破,一个家装。他们的共同爱好是阅读和写作,对阅读有着几乎病态般的渴求。陈年喜有着在废弃的工房翻来覆去看墙壁贴报的无奈,姚军有着如厕时发现半截报纸的兴奋。毋庸讳言,姚军的作品影响力无法与陈年喜相提并论,但一样真切可感,从中能清晰地拼接出一个过早与命运对峙、走南闯北讨生活的中年汉子的苍凉背影。
“赶路的人,命里落满风雪。”
姚军生命里的第一场风雪来得猝然。13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母亲卖掉了仅有的一头猪,又四处化缘后才得以办完丧事。流干眼泪的他仿佛一夜间长大。种田喂猪,挑河挖泥,他用稚嫩的臂膀撑起半个家庭。每年的开学最令他揪心,母亲四处求告一把鼻涕一把泪为他争取到了旁听的“待遇”,却因欠交学费,无法领到新书本。同学的目光仿若风霜刀剑,令他穷累的眼皮无法抬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同学们端来的是一盒盒白白的大米饭,而他只有日复一日的蒸山芋。自家亲戚售卖两分钱一勺的菜汤,看到他就会低下头或瞥过眼,因为亲戚明白,他的兜里不会有一个子儿。那一刻,他的双眸里落满风雪。他的文字《受穷罪》里,布满了成长年代的种种辛酸。
贫穷、自卑,像水蛭一样紧紧将他缠绕,直至熬到初中毕业。他悄悄藏起录取通知书,对父亲留下的老旧脚踏车进行了改装,后座上绑上箩筐,用它来做些本钱少周转快的小买卖贴补家用。为了一担货源,时常百里走单骑,屁股钻心地痛。他小心翼翼地掌控车把,一路磕磕绊绊,战战兢兢。他知道,一旦人仰车翻,所有的辛劳将付之东流。遭遇途中下雨,他将携带的雨披覆在箩筐上,自己却淋成了落汤鸡。当他将沾洇着雨水和汗水的一张张毛票递到母亲手中时,母亲哭了,他笑了。他把这一切写进了短文《学艺时节》里。
18岁,伯父给他指了一条手艺路,拜师学瓦匠。这样的一技之长在城乡很有市场。他觉得未来的日子有了奔头,每天天不亮就到师傅家挑粪刷圈扫屋子。后随师傅辗转新疆等地,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他在一篇回忆文字里写道:“我拿起了十字镐,连锛了三下,地上的土纹丝不动,只留下三点白色的痕迹和一些一闪而灭的火星。那一刻,所有的悲屈倾泻而出,泪水沿着镐柄往下流……”满师后的他,不断精进技艺,加之朴实厚道,渐渐地在业内做出了口碑。和陈年喜一样,他的行迹经由大半个中国,留下了一段段泪水与汗水交织的生命体验。
瓦工的工作烈度和危险程度无法与爆破工相比,但职业病的袭扰同样令人心悸。常年与沙子水泥打交道,不少同行患上和陈年喜一样的硅肺,所幸姚军尚未出现明显征候,但亦存隐忧。常年弯腰下蹲作业,致使他的颈椎和腰部出现严重劳损,时而疼痛难抑。饮食的不规律,也令他过早患上了胃病。他的双手布满了砖片吻过的痕迹,加工瓷砖诱发的阵阵耳鸣,不时在演奏一场毫无止歇的风雪交响乐。但他明白,既然认定了这条风雪路,便只顾日夜兼程,“一蓑风雪任平生”。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姚军的个头不高,远不如陈年喜那般“须仰视才见”,见面时却始终微低着头。尽管身形“低微”、出身“低微”、职业“低微”,但他的与众不同的气场里,掩饰不住筋骨的倔强,以及内心的通透和澄明。我想,他的骨头是骄傲的,也是宏阔的,那里,承载有数十载奔涌的心河。
和陈年喜一样,姚军是生活的深度体验者,他为自己呐喊,也为他人呐喊,喊出“低微”骨头里的疼痛、无奈和憧憬。他在家乡晚报发表的多篇文作震撼了很多读者,也使他成为晚报副刊高人气的作者,并引起不少名家的关注。著名学者、诗歌评论界权威、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橹先生曾对《跛脚鸭》一文作出如是评价:“真的是令我不仅感动,而且有点凄伤。特别是跛脚鸭同跛脚妹的互为映衬又颇具深意的对比,令我惊叹作者的‘象征’才具了。”后来,《跛脚鸭》获评2021年度江苏省好新闻(副刊作品)二等奖。
近期,当地文联在晚报推出文学新锐人物专版,挖掘和聚焦文字功底扎实有潜质的中青年写作者。姚军名列其中。专版连发了他的三篇近作。其中《暖冬》一文刊发在头条位置。该文回溯了他学徒的第一站——新疆一个叫作连木沁乡的边陲小镇务工见闻。朔风凛冽的冬日,维吾尔族老板娘一碗免费的热气腾腾的豆浆,赶着毛驴车的维吾尔族大妈捎带他的一段路,这些温馨的桥段,令人地两疏的他由衷喟叹,“别人都说新疆很冷,可我总觉得那一年,应该是我十八岁之前过的一个最温暖的冬天”。维汉一家亲的故事令我感动了许久,我想起了陈年喜笔下哈拉汗的形象。著名散文作家、三毛散文奖得主、无锡市作协主席黑陶先生以“浓郁烟火真切内心”为题为他的三篇作品作了精辟的点评。
4
《我与地坛》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里,有一个共同的人物——母亲。《我与地坛》里,母亲是仅次于作者的灵魂人物。《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里,母亲的着墨不多,但不失丰满、立体和慈爱。而姚军姚林芳兄妹的身后,同样矗立着一位饱经风霜含辛茹苦的母亲。母亲,是他们文字行径中最深沉最幽微的一道辙痕。
姚林芳笔下的母亲知书达理。她严词拒绝了“好心人”劝她遗弃“拖油瓶”的建议,殚精竭虑地护佑女儿长大。和史铁生的母亲一样,她的言语总会有意识地避开“跑”“踩”“爬”“跳”之类的字眼儿,小心翼翼地呵护她敏感脆弱的自尊。姚林芳用稿费给她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她兴奋得像个孩子:“这个鬼丫头,一天学没上,还作怪写文章,幸亏我当年没将那只跛脚鸭扔掉。”
姚军的作品中同样不乏母亲的形象,《学艺时节》中识大体懂分寸的母亲,《跛脚鸭》中舐犊情深的母亲,《不肯穿孝的母亲》中忍辱持重的母亲。姚军的《不肯穿孝的母亲》和陈年喜的《不曾远游的母亲》风格相近,亦是最感动我的一篇。读一次,流泪一次。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充满悬念。父亲出殡之日,母亲拒绝穿孝。依当地风俗,若不穿孝,意味着来日要改嫁。“妇人之心”引得众人的鄙夷和指责。此后,“每一个经过家门前的人,都会伸长脑袋,看看母亲是否还在家里。”这一看,看了二十多年,直至姚军成家立业,母亲及至花甲。
篇末借母亲之口道出原委:家中实在拿不出钱,哪怕一分钱来买布做孝衣。那一刻,母亲笑了,姚军却哭了。
后来,在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不肯穿孝”的母亲,目光慈祥,嘴角盈笑。额头上深深浅浅的纹路,俨然是岁月度化的勋章。
和陈年喜的母亲一样,兄妹俩的母亲也被生活的“大锅”所笼罩,“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她不知道锅外的世界”。姚林芳曾萌生过一个念想,就是带着母亲去远游,看看“锅外的世界”。在她借助义肢实现自如行走后,她陪母亲逛遍了县城和市里的景点儿,并将下一站瞄准省城。这是年内的“小目标”,一定会成行,她的语气非常坚定。
5
痛苦、搏命和自愈,是《我与地坛》《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的共同主题。
手指哗哗掀动书页,那些刻印的故事像一个个灵动的生命,在我的指尖跳跃。我仿佛在和主人公促膝谈心,听他们将那些惊心动魄、热辣滚烫的经历娓娓道来。合上书页,余音不绝如缕,仿若天坛弹奏的悠扬梵歌,又或是矿山炸响的空谷回音。
当一个人的苦难和磨砺的书写,变成了照亮别人暗夜里的一道光束,这样的书写,已然超越了经历本身,变成一种超凡脱俗的价值指引,一种仰之弥高的精神谱系。
我轻轻地抚平书卷的褶皱,缓缓归放于床头柜的丛书之中。好书在侧,慰藉风尘。
文友间有分享书籍的雅好。我想,何不整一套史铁生和陈年喜的全集,与兄妹俩共勉呢?相信如是心灵的“史记”,定化作彼此人生下半场向光而行的不竭力量,在“低微”的骨头里,激荡起更为壮阔的江河。
作者简介>>>>
刘征胜,作品散见于《青海湖》《牡丹》《西部散文选刊》等报刊。曾获第二届刘成章散文奖单篇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