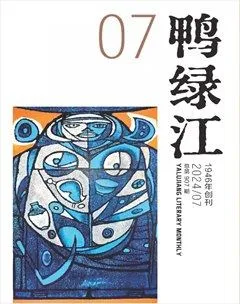经历风雨见彩虹
“痛苦是人生的导师。”我对这句名言感受至深。人或许从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上,便开始领略痛苦的滋味。《大般涅槃经》说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前七苦,易理解,“五盛阴”,解释起来有些复杂,大体是执着于身心的苦,也可以引申简化为一句话:活着就无法避免受苦。
我出生于1956年。听妈说,生我时难产,落草时脸紫,头凸一大包,口无游丝之气,幸亏邻居老薛大婶熟谙接生,将我倒悬,朝我屁股连挥几下“乾坤掌”,我才哭啼转来。渐大时,和众娃嬉戏于城墙上,不慎失足跌落于数丈深的护城河,是我命大,城墙下一棵柳树挂住了我。家里生活拮据,九口人仅靠爸微薄的薪水度日,我上学时因交不起学杂费,曾挨老师剋。
穷且不说,又来了病。先是爷患了脑血栓,后是奶得了偏瘫和老年痴呆,再就是爸得了肺癌。短短几年光景,我失去了三位亲人。我也患了气管炎、皮肤病,常年连声咳嗽,脸憋得通红,鼻涕眼泪的,上医院成了家常便饭。
念中学时,病好了,可接踵而至的是眼睛近视。那时,我很爱看书,却买不起书,只好向人家借。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读到深夜,久而久之,把眼睛熬坏了,黑板上的字根本看不清,成绩每况愈下。
有位作家说过,一个人在20岁之前没有初恋的经历,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当时,我并不晓得让我的人生趋于完整,却稀里糊涂地平生第一次初尝爱的青果,那年,我19岁。
她是中学文艺宣传队队员,不仅长得好,歌也唱得好。每每她在院里练声,我都静静地听着,有时,便站在木凳上透过我家的后窗,往她家前院偷窥,她那声音对于我来说宛如天籁。她和我大妹要好,我便能常常见到她,那时,我们没有什么话,只是偶尔打个招呼或寒暄几句。我那时正值青春年少,对异性有一种朦胧的好感,我很爱和她在一起玩耍、捉迷藏、打牌、看戏剧、剜野菜……
记忆最深的是那次我和她骑行至农村刘姨家做客的情形。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我和她同途,她白皙的脸被北风吹得通红,显现出少女特有的红晕韵致,那色彩犹如一道艳丽的彩虹,辉映在我年轻的心上。
有一次,她来我家帮忙包饺子,包完饺子后,她又在炕沿上捣蒜,没捣几下,那只盛有蒜泥的小碗被她用擀面杖给捣成了两瓣儿。她有些难为情,我帮她收拾残局,又劝慰她几句。同时,我的心里便掠过一丝不祥的预兆,我和她难成正果。果不其然,不久便应验了,她比我高一届,走上了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道路,我因特困留城在家待业,从此天各一方,音信皆无,山重水复、咫尺天涯。加上双方家长竭力反对,那时社会上曾流传“女大一,哭啼啼。”“属羊女命不济,不合婚”……世俗的利剑斩断了我最初的情丝。那是我青葱时代一个凄美的梦,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扉。年少的我无法承受这个打击,大病了一场。这段暗恋经历,在我不成熟的心上留下了一个揭不去的痂。
我们兄妹五人,我是头大的,失去了爸这个顶梁柱,我柔嫩的双肩开始承受生活的重担,先后糊过纸兜、穿过山楂、包装过粉笔,当过力工和烫沥青工。在一次烫沥青时,我的左脚不慎掉进沥青池里,立即被烫得脚无完肤。幸遇鞍山货车在那儿卸货,那位好心的女司机开车将我送到了县医院救治。我在医院足足住了两个多月才出院。到如今,每逢阴天下雨,我布满伤疤的脚面还刺挠难忍。
1975年12月30日,正值年终岁尾,我被分配到一家镇办企业上班。一起分配的有七个人。头天到厂,领导安排我们倒煤垛,便自认晦气。果不出我所料,倒了两天煤后,我们四个倒霉蛋儿,被分配在翻砂车间。人们常说:“车钳铣,没法比;煅铆焊,凑合干;叫翻砂,就回家。”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还强颜欢笑,装作轻松的样子,为的是不让母亲为我担心。
在厂里,我又经历了失恋的打击。我和珍是中学时的同届同学,她妈去世多年,我爸刚去世,失去至亲的际遇,使两颗苦涩的心贴得更近了。她曾为我在小饭铺买过水饼和豆腐脑儿,我也几次给她带些好饭菜。1977年我因公出差南京,回来给她捎条女裤。不久,厂政工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儿追求她,他家条件比我强多了,她向我摊牌了,我的心开始滴血。
国家恢复高考了,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我决定试一试,苦苦哀求厂领导,终于准了一个月的假,于是我便刻苦复习起来。不知是基础不好,还是运气太坏,总之,我榜上无名。失恋、落榜的双重打击接连而至,幸运之神从未光顾过我。
有一天干完活儿,我疲惫地躺在大炉装料的铁平台上,想了很多。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爸不在世了,家境困难,今后我能靠谁呢?后来我转念一想,我得好好干,不能再浑浑噩噩混日子了。
“技不压身,才不压人”,我以前有些语文、美术的功底,被车间主任看中,我就担任了车间记录员,经常给车间写墙报,在厂里黑板报上写写画画,被工友们戏称为“秀才”。
1978年,我们被调转到县砂轮机厂,我由镇办企业的小集体工人转变为县办企业的大集体工人。繁重而低薪的装卸工作并没有使我消沉。一个偶然的机会,厂里的女出纳员休产假,我被厂领导赏识,接过了厂出纳工作,后又做了七年的仓库保管员和一年的行政办总务。
我从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几十篇诗歌、散文、小说等。1990年被调入县文化馆,后调入县文化局工作多年。我一个大集体所有制的劳苦工人,在不懈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后经人介绍,我和一位女工结婚了。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婚后生活宁静而温馨,谁知灾难却悄悄地朝我们逼近。
1991年5月15日,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不祥的日子。妻子乘坐的汽车肇事了。闻讯后,我匆匆地去了县医院,她躺在医院的急救室里,满身是血,满脸是伤,我几乎认不出她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我蒙了,欲哭无泪,感觉晴天霹雳之后,便是天塌地陷。
转院、输血、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她的脸上、胸部已缝数百针,基本毁容了,术后和以前判若两人。半个月后,她才逐渐醒来,开始恢复神志、记忆。强忍苦楚,我开始慢慢劝她、开导她,重新鼓起她生活的风帆,又提心吊胆地怕她照镜子,怕她想不开……
脸,对于女人是相当珍视的。翌年,我带她去沈阳陆军总医院做了些整容小手术。由此,她被所在单位长期放假,直至退休。
她的工作单位是市卫生局辖下的事业单位,但实行企业化管理,属财政局差额拨款单位。因车肇事被放假,薪水比上班人员少。
儿子与儿媳相识于网络,那年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她不嫌我家条件差,于2009年结婚,婚后他们幸福和睦。
2012年夏秋之季,盖州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洪水冲走了儿子租赁房屋内的货物数万元,财产损失严重。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儿媳因父母离异多年,随娘改嫁,打小曾患过孤独症,生完孩子后又患上了产后抑郁症。据亲家母告诫提醒我们,她在娘家就曾有用被捂孩子的危险举动,幸亏亲家母发现及时。但不久,悲剧还是发生了:在那年10月10日风雨交加的夜里,我孙走了,其实他还不会走,不会爬,只会往后退。大脑瓜,亮眼睛,鼻直口阔,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然而,他未满七个月的幼小的娇艳的生命,竟像昙花般无情地凋谢了。
当时在儿子的店里,妻儿正在从店铺往家搬运货物,我睡在店铺一楼,儿媳和孙子住在二楼。我一觉醒来上楼只见儿媳表情呆滞,双手呈掐人状。我抱起孙子,见他已无生命迹象,但尚有体温。妻儿赶过来后,急忙将孙子送至市中心医院,并将儿媳一起带走。值夜班大夫进行了全力抢救,但已失去了最佳抢救时间,于是开出了病志和死亡通知书。第二天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母亲悲痛欲绝,用手猛打大妹,泣不成声,她怕我和儿子会出事,让妹妹们对我和儿子严加看管。
我和孙子在一起的时日,虽然仅六个多月,但我们对其倾注的爱却很深很深。我爱他就像珍爱自己眼珠般,那是一种隔辈的爱啊!虽然他还不会喊我一声爷爷,但是在他幼小的童心里,对我们长辈却表示了他的识趣和纯真。他是那么听话、懂事、活泼、可爱,从不哭闹,也不给家人添乱。他那双纯净的眸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期盼。
一周后的夜里又下了一场大雨,我知晓那骤雨是亲人们为我的孙子——李尚善汇聚而流泻的眼泪,当然也有他冤屈的泪水……那仅仅几个月的生命历程,却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他将永远留在爱他的亲人们的生命里。44天后,我的儿媳经受不住打击,带着悔恨和内疚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嗣后,儿子对我们说,其实那时他也不想活了,想与老婆孩子一起去;他站在高速公路立交桥上想跳下去,一了百了。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自己不在世了,那双亲可怎么活!谁来给他们养老送终?!
后来,儿媳娘家向我们索赔十万元,在我挚友多次调解下赔偿三万元。三年后,我在青石岭腰岭子给亡儿媳买了块墓地安葬了她。
噩梦终过去了……
我已年近古稀,生活对我的馈赠,是许多苦难,也给了我不菲的财富,那就是不断奋斗。我从镇企小集体工人转而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干部、市作协主席、市文联副主席;从入团到入党,从无文凭(初中未毕业)到有专业职称,从读别人的书到自己发表百万字作品,并获省市几十个奖项,就是我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小小证明。2021年我出版散文集《城南拾旧》受到读者欢迎,每一篇散文都倾注着我对生活的热爱,每一首诗歌都是我对未来生活的向往。2021年,我编著出版《营口方言》,2022年再出修订版,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并颁发了收藏证书。经数年收集、整理,《营口方言》存有4000个条目,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者进行方言的抢救、发掘、研究、运用提供了方便,对进一步推动汉语学习和研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学术价值及收藏保存价值。
儿子已于十年前再婚,美满和睦,育有一女,聪颖可爱,今年还被评为“三好学生”。我和儿子住对面屋,楼前辟有花园、菜园。
“不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我有胜有负,但我相信,只要活着就要坦然面对人生,直面现实。我的年龄虽已是“惯看秋月春风”,但我始终愿意听那首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作者简介>>>>
李曰明,中国散文学会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盖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