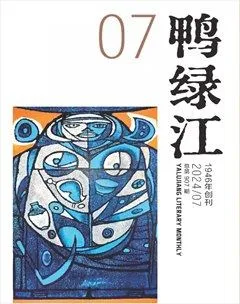借宿之夜
排查完立在山巅上的那根线柱,李欣知道故障不在自己管区内。他已精疲力竭,一屁股跌坐在一块黑黢黢的卧牛石上。苍穹下群山连绵似海,峰峦跌宕如浪。李欣望着随山浪而起伏的战备线路。听班长说过,在自己管区内,有个民兵连连长因为维护战备线路牺牲了,而他的妻子则对他不离不弃,对爱情忠贞不渝。
一阵山风吹过,晴朗天空眨眼间便乌云密布,山海也变得晦暗幽深。李欣立刻锁紧眉头。不大工夫,淅淅沥沥的细雨便洒落下来。李欣没带雨具,衣服很快就被雨水淋透。渐渐地,雪花代替了蒙蒙细雨。山区下午不通汽车,无法回营房,李欣得就近找一个村屯住一宿。他就顺着在线路下面辟出的小路往回走。傍晚雪停了,薄云疏朗的天幕上露出几颗星星。雨雪交融,崎岖的山径滑得像抹上一层油。他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滚得满身都是泥水。
长白山区三月,天气依然寒气袭人。冷飕飕的山风刮来,李欣冻得上下牙齿捉对儿磕架。
李欣摸黑爬上一道山梁。他发现山下有几点稀疏的灯光,峡谷深处传来几声犬吠。李欣知道,这是他白天经过的一个小屯。十几座茅草房,稀稀拉拉地分布在十余里长的沟川里。他吃力地攀扶着树木,走下那段陡峭的山崖路。
山崖附近有一座茅草房,李欣轻轻地叩响小房的木板门。
“谁呀?”屋里响起女人的问话声。
“我,过路的。”李欣轻声回答。
茅草屋里一阵沉黙。
“我是解放军,查电话线时,衣服让雨淋湿了……”他大声补充一句。
哗啦,板门打开了。一个年纪不大的女人,手拿油灯站在门里,灯光在她姣美的脸上泛起光泽。李欣一愣不知该不该进屋。女人却大方,把他让进屋来:“进来吧,烤烤衣裳。”
小屋虽小却隔绝了户外料峭的春寒,他感到阵阵热气扑脸。炕上睡着一个小女孩儿,能有两三岁,白白净净的挺好看。
女人从外屋端来一碗开水:“同志,喝碗热水,赶赶寒气。”
李欣喝水时,女人翻出一件棉袄和一条夹裤。她把干衣服放在炕沿上:“把湿衣裳脱下来,我先给你弄点儿吃的,再烤衣裳。”
她的提醒才让李欣感到饥肠辘辘,他连忙从满是泥浆的背兜里掏出几个外壳冻硬的馒头,说:“不用忙了,我有馒头。”
她看一眼李yXOGu2op8gFfDUhr/Ri6uQ==欣手里的馒头,笑了笑:“瞅你那馒头,能打死人,不馏馏咋吃?”
李欣趁她在外屋忙活时,急忙脱下湿衣服,换上温暖的棉袄夹裤。外屋响起噼噼啪啪的烧柴声,几丝柴烟从门帘边隙中渗进来。微香的柴烟让他感到亲切,心头泛起归家似的温馨。
饭后,女人在外屋洗衣服。李欣眯缝上眼睛,仰靠在炕墙边养神。
年初,李欣新兵训练结束,分配到军区某部通讯连线路班当战士。线路班负责维护长白山区一段战备线路。三月三十日,战备线路突然发生故障,线路班全员出动,分段排查故障。
李欣从县城乘车,下车后又穿越十里沟川,从杆码上找到自己管区的线路。他翻越六七座高山,攀登四五十根线柱。雨雪中又跋涉十几里山路。这时,李欣已经疲惫不堪,困倦阵阵袭来。不一会儿,眼皮就沉重地黏在一起。
女人把洗净烤干的衣服叠成一摞儿,轻轻地放在炕边。动作虽轻,李欣还是醒了。他摸了一把温干的衣服,一股热流在心头涌起。他由衷地感激道:“大嫂受累了,谢谢!”
女人轻轻一笑:“瞅你说的,你们解放军,泥里滚、水里爬累不累?”
李欣抬腕看看手表,已到晚上十点多钟。这时他才想起,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见她丈夫的影子?就是开会、串门,这工夫也该回家了。李欣问道:“大嫂,大哥呢?”
她慢慢地垂下眼帘,低声说道:“他,他不在了!”
李欣心里猛地一跳:“哦,这里就住你娘儿俩?”
她平静地说:“还有我爹,给大队看参园子,下晌到沟外办事去了。”
李欣决定离开这里,急忙换上军装,拿起背兜。她奇怪地问:“同志,你要干啥?”
李欣说:“这里不方便,我到别人家里住一宿。”
她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深更半夜的,到谁家方便?这里的男劳动力,都被公社抽去搞农建。沟里这几家都是迁户就田的,谁也不挨着谁,离这儿最近的也差不点儿有一里地呢。到沟外大队部还有十里多地,道又不好走,你还想滚一身泥水?”
她见李欣面有难色,就说:“这么晚了,知道你从这里走的,那些长舌头老娘们儿还不知咋编排呢!要我看,你就在这里对付一宿吧。”
她见李欣还在犹豫,就指着炕上的孩子说:“再说,也不光是咱们俩。”
他望了一眼熟睡的小女孩儿,说:“一个小孩子……”
“别胡思乱想,身正不怕影子斜!”
小屋只有两间,外屋是厨房,除了锅灶、水缸和柴堆,没有住人的地方。里屋小炕上只能住下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女人看出李欣的心思,就说:“你在炕上睡,我在地上睡。”
李欣不肯:“我在地上睡吧。”
她说:“别争了,哪有让客人在屋地睡觉的道理!”
女人把孩子往炕梢挪挪,给李欣铺上被褥,然后就在屋地铺上两件棉衣和被褥。
他们无言对坐一会儿,她见时间不早了,就说:“睡觉吧。”
李欣点点头:“嗯,这就睡。”
李欣和衣而卧,他这样做似乎觉得心理上平衡一些。油灯点着,谁也不想把它吹熄。他太累,脊梁一贴炕就呼呼睡着。
深夜,李欣被一阵细微的声音弄醒。睁眼一看见她在地上翻来覆去烙烧饼。屋地太凉,铺得又少,让她无法入睡。李欣感到非常歉疚,就说:“大嫂上炕睡吧。”
话一出口,李欣就后悔了。说这话,会不会让她觉得自己图谋不轨?她倒没在乎:“上炕就上炕,住一个屋跟住一铺炕,有啥区别?”
女人望一眼红头涨脸的李欣:“军人是睡床的,不习惯热炕,你就睡炕梢吧。”
她把女儿向炕中间推推,把李欣被褥挪到炕梢铺好,又在炕头铺上自己的行李。女人笑着对李欣说:“咱俩可要讲好,谁也不兴碰着谁!”
“跟一个生人睡在一铺炕上,你真的不怕?”李欣望了她一眼。
“因为你是解放军,我才不怕呢!再说了,你是个大孩子,我是你大嫂。你没听说,老嫂比母吗?”她说这话时,脸上露出少有的严肃。
炕中间虽然有孩子,但炕小,他们的间隔,也只是咫尺之间。
说来也怪,刚才还沉睡得鼾声大作的李欣,现在却一点儿睡意也没有。连她翻身和掖被的细微声音,他都听得清清楚楚。李欣偷偷睃了女人一眼,好像她也没有睡着,喘气挺粗,身上的被子轻微地起伏。他和她近在咫尺,让他好不自在。好一会儿,她轻轻地翻身面向炕头。
“啪”,结大的灯花爆了。煤油灯的火光一阵摇曳,灯光转暗,屋里变得朦朦胧胧。
炕烧得很热,尽管在炕梢,李欣身上也已是汗水津津,他把被头使劲往下拉了拉。女人也睡热了,把被头拉得很低,露出汗衫领口上面雪白的脖颈和浑圆的肩头。一阵年轻女人所特有的馨香,从她被窝里漾出来。她那白皙的肌肤和醉人的气息,让李欣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李欣为自己的心跳感到羞愧,但又管不了它。
“咕咚”,外面响了一声,接着鸡窝里响起小鸡瘆人的惊叫声。她忽地爬起来:“不好,狐狸又来掏鸡了!”
她急忙披上衣服,拿起手电筒就冲出屋去,李欣也跟着跑出去。手电光柱中,一只灰黄色的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向远处逃窜。顶鸡架门的两块大石头,被狐狸掀翻一块。
这一番折腾,李欣睡意全无。他强迫自己快点儿入睡。他使劲地闭上眼睛,可是没有用,闭着眼睛睡也不着。李欣开始数数,不行,越数越精神。他真盼天快点儿亮。这时她说话了:“你睡着了?”
李欣说:“没睡着,一点儿也不困。”
“我也是。反正睡不着,咱们起来唠会儿嗑吧,别躺着受罪了!”
“我看也是。”
他们都坐起来,她拨去灯花,把油灯挑亮。
李欣问:“大哥什么时候去世的?”
她的眼神突然黯淡下来,低声说:“他是去年这个时候死的。”
他很后悔,要说的话有千句万句,为啥偏提起这句勾起她内心哀伤的话?她似乎没有注意李欣的神情,幽幽地说:“他是大队干部,因公而死……”
李欣心里猛地一动,莫非她就是民兵连连长的妻子?
在他们继续交谈中证实了,她的丈夫就是那个为维护战备线路而牺牲的民兵连连长。她丈夫的那个民兵连曾向县备战指挥部倡议,基干民兵要协助解放军保护一些野外的战备设施。她丈夫那个民兵连的基干民兵,就负责保护通过本公社的这段战备线路。
民兵连连长把好攀登的线柱分给其他民兵,把立在山崖畔、最险的的那根线柱留给自己。就在他们结婚第三年春天,在查看战备线路时,她丈夫发现自己分担线柱的左边,有一根电话线松弛。大风天,那根松弛的电话线,很容易和下边的电话线纠缠在一起而引起故障。民兵连连长回到连部,用铁线做了一个环钩,把用塑料绳缠住的石块系在环钩上,挂在松弛电话线下面的那根线上,石块能把两根电话线坠出距离。
一天,她丈夫带着一个基干民兵去沟里,他登上陡峭崖畔上那根线柱。由于电话线有锈,环钩滑不到相应的地方,他就用长杆使劲往前捅。好容易把铁环钩捅到地方,他却不慎从线柱上闪下来,滚到山崖下摔死了。
县革命委员会追认民兵连连长为烈士。不久,女人把丈夫葬在殉职的地方。她向大队申请,要和父亲一起给集体经管人参种植园。她把看园小房建在丈夫坟旁,天天厮守在丈夫身边。那年她只有二十三岁,很多人都劝她改嫁,她没有应允,决心把丈夫留下的骨血拉扯成人。
她的讲述让李欣唏嘘不已,他觉得刚才的话题过于沉重,就决定换个话题缓和一下气氛。这时女人的女儿醒了,小女孩儿没有哭也没有闹,悄没声地爬到母亲怀里,瞪着两只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陌生的李欣发愣。李欣马上把话题转到女孩儿身上。
“大嫂,这个漂亮的小妹妹几岁了?”他急忙改口,“我有个五岁的妹妹,叫惯了……”
她泪眼婆娑望了他一眼,说:“你看呢?”
李欣伸出三个手指:“三岁。”
“不对,两岁。”
“她的名字……”
“叫丫蛋。”
“不好,太土气。”
“你嫌土气,就给她起一个吧。”
“向东、迎春、红心、小螺号、红烂漫……”他认真地挑着时兴的字眼儿。
她“扑哧”笑出声:“不行,农村叫不出口,你嫌土气,还叫她小妹妹吧。”
“嘿嘿,让大嫂捡个便宜。”
“不吃亏,老嫂比母嘛。”
这时,女人怀里的小女孩儿,头枕着母亲的胳膊,渐渐地眯上眼睛。见女儿犯困,女人把她放进被窝,轻轻地拍几下,小女孩儿便安静地睡去。女人深情地望着女儿喃喃地说:“丫蛋啊,快快长大吧。好好念书,做个有出息的人,给你爹长脸,也让妈妈的心血别白费……”
“她会的……会的……你的心血……不会白费……”
他俩又唠一些别的,一直唠到鸡叫头遍。她也不睡了,就下地做饭。
在外屋锅碗刀勺交响声中,李欣又感到困乏,一闭眼就睡着了。他是被女人叫醒的。她给他端来洗脸水,香皂盒里放着一块用猪胰脏和面碱自制的胰子。一条带窟窿的干净毛巾,搭在洗脸盆的沿儿上。
早饭是苞米面酸菜馅儿饽饽,虽然少油无肉,但她调制得很可口。饭后,李欣掏出粮票和钱,她见状杏眼一瞪:“收起来吧,俺家不是饭店!”
见她生气了,李欣只好收起粮票和钱。趁她去外屋时,他把粮票、钱、毛巾票、肥皂票都掖在枕头底下。那年头,毛巾、肥皂都是凭票供应的。
太阳没有升起,李欣离开女人的家。临走时,他站在民兵连连长的坟头,深深地鞠了一躬。至于昨晚他住的地方是什么屯,她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走得很远了,李欣回头望了一眼,见她还伫立在清晨的曦光下,他心里掠过一丝隐约的怅惘。
回程路上,李欣发现背兜里有几个煮鸡蛋,他心头一热。在山间小路休息时,他剥了个鸡蛋充饥。哦,这鸡蛋真香。他从没吃过这么香的鸡蛋!
两个月后,李欣被调到通讯连当文书。一九七八年,他上了军校,再也没机会回长白山区。毕业后,分配到军区,他成了一名军官。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已经是副师职的李欣,又一次来到长白山区。曾经熟悉的山区景致,又一次出现在眼前。苍穹下群山连绵似海,峰峦跌宕如浪。黑黢黢的卧牛石,像一个忠实的老友,几十年没有一丝变化,在原地静静地等着他的归来。他心头一动。现在,山区已经修了公路。他的司机告诉他回程的路线——真巧,恰恰要经过多年前曾借宿的那个山沟。
公路蜿蜒伸向远方,静默的大山沉浸夕阳的照射中——他的眼睛辨认着,他的心回忆着,他的心跳动着。“小张,停一下!”他忽然说,“我到这里去看看!”他爬上一道山梁。山下的峡谷青翠、幽深,十余里长的沟川没有一户人家。他还能回忆起那陡峭的山崖,它还在那里。他还记得他吃力地攀扶着树木,走下那段陡峭的路。现在,山崖边上,那座茅屋呢?没有了。远远地,有一个小小的凸起的影子——那是不是民兵连连长的坟?山风呼呼吹过,呼呼吹过。时隔二十年,他向那山崖又一次深深躹躬。他默默回转,下山。他想,回去一定要问问,这里曾经的小屯子叫什么名字,这里的人们迁去了哪里。
作者简介>>>>
张殿刚,1941年6月出生,大专文化,原籍吉林省梅河口市。1960年参加教育工作,历任西丰县安民镇小学教师、西丰县教育局教志办主编。退休后主持编纂《西丰县教育志》《西丰县志》和《西丰县军事志》,出版长篇小说《春秋美人》。另有短篇小说在多家报刊发表。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