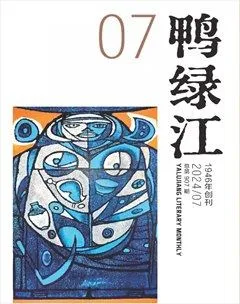钢铁狍子
米忠诚把一条死狗扔到车上。他拍拍身上的雪末子,说,还好,死的是一条狗。马春放乐了,说,得,下一站,咱们找个小馆子,有酒有肉,庆祝我死里逃生。车马炮正在机车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他师傅李留财一把将他薅起来,你想干啥,想害死人啊!车马炮赶紧给大家跪下说,下回我再也不敢了。
车是滨绥线的货运列车,一种新式的蒸汽机车。它跑起来像患了哮喘的病人,浑身顶出的白烟是这列蒸汽机车倒出的气,少倒一口就死了。机车上挂了二十节货厢,他们这个车组负责将南边的生活物资运到东北边陲,再将东北的大豆、煤炭、木材运出去。
米忠诚是这列列车的副司机,马春放是正司机、班组长,他们两个人负责开火车。另外两个是他们组的司炉——老司炉李留财、小司炉车马炮。司炉也叫小烧,负责烧炉。车马炮刚上岗,年龄十八,长得像十五,对啥都新鲜,还没把蒸汽机里的炉烧明白,就敢动车头上的开关。车刚出哈尔滨,他趁车停在四等小站加水的空当,坐上了正司机的位置,一拉手刹,车顺着铁轨滑了出去。眼见就要撞到几米外的马春放,米忠诚“妈呀”一声跳上车头,一把拉住手刹,车轮在铁轨上发出刺耳的尖叫,马春放顺势躺倒在枕木上,这才躲过一劫,但车头的惯性还是撞上了前面的一个活物。米忠诚吓出一身冷汗,他跳下铁轨,在五米开外摸到一只被撞飞的大黑狗。
大黑狗死透了,但死相不难看,头上裂开个口子,流了一地的血,渗在雪地里,看样子是脑袋撞到了铁轨上。马春放跳上车头,给了跪在地上的车马炮一脚,骂,小青棒子,再敢乱动,老子整死你。
米忠诚在马春放胸脯捶了两拳消消他的火,得了,你挺机灵,这不没啥事吗?他的嗓门挺大,嘴里呼出的热气迅速凝成一团团的雾,让人觉得他的脸不那么真实。
米忠诚觉得最近是被倒霉催的,先是媳妇贾桂花闹着要离婚,理由是米忠诚总不着家,三天两头往外跑,弄得她心里没有抓挠,日子没法过。只有米忠诚心里明白,他老婆在那个事上瘾大,一天没男人弄几遍就浑身不舒坦。可是,他米忠诚是跑车的,三天两头离家是正常的事。难不成还把她拴到裤腰带上?
裤腰带上是拴不成,米忠诚就在下班后,加班加点地耕他老婆那块不产粮的地,一天下来,比跑夜车还累。后来,他老婆变本加厉,居然给他弄了个小红本本,上面用各种别人看不懂的符号记录着米忠诚的“工作”完成情况,弄得米忠诚哭笑不得。他几次起了离婚的念头,但转念一想,婆娘就是这个样,娶到自家炕上就得受着,可没想到,这婆娘还主动要离婚,搞得米忠诚措手不及。
mO+UZio2CzTv9/T5pRe7Ej8Az7EdeUWtuizQ0ooPDEY=米忠诚觉得这里面有事,他特意调了一个班,大雪天蹲在自家墙根儿守夜。果然,半夜里一个男人溜进他家大门,米忠诚一个箭步冲上去将男人按倒在地,借着雪光一看,原来是贾桂花的爹,他的老丈人。这下子贾桂花可不干了,她的一声号叫哭醒了整条春阳街,春阳街东头是铁路职工家属宿舍区,米忠诚的这点事很快传到了单位,离婚的事这下成了铁板上的钉,人尽皆知。
倒霉就像个老母鸡,开张就连蛋。这边贾桂花闹离婚,那边机务段上要调岗。段长说,忠诚,原来为了你家庭和睦让你跑短线,现在反正你也要离婚了,就紧着有家有口的来,你去跑长线吧。米忠诚一听不高兴了,嘴上说,凭啥!心里骂,娘的,离婚成了自己的短儿。米忠诚反复想也想不明白,他是不是最近得罪了段长?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正常的调动。思来想去,他唯一得罪的应该是老天爷。
本来米忠诚想跟段长耗着:我就是不去,看你能把我咋的,可偏偏又出事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一场北风烟雪过后,他刚闷在机车厢里打了个盹儿,后来他从火车滑行的距离测算,这个盹儿也就五分钟。五分钟里他梦见了贾桂花的大屁股,他正在这之间动作,身子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把他晃醒了。恍惚间,他觉得火车撞上了什么东西,可是他又觉得这种撞击来自梦中他对贾桂花的动作,他没在意,却也睡意全无,一口气跑到天亮。
天亮时,米忠诚的列车停在了一个小站加水,他拿着检修钳检查车体,蓦地发现机车头下的铁环弯成一个月牙形的弧度,铁条上还黏着星星点点的血渍,一块巴掌大的红色碎花布片ZOWUZj9VRG053+C7korwGgV1KAy2t9MLuwBFu1vVVwA=挂在铁条粗糙的“刺儿”上,像风中摇晃着的一面小旗帜。米忠诚的头“嗡”的一声大了,他赶紧拽掉那块碎花布,跑回车厢,拿出工具箱,用铁钳将弯铁条掰直复位,又攒起一团雪,将铁条上的血渍擦干。
从这天开始,米忠诚就一直在等,等消息。如果真撞了人,肯定会有消息传过来,说不定啥时候铁路公安就该找到他了。他对这条线路的情况无比熟悉,其中有一段最容易出事的地方,铁道两边是外地人搭建的违建板房,这些吃铁路的外地人在这里居住,就是为了扒火车方便。车头上的花布和血迹在米忠诚的脑海里已经丰富成了具体的人物,肯定是一个女人,不知道为啥大半夜跑到铁轨上,被他给撞了。米忠诚早就听说过,铁路上撞人也不是啥稀奇的事,顶多蹲半个月拘留。可这种说法根本说服不了米忠诚,那可是一条人命啊!他害怕,不敢再开原来的车,一出车就觉得那女人的鬼魂挂在车头上。半个月后,米忠诚灰头土脸地申请调班组,段长瞄了他一眼,说,自己想通了?正好滨绥线上的货运没人跑,你去吧,给你配个新班组。
滨绥线的货运,是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东北,过张广才岭,穿大海林,下牡丹江,再一路向北,一头扎进兴安岭的老林子里,过多敏河,最后到达绥芬河中俄边境。米忠诚头一回跑这条线,那叫一个越跑越冷,越跑越没人烟,心也跟着越跑越凉。
货运与客运不同,货运的载重量太大,得到横道河子补机。所谓补机就是要加挂一个车头。出哈尔滨,过尚志进入大海林之前,一定要翻张广才岭。这道岭是北边最长最高的山岭,俄国人修建东清铁路时,为了越过这道岭,特意在岭上设了个“S”形的转弯,翻这个弯,一个车头带不动整列车,要加挂一个车头,一个在前面拉,另一个在后面推,才能使列车顺利地翻过这道山岭。因此,横道河子建了个大机车库,设了补机站,这里也自然成了个二等大站。
火车停靠横道河子,米忠诚从车上下来,望一眼野茫茫冷冰冰的群山,心里那种忐忑仍放不下半分。跑了这么远,心还是悬着,说不定回去就该有人找他了。一股凄冷之感顿时让他打了个冷战。
死狗被马春放弄到了横道河子镇上的一个小酒馆里。酒馆里的老板娘是马春放的老相好,马春放常年跑滨绥线货运,进酒馆跟回家一样。酒馆里的大厨剥了狗皮,将狗肉扔进大锅里,灶里烧上松木的劈柴柈子,将入冬前阴干的小白菜扔到锅里,混着狗肉煮,片刻间,一股好闻的狗肉香就在柴火噼噼啪啪的响声中弥漫开来。
酒馆老板娘长得粗壮,一张胖脸上常年飘着两朵红云,挂在那儿从不散去,知道人说是她家的烧酒泡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画了腮红。老板娘将狗肉端上桌,独少了一只狗腿。马春放叫道,我的狗腿呢?老板娘将两朵红云笑到耳朵边,说,你的狗腿长在你身上啊。马春放就敲她的肚子说,我的狗腿进狗肚子里了!
米忠诚没心听他们说笑,更没心吃狗肉,他怎么都觉得这狗肉是那死去女人身上掉下来的。他跑车十几年,这是头一回出事故。车马炮也不动筷子,他还惊魂未定,看着一盆狗肉汤抹眼泪,嘴里还说,是我害死它的。只有马春放和李留财,两个人对着一盆狗肉大吃特吃,直喝得两只眼睛血红,浑身上下冒着热气,马春放就在这样的热气里睡在了老板娘后院的炕头上。李留财不在意,拉着车马炮继续喝。车马炮不敢不从他师傅,喝了两杯烧酒,借着月光跑出去撒尿,吐了一地菜叶子。米忠诚背上车马炮,拽着李留财回了职工宿舍。
第二天一早,补机已经挂好,这次没有采用一前一后的办法,而是用了双挂。所谓双挂就是两个车头挨在一起连挂,前面是主机,后面是辅机,两个机车同时运转。马春放这组做主机,后挂上的这组做辅机。多了一个车头,就多了一个班组,这趟车顿时热闹起来。辅机的班组长是黑子,一个黑大个儿,四十来岁,一脸的胡楂儿,跟马春放很熟。一见面就称兄道弟,马春放迫不及待地将头一天吃狗肉的事向黑子炫耀,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想炫耀由这顿狗肉引起的风花雪月的事。说完,马春放还扔给黑子一只狗腿,说,哥们儿,分给你的弟兄。他居然把少的狗腿要了回来。
黑子说,就这?他晃着狗腿说,小意思!马春放眼里闪过一道光,你给哥们儿演个大的?黑子拿眼把这道光接住说,等机会,我必须给你演一个大的。
车终于在一段粗重的喘息声中驶出了月台,它如一条黑蟒在雪白的张广才岭上盘桓。
车是刚下线的前进型蒸汽机车,光亮油黑的外壳,簇新的驾驶室,光亮的仪表盘,就连锅炉里的底灰都是新的。这趟车是包乘制,六个人一班,三个人一组,每组设一个正司机、一个副司机、一个司炉。正司机负责开车、瞭望和填写行车记录,副司机坐在右侧帮司机瞭望、鸣笛和加水。当然,正副司机也得调班,不能可一个人累死。司炉一般一个人就可以,但马春放这组特殊,多出一个车马炮。
李留财带着车马炮,正把一锹煤扔进炉中,自动开合的炉盖里闪着红灿灿的光。
这个铁家伙长个大胃,跑150公里就得10多吨煤,你需要一口气不停地扔600多锹,能行不,小子?李留财一边将煤扔炉膛里,一边对车马炮说。
车马炮点头的节奏跟炉盖开合的节奏一致,他的头随着李留财的锹头摆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也不说话。
李留财放下锹,说,你干吧,这玩意儿不用学徒,上手就能干,只要有把好力气。
车马炮接过铁锹开始扔煤,汗水顿时爬到脸上,在他被煤灰熏黑的脸上冲出一道痕迹。
李留财点了一根烟,对马春放说,下一站我去后车睡觉了,这徒弟出徒了,他跟车。
马春放看了一眼嘴上的毛还没长齐的车马炮,说,段长也不知咋想的,给我们组整了这么个小青棒子。
李留财打开窗,把烟吐到窗外,说,还不是嫌我老了,给咱组整个接班的。
马春放车开得带劲儿,昨晚一场欢爱让他精神头倍儿足,一边开车一边嘴里吹着口哨。米忠诚却没有心思,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不敢眨眼皮,生怕前方有什么障碍物被撞上。虽然他知道发现障碍物刹车通常来不及,但他也不想再有事故发生。如果他当班的副司机不跟他一起打瞌睡多好,也许那个女人就不会死。这个念头已经折磨他成千上万遍。
车窗外是北方初冬的原野,刚下过一场雪,张广才岭的山头蜿蜒起伏,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和乔木一片片地掠过,仿佛倒下去的一排排哨兵,不开车窗也能感受到窗外的阵阵寒意。车翻过张广才岭,地势渐低,但也有些起伏。初冬的光线轻薄,一晃一晃地漫过路边的风景。
黑子上了他们的主机,坐上了马春放的位置。他们班组属牡丹江车务段,跟米忠诚和马春放不是一个单位,但出车在外,没人介意。
黑子说,明天到绥芬河,我请你们吃大餐。马春放一听来了神儿,说,啥大餐?黑子得意地一笑说,等着,别急,到时候就知道了。
过了大海林,火车开始在兴安岭的林子里穿行,兴安岭里多是松树和桦树,树密林深,使原本就轻薄的光线更加暗淡,仿佛提前进入了黄昏。米忠诚的神经松弛下来,山高林密,又是冬天,铁路线上不需要瞭望,他将眼睛轻轻地合上。
忽然,他被黑子的一声大笑惊醒,哈哈,有了!米忠诚睁开眼睛,远方,一群小黑点儿在铁轨上缓慢地移动,仿佛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
米忠诚大喊,快刹车!但黑子却瞪圆了眼睛,脸上挂着兴奋的表情,嘴里喊,车马炮,加把火,大餐来了!车马炮不明就里,加快了扔煤的速度,锅炉里的火烧得更旺。
火车撞上去之后,发出刺耳的车轮摩擦钢轨的刹车声,在山林里回响。火车又向前滑行了大约200米才停下。凭米忠诚的经验,刚才的火车时速能达到80公里,比规定时速要快得多。
米忠诚拽过黑子的衣领,举起拳头就打。黑子被迎面的拳头打蒙了,说,你干啥?
米忠诚吼,你干啥!
两个人撕扯的空当,主机辅机上两个班组的人都聚拢过来,没有人在意米忠诚的愤怒,大家都跑去围观“猎物”。
撞上的是一种似鹿非鹿的动物,黄色的皮毛,屁股上的一条短尾巴夹在裆里,头上顶着老树叉一样巨大的角。它们在火车撞上去的一瞬间四散奔逃,但还是有一只被撞出铁轨,甩在了旁边的松树干上。
被撞倒的是只傻狍子,这种动物在东北山林里很常见。之所以被叫成傻狍子,是因为它们不机灵,好奇心重,一副人畜无害没心没肺的傻样子。这只傻狍子看不出大伤,肚腹处因为甩在树干上被剐出几道带血的伤痕。它躺在地上不动弹,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惊恐地望向围观的人们,嘴角流出的血滴在雪地上,像一朵红色的花儿。
人群中忽然冲出来一个人,他分开人群跪在狍子跟前,把狍子抱在怀里,嘴里叨念着,你们这是干啥?是车马炮。
马春放一把将车马炮拎起来,像拎一只瘦鸡。你个雏儿,在这儿发什么羊角风,滚回去。米忠诚看不过去,拉开马春放的手。李留财跑过来,拉开米忠诚,说,这条线上,你也是个雏儿。米忠诚说,啥意思?李留财说,这叫撞狗,啥都当狗撞,是这条线上的规矩,弟兄们就靠这个解馋,等着吃狍子肉吧。
车马炮执意要把受伤的狍子抱进车头。大伙拧不过一个孩子,只好随他去。狍子体形大,被安置在煤堆边,身上盖着车马炮的工装棉袄,棉袄的一角被狍子身上的血染红了,在黑色的车厢里很刺眼。车马炮说,我要守着它。狍子的眼睛在黑暗中黑亮亮的,闪着幽光。车马炮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喂给它,它拿舌头舔了舔,黑子看了这一幕,叫道,跑车十几年,头回遇上不稀罕吃肉的,晦气。黑子下了车,马春放替了黑子,火车拉响了汽笛,重新启动了。
到了绥芬河,黑子要把狍子扛到饭店里宰了,车马炮说啥也不干。火车进站,跟站里的人交接班,车马炮非要留下来守着狍子。整个班组的人显得很丧气,有人笑话黑子第一次失了手,没办法,黑子只好拿马春放给他的一只狗腿请大家在小酒馆里喝酒。可米忠诚却没心思喝酒,更没心思吃肉,他一个人在绥芬河的街上游荡。
他撞死的肯定是个女人,那一小片红色碎花的布片提示着他,也许还是个爱美的女人,像他媳妇贾桂花一样。可到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就连私下里的议论都没有,好像那个被撞死的女人根本不存在一样。难道是自己被梦魇住了?可那挂在车头上的碎布和血迹是那么真实。要真是一场梦就好了!等着吧,该来的一定会来的。米忠诚使劲裹了裹身上的工作服。
绥芬河的街上冷得出奇,冰雪覆盖着街路,一片银白。街上的行人少得可怜,仅有的几个人也缩着脖子,像一个个缩头乌龟。小城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有许多俄式的建筑,就连大街上也飘着俄罗斯的大列巴味儿。
米忠诚一路走,绥芬河小城里高低不平的街道像他不平静的心。米师傅!忽然有人喊他。他回过头,是车马炮。
你怎么不去吃饭?米忠诚问。
我吃不下去。车马炮抽着两筒鼻涕,走了上来,眼里还汪着泪。
狍子呢?
在车头里,我出来给它弄点儿吃的。车马炮说。
有救?
不知道。
米忠诚的脑海里迅速闪过那只狍子黑幽幽的眼睛,清澈又无辜,也许,那女人也有这样的眼神。他摸摸车马炮的脑袋,像是安慰。
为啥要救狍子?
因为我妈。
你妈?
我妈就是被火车撞死的。车马炮忽然说。
米忠诚心里一惊,他忽然明白眼前的少年为什么对一只被撞的狍子反应如此激烈。
什么时候……被撞死的?米忠诚说得很小心,声音极小,嘴里呼出的热气游丝一样,像此刻他发出的声音。
车马炮低了头,十年前了,我刚记事。
米忠诚松了一口气,说,所以,你恨撞狗?
嗯,我打小就恨铁道线,恨火车。
那你还来铁路上当小烧?
我爸说,得来,这是我妈拿命换的。
米忠诚脑海里闪过那个被撞死的女人,尽管他不知道女人的样貌,但他却不自觉地按照眼前车马炮的样子勾勒起来。也许她也是单眼皮,眉心上有颗痣;也许她的皮肤也很白,因为他注意到车马炮除了一张被锅炉煤烟熏黑的脸,其他裸露的皮肤都很白;也许她也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像车马炮一样。
米忠诚搂过车马炮,拍了拍车马炮的背,这一次他是在安慰自己。他在心里默默地说,幸好不是。
米忠诚说,给我讲讲你妈妈吧。
他和车马炮沿着绥芬河的街道往回走,被雪覆盖的街道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应和着车马炮的讲述。
我妈是个傻子,她啥也不懂,但她会生火做饭,养她的五个孩子。本来我家住在大兴安岭,后来,跟我爹到了铁路上,我爹也是铁路上的小烧……
后面的故事没有出乎米忠诚的意料,傻妈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扒火车。
知道是谁撞死的吗?米忠诚问得小心翼翼,仿佛答案跟他相关。
不……知道。我爸说,铁道上撞死人白撞,因为铁道线上是禁区……车马炮目光闪烁,闪出跟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清冷的光,让米忠诚不禁打了个寒战。
老米,你咋跑这儿来了,快,组长喊你回去。李留财哼哧带喘地跑过来,他看了眼车马炮,咋不去伺候你的狍子?
小酒馆里热闹非凡,马春放和黑子正领着各自的人马在拼酒。马春放已经喝得汗毛孔都发红了。黑子的脸本来就黑,这会儿黑里透出一层红,仿佛全身被泼了一层黑酱油,油光发亮。看到米忠诚和车马炮进来,马春放一把薅住车马炮,把他按到黑子身边,说,小子,今天因为你,咱们少了一顿狍子肉,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替咱们班组喝倒他们。
车马炮拧着脖子,说,我不喝,我来要白菜帮子。
要白菜帮子干啥?
喂狍子。
马春放一听,火了,哟,小子,给你脸了是不,今天不喝倒,甭想要白菜帮子。众人起着哄,对,少吃一顿狍子肉,该罚。
酒是散装高粱酒,泛着一股土腥味儿,一口下去,整条肠子都火辣辣的。黑子一看马春放派了新兵,一副不乐意的样子,他数了数,说,你们欺负人,你们班组比我们多一个人。他指的多出的一个人是车马炮。
马春放说,他不能算人,他顶多算个小傻狍子。说完放声大笑,引得两个班组的人都一起哄笑起来。
车马炮夺过酒杯,好,喝就喝,但我有一个条件,我归黑子哥。说着,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黑子兴奋了,好小子,有你的。因为有了车马炮,黑子班组一副兵强马壮的模样。马春放不乐意了,他半开玩笑地转向李留财,说,你咋培养出一个叛徒。他表面上不乐意,心里却很高兴,因为车马炮的叛变,酒桌上的气氛起来了,对于一个酒鬼来说,没有什么比酒桌上的气氛更加重要。车马炮虽然不会喝酒,但仗着年轻力壮,还有股虎劲儿,很快就替黑子拿下了马春放。马春放兴奋,黑子更兴奋,现在,整个酒桌上唯一清醒的应该就剩下米忠诚了。
酒喝多了,话就多。主题当然离不开女人,马春放把他相好过的女人细数了一遍,黑子也不甘示弱,两人言语已经不堪入耳。米忠诚看看车马炮,担心这孩子受不了。可车马炮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俩人没啥可吹的了,黑子起了头儿,开始吹撞狗。他说,撞狗你们懂吗?就是撞着啥吃啥!满桌人都是铁道线上的老油条,不可能人人都有女人,但人人都有撞狗的经历,这个话头一起来,气氛更加热烈,它变成了酒桌上人人都能参与的一个话题。
黑子说,我头一回跟车,那时候还是老机车,车头是闷葫芦,根本看不见外面,只听车头外面“嘣”的一声响,我师傅赶快刹车,让我下车看,我一看,撞死了一只野狗,死相挺惨。我吓坏了,我师傅让我扔车上,到站吃狗肉。
所以,你们这儿管撞活物叫撞狗?米忠诚说。
对喽。黑子接过米忠诚的话,你跑南边,不明白北边的规矩,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马春放不服气,你那算啥,那时候我跟我师傅一到晚上经常听到车头外面嘭嘭响,我师傅根本不停车,到站一检查,车头上都是血……
黑子说,你都撞死过啥?亮亮底。
啥都撞死过,狗、鸡、鸭、牛、羊,有一回,居然撞死过一只熊瞎子。后来,我师傅学会了,只要听见车头上“嘭”的一声响,就赶快刹车,死啥往车上扔啥!撞死啥咱吃啥,那时候,咱们的嘴天天抹油似的。
黑子忽然神秘起来,说,你撞死过人没?
人?马春放顿了一下,他咧着大嘴,支出来的门牙碰着下嘴唇,人谁没撞死过呀,咱可是老司机。你撞死过没?马春放彻底喝高了,舌头打着卷,桌上的剩狗肉都已经凉透。
我撞死……过一个老爷们儿,等我下车看的……时候,他还没断气,可他半个身子卷在车轮子里,说啥也拽不出来,我眼睁睁……眼睁睁地看着他血流干了……黑子说,一口酒又下了肚,舌头也跟着打卷。
你那……算啥,我……撞死过一个女的,我以为是……是一只大黑狗,赶巧那阵儿狗肉吃腻了,我就没……没停车,等我停车……发现时啥……啥都晚了,人一直挂在……我车……车头上……两只眼睛还瞪……得滴溜圆,跟没死似的……
一听你就是吹牛,人要么撞飞,要么卷车轮底下,死了咋挂在车头上?还瞪眼睛?吹吧,你就!黑子问。
你不信拉倒。反正那女人就一直挂在车头上。
车马炮两只眼睛冰锥一样盯着马春放,啥样的女人?
我哪知道啥样,黑灯瞎火的。
你在哪儿撞死的?车马炮追问。
我哪知道……我给段长打电话,段长问在哪儿撞的,啥时候的事,我也说不上来……但我觉得不一定是我撞死的,我想不认账,段长说挂你车上就算你干的……你们说我……倒霉……不……大家正等着马春放说下文,他忽然上眼皮打下眼皮轰地倒在餐桌上没了声响,片刻打起了鼾。
大家轰的一声散了,有人咂着嘴,说,吹吧,一个比一个能吹。酒喝不去,有人推开酒馆的门出去了,将外面的凉气带了进来,人们也瞬间清醒了。黑子推了一把马春放,你个货,吹牛有本事,酒量太次了吧。马春放没反应,黑子带着他的班组悻悻地走了。临走,他对米忠诚说,手下败将,你们收拾残局吧。米忠诚看着马春放,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阵阵难受。
李留财说,得了,走吧,这回他成死狗了。车马炮呆坐着,看着马春放不吱声。李留财碰碰他,走啊,发什么呆,往后这样的故事多着呢。说着,就要把马春放往车马炮肩膀上架。
干啥啊?车马炮一扭身子。
你年轻,你不背谁背。
我不背,他是杀人犯!
李留财给车马炮一个大脖溜子,这你也信,小傻狍子,他喝多了,吹牛呢。米忠诚架起马春放往门外走,车马炮忽然抢下马春放的胳膊就往身上背。李留财人虽老力气在,拿手一,马春放变成了车马炮身上的猪肉柈子。
你不知道,他就这尿性,喝多了啥都嘞嘞。李留财跟米忠诚解释,屋外,月亮将雪地照得一片银白,远处的铁轨银带子一样,一列列火车卧在交错的银带子上,沉默着。
走在前面车马炮忽然加快了脚步,向铁道线走去。他几步走到铁轨上,忽然发出一声长啸,一个大背把马春放摔在上面,接着他跃到马春放身上,抡起两只拳头朝马春放身上一顿乱砸,还没等李留财和米忠诚反应过来,马春放已经满脸是血。他晃晃悠悠地欠起身子,用手抹了一把脸,喊道,浪费啥不能浪费酒,咋能把酒往我脸上倒呢,不服接着整!说完又躺倒,竟打起呼噜来。
李留财蹿上来,一把将车马炮从马春放身上抱下来,甩一旁,吼道,你他妈的想咋样?他就是吹个牛,你至于吗?!
车马炮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鹿,从地上爬起来,朝李留财一头撞过去。想不到他这瘦弱的小身板竟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猛然将李留财顶翻。李留财捂着屁股疼得龇牙咧嘴,喊,你个傻狍子,反了你了!米忠诚,你干杵着干啥,救命啊,傻狍子疯了。
米忠诚仍站在原地,苦笑了一声,莫名来了一句,傻狍子?那他妈不是傻,是心里干净。
车马炮蹲在地上,埋头呜呜哭起来,还是个没成年的孩子模样。
这时,那只受伤的狍子竟一瘸一拐地走来了,凑近车马炮,用柔软的舌头轻轻地舔他的手,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唤醒他。车马炮抬起满是泪水的脸,从衣兜里掏出白菜帮子。狍子一边啃着车马炮手里的菜叶,一边温柔地舔着他的手指,黑黝黝的眼睛里闪耀着明亮的光。
月银如洗,两条晶亮的铁轨伸向苍茫的远山。狍子已然恢复了体力,蹦蹦跳跳着朝山间走去。它不时停下,回头呆呆地望他们一会儿,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尽头。
作者简介>>>>
易可,原名郭少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北2830成员。1999年开始写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共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万字,散见于《作品》《飞天》《清明》《鸭绿江》等刊物。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去阿尔巴的路上》。另有儿童文学、散文、剧本等作品出版。
[特约责任编辑 万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