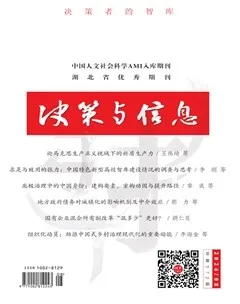论马克思生产正义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
[摘 要] 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依据,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范畴。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建构出了基于价值追求的生产正义。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建立在马克思生产正义的理论基础上,具备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态三重正义性维度。此外,马克思生产正义为当前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错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收入分配不合理、知识产权保护过度等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基于此,马克思生产正义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构建,应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自主创新、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创新体系,全方位、立体化地推动新质生产力高效发展,实现生产正义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关键词] 马克思生产正义;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产业要素转型;新型生产关系;产学研融合;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4;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8-0005-09
马克思构想中的未来社会技术基础不仅有量的积累,更有质的规定性。建立在外部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内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为了实现符合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跃升,习近平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的概念,既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思想遵循,更为我国今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技术革命性突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人本逻辑下,新质生产力在推进生产力跃迁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也没有忽视社会生产中可能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这与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批判的正义思想一脉相承,如何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下的生产正义成为新时代必须思考的问题。从学理层面把握马克思的生产正义思想,剖析新质生产力的正义维度,探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生产非正义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实践对策的着力点,希冀为开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局面提供理论参考。
一、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马克思生产正义在场
马克思生产正义思想确立了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其思想内涵奠定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探讨二者的内在联系有助于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与目的导向。
(一)基于价值追求的马克思生产正义
马克思指出,社会制度无法跳脱现有的生产力发展,物质生产只能在既有的生产水平上进行生产,正义所反映的内容正是对当下社会制度的适应,“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式……无非是对物质生产的反映”[1] 69-70。针对马克思这一观点,段忠桥认为,马克思正义观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2],也就是说,人的价值判断会随着生产力状况的改变而改变,关于正义的理解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制度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提高了人的自由度,正义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改变。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一般”观念。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环节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将生产活动视为孤立的、封闭的,与自然界一样具有永恒性,否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性。这种生产观念由于无法看到不同时代生产方式的差别,其研究视域都只停留在个体生产或使用价值生产阶段,从而认为劳动者的劳动积累就是财富增加。而在马克思看来,真实的社会情况表现为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自身就越贫穷,劳动活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3] 157,工人从事生产活动的伊始,生产的劳动能力与生产手段就分离了,生产者本人也就丧失了生产产品的所有权,生产的劳动成果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同工人的劳动相对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人的相对工资却处于下降的趋势,继而整个社会都处于异化的状态,工人阶级愈发贫穷的现象成为事实。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以萨伊、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囿于分配关系的局限中探讨正义,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见,所有权不平等的问题不可能在分配领域得到根本解决,因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
其次,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家通过宣传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来掩盖资本的剥削本性。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生产正义与私有财产、劳动异化等概念相结合,对工人在劳动中被异化的现象表达了强烈的批判并道出,其本质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将劳动者对公平的思辨和正义的追问转向了对整个社会生产方式非正义性的审视。“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4] 894,工人的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资本家创造出了逐利的、具有增殖属性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5] 265,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不再只限于满足自我需求,资本家的生产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5] 683。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前提,不凭借劳动便可以实现剩余价值占有的最终目的。这种生产目的导致了劳动者被异化,阻碍了人的自由、平等的实现。
最后,马克思指出生产正义的核心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马克思否定了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正义观,并从物质生产中探讨了生产正义何以实现,即要想真正实现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就必须触及生产领域,变革现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5] 96。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自由人联合体”下的生产能够合理分配全社会的生产资料与劳动时间,可以极大地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浪费。此外,马克思所建构的生产正义突出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劳动者也就是人民群众通过掌握社会的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强制劳动中解放出来实现“自主活动”的状态。直至扬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生产正义所追求的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
(二)马克思生产正义思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支撑与目标追求
尽管马克思所建构的生产正义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但却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形成场域。关于正义的价值判断与人的解放程度和所处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基于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的现实具备、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背景,新的发展时代下的正义观念也随之变革,更加注重富足的精神需求、多元的职业选择、畅通的发展通道等。制约社会变革的旧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亟须升级。习近平高屋建瓴、审时度势,以宏阔的战略思维和前瞻视野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顺应了我国经济从工业时代走向数字化时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纵观马克思的生产正义思想,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财富不断增长的剥削属性,手段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归根结底是为了消除异化劳动、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以看出,马克思关注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关注人的解放,这也是马克思生产正义的最终价值追求,这与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一致,即从根本上实现了现代性从资本至上到劳动至上的原则性转变[6]。对于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方式与过程,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7] 602,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科学技术的相互促进,这与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特征内在统一。马克思还就机器普遍化应用对工人的影响进行讨论,机器的应用是为了辅助人类的劳动过程,“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5] 508-509,马克思批判了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直接等同于机器应用的思想,主张通过正确使用机器,实现社会的进步。提高劳动效率、推动科技发展的力量始终在于人类本身。这一观点也体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力三要素提出的跃升要求。
质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马克思生产正义的继承,同时也是将生产正义落在实际的重要举措,其内涵特质归根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也推动了生产领域的理论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新质生产力正义性的三重维度
新质生产力在继承马克思生产正义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正义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正义性。
(一)生产力维度:推进了先进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深度耦合
以社会分工为逻辑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向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通过分析三大叙事主题即所有权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和剥削问题,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8],并构想出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性质,同时这也是构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涵盖自然与人造资源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过程中加工对象的存在,还深度参与到生产力结构的整体构建与演进中。科技创新打破了传统生产活动的物理边界,将越来越多不受时空限制的非实体要素引入生产力系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场域。以数据生产要素化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强调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生产资料的革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此时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力量的叠加,而是知识、技能、创新思维与先进科技的深度融合。先进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拓展自身能力、实现主体性回归的媒介,智能化、自动化技术赋予了新时期劳动者新的技能与角色,从过去被动的执行者转化为创新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与传统制造业相比,新质生产力开拓了以数据资产为代表的新的价值源泉,并由数据的生产者、使用者以及维护数据系统的参与者共同创造与分享。通过合理的数据要素分配机制、创新的劳动价值计量方法以及新的收入分配政策,使得剩余价值更加公平合理地流向新时代的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助推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高效整合,不仅关乎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优化,更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共同富裕构想的现实回应与创新发展。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提升劳动者素质,使其能够适应并驾驭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打破资本对高级生产资料的垄断,实现劳动关系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步创新,确保劳动者在生产革新中获得稳定的社会支持。
(二)生产关系维度:保障了劳动者作为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
生产资料的组织形态是建构生产过程的关键因素。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工厂、矿山、铁路等大型工业设施遍布各地,劳动者主体间的社会联系规模空前扩大。随着机械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过程中主体间的联系逐渐由直接的人际交往转变为间接的人机交互,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日益沦为维持机器运转的附属角色,其劳动价值被机器的高效生产所掩盖,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同人相异化”,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的主体性削弱与异化现象。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4] 96。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通过重塑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关系,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深度变革与价值创造方式的升级,为劳动者的个性解放创造了条件。新质生产力在构建我国新型工业化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加工制造业向尖端技术创新、高价值生产环节迈进的过程,亟须培养大批能够紧随科技与社会生产力进步步伐、在技术攻关与创新发明中完成“临门一脚”的新型人才。劳动者能够凭借知识技能与创新思维,通过与智能设备的有效互动,更好地从事复杂的劳动生产。因此,应着力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创新型劳动者培养机制,引导并激励他们积极投身于创新型行业的建设与发展,充分释放并发挥创新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的创新动能。此外,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产业升级,一方面通过创新引领与收入提振的双重效应,有力推动了消费市场的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消费升级与产业革新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均衡国内供需格局、畅通经济内循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消费升级为驱动的生产模式在倒逼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处于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利用技术优势实现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定制化,彰显劳动价值的同时惠及了更多消费群体,这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9] 214的直接体现。
(三)生态维度:巩固了以绿色生产为基础的生态正义理念
追逐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难以维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与民众思想状态的提升,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纷纷转向对生态领域的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超越了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但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案,使之陷入了理论的乌托邦。现实来看,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资源环境可承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跳脱出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发展思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过去以西方模式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为人类探索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选择。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质生产力在绿色现代化的实践深入下应运而生。新质生产力生态维度的正义性建立在对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继承和对西方生态治理模式超越的基础上,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同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的统一。首先,新质生产力为绿色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清洁能源技术、节能降耗技术、循环经济模式、环保新材料等的应用极大降低了生产中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保证了从源头到终端的全链条生产绿色化。其次,实体产业与虚拟互联的双重模式为全社会建立起大型的绿色网络,融入了人们日常的交往活动中,为摆脱粗放型生产方式、引导全社会对绿色生产方式的价值认同夯实了基础。新质生产力巩固下的绿色生产方式,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为重塑全球生态正义贡献了中国之治。
三、新质生产力推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产非正义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新技术的发展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利用”实现社会化的建构。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导致的异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批判,而应将技术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建立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技术基础。马克思还强调了正义的关键在于是否与生产方式发展相符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4] 379。因此,新质生产力下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释放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离不开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则可能出现非正义悖论。
(一)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错配
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现象日益凸显,给生产效率的提升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显著影响。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当下,科研机构与大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其决策过程却常常受到信息不对称、市场感知局限以及短期商业利益导向的困扰,导致创新成果与实际产业需求间出现错配。此外,创新设计与执行效果偏差、执行力不足等问题,亦进一步加剧了技术与产业需求的脱节。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倘若技术更新的步伐未能与产业结构调整保持同步,就会导致旧技术与新的产业需求出现错配,形成资源浪费。相反,新兴产业的过快发展,而配套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条件尚不成熟,则会导致先进技术无法在实际生产中得到充分应用,形成“技术过剩”。这就形成,先进技术无法有效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优势,产业需求同样无法得到适配技术有效支撑的尴尬境地。由此,无效的技术投入与资源配置的错位所引发的社会资源浪费,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语境下不容忽视的重大风险。破解产技错配难题,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避免社会资源浪费至关重要。
(二)产业结构与就业形势失衡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显著特征。在科技进步、市场需求变化、政策引导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经济体系中各产业部门的产出和投资结构发生大规模调整。新质生产力作为引擎,加快了这一调整的规模与速度,产业结构的骤变产生了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智能网联、云计算、生物科技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强势崛起,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对传统劳动密集型岗位产生了替代效应,导致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另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促使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尤其是中高端环节的回流趋势,导致部分地区产业空心化,引发结构性失业与地区性人才短缺。尽管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创新浪潮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其伴随的灵活就业形态却削弱了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职业安全感缺失。此外,技术密集型企业过度依赖自动化设备,可能导致大规模裁员,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新质生产力引领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带来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对就业市场带来了严峻挑战,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凸显。这充分说明,推动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注重解决就业结构失衡、保障劳动者权益等问题。
(三)效率跃升与分配失衡并存
当前,我国经济体系在新质生产力的强劲驱动下正在经历一场深度转型。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生产效能,使得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边际成本大幅降低,实现了利润的快速增加。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互联网巨头与电商平台借力网络效应与算法优化,构筑起难以逾越的行业壁垒,为具备高级技能的劳动者如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等创造了丰厚的收入机会。然而,技术红利的累积与分配不公现象相伴而生,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短期内,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区域间的信息与技术差距,形成了鲜明的数字鸿沟。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劳动者收入的绝对值差异上,更表现在收入增长速度的悬殊以及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程度上。从个体层面来看,掌握稀缺技术的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技术鸿沟在新经济环境中日益凸显。如何在推进技术变革与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弥合城乡、区域间的技术差距,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
(四)知识产权与数据共享冲突
新发展阶段,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产,对企业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分析能力要求大幅提升,数据资源的开放缩减了共享成本,削弱了头部企业对数据资源的垄断。新的生产要素催生了大量的创新成果,作为创新成果重要载体的知识产权,也成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下企业竞争的核心资源。然而,数据资源传播与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内在冲突,涉及公私权益的平衡问题。知识产权强调知识产品的独占性、排他性,以保证创作者的独有收益权利。通过赋予创新成果财产权,明确了创作者对作品的支配权,以此作为激励创新、提升技术转化效率、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然而,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加剧公共知识资源私有化,甚至异化为少数头部企业敛财的手段。当数据与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滑向行业垄断,将阻碍数据流通,加剧技术壁垒与数据孤岛现象,反过来成为制约社会创新的枷锁。因此,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的平衡问题至关重要,既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又要防止过度保护导致的负面效应,以实现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公平分配,保障社会创新的持续发展。
四、基于生产正义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
马克思生产正义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向度涵盖了政治、制度、技术三大层面,旨在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引领方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制度保障、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创新体系,全方位、立体化地推动新质生产力高效发展,实现生产正义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政治保障: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实质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就是将党的先进性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先进性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规定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遵循。马克思指出,“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9] 42,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核心便是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党的先进性。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前提是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目的是发展先进层次的生产力并使现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
发展先进生产力与时代主题紧密结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革命通过推翻“三座大山”解放生产力,到如今“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10] 8,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自冯·诺伊曼发明计算机引发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便不断驱使着世界各国走上了产业革命的道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依靠资源要素投入式发展,是技术层面、产业结构、经济模式等全方位的深度转型升级。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实现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突破。其中生产力要素中的科学技术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水平,洞察未来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此外,发展先进生产力与为生产力发展开辟有利条件是有机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10] 9,在党的先进性理论指导下,我国社会的体制机制在适合国情的基础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为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营造了坚实的政策支持环境,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能。
(二)制度驱动: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自主创新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创立的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被应用在国际贸易及利益分配领域,其通过商品生产与分工模型的分析揭示了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但是,由于简单地将剩余价值与利润相等同,造成了其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从而无法准确分析国际贸易中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关系。在实际的国际贸易中,国家间仍存在着较大的成本差异,这恰恰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悖。马克思“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11] 22。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下,表面来看各国都能参与贸易实现互惠,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大多被限制在价值增值较少的生产环节,而发达国家凭借核心技术的垄断获得了大部分的收益,加重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贸易的自由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国际技术转移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方式,在创新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被发展中国家视为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如今,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更加注重对关键性技术的保护,防止技术外溢。如果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输入,就会造成自身创新动能不足,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力薄弱。从长远发展看,将丧失一定的经济自主性,发生技术封锁的风险。要摆脱技术依赖的状态、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本出路就在于坚持自主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自主创新反映的是国家的创新意志。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自主创新型国家总能抓住每一次的技术转型机会,率先抢占前沿技术的制高点,开拓新的创新领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迅速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取得重大突破。因此,中国式自主创新发展道路离不开国家的引导力和意志力,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10] 36,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强化国家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根据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清晰的科技创新战略,明确重点攻关领域和目标,为自主创新提供方向性指引。其次,始终保持敏锐洞察力,密切关注世界市场生产力演进的最新动态与未来趋向,以前瞻性思维精准把握技术变革的脉搏,致力于抢占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以期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9] 273,发挥自主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驱动力,坚定不移地依托并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作用,确保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中,国家意志得以彰显、公共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全社会创新活力充分激发,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与制度保障。
(三)技术支撑: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创新体系
《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这意味着还存在大量的科技成果难以实现产业转化。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利用率、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协同发展创新体系,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大背景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新的技术文明发展路径下,商业航天、新兴氢能、创新药等新产业加速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为了解决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重大需求中的科学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2020年起成立第九大学部:交叉科学部,为推进多技术、多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对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从发达国家完成技术转型的历史来看,它们大都离不开研究型机构的设立与教育体制的完善。科技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方单打独斗,而是在社会全要素的参与下对制度、技术的全方位创新。此外,新技术的研发往往面临资金、人才、设备等资源瓶颈,单靠企业或研究机构的力量难以独立解决,产学研深度融合可以打破资源壁垒、实现优势互补、降低创新风险,从而加速新技术的研发进程。
科教兴国战略支撑背景下,我国要继续“深化产学研用结合,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12]。新质生产力在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建立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尤为重要。由于人才培养周期较长、人才培养模式的滞后性,过去企业或地方政府机关为了实现快速发展而大力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忽略了人才的自主培养,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育也通常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需求。为此,要着力增强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单位在创新活动中的贡献度以及对接、服务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履职效能。鼓励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入驻科技创新园区,加强新型研发项目合作,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营管理模式,着力开展涵盖技术研发、企业孵化及人才培育等一系列活动。创新型企业要构建多元化的技术体系,有效规避对单一技术路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注重持续的研发投入、跨领域技术融合与集成创新,以实现技术体系的稳健、多元、弹性发展,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与技术挑战。
[参考文献]
[1] 司春燕.马克思恩格斯法正义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段忠桥.马克思正义观的三个根本性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张威威,薛建立.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决策与信息,2023,(1).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王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6).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二○二四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24-03-13.
[责任编辑:汪智力]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Marx's View of Productive Justice
WANG Yiqi, YANG Wenliang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social change, productivity is the core categ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Marx constructed a production justice based on the pursuit of value through his critique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The proposition of new productivity is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on justice, which has three dimensions of justice: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cology.In addition, Marx's production justice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olve the mismatch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mand,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Based on thi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roduction justice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 in build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d by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i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reated by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system. All-round and three dimensional promotion of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needed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production justi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s production justic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factors;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24-04-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YJC710077)
[作者简介] 王祎琦,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文亮,男,河南平顶山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