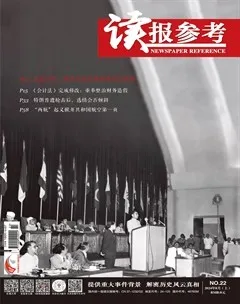不足五十克的素纱单衣如何“炼”成
近日,“彼美人兮——两汉罗马时期女性文物展”在湖南博物院开幕,国宝级文物曲裾素纱单衣等展品为首次展出。素纱单衣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也是目前最早、最薄、最轻的服装。
“素纱襌衣”
1972-1974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共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文物,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辛追是利苍的妻子,去世时年约50岁。一号墓墓葬中,四壁最外层的椁板与内椁板之间留有东、西、南、北四个边箱,用于存放大量随葬品,供辛追在地下的吃穿用度。素纱单衣与绵袍、裙子、袜子等一共14件衣物,就出土于西边的一个竹箱子。
素纱单衣中的“单”字,是说它很单薄的意思吗?其实不然,这件衣服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素纱襌衣”。《说文》说:“襌,衣不重。”《释名》言:“襌衣,言无里也。褠,襌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宜形如沟也。”三号墓的衣衾腐朽严重,但是遣策(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较为详尽,出现了许多有关“襌衣”的内容,涉及了帛、绪、绮等多种材质,白、霜、青、绀等多种色彩,可见“襌衣”是当时比较常见的服饰种类。由于“襌”这个字没有简化体,加上也不是一个常用字,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写作“单衣”。
据介绍,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有两件,一件是直裾,一件是曲裾,都是右衽。其中,直裾的是49克,衣长128厘米;曲裾的是48克,衣长160厘米。曲裾的素纱单衣在工艺上相对更高超,因为它更长、更宽,却还轻1克。直裾素纱单衣在馆内马王堆汉墓基本陈列中常年展出,此次展览中,主办方特意安排了这件从未对外展出过的曲裾素纱单衣真品。
制作过程
素纱单衣不仅轻,且透光率达到75%,衣服叠十层放在报纸上,仍能看清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这主要得益于其材质,经科学检测鉴定均属于桑蚕丝纤维,单根纤维的投影宽度为 6.15-9.25微米,单根纤维的横截面积为77.46-120平方微米,如此细小的纤维自然是历经先秦、秦汉时期长期饲蚕方法经验的积累成果。
汉朝历代政府都提倡饲养已经驯化的家蚕, 禁止饲养“原蚕”。原蚕因为饲养的桑叶属于夏秋季的,桑叶质量不好,即使辛辛苦苦饲养,吐出来的丝也质量不高,而当时倍受推崇的桑蚕品种很可能是已饲养的“眠化蚕”。而当时最顶级的纱则来源于汉代培育的三眠蚕。与现代蚕相比,吐出的丝更细,用蚕丝纤度单位来测量,只有10.2-11.3旦(旦数越小,蚕丝越细)。
由于缫出的丝纤维十分精细,所以织造的衣物看上去像轻雾一般,故而在汉代文献中又称这种纱为“雾縠”,如《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曰:“雾縠,言其轻若云雾也。”十分形象地描述出这种纱丝线的精细程度。这样微细的纤度,和近代缫出最精细的蚕丝十分接近。
这充分说明至少在西汉初期,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相当完善的缫丝技术,能够应用蚕丝中各茧层丝纤维的不同纤度配茧,进行较科学的煮茧、添绪和缫丝,并能均匀地控制蚕丝的条份,缫出丝织物品种所需要的生丝纤度。
织好的丝帛还属于生丝,需要进行煮练熟。其技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掌握。大致是放入热水中煮练,使丝帛脱胶,在经过捣洗或捶洗就会变得柔软。唐代的《捣练图》为我们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形象资料。
在制衣裁剪之前,捣练过的丝帛还需要熨烫,把烧红的木炭放在斗中,用底部的热度把织物熨平整,以保证后期缝制的衣物平整。熨烫平整之后的素纱就可以用来裁剪、制作衣物了。有的布帛在裁剪制成衣前,根据不同需求还要加以髹漆、染色、砑光等工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件素纱单衣,保持基本完好,制作精美,一方面说明保存好,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熨烫、裁剪缝纫技术的成熟。
1980年代起,国家文物局有一个课题就是复制素纱单衣。当时,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了两件,但是两件的重量都超过了50克。素纱单衣的仿制难度之一来源于蚕。据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中心主任杨冀元介绍,制作素纱单衣时,西汉人使用的三眠蚕丝纤度只有10.2-11.3旦,而现代人培育的四眠蚕丝纤度却有14旦。如今吐丝的蚕宝宝被驯化后更胖了,吐出的丝更重了。为了更真实地还原素纱单衣的面料,制作团队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批瘦弱的三眠蚕宝宝,它们蚕丝的纤度仅为11旦,比较适合作为原材料来进行面料的织造。直到2019年,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两年,终于成功仿制出一件重量约49克的素纱单衣。这也是素纱单衣出土40多年来,首次得到官方授权,经博物馆相关专家鉴定认可的仿制品。
(摘自《北京青年报》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