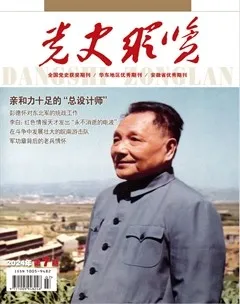寻访红军的足迹
这是一块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誓死捍卫的革命圣地
这是一个中国红色政权的生命摇篮
这是一片将革命星火燃成燎原烈火的战场
——题记
暮秋时节,赣南大地天高云淡。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就诞生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曾带领红军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这里的几乎每一道山岭、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城乡村镇,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身影。近日,笔者一行带着对先辈的崇敬和缅怀,驱车来到这里,寻访先辈们当年的战斗遗迹,追忆那段峥嵘岁月。
广昌路上
在即将进入广昌县城的高速公路出口处,一座巨型雕塑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拾级而上,雕塑上硕大的红五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种踏入革命老区特有的崇敬感油然而生。
山坡高处,风展红旗如画,一座展现毛泽东策马扬鞭、红军战士持枪紧随的雕塑,巍然耸立在蓝天白云间。后面巨幅照壁上,镌刻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吟咏着这些著名词句,我们仿佛又走进了当年的烽火岁月。广昌是苏区的北大门,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屡次进犯的要塞。1930年1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由闽西北抵达广昌赤水,24日在宁都东韶与朱德的红四军会合,之后毛泽东随红四军司令部一同抵达永丰藤田。24日至26日,红四军与刚成立不久的红六军一部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与国民党独立十五旅激战取得胜利。毛泽东欣喜不已,于是在雪里行军的征途上,欣然吟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这篇不朽词作。
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相继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在苏区的胜利,让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分。为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多支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集结1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进攻。由于当时的中央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错误地运用了“卸敌于国门之外”的主张,与力量数倍于我军的强大敌人死拼硬打。历时18天的广昌战役,虽毙俘敌2600多人,但红军的伤亡也达5000多人,最后被迫撤出广昌。广昌失守,意味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随着敌军的步步进逼,红军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处处被动、节节败退,苏区越打越小,直到被迫长征。
红都瑞金
离开广昌,我们驱车抵达红都瑞金。创建于1927年的赣南苏区,是依托农民武装暴动后割据形成的几个小块红色区域发展起来的,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人口280万。中央苏区形成后,鼎盛时期人口达3000万,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毛泽东任主席。据资料记载:苏区时期,投身革命的赣南儿女就有93万人之多,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烈士有名有姓的就有10万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革命斗争,不仅改变了这块土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也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瑞金叶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座建筑,几乎都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谢氏宗祠到红军烈士纪念塔,从中央苏区中央局旧址到红军检阅台……这一栋栋旧址、一处处建筑无不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让我们顿生敬意。
沙洲坝的红井,一直是笔者心中向往的地方。当地曾流传着一首民谣:“有女莫嫁沙洲坝,天旱无水洗头帕。”说的是沙洲坝是个缺水干旱的地方,因风水先生断信此地的龙脉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因此,这里的群众用水是个大问题。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就住在沙洲坝的村子里。得知这里的旱情后,他带着警卫员亲自勘测,寻找水源,并根据土壤潮湿程度,选定了井的位置。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乡亲们一齐上阵,很快就挖出了一口井,结束了祖祖辈辈挑塘水喝的历史。因为是红军来了以后挖的井,这口井被称为“红井”,井旁还立了一块碑,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此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和思念之情。9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这口红井前,亲口品尝了甘甜的井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当年苏区政府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办实事的历史见证,也是我们需要永远继承的光荣传统。“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旁广播里正在播放《红井水》的歌曲,旋律回荡在沙洲坝上空,传得很远很远。
到沙洲坝,就不能不去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这栋由红军自己建造的房子,从空中鸟瞰,宛若戴在大地母亲头上的一顶红军八角帽。房屋正门上方塑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与红星图案,两旁则为工农红军军旗图案浮雕。走进大厅,正面为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会标横幅,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两面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格外醒目。台上立有几尊蜡像:毛泽东正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肃立在这庄严的会场,笔者倾心聆听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仔细寻觅伟人们留下的光辉足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这些简陋的房舍里,革命领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呕心沥血、运筹帷幄,用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品格,为新中国的建立画就蓝图。
激战高兴圩
告别瑞金,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濊水河畔的兴国县高兴镇,这里古称“高兴圩”,是中央苏区的西大门,也是红军第三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之一。圩北的竹篙山,见证了1931年9月红军反“围剿”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竹篙山争夺战。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红四军等主力与来犯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夺取高兴圩这块不足200平方米的竹篙要地,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阵地几易其主,红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亲自组织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敢死队,把手榴弹、刺刀集中起来,高喊口号,向正面之敌扑过去。这场激战让敌人天黑前拿下阵地的计划成为泡影,但包括曾士峨在内的2200多名红军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高兴圩,我们还听到了有“绝命后卫师”之称的红三十四师血战老营盘、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烈往事。1934年8月,敌人以3个师的兵力进攻兴国之北的老营盘。为保卫苏区西大门,中革军委派红五军团驰援,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奉命进驻文溪、高兴圩至兰田圩一线。9月8日上午,敌约一个团的兵力向驻守竹子坑的红三十四师阵地发起攻击。他们先用炮火轰击,接着用机枪掩护冲锋,但在红三十四师官兵用血肉铸成的防线前,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9月22日,著名的“心田夜战”打响,这是红军长征之前的一次硬仗,红三十四师再次大显身手。这天晚上月黑风急,阵地上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双方射出的弹丸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淡绿色的火光。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时候,在高多村一侧的河边,红军战士端着刺刀,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展开肉搏拼杀。这一仗红五军团及红三十四师损失惨重,但为阻滞国民党“围剿”大军南下瑞金、掩护主力红军集结于都河、完成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时隔9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高兴圩战场遗址目睹高兴镇的历史变迁,深深感到红军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企盼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美好生活已经变为现实。当年的穷乡僻壤,如今已形成了以种植脐橙、烟叶、蔬菜、油菜为特色的产业链,创建了以比利时杜鹃、杨梅、葡萄、蓝莓等鲜花瓜果为主导的休闲采摘带,形成了“千年古村,十里香樟,四季采摘”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并被评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镇、全省十大文明村镇、全省百强中心镇。
梅岭抒怀
循着红军战略转移的脚步,我们一路前行,来到了位于赣粤两省边界的梅岭。相传开元四年冬(716年),唐朝宰相张九龄奉诏在梅岭劈山开道,修建驿道关隘——梅关,使其成为南岭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梅岭古道虽不陡峭,但用块石铺成的山道十分崎岖坎坷。爬到半山腰,一块褐色的碑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上书“北伐部队由此出发”字样。当年北伐军就是从这一路向北、所向披靡,为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途夭折。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登上梅关,向北眺望,笼罩在薄雾中的江西省大余县城时隐时现。当年被迫长征的红军队伍从大余城外一路西行,后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
与此同时,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多人,遭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大部分官兵牺牲。其间,著名共产党人何叔衡、毛泽覃等在突围时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后遇害,因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负伤而未能参加长征的陈毅,和项英一起带领突围出来的少量兵力,转战于赣粤边油山地区和梅岭一带,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1936年深秋,梅岭山区寒气袭人,正在山沟里坚持斗争的陈毅接到去大余县城接受中央指示的通知。当他带着特委的同志抵达县城时,发现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便立即撤离,返回梅岭。敌人迅速出动5个营的兵力搜山。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陈毅和特委人员住窝棚、钻山洞,昼伏夜出,在梅岭深处与敌人周旋。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不动烟火,渴了,喝一口山涧的泉水;饿了,摘几颗野果充饥。面对绝境,陈毅坚强不屈,并利用战斗间隙,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抒发了一个身经百战的革命将领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对党对革命至死不渝、豪情无限的彻底革命精神: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今天,当笔者屹立梅关,远眺绵延群山,遥想昔日峥嵘岁月时,激情的思潮在放纵奔流。如今已无从考证当年红军战士是如何在弹尽粮绝的境遇中与敌人拼死抗争的,也无从考证陈毅是在哪一座窝棚里写下光辉诗篇的。其实无需考证,梅岭赤裸的山脊和蜿蜒的石阶,恰似他们前仆后继、顽强抗争的铮铮铁骨;那簇拥着山岭的金黄硕果和日新月异的赣粤风貌,正是他们的骨肉镌刻在大山间的符号、生命书写在大地上的诗篇。
(责任编辑:计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