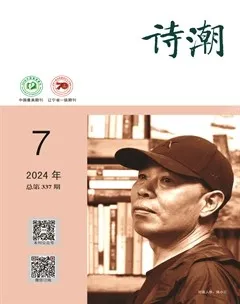是谁用庞大的话语宽慰我们 [组诗]
残 鹅
山坳的北坡残雪凝固
荆棘丛挂着一只滴着雪水的雪鹅
能够摆出鹅或天鹅的姿态
那么它的头颅是向上的,至少是
挺拔矗立的。尽管残缺不全
还似乎已开始凌迟,但它雪白着
在碧蓝的天空之下
像个英雄
听不到它的歌唱,却振聋发聩
处境很危险。不是春江花暖
数不清的绒毛,是它的人民
护卫着,甚至爱戴着
也许已经就义了,体骨支撑着
才没有倒下
洁白的灵魂裸露着,遍地都是
所有温润的液体渗入土地
它凝固着,用最后一点儿力气等待
等待夏花如火如荼地开放
现在,临近酷热的季节
除了一丝清凉,再也做不了什么了
夕 晖
帕米尔高原到柴达木河上游谷地
昆仑山脉的暴风发出鞭子的呼啸
龚格尔山脊, 起雪粉的鬃毛
在东北,我插队的落马湖村
车老板黄老大的马车正经过饮马河畔
水库泄洪,吞了下村农舍和庄稼
满车驮着粮食、水罐和主人的慈悲
这可马虎不得
他的老马并不识途
老蹄蹬着陌生的石坡
臧克家的鞭影晃过五十载
未有一鞭嵌进枣红的肌肤
老黄帮老马在车后推车
呵斥和鞭声响彻山谷,严厉而空洞
而此时的夕晖已爬上山冈
在人畜的清眸和额头粗糙的汗珠里闪耀
省 亲
一个中年汉子坐了三夜火车
他的军大氅裹着晨曦
从沿海城市工地回到村里
那束白菊被轻轻放下
他的眼泪已风干
他把头抵着黄土新坟:
妈妈,我爱你
江水流进来
夜幕垂下。十年间的夜晚
都回到今晚。对岸的街灯相离
它们彼此间的倾谈
被江水知道,闪着橘红的粼光
夜风吹动,把远处晚礼的钟声
送给熟睡的人。一道流星掉进江中
这些深夜的景象都从窗子进来
渔火似的光影在地板上流淌
十年间的夜色被我挥霍
只有今晚,江水流进来
是谁用庞大的话语宽慰我们
它们混进春风从窗棂中穿行
撞到透明而薄弱的玻璃上
用庞大的话语宽慰我们
它们经历远途来看我们
抚摸过我们的孩子和老人
女人们在河滩洗濯
收起被吹干的衣裳和美貌
暖言软语都舍掉了历史部分
只让我们认知祖上活着的气息
它们从坟墓里复活,在供养下永生
它们原始地护佑我们和我们的土地
我们古老地爱着,就像牛们依恋鼻栓
就像被收割后的大地刮过庞大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