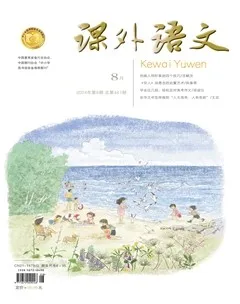家国情怀,一曲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浩如烟海的书籍文献中,爱国诗篇一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专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古诗三首》,共同体会历史长卷中不同朝代诗人的家国情怀;跨越历史的长河,共同收听这曲永不消逝的电波。
一、深学《从军行》:共悟王昌龄的铁马冰河
说到爱国诗篇,就不得不提王昌龄的《从军行》。王昌龄是大唐极具盛名的边塞诗人,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朝堂文人群体掀起了从军热,纷纷请命外派,以求边功。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从而有了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成为边塞诗的创始和先驱。而彼时的大唐正值盛世,国力强盛,那是一个人人渴望崭露头角、建功立业的时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那时的沙场充斥的不仅是腥风血雨,更有着戍边战士们的豪情壮志。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青海湖上浓云蔽日,低沉的天幕掩映着连绵的雪山。极目远眺,翻过远处的雪山,再穿过河西走廊茫茫荒漠中的孤城,就是连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在唐朝时,青海西有吐蕃,北有突厥,青海作为重要的边防城市,唐军曾多次在此与吐蕃激烈交战。杜甫曾在《兵车行》中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而诗人此刻看着这青海城与玉门关,看着眼前辽旷苍茫的景象,仿佛就看到了古往今来众多将士们浴血奋战的场景,不由得心潮澎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诗人笔锋一转,由写景转向抒情。战争时间的漫长,战斗场景的激烈,戍守边陲的苦寒,只需“黄沙百战穿金甲”七字便诉诸笔端。千百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将士们的金甲都被沙土磨穿了,但能磨穿的只是铠甲,无法改变的是战士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保家卫国的决心,他们的意志只会在漫天黄沙的吹卷中愈加坚定,在风沙中他们彼此约定,戍守边关,不击退进犯的敌寇,誓不返回家乡!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大唐盛世的浩荡长卷中,他们用青春和鲜血谱写了最铿锵有力的璀璨诗篇。
二、细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感受杜甫的心花怒放
星移斗转,日行月逐。盛极必衰是每个朝代都难以逃脱的规律。广德元年(763),大唐王朝早已不复王昌龄创作《从军行》时的方兴未艾,已经隐隐有风雨飘摇之态。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冬十月,唐军破贼于洛阳,进取东都,河南平。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败走河北。广德元年春,史部幽州守将李怀仙请降,史朝义兵败至广阳自缢而死,李怀仙斩其首以献,河北平。长达七多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布告终,举国欢庆,人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而此刻远在梓州的一间草堂内,也有一个年过半百老人得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就是诗人杜甫。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逃跑,太子李亨继位为肃宗,杜甫听闻这个消息,当即只身北上灵武,投奔肃宗,结果于途中被叛军俘虏,押至长安。转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挥兵进军长安北方,杜甫才得以趁乱出逃,一路风餐露宿追至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终于得以面圣,官拜左拾遗。然而很快杜甫便因为营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虽得当时宰相张镐相救,但还是两次被贬华州。杜甫身在华州眼看朝政乌烟瘴气,百姓流离失所,自己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满腔热忱却报国无门,遂而愤然辞官,一家老小辗转来到了成都,在严武等友人的帮助下在城西的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收到王军大胜的消息时,杜甫正身在草堂一隅,当时的他欣喜若狂,当即挥笔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首联“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诗人身处剑门关外,为故土难归日日悬心,此刻忽然接到了“收蓟北”的消息,惊喜猝不及防,刚刚收到消息眼泪便夺眶而出沾湿了衣裳。这不仅是一封捷报,更意味着百姓颠沛漂泊、流离失所的日子即将迎来曙光,让诗人怎能不喜极而泣?颔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回头看看妻子儿女脸上哪还有忧愁的神色?诗人随手抄起一本诗书,欢喜得几乎要发狂。“却看”“漫卷”两个连续的动作描写,我们仿佛回溯了历史的长河,看到了那个已过天命之年,却沉浸在欢喜中如同孩子一般简直不知所措的杜甫。笼罩在草堂上愁云惨雾一下子被风吹散了,一家人都沉浸在大获全胜的喜悦之中。颈联“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通过对生活细节的描写,生动刻画了诗人心中的喜悦,在晴朗的天气里放声歌唱,纵情饮酒,这也正与上一联中的“喜欲狂”相互呼应,“青春”是指春天的景物,在生机盎然的春天里,与妻子儿女“作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在心中规划着,就从巴峡穿过巫峡,再经过襄阳直奔洛阳。诗人身在梓州想象着回家的路线,即使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点之间相隔遥远的距离,不能“即从”,“便下”又如何呢?想必诗人的心此刻已经乘上了最快的车马,顺流直下,到达自己阔别已久的故土了吧。多年来故土难归的痛苦一夕化解,让诗人怎能不“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呢?
三、品读《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体会陆游的衰世遗恨
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但古往今来的人们为国家兴衰而时刻牵肠挂肚的心情是亘古不变的。悠悠百年已过,杜甫草堂边的浣花溪畔,又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也曾隔着遥远的时间与空间,印着先贤的脚印,辟田躬耕,他就是诗人陆游。生于两宋之交的时代夹缝中的陆游可谓一生坎坷,那是时代赋予当时文人无处可逃的枷锁,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才成就了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爱国诗人。绍熙元年(1190),陆游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陆游再次上疏光宗,提出治理国家、完成北伐的意见,劝谏光宗广开言路、慎独多思,带头节俭、以尚风化。由于陆游“喜论恢复”,谏议大夫何澹便弹劾陆游之议“不合时宜”,主和派也群起而攻之。朝廷最终以“嘲咏风月”为名将他削职罢官。陆游人到晚年几经宦海沉浮,如今再次离开京师,悲愤不已,回到山阴老家立即提笔把他在镜湖旁的住宅题为“风月轩”。虽云“风月”,实则是发泄他被奸人所害、壮志未酬的满腔愤懑。而这首《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便是他蛰居山阴老家时所做。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三万里长的黄河奔流不息涌入大海,五千仞高的华山高耸入云直触青天。一水一山,一横一纵,仅仅两句就使已经沦陷于金人手中六十多年的北方中原图景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了。如此广袤无垠的中原沃土就这样沦于敌寇之手却无力回天,让诗人怎能不痛心疾首呢?“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群,他们是生活在金朝占领区,但始终认同南宋王朝的统治的人民。漫天胡尘隔断了他们的视线,但他们仍然不肯放弃地日望夜望,渴望恢复中原的眼泪流了六十多年,早已流尽了。他们年复一年地盼望王师挥兵北伐,救他们于水火,然后愿望再年复一年地落空,许多人就在这样的盼望中至死没能等来王师“北定中原”的日子。诗人写北地人民的盼望,其实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心中的期盼?可就在百姓这样盼望的眼神中,南宋统治者却不断奴颜婢膝,退让求和,偏安一隅,乐不思蜀,将国仇家恨抛诸脑后,诗人为遗民大声呼告,也是为了唤醒统治者收复中原的决心。言有尽而意无穷是这类诗歌的普遍特点,从本质上来讲,诗人和这些年复一年等待着的遗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家国情怀,是一种宏大的英雄气概,更是一种历史积淀的生命自觉,它像是一曲永不消逝的电波,贯穿古今,将古往今来无数中华儿女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最纯朴的气质。涓涓不塞,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