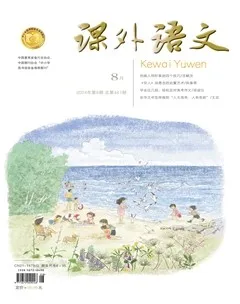探索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第五次入仕为县官不久后弃官归田所作的抒情小赋,因文字不事雕琢,意象潇洒出尘,审美自然脱俗,备受后世文人墨客追捧与喜爱。欧阳修称赞其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而陶渊明远离官场后,对自然的回归,关于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心”的推崇与坚守,让苏轼都发出了“师范其万一”的感叹。此处,就让我们结合陶渊明毕生的经历,从《归去来兮辞》中感受一下他对生命意识的觉醒。
陶渊明一生经历了五次官场上的进与出,在周而复始的出仕与归隐交替中,他最终理顺了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毅然放弃仕途,远离官场,并以一首《归去来兮辞》正式与官场隔绝开来,走向他一直以来都心驰神往的田园生活,选择了以余生亲近自然。仕途进出中始终难以化解的身心分裂与煎熬,也随着他对“天命”的顺应遵循与对造化的看淡臣服,逐渐消散于云烟中,生命意识的觉醒,让他如愿获得了人生的解脱。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探索一番隐逸之宗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解脱,寻求精神上的宁静恬淡和自然乐观。
一、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摆脱形役
陶渊明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此一句中的“心”指的是心灵与精神,“形”则指身体,他觉得既然身体已经被心灵所役使,为了更好地活着,违背精神意志步入仕途做了官,就应该安然面对现状,既来之,则安之,可是他为何还是因失意而独自悲伤?可见,一次次的出入仕途让他身心分裂的意识与警醒更加清晰与急迫。“以心为形役”让心的追求与身的浮沉严重分裂,甚至南辕北辙。站在我们今天研究和品鉴的角度来看,陶渊明一生的作品中以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而且作为我国的田园诗鼻祖,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对乐天自然的安宁隐逸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陶渊明自幼受庄子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但精神上的追求并不能让他和家人有餐食果腹,想要自由翱翔的心灵和为了利益与生存陷入虚假沉浮、奉承阿谀的官场混沌的身体,在不得不面对现实入仕谋生时被割裂开来,“为口腹以心役身”成为意料之中的结果。然而,身与心的分离带来一系列精神与肉体上的紧张与困顿,这让陶渊明的心灵和精神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奚惆怅而独悲”在所难免。用梁启超的话说:“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惭耻悲痛,真是深刻入骨。”是啊,身与心的撕扯会让人精神溃败,身体疲累,值得庆幸的是陶渊明虽偶有几分厌世之感,最终都由消极走向乐观。而至此时,他也深刻意识到了身心分离的困苦,正视并顺09dfe569758f95c808c9370b183c55f5f210123c9833b8514731965458b4bac1应了二者分裂的传警告急,所以他开始摆脱“形役”,在身心分离中深刻意识到“今是而昨非”,并彻底远离了水深临渊、如履薄冰的官场,由“心役身”转向“奔心而去”,开始享受自然与生活,恪守求真,与俗事告别,走向美好田园生活,以身心合一“护身随心”,看着让人“迷途”的官场在身后徐徐远离,终于有了那种心静气舒的感觉,所以“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他也在身轻气闲、意似飘风的悠然自得中有了几分真实之感,是“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只“恨”不能快点回归净土,走向宁静自得。
二、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傲世心安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历经一路恨不能飞奔而去的内心急迫与煎熬后,陶渊明终于再一次看到了“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熟悉场景,也看到了“僮仆”“稚子”的熟悉面容。尽管这堆砌满精神意志的一方天地实则小得可怜,仅有“容膝”之大,但当精神不再囚困于现实的樊笼,也不再被名利所羁绊时,这一方小天地成为他精神与心灵获得美好寄托的最佳之所。小又如何,情之所至,神之所托者,即为上佳之选。既已回到家中,免不了呼朋唤友,寻几分怡然自得,故而“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而这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生活。正如他在《杂诗十二首·其四》中所刻绘那般:“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因此,享天伦乐趣,畅怀饮酒,即兴成诗,便是他此生难以抗拒之“夫所求”。“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可以显见他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多么淡定坦然与笃定自持,纵是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他也可以以高傲姿态无视之,而不再是折腰乞怜。一个“眄”字,将陶渊明远离世俗洽酒怡颜的情志意趣与傲世心安的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概也只有身心无所欲累和物役者方能从中感受到妙趣,乃至人们习以为常的“云出岫”“鸟知还”等美妙景致,也唯有那些淡名薄利之人才能参看一二,而追名逐利之人又怎会有心境与时间去感受?
三、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生的喜悦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陶渊明得了身心分离的传警告急,付诸行动实现了身心合一,得到了傲世心安。然则,他对生命意识的觉醒仪式并没有充分完成。因此,又有了“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尽管不再“形以心役”,难得享受几分天伦乐趣,但这显然不够,他还需要和喧闹冷冽的官场作彻底的了断,以“请息交以绝游”让内心营造的世外桃源能保留与坚守。而一句“世与我而相违”的决绝告白,既是他毫不避讳的真实心灵感受,无疑也是充分体现出了他独善其身的人生自我追求,他需要的是“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的简单质朴却又欢畅愉悦的平凡生活,而不是流于俗世的志得意满,所以他更享受“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只想有亲友几人聊得片刻闲适,在琴书的宁静中充实精神家园。而精神的满足日渐充沛后,他的眼里融入了万物,赋予了万物无限生机,生命的喜悦跃然纸上。所以万物都能以自然为载体舒适展逸,人又何必继续困顿于名利中“交病”不已?所以生命的喜悦理应以自然契机走向繁盛,从曲折蜿蜒的起伏交叠中感悟自由与绽放。所以“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何必再时光错付?
四、生命意识的觉醒就是无惧无忧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对于死亡,任何人都是难以抗拒的。既知如初,为何不坦然接受死亡?尤其那句“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刻画出了陶渊明面对之前身心背离却没有“以身顺心”的悔不当初。也是,人的一生中,生命的由盛转衰,人生的得失进退,哪样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再多的名利富贵在人的化归面前都显得虚无缥缈,人们又何必为了追求这些身外之物而惶惶不可终日,强求不可得而困厄无以所措?可是明明解脱唾手可得,人们却一再错过,不如放下那些不值得的执着,去“植杖”“耘籽”“舒啸”“赋诗”,以一种忘我之境填补追求外物带来的困苦与愁虑,以身之消融促成心之解放。“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条茫茫归途,虽然道不尽悲与愁,但又仿佛道尽一切,既是与题目前后映衬,遥相呼应,也将陶渊明“归去来”的意志充分且坚定地表达出来。
历经五进五出,忍受十几载春秋交替的身心割裂后,陶渊明选择了回归田园,以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追求隐匿的快乐,不再受官场倾轧与折磨。因此,《归去来兮辞》可以说是他经历大悲大苦后获得觉醒与解脱的完整反映。这样的觉醒与解脱谈不上刚强猛烈,却在身心合一的不断摸索中撕开了一条口子,将名利羁绊剥离并从中抛掷而出,最后陶渊明才获得了对生命喜悦的自然感知,并安于天命,不再畏惧尘世浮沉,他的心也逐渐走向安逸宁静。
千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在这时光飞逝的岁月长河中稍加停留,是不是也能在晨光熹微中看到天空慢慢泛白,日落时霞光染红半边天空,然后在感叹这朝暮美景的同时,产生几分对生命的别样体悟,然后让精神的追求得到更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