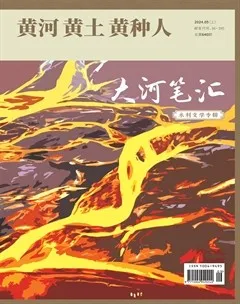我的读书故事
彦妮


一
小时候,我几乎没读过什么书。那时看到别人看小人书,就羡慕得不行,知道自己买不起,就四处跟同学借。一旦借到,就十万火急地看完,生怕人家要回去。村里有个园艺站,那里有个叫小鱼子的,他家里有一纸箱小人书。我逮着机会就软磨硬泡,想尽各种办法,让他答应借给我看。那时我只要有一毛钱,就会去县城的新华书店,来回步行60多里路,就为了能买一本小人书。
去邻居家串门时,我会先看墙上贴的图画。三年级时借到一本没有封皮的长篇小说书,字认不全,还连蒙带猜地给同伴讲。设法借到一本《邱少云》,我怕人家第二天要,就趴在炕头上,一整夜也不睡觉。早上起来,我的鼻孔里都是煤油灯熏的黑烟。大哥家用旧报纸糊顶棚,叫我过去帮忙,结果,我一看见那一大堆旧报纸,就一张一张地翻,再也挪不动腿。
父亲去世后,我得了一场病。后来家里没人放羊,我又回去放了两年羊。放羊的日子是寂寞和无聊的,为了打发时光,我有时会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翻一翻,有时会捡起地上飞来的油腻报纸看半天,有时我甚至会顶替另一个羊把式放一天羊,就为了能跟他借到全套的《三国演义》。
有时实在孤独得无法忍受了,我也会跟一个在城里工作的老乡张口,让他借我一本书看。他看我饥不择食的样子,就借了我一本《小说林》杂志。也就因为那本杂志,我看得太过专注,没顾上管羊,羊就偷吃了别人的庄稼。结果,就在那个下午,当我急急忙忙把羊从庄稼地里赶出来时,庄稼的主人已拿着一根长长的柳条在地头上等着我——来不及叫喊,我的心只是随着柳条的起落而抽紧。太阳火辣辣地在头顶照着,我的身上火辣辣地疼!
感谢那些飞起又落下的鞭影,是它忽然让我对写作感了兴趣。自那以后,我擦去梦中的眼泪,伴着一盏油灯,我在妹妹写过的练习本上,开始认真地写下一行行受伤的文字。
二
半坡暖阳,一处旮旯,这是我最期望的所在。
堂叔已到崖边去拔芨芨草了,我躺在冬日的阳洼里,感觉万事皆休。我就是台下唯一观众,所有演员都只为我一人表演。
没有谁能从我的手里夺走我从堂兄手里借来的《西游记》。我就是这里的王,谁都对我无计可施。
从清明开始,到白露结束,我没有一天不操心,没有一天不和羊斗嘴。现在,终于到我优哉游哉的时候了。
赶在清明前后让羊啃上青草芽、找寻刚拔完粮食的庄稼地让它们吃到新鲜的嫩草。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里,即使有无数只乌鸦对着我怪叫,有旋风将我团团围住,我也要自己为自己壮胆:我会喊着我给羊们起好的名字,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对着羊群“点将布阵”;或者大声唱歌,然后要求“马耳子”或“花脸贼”给我鼓掌……
外面愈加黑了,繁星如豆。堂叔在卷他的老旱烟,我坐在煤油灯下,继续看《西游记》。先前看过小人书,知道孙悟空有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本领。但小说更加引人入胜,它使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念出了声。堂叔听不大懂,但还是让我给他也讲一段。我便挑最经典的故事给他讲——“大闹蟠桃会”“大战红孩儿”“火烧盘丝洞”……
夜是如此寂静,除了羊圈里羊的咩咩声和咀嚼声,就是我讲故事的声音。堂叔听得过瘾,烟也不抽了,就躺在炕上睡着了。我捧着书,看灯花愈来愈大、窑壁愈来愈暗、夜猫子的怪叫声愈来愈近,便也有些不舍地吹灯睡下。
冬天没有庄稼,不担心羊吃谁家的粮食,只要看见它们撒开在山坡上,我就会躺在阳洼旮旯里,捧出那本被身体焐热的《西游记》,在唐僧师徒与各类妖魔的周旋与搏斗中,将时光读得风轻云淡,甚至有些禅意。
是的,这都是我的领地,是我的“花果山”和“水帘洞”。无论我吼乱弹还是漫花儿,无论我躺着还是睡懒觉,谁都不能拿我怎么样。就算我把这里幻化成“西凉女国”,或者将一朵随风而起的干刺蓬想象成三头六臂的哪吒;即便是我将羊粪豆儿看成是太上老君的“九转还魂丹”,还是将崖畔上摇曳的干菊花看成是观音菩萨的杨柳枝,都没人指责我神经有问题。
我再也不密切注意“马耳子”的动向,再也不操心半坡里的糜子或梁顶上的荞麦——不识人抬举的家伙,现在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们不和蜘蛛精一样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俺老孙”就能牵着你们乖乖儿回到羊圈里。
清风不识字,帮我乱翻书。遇到好的诗文,我有时甚至会脱下皮袄,在山坡上摇头晃脑地“表演”朗诵:“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那种有点古怪的神情,有时让堂叔瞧见,他以为我在这里被圈疯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每天赶着羊群游荡在山沟中,也每天在《西游记》的故事里畅游着。我一边坐在山头看书,一边看着羊儿在山间吃草。我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学到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或者一翻筋斗就能穿越十万八千里,刹那间就能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品读着,没人催促、没人干扰。只要不是刮风或是下雪天气,我都要在太阳下随心所欲地看个够。那是一年最寒冷的三个月,但因为一本《西游记》的陪伴,我却不记得它有多么严酷。春天尚未来临,尽管我省着看、惜疼着看,可书到底还是看完了。我就看完了再看,看完了再看,一点也不觉得倦怠。
就是这样,在那个或许是世界上最简陋的羊圈、最狭小的窑洞、最荒芜的山梁上,我度过了此生最寂寥、最清苦也最惬意的岁月。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时时想起那段牧羊的日子,想起那本《西游记》带给我精神上的支撑。无论我后来又看过多少书,我都觉得《西游记》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集于一身的伟大作品。它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把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在一起,将古代浪漫主义小说推向了高潮。而且它老少皆宜,给每一个读过它的人,都给予丰厚的回报。
《西游记》也是我人生当中读过的第一本“大书”。它鼓励我在困境中百折不挠,为达目标永不言弃。无论我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会有意无意拿唐僧师徒取经的经历告诫自己。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在深山戈壁里将捞盐、打硝或修公路的工作顽强坚持下来,或多或少都是受了那本书的影响——正是那本发黄的小说书,让我在生活拮据的年月里,依旧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
三
后来,我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以及张海迪的一些先进事迹。保尔和海伦·凯勒面对苦难时百折不挠的情景,以及张海迪高位截瘫却学了12门外语的真实遭遇,又大大增强了我面对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变得坚强起来。这些人面对苦难时百折不挠的情景,常在我的眼前复现。我身在盐碱地,心与苍生行,嘴里时常念叨着川端康成的那句名言,“如果一朵花很美,那么,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要活下去!”
是的,我比人家保尔还苦吗?我比双目失明的海伦·凯勒条件还差吗?我有眼睛有双腿,我有无数的光明可以享用,我还抱怨什么?
在最清贫的时候,从那些书本上接受的礼教和熏陶,使我久病成良医。渐渐地,我开始有意识地写稿和投稿。虽然我当时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东西换不来一个干粮馍,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内心竟不由自主地安静和喜悦起来。
和我一起落榜的同学都到城里谋生了。他们有的开了商店,有的经营了理发店,有的去市场卖菜,有的骑了车子回收废品。只有我还头脑发热地将打工的工资大多买了书。
正是那一本本廉价的书籍,让我在最拮据的年月里,依旧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梦想。我一度坐在低矮的旧房子里想过,如果人能喝着西北风坐拥书城一辈子,那该多好!通过写作,我也认识了不少的老师和朋友。有他们的鼓励和认同,我再也不会感到孤单和郁闷,我就有更多机会接触一些外国作家的优秀作品,比如《太阳照常升起》《瓦尔登湖》《忏悔录》《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等。那些书好像使我站在了村里最高的山头上,看到了先前从没有看到的景色。我似乎愈加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和局限,也明白自己为啥像个行吟诗人一样,落魄、无能,还有点儿忧伤。
盖楼时伙伴说附近有家阅览室,可免费看。我一去就惊呆了,以为到了另一个世界,看着满架子的报纸和杂志,一时竟不知该从哪儿看起。我像一只有幸发现了嫩草的绵羊,头低下再也没有抬起来。我都没想到要坐下,就那么直愣愣立在书架前,一本一本地翻。等同伴喊我去上工时,我已两眼昏花、两腿发麻,不知当时是中午还是下午了。
感谢县城图书馆,它为我留了最后一扇门。《复活》《莎士比亚戏剧》《骆驼祥子》等大师级作品,使我就像夜行的旅人,在酒旗和灯光的召唤下,终于沿着前辈们探索出的路径,渐渐找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某种语境。我不再是盲人摸象般地写作,也不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看书,俨然受了指教似的,我开始有意识地朝一条路上前行了。
四
三十多岁时,我偶然买一本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到家翻阅几页,便忽然惊坐起来!记得当时我似乎有些发蒙,感觉之前的书都算白读——见惯了暴露隐私、吸引眼球、刺激感官欲望的所谓文学作品,忽然接触到如此平白直叙的文风与率真有趣的语句,我的阅读口味完全被颠覆了!
“相逢情便深,恨不相逢早。”初识汪曾祺,便被他的质朴醇厚与文字里隐藏着的淡淡禅意所倾倒。他的文章不拘一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精彩之处,让人忍俊不禁、心服口服。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绕口的句式,没有过多的道德与戒律,没有狗血的情节,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小农的、桃花源式的曼妙意境。读他的作品,仿佛和一位老人在树荫下拉家常,他斜躺在竹椅里,慢摇蒲扇,柔声细语地说;而我坐在马扎上,也不必神情专注地问什么,就只是轻松惬意地望着他的笑脸。我们谁都不用准备,不用担心哪个地方说错了或是没记住,不用刻意做安排,更不用拿话筒或找观众互动……
从此我不再喜欢“重口味”,开始有意识地看一些平白直叙的、淡淡的、能被作者“轻处理”的书去读。尤其是汪曾祺的书,我更是搜到一本就迫不及待地读一本。他的小说集《邂逅集》《鸡鸭名家》《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塔上随笔》等,都让我醍醐灌顶、如饮琼浆。相比而言,我更偏爱他的散文集《人间草木》,以及短篇小说集《受戒》。他对每一个建筑都有深研究,对每一处街巷都有深感情。他追求自由,生性乐观豁达,对普通人有大悲悯。他喜欢生活,身上有一股人们失落已久的生活趣味。他会苦中作乐,老想把日子过成诗。唯有心安若常,方能视崎岖为坦途。虽然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挫折和苦难,但是他总能让自己过得有滋有味。他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事实上他吃的也是寻常食物,看的也是寻常草木,却难得心境开阔,不废风雅。他随遇而安,爱吃,会吃。就在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尚且从容不迫,煮冰糖莲子、打热水洗头,何况在当下这个和平盛世,他更是如鱼得水。
他爱玩、爱逛菜市场、爱看电影、爱听戏。任意的花草树木、随便的一餐一饭,都能成就他笔下的快活。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小吃,譬如高邮的咸鸭蛋、地方的芥菜、全国各地的豆腐,他都能用凝练生动的文字,写得让人垂涎三尺。无论是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果蔬菜,还是全国各地出产的香烟,他都能绘声绘色地写出一篇绝妙的文章。他还特别喜欢花草,每次都是他有心发现身边的植物哪个最先开花。他写过的文章提到的花草树木种类和数量众多,堪称植物学家。
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传统的民俗风情,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纷争,都充满着温馨、平和的人情味。他以谦让忍耐的姿态,让那些过目难忘的情节和氛围,犹如全都笼罩在一片祥和的真空里,用以温暖我们匆忙而麻木的生活,让我们从中得以找到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依据和能量。他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悄无声息地渗入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纷争、摒弃狭隘迂腐后的高远平淡与自然随和。
是的,汪曾祺继承和发扬了明清和五四散文的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拥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他的作品里,不见轰轰烈烈、夸大失真的优美叙述,不见刀剑相对的血腥和眼花缭乱的悬疑;可是,他的那些恬淡忧伤的文字,却凝结了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人性之美,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的美学价值。
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也自称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人世,他用77年的时间,在历史的大潮中经历了天灾、战乱、奔波和饥饿,但他的笔下却始终都是普通人的平常生活。他一生创作了180多篇小说,幽默风趣的语言下,掩藏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是细水长流。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个性。他的早期小说追求诗化的风格,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中年的小说语言糅进了不少方言,不同地域人物的对话犹显文化差异;越近晚年,小说语言越平实,基本上走了一条从奇崛向平淡的发展道路。包括《复仇》《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名篇,皆为我们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风俗画面。再比如名篇《岁寒三友》,写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的友情,平静、自然,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在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在新中国经历了70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我们闲暇翻阅汪老的作品,看他留下的温情文字,依旧会见字如面,字字戳心。他的作品里浸透着的那股亲和力,以及不矫情、不做作的简洁神韵,几乎无人能及!
没有选择。还好,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