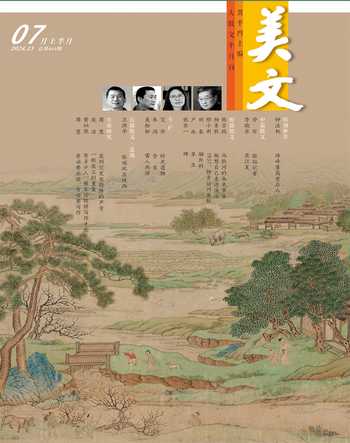白炽灯【时光遗物】
艾华
白炽灯日渐稀少了,偶尔夜间遇见,某条老街的电线杆上,某栋老楼的楼梯拐角,水滴形的火焰兀自燃烧。电线或显或隐,显而后隐,牵扯不出遥远的来处。不过人类的电源其实是唯一的,或者说上天的启示是唯一的,那就是闪电。
古罗马人有埋葬闪电的习俗,一种独特的祭神仪式,凡闪电击中之地,就是被神宣告占有了,人们立碑以记,碑上刻拉丁文:闪电埋葬于此。2022年夏天,有一块碑石随“古罗马文明展”到北京展出,我在手机上看到图片,想象中仍有触电般的感觉。如果在展览现场,碑石置于玻璃罩内,无从触摸,凑近然后退远,我眼前会不会闪现一盏白炽灯?
在老街区或老厂房的新鲜废墟上,不通电的白炽灯倒是容易见到的。废墟上除了镜子,反射天光的就是灯泡,各式各样的灯泡,跟镜子一样,大多是破碎的。白炽灯的灯泡不少见,有的还连着灯座和灯罩,如果遇到完好无损的,我总有给它通电的冲动。“点亮废墟”,在天黑下来的时候,也许是一件独特的地景艺术作品。如果玻璃已破而钨丝仍在,我也有给它通电的冲动,因为除了少年时见过一回,我再也没有见过钨丝在空气中的“升华”。
1979年春天,一个少年“耳朵识字”的新闻传遍中国,当然也风一样吹到了我的故乡。至今我记得这个少年叫唐雨,最初在我们耳中却错成了唐宇,可能“宇宙”的“宇”才配得上他的“特异功能”吧。镇上的大人小孩都兴奋,大人纷纷躲着写纸条,虔诚地折几折,然后让小孩拿了凑耳朵边上,一只耳朵认不出就换另一只。
“都不用认!”镇上的电工、外号“大灯泡”的刘师傅很快发话了,“不管谁写的,我耳朵一动就晓得,不是个唐字,就是个宇字,顶多就是唐宇两个字!”
“你也有特异功能?”大人们都佩服了。
“没有!”
“没有?那你耳朵会动?”
“那是返祖。”
“那你让我们也返个祖?”
“我哪能让你们返祖?我只晓得耳朵不能识字,唐宇两个字也没有神力。”
“那你怎么晓得我们写的字?”
“是你们自己扮巫师嘛。”
过了一天,班主任兼教语文的蔡老师在上课前问有没有耳朵能识字的,大家都不出声,都摇头。蔡老师默默笑了,写张纸条,折好,叫全班同学一个个传下去认字,于是这张纸条经过一只只、一双双耳朵,最后传回了蔡老师手中。蔡老师又默默笑了,把纸条展开,叫全班同学一个个传下去认字,于是这张纸条经过一只只、一双双眼睛,最后又传回了蔡老师手中。
“科学!”蔡老师把纸条上的字写在黑板上,打了个大大的惊叹号。半节课过去了,课堂内外都被惊叹号惊得安安静静,远处传来铁匠铺里打铁的声音。
当天中午,蔡老师拿着新到的报纸,带几个学生到访刘师傅的电器修理店。修理店就在学校大门斜对面,以前我从店门前走过,总看到一个光脑壳悬在长桌上,真的就像一个“大灯泡”。其实刘师傅不是秃头,头发是剃掉的,不是在理发店,是“自己动手,削发光头”。刘师傅也不是老师傅,老人们叫他小刘师傅,叫他新婚的妻子小李师傅。两个小师傅,一个当电工,兼修电器,一个当裁缝,兼补衣裳,就像蔡老师既当班主任,又教语文课,各自凭本事吃饭。这回因为都讲科学,师生几个,夫妻一对,就在镇上最“来电”的店里开起了科学小会。
七嘴八舌,嘴巴们很热闹……吸引我的是店里的灯。大中午,从大门和门上端亮窗进来了足够的天光,但刘师傅还是把灯都打开了。天花板下一个圆球吊灯,乳白色玻璃灯罩隐藏了灯泡,看上去仿佛雾中的白太阳。修理电器的长桌上物件凌乱,手电筒、收音机、电风扇……一盏软梗台灯照亮一块桌面和几个零件。彭春同学忍不住伸手去弯软梗,刘师傅抢先把软梗扭了个圈,灯罩朝上了:
“别动,这是我的饭碗。”
我一看,朝上的灯罩真的像个饭碗,碗里的白炽灯不大,但光线漫出来,是怎么也吃不完的白米饭。彭春龇牙咧嘴咬了口光线,抿紧嘴,嚼着,把我们逗得笑起来。
快活的笑声中,我注意到李师傅笑得特别明亮,不是笑声明亮,是她的脸明亮。她的脸不在台灯翻转朝上的光线里,但脸上好像自身有光。笑完,她脸上的光就变淡了。
“蔡老师,你们谈。”李师傅打声招呼,回到缝纫机旁又嘀咕,“耳朵识字?只当耳边风。”
李师傅坐下来,扒拉一下缝纫机面板上的台灯,我又被那盏灯吸引了。台灯底座是夹在面板边缘的,支撑杆不是软梗,是两节细胳膊,肘拐灵活,李师傅一扒拉,好像比她的肘拐更灵活。等李师傅开始踩缝纫机,我才看出还是人的关节灵活,不论踝关节、膝关节,还是肘关节、腕关节。
这次科学小会的意义,秘密的是,我从此有了想要一盏肘拐台灯的心愿。公开的是,蔡老师和刘师傅从不同的报纸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唐yǔ不是唐宇,是唐雨。迅速传播这个结论的是赶上了会议尾巴的“长发彭健”,镇上不良少年的大哥。当彭健在散会时闯进修理店,长发一甩,骂骂咧咧也讲起了科学,我才发现店里头比街面上亮堂,我们的心里更亮堂,“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
春天多雨。何况大人们又偷偷给小孩写了“雨”字纸条。有机灵的耳朵认得出“雨”字,别的字还是认不出。消息传开,都说人把“雨”字写多了,老天以为人在求雨,求更多的雨,所以相比往年,1979年春天的闪电好像更多,更大,更有神力。就在科学小会后不久,有闪电击中高压线,更高的电压导入镇上的变压器,一声响,一阵烟,变压器烧坏,停了三天电。
“敬惜字纸!要敬惜字纸咧!”平时在变压器围墙边摆摊的周瞎子说,“没把字纸收起来烧掉,报应啊!”
周瞎子露天摆摊,所以恨雨。在变压器当街一面的围墙边,只要不是雨天,他的书摊总摆在那儿,方方正正的。地上一块塑料布,四角各压一块砖头,十几本书就平躺在塑料布上,等着好奇的小手。有连环画,有文字书,也有文字带图画的,不管大小厚薄,都是两分钱一本,随你在边上看多久。如果想把书带走,只需跟周瞎子说一声,报上自己的名字和书的名字,当天路灯亮起前还回即可。所谓路灯,是镇上唯一的,就在变压器电杆上,由刘师傅负责按时开关。有一天天刚黑,路灯亮了,彭健在街上游荡,发现周瞎子仍旧在变压器围墙边等候。
“谁没还书?”
“彭春,《木偶奇遇记》。”周瞎子模仿彭春的声音,仿佛回到了变声期。
彭健转身,撒开双腿就跑。一刻钟后,撒腿跑回来的是彭春。彭春把《木偶奇遇记》还回来了,又心有不甘,想再花两分钱把书带回家。
“不行,不能坏了规矩。”周瞎子恢复了老人的嗓音。
所谓规矩,是周瞎子的规矩:任何人不能租任何书回家过夜。所谓理由,是周瞎子的理由:夜里看书会把眼睛看瞎。告诉他现在有电灯了,照得比白天还亮,他就吃惊了:
“那就是闪电啊。”
“是闪电……是凝固的闪电!”长发一甩,彭健有流氓气质,也有诗人气质。
“那……”周瞎子侧耳倾听,“怎么没有雷声啊?”
听老人们说,周瞎子是少年时瞎的,夜里在煤油灯下读书,读多了就得了眼疾,一直没治好。前两年死了父母,自己也是个老人了,周瞎子就对分家的兄弟说,要出门摆个摊,以为他摆算命摊呢,结果摆了个书摊。
周瞎子不住镇上,家在镇子东边的村子里,早上太阳从东边出来,红光照到镇上,他的人和书也到了镇上了。等太阳从西边下去,暮色从东边过来,他就收摊,依凭一根竹杖,慢慢走进了夜里。
“你又看不见,怎么知道天亮了,天黑了?”我问他。
“天亮如白纸,天黑如黑字。”他说。
这大概是他变瞎时的最后印象,也可能是他仅剩的一点视觉。
“你把书贴在脸上。”他又说。
我把摊开的书贴上自己的脸,白纸黑字在我睁大的眼中果然模糊了,一个不瞎的少年就这样体验到了一个瞎少年的视觉。如果永远这样……我急忙移开了书,看看周瞎子的墨镜,黑黢黢的,深不见底,不像彭健的墨镜是反光的,可以照出人影。
“你们这些亮子!”偶尔有小孩捉弄周瞎子,摘下他的墨镜,他就生气,“少骗人,多读书!不然就是睁眼瞎!”
我相信周瞎子读过不少书,心里是亮堂的。因此他不像别的瞎子那样随地摆算命摊,而是在学校附近摆了个书摊。来看书的人里面总有嫌两分钱看一本书太贵的,两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呢,周瞎子就不管别人读没读过,听没听过,一概从头讲起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从前,有一天,天气冷死了……”
于是不论晴天、阴天、多云天、大雾天,书摊边上的人都进入一个下雪的夜晚了。小女孩说话,周瞎子就模仿小女孩的声音。小女孩在墙上擦火柴,周瞎子也一遍遍假装在墙上擦火柴,于是火炉、烤鹅、圣诞树、慈祥的奶奶……都在他擦亮的火柴里出现了。
“幸福的火柴,是在书里擦亮的。”他最后说。
幸福的火柴,是在书里擦亮的。这句话让彭健很佩服,他以诗人自居,但嘴里出来的永远只有这么一句:我歌唱带电的肉体!每次经过电器修理店,他都要冲店里喊一句,但是刘师傅不理睬,再喊一句,李师傅也不理睬。
最终理睬这句诗的是蔡老师,蔡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起了惠特曼,戴草帽的美国诗人。不过蔡老师没有歌唱带电的肉体,只带领我们朗诵了《自己之歌》:
“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对你们也一样合适,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周瞎子的书摊上没有诗集,本来书也不多,但仍然是学生课外书的主要来源。学生中自己有课外书的,也喜欢到书摊边上交换。已不是学生的彭健,更是把书摊看作镇上最有书香和诗意的地方。每天中午,书摊边学生最多,彭健也喜欢到书摊边转悠一下。每天放学后,来还书的学生中则夹着一个蔡老师。
蔡老师不没收学生在课堂上看的课外书,是别的老师没收,书上有“周记”印章的,就交给蔡老师。蔡老师也不关心是哪个老师没收了哪个学生的书,只管放学后一起郑重其事还给周瞎子,时间绝对在路灯亮起之前。全镇公认,周瞎子的规矩,蔡老师遵守得最好。
据说周瞎子起初按照少年时的习惯,把蔡老师称作蔡先生,蔡老师一惊,也急忙称周瞎子为周先生,不料周瞎子说:
“不要称我先生,听起来像个算命先生。”
“那,也不要称我先生。”蔡老师说,“现在都叫老师。”
“好,蔡老师!跟别人一样,叫我周瞎子。”
“好,周瞎子!”
两人都笑了,从此避讳“先生”称呼。科学小会后,彭春和我把蔡老师的半节科学课传到了周瞎子耳中,周瞎子就说起了赛先生,赛因斯,英语里的“科学”。去问英语老师,老师说Yes,还把“赛因斯”拼写出来:Science。
我在周瞎子书摊上租的课外书中,被老师没收过的是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科学和幻想搅在一起,让少年的我特别入迷。我的幻想很多,茫无头绪,大的大到跟宇宙一样无边,最小最具体的一个是弹簧鞋,心想穿上后一定走得比别人快。和彭春一说,彭春笑了:
“那还不如脚底抹油,溜得快!”
请教刘师傅,刘师傅也笑了:
“抹油,安弹簧,都不行。鞋底安轮子,轮滑鞋,早有啦。”
于是我的幻想少了一些,心愿多了一个。刘师傅接下来说起轮子,说轮子是伟大的发明,又说起白炽灯,白炽灯也是伟大的发明。
“一百年!”刘师傅突然一拍脑壳,耳朵动几下,“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今年正好一百年!”
凑巧了,1979年,赛先生来到中国六十年,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一百年。至今想来仍觉得神奇的是,1979年春天,中国南方一个小镇上,一名电工居然举行了一场纪念。
记得是个阴天,星期六,也是个赶集日。早上,赶集的大人和上学的小孩都被电器修理店吸引了,店面屋檐下挂着两匹银灰色的布,布上是五颜六色的字,碎布缝成的。我伸手摸摸,想起李师傅,漂亮得脸上发光的李师傅,踝关节、膝关节、肘关节、腕关节,和缝纫机一起完成了这样两条……两条老人们嘴里的“幌子”。现在回忆,这大概是我最早见到的拼贴艺术作品吧。店门关着,门上的粉笔字就差劲了,“中午营业”,简直让人生气。想趁早进店修电器、做衣服的人走开了。我再看一眼幌子,也赶紧上学去,一边走一边默念着幌子上的字:
赛先生六十岁,白炽灯一百年。
终于熬到中午,天仍阴着,星期六只上半天课,照常放学了。赶集的人大多完成了各自的买卖,在街上闲逛起来。电器修理店的大门已经开了,我挤过去时看到刘师傅正把一只很大的白炽灯连同电线拉出来,然后站上一把凳子。
站稳了,刘师傅左右摆头看看两边的幌子,抓住灯座把灯泡高高举在右手上:
“感谢爱迪生!看啊,这才是伟大的‘大灯泡,两百瓦!”
突然灯亮了,灯光盖过天光,照亮了看热闹的人。
“好!”喝彩随光而起。
我已挤到前面,发现陌生人中间夹着几个熟人:蔡老师、彭春、彭健……意外的是,周瞎子也来了,就站在彭健身前,一根竹杖撑着地。
“看,磁铁!”
刘师傅左手亮出了一坨磁铁,举着贴近灯泡。突然,灯泡里的钨丝开始发起抖来。
“看啊,闪电,闪电!”刘师傅喊起来。
“好!”发抖的喝彩声。
突然灯灭了,又一阵不再发抖的喝彩,倒彩。刘师傅笑了,把双手降下来,撩一层衣服包了灯泡,贴在胸前,然后用磁铁猛地一敲。
“好——”这次的喝彩不亚于看见“胸口碎大石”了。
刘师傅又笑了,把敲破的灯泡拿出来,不顾碎玻璃落地,满意地看看完好的钨丝:
“看啊,钨丝,钨丝就要升天了!”
刘师傅右手举起了破灯泡,突然钨丝一闪,很亮地烧起来,一道白烟一冒,钨丝烧得无影无踪。
“好……”这次犹豫着要不要喝彩了。
“升华!这是升华!喝彩啊!”
人群中有声音冒出来,是蔡老师,没有忘记老师身份的蔡老师。喝彩声再次响起,天空好像也亮了一些。我从此理解了“升华”一词,心里充满了对爱迪生的感激。传说中的从头发丝到钨丝的实验过程,无疑也是一次次升华。一个点亮世界的人,确实是值得纪念的。
刘师傅表演结束,从凳子上下来,看看残余的导丝、蕊柱、灯头,连同灯座和电线一起放回店里。又拿出扫把撮箕,清扫玻璃渣。看热闹的人很快散去,两条幌子安静地悬垂着。修理和缝纫生意看来早已接下,剩在店门前的就是我们几个熟人了。应该是一直在店内配合表演的李师傅出来,大大方方抱起了凳子,我眼前又一亮,一个大胆控制电源、及时通电断电的女人,在阴沉的天空中,她的一张脸就是阳光。
“都陪周瞎子进来吧。”她说。
于是我们拥着周瞎子和他的竹杖,一起进了店。李师傅给每个人倒茶,顺序是讲究的,周瞎子、蔡老师、彭春、我,最后是彭健。彭健接过茶杯说:
“快点让周瞎子摸个灯泡吧。”
“不急。”李师傅说。
“不急。”刘师傅也说。
“那我先走了。”说完,彭健就真的放下茶杯,走了。
等我们陪周瞎子回到书摊,才发现彭健在帮周瞎子照看,跟彭健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原来这个女朋友是一直守着书摊的。
“白炽灯长什么样啊?”彭健问周瞎子。
“一颗巨大的泪珠,滚烫的。”周瞎子说。
这又让彭健很佩服了,一同佩服的还有蔡老师、彭春、我。我那天的确看到了泪珠,先是在李师傅脸上,后是在彭健女朋友脸上。大概女人喜欢流泪吧,当一个瞎子变成诗人的时候。
我也曾经差点为周瞎子流下眼泪,是他告诉我不要告诉别人的秘密的时候。我问他相不相信耳朵识字,他低声说:
“我不相信,但我试过。”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