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恩情到爱情:古代小说人神恋的一个范型
于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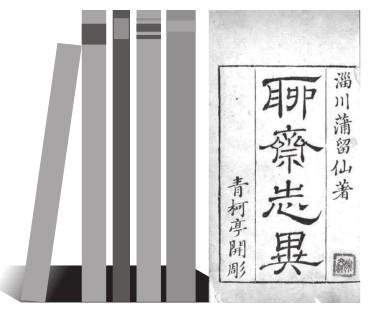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神恋题材存在一个范型,即女仙(广义)被救助后,因感激而以身相许,即爱情由恩情转化而来。如《聊斋志异》中便有这样一批基本情节框架相同的作品。而其典型之作前有《柳毅传》,后有《白蛇传》。从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伦理追求。
壹
在西方的神话世界中,“爱神”占有重要的位置。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她掌管人间的爱情和动植物的繁衍等神职。她的儿子丘比特长着一双翅膀到处飞来飞去,他手中的金箭也传播着爱情。维纳斯与丘比特是西方最典型的“爱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爱神”?这在学术界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巫山神女、织女,以及田螺姑娘等,都被拎出来讨论一番,至今也未形成共识。
事情的症结似乎是论者有些削足适履了。拿着古希腊、古罗马的名词,检验东方的文学艺术活动,凿枘不合是必然的。可行的思路是从本土文学艺术的实际出发,发掘材料,寻求规律,从而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有助于当今的文艺创作与批评。
如此,便不必纠缠于“爱神”的概念定义,而是直接到作品中,考察我国传统文化中带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分析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质以及相关的创作、阅读心理。
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到仙女——这里的“仙女”取广义,即超越人类现实的美好女性形象——之情感世界,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夫妇双修。最典型的是唐代裴铏的《传奇·裴航》,写裴航与云英成为神仙眷属的故事。这一篇小说宋代收入《太平广记》,又被改编为话本《蓝桥记》,元明两代杂剧《裴航遇云英》、传奇《蓝桥玉杵记》也都演绎这一故事,足见影响之广。第二种是仙女主持情感活动,促成人间的男女欢好。最典型的是《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子。第三种则是人神恋,这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在传统文化中,“神”的内涵并不固定,往往视其相对语境而有所不同。如神与鬼、神与魔、神与仙、神与人等,其含义皆有细微的差别。尤其是与“人”相对待的时候,其内涵之宽狭可以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本文讨论的“人神恋”,“神”取最宽泛的意蕴。举凡相恋为人与超人,双方感情活动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内容,皆在考察范围之内。这样的人神恋故事大半为“仙女”恋“凡男”,在《聊斋志异》中颇有几篇,且为全书的翘楚之作。
贰
其中最典型的,可推《西湖主》。《西湖主》的基本情节是:书生陈弼教在军中当文书,驻扎在洞庭湖畔。将军射伤了一条鼍龙,拴在船上,奄奄一息。陈生为它治伤,然后放生了。一年后,陈生过洞庭湖时,落水逃生。偶遇洞庭湖君的王妃,原来就是那条鼍龙。王妃设席招待,说:“再造之恩,恨无所报。息女蒙题巾之爱,当是天缘……”洞房之中,新娘子表示很喜爱陈生的才华,现在终于成了良缘,可以一起修仙了。从此陈生分身两地,既尽人世之责,又修成了仙体。
故事的核心是人神恋,而人神恋的起因是书生偶然行善结下的恩情。对此,作者的评论是:
竹簏不沉,红巾题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恻隐之一念所通也。
何守奇的评论则是:
德无不报,神亦犹是也。
此二论都强调人神之间的好姻缘源于神女“报恩”的心理。另一位评论家但明伦洋洋洒洒写下了数百字的评语,核心内容是分析作者如何把报恩心理转化为曲折动人的情节。
《西湖主》的故事其来有自,当属蒲松龄的改编之作。同出于前述唐代裴铏的《传奇》,有一《张无颇》,也被收入《太平广记》。其基本情节为:读书人张无颇旅途困顿,某袁大娘赠一灵药,为江神广利王的女儿治病,后被招为驸马云云。读书人被水神青睐,赐婚尚主,《西湖主》与其如出一辙。但不同的是,袁大娘为何相助?广利王之女为何心许?小说没有任何交代。张无颇的桃花运从天而降,无因而至。于是,故事的核心就是一个奇遇,讲述起来也是平铺直叙,波澜不惊。经蒲松龄再创作,《西湖主》为人神恋情设置了一个逻辑起点:施恩报恩,同时又匠心独具,据此设计了悬疑叙事的复杂路径,使得整个故事焕然虎变,成为全书的名篇之一。
有趣的是,蒲松龄对这一设计、安排很是得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衍生出精彩动人的人神恋新作。
《花姑子》可以看作《西湖主》的姊妹篇。基本情节是:书生安幼舆山行迷路,得章姓老人收留招待。其女儿花姑子以身相许。后有蛇精迷安生几死,花姑子尽力相救,终于起死回生。床笫之间,安生得知,是自己五年前放生了一匹香獐,香獐的父女特意报恩,得结良缘,并为安生产下一子。安生感其情义,终生不再别娶。对此,“异史氏”评论道:
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至于花姑,始而寄慧于憨,终而寄情于恝。乃知憨者慧之极,恝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这里,蒲松龄特别强调了“蒙恩衔结”——知恩报恩,以及恩“情”的极致乃人神之间的爱情。
检点全书,《聊斋志异》中以“恩情-爱情”模式来写人神恋的,有一批作品。如《青凤》,讲的是书生耿去病是个狂生,他在一座凶宅中结识了胡姓老人,还有他的侄女青凤。后来因故分开。清明节上坟,耿生从恶狗口中救下了一只小狐狸,却是青凤。青凤感激救命之恩,便委身相从。两年后,耿生又救了胡叟,从此如同一家人般生活。这里写耿生两次施恩于胡家,又写胡叟与耿生多次冲突,而结局是行善终有善报,恩情转化为爱情与亲情。小说设置了起伏跌宕的情节变化,于是更加深了情感转化的力度。作品中,由青凤口中讲出:“此天数也。不因颠覆,何得相从?”把患难感恩上升到规律性的“天数”。
又如《连琐》,讲的是书生杨于畏与女鬼连琐相遇(连琐生前为一才媛),二人遂结为才艺之交。后连琐为恶鬼相逼,杨生舍命相助,又甘冒奇险使连琐还阳。此篇亦属蒲松龄改编之作。原作为一佛教传说,见于《法苑珠林》,只是一个女鬼还阳的奇闻而已。经蒲氏加工之后,写出了杨生英雄救美式的侠气,既给了连琐报恩的缘由,也使连琐的爱情更显其美好。
以上几篇,都是男方的善行惠及女“仙”(广义上的“仙”)。还有一种是间接的恩情转化为爱情,作为名篇的则有《白秋练》《娇娜》等。
《白秋练》的故事与《西湖主》接近,也写是水中仙女与书生的情感因缘。不过情节另有一番处置。该篇中,慕生与白秋练结缘是因为共同的诗词爱好。白秋练乃长江白鳍豚的精灵,因美貌被老龙觊觎,遂陷其母于危难。后经慕生祈求真君助力吓退了老龙,于是伉俪情笃。同是恩情与爱情的缠绕,由于加入了吟诗诵词,用里面真君的话来讲,就是“此物殊风雅”,又有解救母难的情节,遂使故事另有几分风味。《娇娜》则是写孔生不顾生命安危,仗剑与雷神搏斗,救下娇娜全家的性命,于是赢得了芳心。
归纳起来分析,这些故事虽然各具风采,但隐然有一共同的范型在其中。这一范型具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男方为一文士,女方为一另类,或者说是广义的女“仙”;第二,女“仙”遭遇某种危难,处于某种困境,得文士大力相助;第三,女“仙”感恩相报,于是开启了美好的爱情。至于还有一些辅助性的要素,如文士要痴情、要脱俗,女仙要美貌、要有神通,等等,都是支撑大框架的细枝末叶了。
这样一个故事范型,当然源自书生的男性白日梦。不过,这是一种逻辑自洽的白日梦。
首先,男主人公梦想得到的是既有情又有貌的配偶,而自身的条件又不免“阮囊羞涩”,于是施恩于对方,便成为平衡双方的关键配比。
其次,在这样的白日梦中,男主人公总是能表现出义气、侠气,作为写作者的自我投射,其情节自会酿造出自我满足的醉意。
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样的情节构建,与社会伦理的“超我”达成高度的默契。《周易》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格言;佛教更有报应之说,如《四十二章经》《佛藏经》等都包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语,传到中土与汉地传统伦理结合后,更是把其中的因果强调到了极致,如《归元直指集》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言不报,时节未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这显然是“恩情-爱情”故事范型的最强大道义支撑。
叁
此类小说与佛经的联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例子,就是唐传奇的名篇《柳毅》。
《柳毅》为中晚唐时期李朝威的作品,原名《洞庭灵姻传》,收入《太平广记》时题为《柳毅》,后世或题《柳毅传》。小说写书生柳毅落第,路过泾阳,见一女子牧羊于野,样子很凄惨,并得知她原来是洞庭龙君的女儿,嫁给了泾阳龙王的儿子,却遭受家庭暴力,欲通音讯到娘家,苦无途径。柳毅见义勇为,将龙女救拔脱离苦海。又经若干曲折后,二人终成连理,龙女遂对柳毅敞开心扉:
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遂闭户剪发,以明无意。虽为君子弃绝,分见无期。而当初之心,死不自替。……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毅曰:“……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觐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
这是“恩情”转化为“爱情”的最为直接、深切的一段表述。“衔君之恩,誓心求报”“当初之心,死不自替”以及“得遂报君之意”“固当知报耳”等,可谓于此题旨再三申述矣。
对于这篇小说,历来评价甚高。汤显祖称为“风华悲壮,此传两有之”,胡元瑞赞许“撰述浓至,有范晔、李延寿之所不及”。不过,其故事框架,特别是救龙女而得感恩报答的核心内容,其实来自佛经。《摩诃僧祇律》载:
(离车)捕得一龙女。龙女受布萨法无害心,能使人穿鼻牵行。商人见之形相端正,即起慈心,问离车言:“汝牵此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杀噉。”商人言:“勿杀!我与汝一牛贸取,放之令去。”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为汝故我当放之。”即取八牛,放龙女去。时商人寻复念言:“此是恶人,恐复追逐更还捕取。”即自随逐,看其向到池边。龙变为人,语商人言:“天施我命,我欲报恩,可共入宫,当报天恩。”……赠以八饼龙金,截已更生,尽寿用之不可尽也。
这一篇又见于《法苑珠林》,可见在汉地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当然,从佛经到小说,李朝威的贡献还是很大的。经过他的生花妙笔,一个比较简单的“善有善报”的宗教故事,演化为集神仙、爱情、侠义于一体的文学作品,塑造出柳毅、钱塘君与龙女等性格分明、栩栩如生的形象,而且为“恩情—爱情”这样的人神恋范型树立了不朽的标杆。
蒲松龄深受《柳毅》的影响。他对前辈这一范型十分熟悉,其作品《织成》可以看作对李朝威的致敬之作。《织成》写书生柳某过洞庭的一段奇遇,其中数次直接提及柳毅,如:
闻洞庭君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君得遇龙女而仙……相传唐柳毅遇龙女,洞庭君以为婿。后逊位于毅。又以毅貌文,不能摄服水怪,付以鬼面,昼戴夜除。久之渐习忘除……
足见由《柳毅》而《西湖主》《白秋练》等,实乃一脉相传,终成一类爱情小说的范型。
此范型于后世之文学创作影响久远,代表作即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白蛇故事的成形之作,为《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以游湖借伞发端,白蛇精游西湖遇雨,搭乘了许宣的便船,后又蒙其大度借伞,于是有所感念,以身相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报恩、生情的故事。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刊行的文字版也有《雷峰塔奇传》《义妖传》等,最终衍生出了《白蛇传》,里面便有了分量更重的“恩情”:当年白蛇遇难,得前世许仙救命云云,故转世报以夫妇之情。从文学创作来说,这显然是前述范型的一个翻版而已,但由于有了法海的形象,以及雷峰塔这样象征意味十足的桥段,白蛇故事后来居上,可以说是“由恩情到爱情”的人神恋范型的第一代表作了。
从“由恩情到爱情”的人神恋范型的形成与流变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生生不息的深层动力,是由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追求产生的。
(作者系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为珠海科技学院“博士提升计划”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