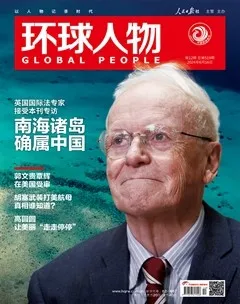93岁“敦煌少女”,传奇还在继续
陈娟

2024年5月21日,常沙娜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张森绚 / 摄)
常沙娜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小楼里,小区管理严格,非常安静。《环球人物》记者按约定的上午10点到达时,她刚刚睡下。93岁的她,生活渐渐慢了下来,不再每日奔忙,过得随性自然。
我们在客厅里等她醒来。整个客厅很整洁,茶几上摆着一排书,有《敦煌!父亲的召唤》《洞之以情——寻找天籁敦煌之音》等,书上放着老花镜。靠墙的书架摆得满满当当,也大都与敦煌有关。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偶闻鸟鸣声,窗边有一张姜黄色沙发,保姆说那是“奶奶专属的座位”。很多时候,她都坐在那里读书、听新闻、看电视,打打瞌睡。兴起时,她也会摊开稿纸画画,默画一些石窟复原的图案。
将近11点时,常沙娜睡醒了,梳洗一番后坐在我们面前。她身着暗红花色衬衣,外罩棕色小坎肩,一头白发梳成小马尾,一丝不乱,从容而优雅。“你这衣服穿得太不讲究了。”看着记者,她一边说一边摇头。一向爱美的她,习惯性“批评”身边人的着装。在她的眼中,“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大小、比例、色调、尺度、功能、材料的结合,来不得半点儿马虎。
常沙娜一辈子都在从事与“美”有关的工作。她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女儿,少时便跟在父亲身边临摹敦煌壁画;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学生,由此走进工艺美术的大门;她是工艺美术设计家,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设计,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她是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教授设计课,整理、编绘《敦煌历代服饰图案》……

“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计展”现场,观众正在参观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
一个多月前,“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计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满头银发的常沙娜出现在人群中,回望从艺之路,她说:“‘花开敦煌的展览是我对父亲常书鸿推广敦煌文化遗志的实践,因为父亲告诉我,沙娜,不能忘了你是敦煌人。”
从巴黎到敦煌
“每天不断地翻阅父亲与我出版的书,让一段段的回忆慢慢涌现。”常沙娜说。她拿起茶几上的《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带着我们回到人生之初。
1931年,她在法国里昂出生,父亲常书鸿正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第二年,为了艺术深造,常书鸿将家搬到了巴黎。一到周末、假日,家里便聚满了人,大都是同期留学的中国艺术家,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等,大家谈古论今、畅谈艺术。在这样一个“空气都渗透着艺术气息”的家庭中,常沙娜度过了欢乐无忧的童年。
然而,这份平静却因一次偶遇被改变。1936年秋,常书鸿在塞纳河畔散步,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画册《敦煌石窟图录》,为之震撼,遂决定要回国去寻访敦煌。当时,中国正值战乱,回国后,他们一家颠沛流离。直到1943年,常书鸿不顾各种反对,将家安到敦煌,并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那一年,常沙娜12岁。她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抵达敦煌时的情景,冬天的深夜,莫高窟前大泉河里的水已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大家肚子都饿了,但没什么吃的,“欢迎晚餐”令人难忘:一碗盐、一碗醋,每人一碗水煮切面。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为自己家画的《画家家庭》。
第二天一早,晴空万里,父亲就带她去看莫高窟。凿在长长一面石壁上、蜂房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却因风沙侵蚀、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然而一进洞,她立刻着了迷,“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
从此,常沙娜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
每天早上钟声一响,研究所里的人就进洞,临摹的临摹,调研的调研。常沙娜一放假,也跟着大人进洞,爬“蜈蚣梯”,临摹壁画。“爸爸要求我将各代洞窟的重点壁画全临一遍,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常沙娜说。同时,父亲还为她制定了一套学习计划:每日临帖练字,朗读法语一小时,并安排两个学生分别辅导她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
在大漠荒烟中,常沙娜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1945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先是母亲出走,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抗战胜利后研究所重建又经历“复员潮”,工作人员纷纷离开,只有常书鸿依然坚守。这年冬天,常书鸿将父女二人临摹的一批壁画作品,以及速写、油画写生等拿出来,在兰州举办“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轰动。
也是在这次画展上,常沙娜结识了一位外国人叶丽华。3年后,在叶丽华的邀请下,常沙娜去往美国留学,学习西方艺术。
“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
1950年底,在留美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常沙娜放弃在美国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回国。
回国第一件事,便是协助父亲举办“敦煌艺术展”。有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参观展览,常沙娜负责接待。之后,梁林夫妇二人邀请常沙娜到他们身边做助教。当时,林徽因肺病已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她的头脑非常好,思维异常敏捷,只是身体太差了,只能把构想告诉我们,我们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林徽因还常常鼓励常沙娜,将敦煌的图案用在工艺设计上。
有一次,林徽因让学生们设计头巾,“记得当时她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和平鸽。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感。”根据建议,常沙娜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形式,并在上面穿插了来自敦煌洞窟中的鸽子。当时正值“亚太会议”召开,头巾还作为礼品送给了各国代表,深受喜爱。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走上工艺美术之路,后来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对中国的传统图案及民间艺术进行专题整理研究。再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图案基础课和染织设计课,上世纪80年代担任院长,一当就是15年。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与父亲有所不同——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和敦煌艺术研究推广,而她偏重于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
1958年至1959年间,北京建造首都“十大建筑”,其中之一是人民大会堂。常沙娜参与其中,负责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的设计。起初,受敦煌藻井形式的启发,她在大厅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人民大会堂总工程师张镈看后,提示她:“这样只设计花瓣不行,你得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在里面;中心也不能只搞花蕊,要把中心与灯光组合起来;仅中心的照明灯还不够,在外圈也得设通风口。”她连夜修改,拿出新方案,解决了照明、通风问题,也展现了敦煌艺术之美。
这次经历给了常沙娜一个启示: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共同努力反复研究的结果,而且一定要按照功能的需要,按照它的含义宗旨来进行。这一理念,贯穿于她各个时期的设计中,从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到首都机场、中国大饭店,等等。1997年,香港回归,她还受命主持并参与设计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常沙娜一直遵从父亲“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建议,不断从敦煌汲取灵感。“敦煌的东西,即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有了它,我们创新也好,搞任何设计也好,才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

2024年央视春晚节目《年锦》上演后,备受好评。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常沙娜这一生都离不开敦煌,也为宣扬敦煌艺术奔走一生。80岁以后,她名气突然大增,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
10年前,常沙娜开始举办“花开敦煌”巡回展览,如今已走过北京、深圳、高雄、巴黎、莫斯科等地,每一次她都跟随。年岁渐长,身边不断有人劝她,年纪大了,不要再到处跑了。她不听,“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要到处说敦煌”。
近两年,常沙娜已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也极少动笔创作。她最新完成的作品是2024年央视春晚创意节目《年锦》。舞台上,4位表演者分别身着汉、唐、宋、明服饰,演绎着历朝历代的流行经典。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每套服饰的衣、裙、领边、袖口上都有不同的纹样,均寓意吉祥。观众看后,纷纷点赞:“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式审美!”常沙娜也在当晚被推上热搜。
“我这一辈子都在跟传统图案打交道,但给春晚设计纹样,还是头一回。”常沙娜说。当时,春晚节目组邀请她和儿子崔冬晖担任艺术顾问,想做一个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节目。经过多番讨论,最终决定以传统图案为主要元素进行设计。团队先从博物馆搜集文物原型,然后进行图案提取,再绘制电子设计图,最后由常沙娜逐一手绘修改。“母亲根据她70多年图案设计的经验和敦煌研究的积累,进行一些修改。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让它尽可能饱满、完整而且舒服。”崔冬晖说。最终,历经无数次打磨,才有了舞台上的样子。
“传统图案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厚度,感受到感性的温情,更可以通过现代设计的形式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品格。”常沙娜说。通过这次合作,崔冬晖体会到常沙娜总提的创作理念“守正创新”,“她更多时候像是老师,教会我如何一生择一事,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
在很多人眼中,常沙娜的一生是一部长篇传奇,她自己也说“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了”。
年少时,她拥有过幸福的家庭,后来母亲出走,十几岁时既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年幼的弟弟;青年时,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中年时,丈夫离世,儿子只有13岁,独自一人将儿子养大;晚年时,罹患乳腺癌,做手术、化疗,她生活如常,搞设计,当院长,听喜多郎的《丝绸之路》。
“喜怒哀乐,去经历就好了。”“能做啥就继续做啥,高高兴兴,这样心情就会很痛快。”每当想起前前后后那些用言语难以讲清的故事时,她的脑子里就会闪出一句法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常沙娜一直记得父亲的那句话:生命不息,跋涉不止。生活还在向前,常沙娜步履蹒跚,但未停下脚步,她的传奇还在继续。
编辑 余驰疆 / 美编 徐雪梅 / 编审 张培
常沙娜
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著名工艺美术设计家、教育家。著有《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等。主要设计作品有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近日,“花开敦煌——常沙娜从艺八十年艺术与设计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
——常书鸿与敦煌的不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