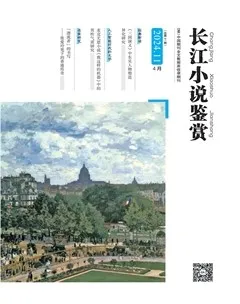《补江总白猿传》在明代的接受与改写
[摘要]唐传奇对明代小说的创作和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明代瞿佑的《申阳洞记》及冯梦龙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均为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改写之作,两者对原有故事的改写存在共同之处,体现出由唐至明小说创作意图和创作观念的变化。此外,《申阳洞记》诞生于明初,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则编成于明末,在明代不同阶段政治统治和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同为明代作者的改写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关键词]《补江总白猿传》 明代接受 《申阳洞记》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98-06
短篇小说在明代大盛,无论是白话短篇小说还是文言短篇小说,在明代均有长足发展。明代创作者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多以前代小说为基础进行再创作,而其中又以对唐传奇的改写最为突出,他们对唐传奇中的故事加以演述或摹拟,使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明代小说中。《补江总白猿传》作为流传甚广的唐传奇作品,自然就成为明代小说创作者争相取材的对象。在文言小说方面,有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而在白话小说方面,则有冯梦龙参与编撰的《喻世明言》中《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一篇。尽管这三篇故事发生时间不同、出场人物姓名不同、人物关系发生变化,情节上也多有增删,但就故事整体而言,它们都以“猿猴窃妇、众人救妇”作为主线进行讲述。同时,在某些场景的刻画中也表现出了极高的一致性,比如“窃妇”的发生必是在“一阵风”之后、猿猴藏身处均隐于无人的险峻山壁之间等。无论是从情节发展还是场景描述出发,均可认为《申阳洞记》《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以下简称“明代两改本”)是在《补江总白猿传》基础之上的重新改写,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在这两篇改写篇目中,不仅可以展现出不同朝代对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追求,而且还可通过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作品之间的差异来窥探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想所发生的变化。
一、《补江总白猿传》在明代的整体接受
《补江总白猿传》作者不详,据考证应完成于初唐时期,全篇基本以“一人一事”的方式展开,讲述平南将军别将欧阳纥携妻子驻兵在外时,妻子不幸被白猿神掳走,在艰难的寻找和众人的帮助下,欧阳纥终于斩杀白猿神,解救妻子和其他被掳妇女之事。明代两改本作为《补江总白猿传》的重新改写之作,对原文中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等方面均有所改动,但同作为明代小说,两者的改动又具备一定的趋同性。
1.对小说虚构性认识的加强
无论是《申阳洞记》还是《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对《补江总白猿传》的改写都属于间接取材,并非直接套用出场人物。同时,《补江总白猿传》中主人公欧阳纥的姓名和经历都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南朝官员欧阳纥有着高度相似,但明代的两篇改写小说均以虚构人物来代替原本中的真实历史人物。这是由于《补江总白猿传》有“假小说以施污蔑之风”之嫌,该篇主人公欧阳纥的妻子在被白猿掳走后生下了一个貌似猿猴的孩子,而与主人公同名的、真实存在的欧阳纥之子欧阳询也被人嘲笑其外貌类似猿猴,这就与小说中的情节相对应。故而《补江总白猿传》常被认为是欧阳询的政敌为贬低和嘲笑欧阳询所创作的污蔑之文,是借“猿猴窃妇”这一由来已久的故事对欧阳询的外貌进行攻击,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后世也对这篇小说产生了不少的议论和纷争。而明代两改本并无此类政治目的,仅出于创编意图将其视作可供取材的唐传奇之一,借鉴其故事情节进行改写创作,因此并不需要保留原文的政治目的。
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由唐至明,对小说虚构性特征认识的加强。唐传奇仍然未摆脱史传文学的影响,存在将故事依托于真实事件和人物的倾向。因此,唐传奇的描写多关注于人物的外貌和动作,而甚少涉及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从《补江总白猿传》中未有一句涉及心理描写即可看出。而在明代两篇改写作品中则体现出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逐渐重视,《申阳洞记》中已有“生念深山静夜,安得有此?”这样简单的心理描写,而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则出现更多“自忖”“自思”“寻思”的明显心理活动的内容,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见明代小说的作者已几近彻底冲破史传实录观念对小说的束缚,实现小说创作的自主性和虚构性。
2.对“大团圆”式结局的追求
《补江总白猿传》的结局并未止于欧阳纥斩杀白猿,取其珍宝后与妻重聚这一美好结局,反而增添了妻子生子如猿、欧阳纥被诛杀等较为负面的情节,同时也对其子长大之后的境遇进行了交代。从中可看出《补江总白猿传》在一定程度仍旧沿袭史传的书写方式,倾向于对主要人物的一生经历作完整叙述,而并不在乎其结局是否圆满。
明代两改本则仅聚焦于杀猿救妻这一个事件,并为其画上完美句号。《申阳洞记》中的李生不仅救出了包括当地富豪钱翁之女在内的三位美人,还获得了来自钱翁的大笔财产,摆脱先前困窘的境地并娶得三位美人。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陈辛,不仅在众仙的帮助下救出妻子回到故乡,还同妻子深情厮守,百年而终。改本的结局没有出现任何负面的情节,这是有意追求“大团圆”式结局的结果。
尽管均以“大团圆”式结局结尾,但明代两改本的作者对圆满结局追求的原因却各不相同。《申阳洞记》作者瞿佑的少年时期在元末的战乱中度过,饱尝兵火乱离的痛苦。因而在瞿佑的创作中,大多数作品无论过程多么曲折艰难,几乎都会给予故事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同时,《剪灯新话》大致创作于明代初期,彼时的明王朝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无论是朝廷还是百姓均未从与元的战乱中恢复,仍然没有摆脱战争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阴影,以悲剧结尾或存在负面情节的作品可能会使读者再一次回忆起战乱带来的伤痛。因此,瞿佑作为自幼受到儒家教育的士大夫,或许会出自文人情怀而在创作中选择以“大团圆”式结局作结。
而冯梦龙对“大团圆”结局的追求既同其创作目的有关,又受到读者群体的影响。在《古今小说》的序言中,冯梦龙充分肯定了小说具有巨大的情感感染力:“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 体现出他对小说的教化功用格外注重,其在“三言”的编撰过程中亦是如此。而教化内容中最普遍的就是“劝善惩恶”的思想,因此故事中作为“善”的一方必定会得到圆满的结局,而作为“恶”的一方则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在此影响下,《陈从善梅岭失浑家》自然就以作为“善”一方的陈辛获得圆满结局作收尾。此外,冯梦龙所编撰的“三言”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其所面向的受众是市民阶层,因此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一定程度上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创作市民阶层爱看的、以“大团圆”喜剧为结局的小说作品,以获得市民阶层的喜爱,促成小说的进一步传播。
3.小说创作意图由追求“奇”到关注“人”
明代两改本在对《补江总白猿传》的改写过程中不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白猿形象,而且着重叙述了有关人的情节,由此体现出由追求“奇”到关注“人”的创作意图变化。
《补江总白猿传》作为唐传奇,“求奇”仍是其最主要的创作目的。在对“奇”的追求下,《补江总白猿传》将叙述的重心置于“白猿”这一非人的奇特形象上,用大半篇幅细致地刻画了白猿的外貌、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行为等,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甚至同故事主要情节并无任何联系。无论是白猿能文能武、威猛高大的动物神的形象,还是其隐于翠竹之间、嘉树名花列植、绿芜如毯的居住之地,都是为了赋予故事奇幻色彩而设置的。单纯从故事情节来看,《补江总白猿传》正如其题名一样,想要突出强调的是“白猿”这一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奇”的形象,至于欧阳纥救妻杀猿等情节,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凸显白猿居住地宛若仙境及白猿“全身坚硬如铁,唯有脐下几寸柔软薄弱”这一奇特的身体特征,可以说对白猿的多重刻画都是为了追求内容之“奇”而服务的。
与之相比,明代两改本中对白猿的叙述不仅只以寥寥数笔带过,且均以负面形象出现。在《申阳洞记》中,对白猿的描绘仅有“窃妇之恶”和“抢占他人领地”。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白猿面相丑陋,不仅同山神合计,在陈辛妻子如春熟睡时将她窃走,且在盛怒之时意图将如春剖腹取心以平息心中的怒气,足以见其诡计多端和粗鲁暴戾。可见明代两改本中的白猿在形象上逐渐趋于片面和单一,完全成为与正义主人公相对的反面人物,其身上的奇幻色彩被大大削弱。
明代两改本在叙述中相较于白猿这一具有奇幻色彩的形象,更注重对“人”的刻画,呈现出更为丰满的人物形象。《申阳洞记》中多处扩写了主人公李生同白猿之间的交锋,由此体现出李生的勇敢和机敏。李生夜晚投宿古庙时偶遇出巡的白猿及跟随的众猿,在发现它们为妖时立刻以毒箭射之。他在误入白猿居住地时,又以为白猿治疗剑伤为由哄骗白猿及其手下吃下毒药,成功除掉了白猿一党,拯救一众被掳女子。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扩充的情节则更丰富多样,不仅多处着笔刻画主人公陈辛及其妻如春之间的情深意笃,还描绘陈辛为官清正严谨以及妻子如春被掳后对白猿的勇敢反抗等。明代两改本中扩充了和人相关的情节、增加了人的性格塑造,呈现出更为丰满多面的“人”的形象。
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在叙述中重猿,强调白猿所具有的超越人的奇特形象和力量,而明代两改本的叙述中均侧重于人,强调人的多面形象并将白猿塑造成单一的负面形象。这种情节侧重和人物形象上的变化均体现出明代两改本在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改写过程中,其创作意图已经从追求“奇”转变为关注“人”。
二、《申阳洞记》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的不同改写
即使同样创作于明代、同样为对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改写的小说,但将《申阳洞记》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对比即可发现,两者之间除了语言和形式之外,仍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剪灯新话》成书于明初,而《喻世明言》则编成于明末,两书之间存在着二百余年的时间差,因此两书对原本的不同改写,不仅体现出身处不同时期作者文学观念的差异,且反映出由明初到明末的历史演进中,整个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统治、社会思想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1.仿效对象不同带来的不同情节侧重
《剪灯新话》有明确的仿照唐传奇而创作的意图。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表示“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2]鲁迅也评价《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3],因而《申阳洞记》的改写可以说更多地保留了唐传奇的风貌。
从篇名的命名方式上来看,《申阳洞记》保留了唐传奇史传文学的影响,即多以“记”“传”“闻”等命名方式进行命名[4],同时也延续了唐传奇“一人一事”的叙述方式。在故事内容的细微处,《申阳洞记》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本故事中的怪奇面貌。李生与白猿的初次见面是在深夜无人的古庙中,当时正值白猿及随从仪仗出行,因而对随从和白猿的队伍排列、穿着打扮等都有着具体的刻画,并且对白猿居住的地点“申阳洞”也进行了神秘化处理,“复至其处,求访路口,则丰草乔林,远近如一,无复旧踪焉”[2]。小说将申阳洞塑造成如同桃花源一般的世外仙地,使得李生杀白猿救三女的故事更加蒙上一层奇幻的色彩。另外,《申阳洞记》一篇中显现出对唐传奇“多讲近事”特征的继承,这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明朝立国之初,战乱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统治者主要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复苏社会经济,因此并未过多地干预小说等具有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者们得以将“近事”纳入小说创作中。《剪灯新话》成书大致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而《申阳洞记》故事发生在1304年至1332年间,两者在时间上是比较接近的。由此可见,《申阳洞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唐传奇有着较为紧密的继承关系,隐隐透露出唐传奇的文体风貌。
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作为明末的拟话本小说,则更多地承袭自宋元话本的体制和形式。在命名方面,不仅题名字数增多,且舍弃了“记”“传”等史传文学的命名形式,改为包含故事人物、地点、事件等具体信息的题名,使得故事内容能够在篇名中一目了然。同时,话本小说作为从说话表演艺术中产生的文学形式,保留了一些说话表演程式中的特殊形式,而这些形式也在拟话本小说中被部分继承下来。《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仍以诗的形式保存着延宕正话开始时间、等待更多观众聚集而产生的入话部分,以及对整篇故事进行概括和总结的结尾部分。同时,在一个情节告一段落后,会有诗句对该情节进行总结,并且也会运用诗句来对场景或人物心理进行描绘,呈现出白话中夹杂文言的面貌。
另外,由于《喻世明言》与宋元话本和说话艺术的紧密关联,其读者群主要是以普通百姓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类通俗文学作品也被赋予了一定的商品色彩。因此,与主要面向文人读者群体的明初改写本《剪灯新话》不同,《喻世明言》的改写一定程度上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取向以及经济盈利需求,这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则体现为情节的多线开展以及非主线故事情节的增加。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颠覆唐传奇“一人一事”的叙事方式,而是以陈辛、紫阳真君和申阳公白猿三人为中心展开三条叙事线,而这三条叙事线又经由“杀猿救妇”这一主线情节的需要而汇合交织。除了“杀猿救妇”的主线情节之外,这一改本着重刻画了陈辛和如春夫妻间不离不弃的动人爱情、申阳公白猿及先前被掳二女劝说如春委身屈从,以及紫阳真君预知如春会被掳后暗中相助等情节。这些情节与推动主线故事发展并无必要关系,但却是市民读者群体最喜闻乐见的内容,是最吸引他们的故事情节。因此,尽管这些情节对于原本的故事来说可有可无,但却在明末的这一改本中得到细致具体的刻画。
2.教化意味的逐渐浓厚
尽管明代两改本都在唐代原本的基础上增添了“劝善惩恶”的教化意图,但《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与《申阳洞记》相比,其教化色彩更为浓郁。以主人公为例,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主人公陈辛同妻子情深意笃,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一心向善,还能在为官期间始终保持清正的同时做到为民除害,才能在妻子被掳走投无路时获得众人的帮助。陈辛的“善”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叙述,也正是因为他的“善”,才最终带来了夫妻团圆、健康长寿的结果。而在《申阳洞记》中,主人公李生的“善”仅体现在误入申阳洞解救被掳女子一事上,而被掳女子中恰好有一人是富人钱翁之女,李生才摆脱贫困生活并娶得三位美妇。李生身上所体现出的“善有善报”更多是机缘巧合下的结果,其教化意味就不如强调日常生活中也要行善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浓厚。
除了“劝善惩恶”的思想之外,《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另有对女子守贞品质的强调,这进一步加强了其中的教化意味。
《补江总白猿传》中被掳的欧阳纥妻子生下酷似白猿的孩子,暗示了她已委身于白猿而失贞。针对这一情节,明初改本《申阳洞记》避而不谈被掳女子的贞节问题,而直接以三女同嫁主人公李生作为结局。而明末改本《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则多次加入了如春捍卫自身贞节的情节,即使遭受剪头赤足的羞辱和面对死亡的威胁,也未动摇她守贞的决心,这足可见明末改本所透露的“女性无论面对何种境况,都应恪守自身贞节”的观念。从明初改本对女性失贞的回避,到明末改本对女性守贞的格外强调,可见女性守节已成为那个时代教化内容的一部分。
明代两改本对女性贞节问题的不同态度与作者基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女性观紧密相关。
瞿佑生于元末,其成长时期几乎均受到元末战乱的影响,而战乱时期的社会动荡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宋元理学思想束缚的消解,从而形成了瞿佑顺性重情的观念。这使得瞿佑对女性贞节问题持有相对开明的态度,与明代保守的女性观相背离。
明朝初建时,朱元璋下令纂修《女戒》以规范女性的日常生活,其中尤其强调男女有别,要求女性遵守“三从”、恪守妇节[5]。然而瞿佑笔下的女性往往在两性关系中主动热情、不顾男女大防,呈现出对人的自然情欲的肯定,如《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中的卫芳华、《牡丹灯记》中的符丽卿及《联芳楼记》中的薛氏姐妹等。但瞿佑的创作并非没有对女性守贞行为的刻画,在《爱卿传》中,罗爱爱面对张士诚同党刘万户的强娶,选择自缢而死,保全了自己作为赵氏子之妻的贞节。而在《翠翠传》中,翠翠得知丈夫死讯后,因过度伤心而日渐病重,最后殉情而亡。这些女性主人公的行为均可被划入“贞”的范畴,但瞿佑对女性守贞行为的刻画是为凸显男女之间的真情,而并非强调女性守贞的职责。罗爱爱在嫁与赵氏子之前是一名娼妓,翠翠在战乱中同丈夫分离后再嫁他人,这两位女性角色从明代对于女性贞节的标准来看,已是失节妇女,然而瞿佑仍然对她们予以赞扬并赋予她们美好的结局。
可见瞿佑所认为的“贞”是情感层面的始终如一,而并非明代对女性所要求的身体层面的忠于一人。他对女性守贞行为的刻画并非出于教化意图,而是基于对情感的崇尚,这也是《申阳洞记》中未提及被掳女性失贞的原因。
出生于明代的冯梦龙则直接受到明代女性观的影响。尽管自明代中期以来,新的女性观念逐渐崛起,对女性的礼教要求有所松懈,冯梦龙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崇情抑理的倾向,其作中也不乏对女性大胆追情的肯定,然而这些女性观多停留于对女性见识的肯定、对世情的纠偏等方面[5],对女性贞节的要求并未松懈。因此冯梦龙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着重刻画如春为恪守自身贞节所忍受的羞辱和痛苦,并借其他人物之口点明如春是因其尽力反抗、保存贞节才得以脱困,由此进一步强调女性无论面对何种境界均要维护自身贞节。
《申阳洞记》的主人公以一时之善获得了美满结局,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不仅强调男主人公日常生活中的行善积德,更着重刻画女主人公誓死捍卫贞节的勇敢,正因男主人公的“善”和女主人公的“贞”,二人才获得了相守长寿的结局。由此可见,明末改本的教化意味更为浓厚。
3.道教色彩越发浓郁
由唐传奇原本《补江总白猿传》到《申阳洞记》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有一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道教色彩越发浓郁。
在明初改本《申阳洞记》的改写中,尽管加入了道教相关的情节,但所占篇幅较小,且并非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内容出现。“虚星之精”作为最富于道教色彩的角色,仅在故事结尾时出现,帮助李生和三妇离开申阳洞。其作用仅限于补充白猿出现的原因,并使得整个故事的叙述更趋于完整。尽管瞿佑在最后借“虚星之精”之口说出:“然吾等居此,与人无害也,功成行满,当得飞游诸天,出入自在耳。非若彼之贪淫肆暴,害人祸物。今其稔恶不已,举族夷灭,盖亦获咎于天,假手于君耳。”[2]这段充满道教思想的话语表达了“人命天定”的观念,但李生仍然是作为故事核心情节“杀猿救妇”的实际操作者,他凭借自身的智慧和果敢毒杀白猿,拯救三妇,同具有道教象征含义的“虚星之精”关系并不紧密。
瞿佑本人对于道教在内的宗教并无虔诚的信仰,其诗《秋日书怀》中有“六通未具难成佛,九转无疑谩学仙”之语,即可见无论是佛教思想还是道教思想,瞿佑都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因此他在《申阳洞记》的创作中引入道教成分,主要是出于对故事情节中奇幻色彩的追求,以及借道教天命观念达到劝惩教化的目的。
而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道教的思想则变得更为浓郁,这首先表现为故事中道教相关人物的增多,且这些出现的道教人物均是作为推动故事情节的主要人物而存在。主人公陈辛虔诚向道,因此获得了大罗仙界紫阳真君的帮助。紫阳真君预知到陈辛妻子如春会被自称申阳公的白猿掳走并遭到近千日的灾难,于是吩咐大慧真人化作道童一路随行暗中相助。而在陈辛妻子被掳三年后,紫阳真君又再次出现,在他的召唤下,两名红衣天将顷刻之间就将白猿制服,解救了陈辛的妻子如春以及其他两位被掳的妇女。最为重要的“杀猿救妇”情节的操作者已由“人”转变为道教代表紫阳真君及其手下,作为人的陈辛在“杀猿救妇”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毫无先前在《补江总白猿传》和《申阳洞记》中作为“人”的主人公的机智和勇敢,只能不断寻求非人力量的帮助来同白猿对抗。在陈辛同白猿正面交锋的描绘中,“陈巡检大怒,拔出所佩宝剑,劈头便砍。申阳公用手一指,其剑反着自身”[6],可见陈辛完全无法同白猿抗衡,这体现出的是“人”的力量有限,必须依靠仙道的力量才能够打败精怪的事实。
除此之外,同《申阳洞记》仅出现道教人物不同,《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除了道教人物之外,还出现了佛教人物,即红莲寺长老旃大惠禅师。旃大惠禅师曾救过陈辛性命,但无论是在“杀猿”还是“救妻”的过程中,他均未能给予陈辛帮助,他对白猿的劝说反而为如春带来又一次的性命危机。直到陈辛得到紫阳真君的帮助,白猿才伏法,如春才得救。这也意味着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这一改本中,作者对于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佛教人物不能解决的问题却被道教人物解决,足可见其文中的崇道倾向。
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道教仙力完全取代《申阳洞记》中“人”面对困境所展现出的勇敢和机敏,呈现出更为浓郁的道教色彩。
三、结语
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经由明代作者改写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瞿佑的《申阳洞记》和冯梦龙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除了“杀猿救妻”的主线情节并未改变之外,出场人物、故事结局以及小说主旨等都在唐、明两代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貌中被赋予新的色彩。而同样是创作于明代的两篇改本,明初的《申阳洞记》和明末的《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也仍有诸多相异之处,这与明代社会思想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体而言,由唐至明,小说创作意图从追求“奇”转变为追求现实教化,因此人物刻画重心和结局都发生了转变。而从明初至明末,小说在体制和情节书写上都有着巨大的革新,所反映的社会风貌也更加广泛。这些变化与政治背景、社会思想风貌等紧密相连。时代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深远,不同时代的面貌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文学作品的变化为时代面貌的变迁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 冯梦龙.古今小说[M].许政杨,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瞿佑.剪灯新话[M].向志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4] 郝秋霞.明刊话本对唐传奇的取材与文体改编[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5.
[5] 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
[6] 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余 柳)
作者简介:陆泽易,上海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