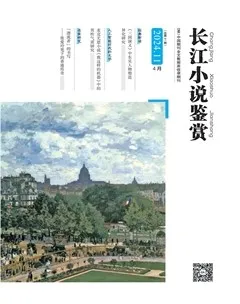森鸥外和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形象比较研究
[摘要]鲁迅动笔翻译森鸥外《沉默之塔》的时间和他创作《狂人日记》《药》的时间几乎重叠,在这三部作品中均有出现的“狂人”形象也具有许多共同点。但与森鸥外的“狂人”相比,鲁迅的“狂人”更具革命性和战斗性。可以说,鲁迅结合本国的时代背景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彻底揭露旧时代中国的病态社会、唤起民众的觉醒为目的,对森鸥外的“狂人”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
[关键词]森鸥外 鲁迅 狂人 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84-04
一、“狂人”之经纬
鲁迅的“狂人”形象首次登场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中。《狂人日记》凭借日记体这一新颖的文学形式和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小说主角的“狂人”也成了各国学者讨论和研究的对象。
鲁迅曾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写道:“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1]由此可见,外国作家及其作品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李冬木曾经针对“狂人之诞生”撰文指出,“狂人”在文学作品和评论中频繁登场,是明治文学的一种突出现象。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狂人”言说的洗礼,完成了自我的确立,并带着一个完整的“狂人”雏形回到中国。他笔下的“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移植外国思想和文艺、将其本土化的结果[2]。针对“狂人”的演变历程,李冬木另撰《“狂人”的越境之旅》指出,今野愚公翻译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狂人”入境日本的开始。松原二十三阶堂创作的《狂人日记》,使“狂人”完成了日本的本土化转型。此后,契诃夫《六号室》译本的出现和二叶亭四迷《二狂人》的发表,引发了文艺界的“狂人”热潮。鲁迅亲自见证了“狂人”的越境,并最终通过翻译和创作将“狂人”带到中国[3]。此处有两点值得格外关注。其一,鲁迅“狂人”的诞生与其日本留学期间的见闻有着密切联系;其二,鲁迅引进“狂人”的方式有两种,即翻译和创作。
结合以上两点,笔者将目光转向森鸥外。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表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喜爱的日本作家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4]。这份喜爱与森鸥外和鲁迅在时代背景和个人身份上的共同点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身处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社会转型时期,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涵养,又因其海外留学经历,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的熏陶,对传统表现出反叛的倾向。两位作家都是医学出身,转向文坛,兼任政府官职,因此他们在剖析社会现实和官僚政治时,总带着医学者的冷静,以独特的视角对保守、反动势力进行辛辣的讽刺。
1910年的“大逆事件”以及日本政府的禁书行为引起了森鸥外的强烈不满,他于同年11月发表《沉默之塔》,通过派希族统治者封禁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品、残杀“危险书籍”读者的故事,揭露了反动者以“危险的洋书”为借口迫害革新者的真相。鲁迅对这些不满感同身受,他于1921年亲自动笔翻译《沉默之塔》,并将其收入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以他山之石,批判反动者对于“走新路”的人的迫害。两位文豪在灵魂和思想上的共鸣由此可见一斑。
巧合的是,鲁迅翻译的《沉默之塔》和几乎同时期创作的《狂人日记》《药》中都出现了“狂人”形象。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鲁迅是否同时以翻译和创作的形式将留学期间接受的“狂人”带到中国?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是否是鲁迅“狂人”的来源之一?本论文将重点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二、森鸥外和鲁迅小说中的“狂人”
《现代日本小说集》和《呐喊》分别于1923年6月和8月相继出版,可以说,鲁迅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所选入作品的时间和他创作《呐喊》系列文章的时间几乎是重叠的。正如崔琦所言:“鲁迅在创作《呐喊》的同时,曾翻译了大量外国的小说和剧本,其规模和数量远超创作……翻译和创作同行,是《呐喊》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5]因此,可以合理推断,鲁迅在创作《呐喊》所收录文章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受到同期翻译作品的影响。
1.《沉默之塔》中的“狂人”
《沉默之塔》写于1910年,是森鸥外对所谓“大逆事件”以及“危险的洋书”的回应。《沉默之塔》的主要情节是:派希族内部发生了血腥的争斗。一部分青年由于阅读有关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危险书籍”被同族人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被运到沉默之塔中喂食乌鸦。“危险的洋书”的创作者、翻译者、读者都成了罪人,文艺的世界亦成为充满疑虑与恐惧的世界。
于是,崇拜个人主义、又用革命家来做小说主角的阿尔志跋绥夫被批判为“连精神都异样”的危险分子;讲述贵族小姐与仆人相爱、传播平民主义的斯忒林培克被人疑心“当真发了狂”;宣扬“超人”、此岸哲学的尼采则是“头脑有些异样”,“终于发了狂”。对于这些离经叛道、走着新路的“狂人”,反动统治者是必然要为他们定下莫须有的罪名趁机加以迫害的。这个罪名,可以是阅读、传播“危险的洋书”,可以是发表过激言论、有不检的举动,也可以是思想、精神有异端。所谓“狂人”,也不过是一个迫害的名目罢了。
2.《狂人日记》中的“狂人”
《狂人日记》是《呐喊》的开篇之作。小说以“日记”为载体,讲述了“狂人”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我”从几十年的昏昏沉沉中苏醒过来,决定劝说周围人改掉吃人的习俗。大哥听了“我”的劝告,不但不悔改,反而为“我”扣上一个“疯子”的头衔,想以惩恶扬善为借口顺理成章地吃掉“我”。
鲁迅通过讲述这个略显荒诞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狂人”是那个蒙昧时代的可悲的觉醒者,他因为反对封建统治,并觉察到封建社会以虚伪的“仁义道德”之名,行“吃人”之实的残忍行径,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被冠以“迫害狂”“疯子”之名,受到警诫和迫害。
3.《药》中的“狂人”
鲁迅的《药》以“买药”“吃药”“茶馆谈笑”“上坟”这四幕短剧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革命者与穷苦大众的双重悲剧。小说由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组成,华小栓是明线的主角,夏瑜是暗线的主角。夏瑜作为暗线的主角,却只是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直接的描写。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始终与民众有着一层可悲的障壁。夏瑜在入狱之后劝牢头造反,宣传民主思想,甚至同情殴打他的狱卒,这些行为在民众看来毫无疑问都是“狂人”之举。作者借三位角色之口,连用三句“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发了疯了”“疯了”表现民众的诧异与不解。甚至在夏瑜死后,他的坟仍然与穷人的丛冢隔着一条“自然的界限”[6]。
综上,《沉默之塔》《狂人日记》和《药》中出现的“狂人”形象在出现时间和内涵上具有一定的联系性。森鸥外和鲁迅笔下的“狂人”,看似离经叛道,不守规矩,实际上,他们是时代的先觉者,是沉默、病态的社会的真正“解药”。“狂人”因为产生了新思想,想要走新的路,所以与旧社会格格不入。
三、“狂人”形象的异同
如前所述,《沉默之塔》《狂人日记》和《药》中出现的“狂人”形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作者自身的革命性和战斗性等因素,森鸥外和鲁迅笔下的“狂人”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1.“狂人”形象的共同之处
“狂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可以用沉默和黑暗来概括。
《沉默之塔》的开篇便是一段细致的景物描写。沉默之塔耸立在黄昏的天空里,呈现出单调的灰色,乏力的马拖着沉重的车,晚潮迟钝缓慢地拍打着海岸。整段描写营造出一种死气沉沉、黑暗肃杀的氛围,生动表现出高压政策下社会和思想界的压抑。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药》中对这种沉默与黑暗有着相似的刻画。例如,狂人在怀疑身边的众人吃人时,感到周围的环境“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药》中的华老栓为儿子买药而出门的那个秋夜,“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夏四奶奶在坟地以为夏瑜显灵而哭诉时,周围亦是“死一般寂静”。森鸥外和鲁迅的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象征着黑暗与死亡的残酷画卷,将极度压抑下令人战栗的沉默传递给每一个读者。
两位作家不仅在小说基调上存在相似性,还默契地选择了坟地和乌鸦这两个意象进一步表现“狂人”所处环境的沉默与黑暗。沉默之塔是派希族统治者用来存放死尸、喂食乌鸦的场所,与《药》中的坟地发挥着相似的作用。运进沉默之塔里的马车走了又来,“货色很不少”,《药》中西关外的坟地亦是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塔里装着的是阅读危险书籍、“紊乱社会秩序”或被意外牵连的家伙,坟地里埋着的则是意图谋反、受了死刑的犯人或穷苦百姓。可以说,沉默之塔和坟地象征着禁锢与死亡,表现出反动统治者对“狂人”的残酷镇压和对穷苦大众生命的漠视。接着,两位作家又默契地使用“乌鸦”来打破“坟地”的沉默与寂静。《沉默之塔》中,乌鸦在塔的周围不断翻飞,发出聒噪的叫声,享用尸宴。《药》中的乌鸦则在夏四奶奶希望破灭之后忽然“哑”的一声大叫,张开双翅如箭一般向远处的天空飞去。乌鸦作为一种食腐动物,常与坟地、尸体等相伴出现,在寂静的坟地之中,乌鸦聒噪的叫声为其增添了一丝恐怖诡异的气息。
2.“狂人”形象的不同之处
《沉默之塔》中,“我”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旁观者,客观叙述派希族的内斗,发表对于政府封禁洋书和压制思想行为的主观看法,并未直接参与到反抗和斗争中,做出“狂人”的行为。对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我”同样持一种感兴趣但未必认同的旁观者态度。总的来说,森鸥外笔下的“狂人”是“我”在报纸上间接接触的“狂人”,因此,作为旁观者的“我”和作为反抗者的“狂人”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我”和“狂人”共同追求的是思想和文艺创作上的自由,提倡文艺革新和思想解放,这种反抗和斗争局限于文艺和思想的范畴。
《狂人日记》中,“我”便是“狂人”,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所有事件的亲历者。与《沉默之塔》中的“狂人”相比,《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更具革命性和战斗性,他是亲自参与斗争的革命者,他勇敢地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真相,劝告众人改掉吃人恶习。与森鸥外的“狂人”相比,鲁迅的“狂人”直接挑战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作为剥削工具的封建礼教,他显然触及了社会架构中比文艺和思想更加深刻、更为根本的存在。
再看鲁迅的《药》,无论是小说第一节“古轩亭口”处对夏瑜原型秋瑾的缅怀,还是第四节作者为夏瑜的坟凭空添上一圈红白的花,都可以看出作者对革命烈士的崇敬和认同。夏瑜所反抗的对象也显然超越了文艺和思想的范畴。无论是向狱卒宣传“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还是同情愚昧的民众,都充分体现出夏瑜作为“狂人”从事革命的彻底性,也反映出鲁迅作为启蒙作家推动社会变革的诉求。
综上,森鸥外的“狂人”是文艺界的革新者,他们反对的是政府不合理的思想镇压行为,追求的是思想和文艺创作上的自由,缺乏触碰社会制度的决心和勇气。鲁迅的“狂人”是“铁屋子”里苏醒的革命者,他们反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追求的是彻底的社会变革和个体解放。
3.异同形成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森鸥外和鲁迅由于所处社会背景的相似性和多重身份的重叠,在思想上存在共鸣,这是他们笔下的“狂人”形象存在相似性的主要原因,在此不再赘述。本节主要探讨两位作家笔下的“狂人”形象不同之处的成因。
竹盛天雄曾敏锐地指出:“在森鸥外的精神世界中,政治家的想法、文学者的见识和科学者、历史学者的感触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共存。他作为官僚必须捍卫国家的秩序,作为科学家和文学者又要推进日本的现代化。”[7]因此,这种个人自由与国家秩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森鸥外的文学创作中,使他的创作立场和写作手法呈现出调和与妥协的暧昧。即使是《沉默之塔》这部最具现实批判性的作品,森鸥外借“狂人”表达的也仅限于对思想镇压行为的抗议和对思想解放的呼吁,不会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
鲁迅同样身处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但与日本表面的繁荣不同,中国面临的是极为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自然不会像森鸥外一样对政府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他反抗封建制度的立场也更为坚定。从鲁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虽出生于封建气息浓厚的富裕家庭,但家道中落的过往让他深刻体会到社会的人情冷暖,对国民精神的劣根性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虽然曾经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但如鲁迅自己所言,只是“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区区佥事[8],与政府、官僚没有多少瓜葛,自然不会因为身处“体制”之内寻求妥协与调和。
四、结语
如孙郁所说,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学术研究与创作、翻译活动是互相交织、渗透的,译文中的思想常常会转化到鲁迅同期的文学创作中[9]。森鸥外和鲁迅都是借“狂人”启蒙民众、改良社会。可以合理推断,《沉默之塔》这一篇译文中的思想极有可能以“狂人”的形式转化到了鲁迅同期创作的《狂人日记》和《药》中。
如鲁迅所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4]可以说,鲁迅结合本国的社会背景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彻底揭露旧时代中国的病态社会、唤起民众的觉醒为目的,对森鸥外的“狂人”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创造出了一个更具革命性和战斗性的“狂人”。这也体现出鲁迅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换自己身上的血,将杂质剔除,引来鲜活的存在”的初衷。鲁迅的作品跨越时代与国度的局限,具有普世的价值。他从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获取灵感,又创作出足以反哺世界文坛的优秀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世界性的作家。
参考文献
[1] 魯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説二集」序[M]//魯迅全集·第8巻.東京:学習研究社,1992.
[2] 李冬木.狂人の誕生:明治期の「狂人」言説と魯迅の『狂人日記』[J].佛教大学文学部論集,2019
[3] 李冬木.〈狂人〉の越境の旅:周樹人と〈狂人〉の出会いから彼の「狂人日記」まで[J].佛教大学文学部論集,2021.
[4]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崔琦.从《游戏》到《端午节》——试论鲁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文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3).
[6] 鲁迅.药[M]//鲁迅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竹盛天雄.森鴎外の現代小説:一九一〇年前後の問題(物語と小説の歴史)[J].日本文学,1959,8(9).
[8] 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M]//鲁迅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孙郁.鲁迅的译介意识[C]//北京鲁迅博物馆.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鲁迅博物馆,2006.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钱浩宇,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