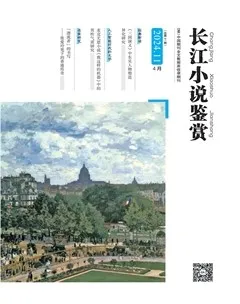姚斯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何去何从?
涂玉 杨小敏
[摘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市场的推动和技术的发展,读者出现了变化。读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向度的精英读者,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式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具有基数大、交互密切、审美倾向更加大众化和通俗化等特点。除此之外,未来人工智能读者也有望成为另一类型的读者。面对读者出现的这些变化,姚斯接受美学理论仍然有其独特之处。通过对姚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核心内容“期待视野”的解读,能够适应当前新的读者群以及阅读环境,更好把握读者的审美需求。总的来说,姚斯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仍有解释力,但也需要与时俱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关键字]接受理论 读者 人工智能时代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79-05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姚斯针对当时文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并发表了《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并与伊瑟尔一起构建起接受理论的框架。接受美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强调读者的中心地位,成为继“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之后的又一文学研究转向。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既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也不是隐藏在文本中,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生成的。读者被赋予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和重要的位置,读者的阅读活动才是作品意义实现的环节,文学的历史应该是接受的历史[1]。因此,接受美学侧重研究读者的阅读效果和反应。姚斯作为接受美学的奠基人,他的理论核心大概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文学史的相关论述;二是他的“期待视野论”;三是针对“审美经验”的相关阐释。在这三部分中,读者作为主体串联起他的全部理论。姚斯的接受美学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我国,经过初期的阐释介绍阶段,作为一种方法论转向文艺、教育、翻译等多领域的运用。
1956年夏,麦卡锡、明斯基等人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成为一门新学科。所谓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研究目的是促使智能机器会听、会看、会说、会思考、会学习、会行动等[2]。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运用到各个领域,文艺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文学艺术这类“主体性”极强的领域,亦有相关研究者研究人工智能与美学、哲学等结合的可能性。目前学术界针对人工智能与美学结合的可能性分为两派:一方面,认为在将来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性突破,如与神经学、心理学、哲学等结合能够赋予人工智能“审美能力”,从而发展出一门人工智能美学。陶峰对人工智能美学作了初步的定义,并且分析了人工智能美学成为现实的可能性[3]。这部分学者认为目前虽不能实现人工智能感性化,但是在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发展出感性思维。另一方面,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仅能够解决一部分文艺问题,但不足以构成威胁。邱月、张颖聪认为人工智能及其艺术并不构成对人文主义美学的革命性颠覆,而只会演化为一种更加深化的人文主义美学版本[4]。这部分学者观点的主要依据在于美学、艺术等有其自身独特的“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其中的精义在于人的“悟”,这部分不是人工智能思维能够模拟实现的。
以上的两种观点笔者不作辨析,但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冲击到了文学艺术领域,如智能体小冰推出了诗集,并且能在诗歌论坛上以假乱真;人工智能谱曲、绘画等在当下已屡见不鲜。人工智能在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正在向文学艺术领域的主体性作尝试。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写作能力和阅读鉴赏能力,也就是说,目前人工智能的写作水平和鉴赏水平已经超越了相当一部分现实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姚斯以读者为主体地位的接受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读者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读者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姚斯的接受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还有阐释效度。本文就以读者的变化为切入点分析姚斯接受美学思想如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二、“读者”改变带来的挑战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读者的定义在之前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或者说,读者的身份变化了,由此引起读者群体范围的变化。传统的读者是精英读者,关于读者的论述在接受美学发展起来之前鲜有人提及,对文学本体论的讨论集中在作者和作品上。但这并不是说读者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处于空白状态,只是传统的读者一直隐匿在作者和文本的背后,并且由于读者概念的模糊,导致读者研究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进入20世纪,人本论思想盛行,人们越来越关注主体的存在,文学研究也有向读者转变的趋势。直到姚斯明确将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读者才从作者和文本的身后走到人们眼前。但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网络发达,人工智能技术也有所突破,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读者已经不是单纯的阅读者,而是消费者,从传统的文学审美体验转为经济领域的购买行为,从精英读者转为一般读者。此为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一大挑战。
读者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处于第二位,作者或文本轮流居第一位,美国批评家罗森布拉特曾将读者比作在舞台黑暗角落中的,没有当过主角的一个角色。一直以来,人们不注意读者的作用,但在以往的批评理论中都有读者的影子。无论是柏拉图所谓的“共和国公民”,还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会受到悲剧的陶冶和怜悯作用的“观众”,还是新古典主义的“阅读大众”等,都显示读者是文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关键要素。谈到读者,必须谈到阐释者,施莱尔马赫作为诠释学之父在阿斯特和沃尔夫的基础上建立了一般诠释学。所谓“阐释”是对文本的理解和说明,是一种人类通过文本达到理解、进行对话的行为,阐释是诠释学探究的基本对象[5]。对文本的理解、说明、对话本身就是阅读过程中的环节,也是作为读者应有的核心素养,只有先成为读者,而后才能阐释。施莱尔马赫将对文本的理解这一任务转移到了读者的身上,是读者特殊的理解赋予作者及作品独特的意义。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进一步将诠释学发扬光大,读者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姚斯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在文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读者终于脱离传统文学研究中的“隐身”状态,聚焦在人们的视野中。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与一般文艺理论中的读者不同,在接受美学中,读者成为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并且读者对文本的具体化是第一性的,强调了读者的能动作用。从“隐身”的读者,到姚斯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都偏向于具有一定创造力和审美鉴赏能力的精英读者,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
但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读者的定义发生改变。随着读者中心论的研究趋势以及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文学领域渐趋商品化,读者这个身份不再囿于传统的精英读者,而是往“消费者”身份转变。也就是读者这个身份本身就面临着“死去”的风险。周志雄等人曾提出“以接受为唯一性的传统读者已经消失,融合体借网而生”这样的观点[6],这是指传统的读者已经转变为融合阅评族、产消者、传受人这三种身份为一体的融合体。早在2006年就有赵毅衡、欧震、刘朝谦、唐小林关于“读者之死”的研讨。刘朝谦认为“读者已死”指一种人类阅读行为的终止,但他对阅读主体和阅读对象做了限定,阅读主体是文学领域内的读者,阅读对象是针对文学经典作品而言,并且对造成文学经典的读者之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7]。欧震则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读者的生存条件,即在消费时代,读者陷入一种意愿不被理解、个性不能体现、不被认同的孤独状态,读者的主体性被市场的力量消解,失去了自我的读者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8]。赵毅衡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本来可能就没活过。职业读者(阐释学主体)的确面临灭种的危机”[9]。诸位学者都已经关注到随着时代的变化,读者不再是传统的读者,取而代之的是消费者,是一般的读者。
如前所述,传统的精英读者被一般的消费读者所取代,这种变化导致传统的读者定义不再能全面涵盖现在的读者范围。读者的范围有所扩大,由原来少部分的精英读者扩大到广大的受众群体,即一般读者。一般读者的特点就在于欣赏文学作品时比较偏向于通俗作品,很少会触及经典作品及其深层意义。并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写作者,一些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低级的作品鉴赏,虽然还达不到像人的思维一样情感丰富,但是人工智能专家们预言未来人工智能与神经算法等跨学科结合有可能突破机器思维,使人工智能向人类思维迈进。也就是说姚斯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着读者身份转变、读者群体范围扩大等问题,甚至还面临着人工智能读者这一可能出现的新事物的挑战。在读者身份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姚斯接受美学理论该何去何从?
三、姚斯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内在生命力
姚斯接受美学思想从诞生到目前为止,仍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当下的读者情况较为复杂,读者与文学创作的环节更加密切,姚斯接受美学思想面临着这些新现象,不禁会使得人们怀疑姚斯接受美学思想对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还有解释力吗?这就需要考察该思想在当今是否还有生命力,而无论是传统纸媒时代的文学作品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作品,未经读者具体化的文本都只是一堆符号而已,不具有意义,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将文本具体化之后才能脱离物质符号成为一部作品。因此,读者确实是整个文学环节中的重要部分,而只要涉及读者,那么期待视野以及审美经验问题就不可避免,这就是姚斯接受美学思想的内在生命力,这也是姚斯接受美学思想在人工智能时代面对新挑战的重要动力。
1.读者的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接受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姚斯将其称之为接受美学的“方法论顶梁柱”。但是期待视野并不是姚斯首创,在他之前,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都使用过这一概念,因此,姚斯并没有对“期待视野”专门作一个定义,而是直接使用这个概念。结合姚斯接受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周宁、金元浦将期待视野理解为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在阅读活动中,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相对的是接受对象,即作品的客观化[10]。期待视野是读者理解文本的重要因素,是沟通作者、作品与读者的重要桥梁,是激发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催化剂。姚斯在讨论如何构建新的文学史时赋予了读者期待视野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构成,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形成,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10]。姚斯在这里提及的读者已经包括了大众,并且肯定了大众读者的能动作用。他在论述重构文学史的第一个论题中提出,文学的连贯性,使一种事件在当代及以后的读者、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野中得到基本的调节,能否按其独特的历史性理解和表现这一文学史取决于期待视野能否对象化[10]。也就是说,姚斯在论述文学史这个问题时,就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不论是当代的读者还是以后的读者,无论是批评家还是大众读者,其期待视野的具体化都是文学史、文学作品存在的基本条件。
期待视野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一个文学作品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产生,同样,一个读者也不可能处于真空的期待视野中,读者总是具有一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就构成读者独特的期待视野。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文学领域中读者身份转变、读者情况复杂、范围大等特点,姚斯用“期待视野”给出了解决方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温斌将姚斯的期待视野作了一个充实的总结。他总结期待视野具有历史性、普遍性、发展性、可知性四个特点[11],这四个特点构建了姚斯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框架。期待视野的四个特点说明了文学发展离不开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具有调节创造作用,反过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读者如何变化,只要读者处于一定的经验生活中,读者就具有期待视野,就能够解释当下出现的文学现象,能够助推文学发展。
2.读者的审美经验
姚斯对审美经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对审美经验的研究是姚斯深化接受理论的一个尝试。在书中,他对审美经验的发展作了探讨,对审美经验的生产与接受以及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等作了翔实的梳理分析。在生产方面,姚斯认为审美经验是人类独有且具有创造性,“随着独立自主的天才美学的被突破,创造性的审美经验就不仅是指一种没有规则和范例的主观自由的生产,或者在已知世界之外去创造出别的世界;它还意味着一种天才的能力,要使人们所熟悉的世界返璞归真,充满意义”[12]。审美经验的创造是自由的,能借助想象创造出“第二世界”,并且生成意义。通过对审美经验生产方面的描述,姚斯肯定了人的创造区别于机器制作,人的创作能超越模仿,能够在历史中获得教训,能够预示未来,获得审美快感。
在审美经验的接受方面,姚斯看到了大众媒介的发展对传统意义上审美经验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下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武瑾说:“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感官反馈总是机械的,作品外观和存在方式由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技术之手所操纵,受众的思想和意识直接进入当下的心理状态,不需要‘虚静,也不用‘妙悟,直接放弃了审美经验的深度感知力。”[13]当代大众的享受态度和批评性的反思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多彩,但视听符号的便利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化的同时,主体的思考也容易流于表面和被“带节奏”。姚斯认为,当下文化工业中的文化产品大多是为了迎合消费者而生产的没有多少实质内涵的商品,而对于经典作品,消费者却又缺乏耐心,视而不见。审美感受的浅显化使得审美经验缺乏一定的深度,这也是读者变为消费者的一大因素。关于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姚斯认为是净化,并将净化界定为“对由演说或者诗歌激起的情感的感受;这种享受在听众或观众身上造成信仰的变化和思想的解放,这个定义假定了通过享受他人的经验,可以产生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自我享受”[12]。审美经验的交流功能将主体从文学感受的封闭性中解脱出来,结合姚斯的期待视野论以及视域融合的方法,以审美经验为媒介,每个主体间可以沟通交流,以此不断挖掘作品的意义,读者亦能重新变为真正的读者。
人工智能时代的读者从传统的“文化贵族”身份变为“文化消费者”,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成本降低,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口基数增大,但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停留在表层,这种审美浅层化意义上的读者被称为文化消费者。面对这种情况,姚斯接受理论中的“期待视野”论和“审美经验”论能够赋予读者“内驱力”,通过自我“期待视野”的改变融合和“审美经验”的交流提高,驱使读者不断深入思考,选择经典作品,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
四、姚斯接受美学理论的未来展望
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尤其是其“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的论述,长久以来在文学与美学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学接受过程的独特视角,也为分析读者行为、期待与审美体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在未来,读者这个概念可能会突破主体限制,一些类似人类的人工智能也有阅读的能力,成为机器读者或者人工智能读者。郭毅可在文章中提到世界经济论坛与多家机构关于“人工智能发展时间表”的若干预测:2028年,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影片;2049年,人工智能写的小说会成为畅销书籍;2059年,人工智能甚至可以自己进行数学研究[14]。虽然这只是初步预测,但是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未来有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感性思维”,那么人工智能成为读者似乎也并不是天方夜谭。在人工智能时代,尽管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读者身份、群体以及审美习惯的变化,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依然显示出了其强大的解释力。
人工智能时代读者身份的转变和群体的扩大,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框架。首先,传统上,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其期待视野受到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影响。然而,在人工智能的介入下,读者的身份逐渐变得模糊和多元。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模拟人类的阅读行为,还可能发展出独特的“期待视野”,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生成独特的阅读期待。这种转变要求我们对“期待视野”进行重新定义和解读,以适应新的读者群体和阅读环境。其次,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出的“感性思维”和“阅读能力”,即未来有可能出现人工智能读者,姚斯的“审美经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这种变化的方法,帮助我们分析人工智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偏好,从而指导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在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人工智能读者可能会拥有更加深入和独特的阅读体验。这就需要对姚斯接受美学理论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发展,以适应新的阅读环境和读者需求。
综上所述,姚斯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学者需要对理论进行不断的更新和发展。通过重新解读“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等核心概念,并关注读者及人工智能读者的发展动态,使姚斯接受美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生命力和解释力。
参考文献
[1] 任卫东.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J].外国文学,2022(4).
[2] 谭铁牛.人工智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J].智慧中国,2019(Z1).
[3] 陶锋.人工智能美学如何可能[J].文艺争鸣,2018(5).
[4] 邱月,张颖聪.人工智能艺术的美学审视:基于人文主义美学的视角[J].江海学刊,2019(6).
[5]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 周志雄,江秀廷.“阅评族”“产消者”“传受人”——数字媒介时代读者的身份叠合与融合体的生成[J].社会科学战线,2022(11).
[7] 刘朝谦.“读者已死”所指为何?[J].当代文坛,2006(6).
[8] 欧震.读者之死[J].当代文坛,2006(6).
[9] 赵毅衡.“死者”身份的几点考核[J].当代文坛,2006(6).
[10] 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1] 温斌.试论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阴山学刊,1993(3).
[12] 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顾建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3] 武瑾.沉浸式体验:被数字时代重塑的审美经验[J].美与时代(上),2023(12).
[14] 郭毅可.论人工智能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战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3).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涂 玉,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杨小敏,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