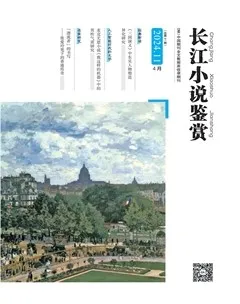物叙事:《觉醒》的新物质主义解读 □ 方传杰
[摘要]凯特·肖邦在小说《觉醒》中重新审视了人与物的关系,强调物的叙事能力和施为能力。作者在描写人与物的互动中,借助物品建构人物身份,明确叙事节奏,使得小说结构更为复杂。小说考察了物的意义生成过程,指出物的意义是复杂的、流动的和模糊的。此外,作为文本对象的物试图重新建构文本秩序,呼唤物的在场,体现了作者对物的反思。
[关键词] 凯特·肖邦 《觉醒》 新物质主义 物叙事 物转向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67-04
受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审视自身与物的复杂关系,而“物转向”(turn to things)促使人们思考物的存在并重新确立人与周围物质世界的关系。与之相关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途径,帮助探索物的存在及其价值。新物质主义质疑能动性的界限,指出所有物质都具有能动性,甚至物质性在本质上就是能动性,认为物质具有创造力,进而强调主体与客体对话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换言之,物质可以不断地实体化,这一过程是在物质的内部相互作用(intra-action)下形成的,而不是此前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如此,新物质主义摆脱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限制,物质不再是被动的存在,从而成为一个“处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过程”[1]。质言之,物质意义生成视角下的物质间性关系是一种趋于固定却永不固定的过程,物质不再是被动的、静止的存在,而是主动的、运动的生成。
后现代主义默许语言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肯定语言与文化对社会的规范作用的同时,忽视了物质世界的能动性。受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及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语言、话语和文化等概念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物转向”的确立直接源于对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尽管新物质主义认为任何语言都无法严格定义物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语言学转向,不再关注语言的存在,而是强调如果不关注物质在语言中的作用,不重视物质通过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以及物质超越语言的力量,那么“纯粹对语言的语言学分析是无用的”[2]。进一步而言,语言在解释现实世界时,永远无法脱离物质世界的存在。基于物质生成意义的观点,物质是文本阐释的重点,甚至物质本身就是具有叙事能力的文本。就此而言,内拉特(Frédéric Neyrat)与布朗(Bill Brown)都认为新物质主义批评的审美对象“既可以是文学再现的物、文学指向的物,也可以是作为物的文学”[3]。那么,新物质主义批评的任务便是通过分析小说文本中物质的施事能力及其意义生成过程,考察物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物的行动与情感,如何推动情节发展,表现小说主题,甚至参与到小说的美学建构。
一、参与人物建构的物
新物质主义指出文学批评应该更多地关注到物的情感功能以及物的意义生成能力,认为物通过塑造或重塑人,显现出物质自身的主体性,人的习惯可以“使物质世界里无生命的物具有生命”[4]。小说一开头就描写了庞德烈先生(人物译名参考齐彦婧译本,个别人名略有改动)坐在自己别墅门前的柳条藤椅上看报纸。而当庞德烈先生从酒店回家时,庞德烈太太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应他的话语,庞德烈先生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庞德烈太太并不关心他在意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责备妻子对孩子不够照顾。面对丈夫的指责,庞德烈太太十分难过,走到走廊上,坐在“那张柳条摇椅上前后摇着”[5],她开始哭泣,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泣。庞德烈太太在结婚后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庞德烈先生对她总是那么亲切,对家庭也总是那么全心全意。但现在,庞德烈太太坐在藤椅上,陷入一种难以压抑的痛苦之中,这是一种陌生的情绪,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她只能坐在藤椅上,这时,藤椅成为她情绪的某种具象化存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藤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互动体现了人物情感的流动,而这种互动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不是单一地从人物流向物品。物品在接收到人物情感的同时,也会在某些时刻传递出情感,如此,物品不再是主体的对象而是变成某种主体性存在。
新物质主义批评选择从文学文本中具体的物入手,研究物如何反映或象征人物的社会身份进而影响其行动。为此,布朗关注到文本中物质文化的表层书写,明确了日常物质在文学文本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对文本的任何阐释都需要考虑文本与读者的社会语境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从而展现出一种与文化相关的“物质性”(materiality)。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物质书写并不是为了表现小说主题或者故事情节,而是揭示出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和变化。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及庞德烈先生抽雪茄和罗伯特抽烟的场景。在小说开头,罗伯特说他“抽纸烟是因为抽不起雪茄”[5],所以他想留着庞德烈先生曾经递给他的雪茄烟,“等吃过饭后再抽”[5]。这样的行为对于罗伯特来说“显得极为恰如其分而又自然而然”[5]。这时罗伯特的经济水平显然是不如庞德烈先生的,而罗伯特自然地接受其他人的雪茄,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无法支撑起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实际上是在暗示庞德烈太太无法独自生活,只能接受丈夫的帮助。而等罗伯特再次回来时,他已经能够负担起雪茄,他的经济状况已经改善。与此同时,庞德烈太太也搬了出来,远离自己的丈夫。随身物品使用情况的转变暗示着人物身份、经济状况的转变,同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介入小说叙事的物
新物质主义批评质疑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商品的论述,指出这一论述既忽视了商品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未能关注到物质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提到“物的时代”[6],认为商品的符号化表明物质消费不仅仅是物质需要的满足,更多的是价值意义上的满足。换言之,物超越其使用价值,转变成具有指称意义的符号,从而脱离商品交换体系,进入文化物质体系。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物质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跨学科性,进而影响文学批评,使其关注文学作品中物的存在,致力于解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并用以描述作为能指符号的物的复杂性。
在小说最开始,埃德娜在和罗伯特游泳回来之后,并没有立刻回到房间。尽管庞德烈先生坚持让埃德娜进去,埃德娜还是拒绝了庞德烈先生的请求。如果是往常,庞德烈太太会按照庞德烈先生的话行动,她会习惯性地服从他的意志,这不是因为埃德娜“屈从他的意愿”[5],而是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当埃德娜再一次拒绝庞德烈先生的请求时,原本已经打算睡觉的庞德烈先生“开了瓶葡萄酒”[5]。他喝了一杯酒后,走到外面也给了埃德娜一杯,但她拒绝了。于是,庞德烈先生在抽了雪茄之后,走进房间又“喝了杯酒”[5]。之后,他再一次给她倒了杯酒,但埃德娜“还是不想喝”[5]。埃德娜通过两次拒绝庞德烈先生的酒,表达了自己反抗庞德烈先生的意愿与抵抗日常生活习惯的努力。尽管埃德娜最后选择走进房间,但她之前的努力是极为重要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埃德娜与庞德烈先生关系的转变,而这里的酒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但这一意义指向是不稳定的。埃德娜的父亲拜访时,庞德烈先生曾与上校爆发了一场冲突,而埃德娜则选择坚决维护上校。但等到晚餐的时候,红酒温热,香槟透凉,这缓和了原本紧张的气氛,“那原本的不愉快也随着酒的泡沫消融而去了”[5]。酒在这里并未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反倒缓和了原本的紧张氛围。如此,酒摆脱了原本的商品属性,将自身的工具属性让渡到其本来的在场性,凸显了自身作为能指符号的复杂性,即物的意义及作用会随着叙事的进行而不断改变,这一点在文本对糖果的多次提及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庞德烈先生出门去酒店时,孩子们希望跟着父亲一起出门,但是庞德烈先生拒绝了他们并答应“带糖果和花生回来给他们”[5]。然而,等庞德烈先生回来时,他“早把买糖果花生给孩子们吃的事给忘了”[5]。尽管如此,庞德烈先生“还是非常地疼爱他们”[5]。然而,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依旧依靠物品的传递而传达。等庞德烈先生乘坐轻便马车到码头坐汽船回到城里工作后,没过多久,埃德娜就收到了庞德烈先生从新奥尔良寄来的盒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甜美可口的食物,以及“许许多多的糖果”[5]。埃德娜在外度假时常常收到这样的礼物,而她总是慷慨地与大家分享。她把水果和其他东西都放到餐厅,而糖果则分给其他人。其他人则一面不客气地挑挑拣拣,一面称赞庞德烈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对此,庞德烈太太“迫于无奈也只得承认她丈夫是最棒的”[5]。这里,糖果并不是情感表达的媒介,反而是一种意愿的传递方式,埃德娜不得不屈从于庞德烈先生的意愿。并且这种行为已经成为某种习惯性动作,她并没有反抗的意识。或者说,即使她有反抗的意识,却也不得不受到既有习惯的制约。之后,埃德娜卖了不少自己的画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收入。于是,埃德娜选择拜访雷兹的公寓,并告诉她自己打算搬出去。这时,埃德娜“已下定决心再不附属于他人,她只属于自己”[5]。当埃德娜从雷兹家出来后,她在糖果商店停了下来,给孩子们“订了一盒糖果”[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糖果已经不再是束缚埃德娜的手段,反而成为埃德娜反抗庞德烈先生的证明。
三、物的缺席与在场
布朗以物的实在性为前提,认为真实的物存在于语言和文化的表征之外,研究物是如何从语言和文化的再现中溢出,从而显现其独立而实在的“物性”(thingness/materiality)。布朗对客体(object)与物(thing)进行了区分,指出客体受主体束缚并服从于主体的意图,“主体物化客体”[7]。但物则不同,布朗认为只有当物不再发挥其功用时,人们才开始面对它的物性,甚至“物体仅仅存在于缺席之中”[4]。就此而言,布朗并不赞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有关主客体关系的论述,强调只有当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中断的时候,人们才会认识到物作为工具之外,其本身也是一个独立存在,即察觉并重视物的本体性。受到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影响,布朗指出主客体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分,是人为的区分,是现代性的努力。现代派文学过于强调物的外在,往往需要借助物的象征与隐喻来表达意义,并没有真正关注到物的内在性,也就是说,只关注到物的意义而忽视了物的内在意义。实际上,新物质主义希望加以阐释的则是“物内在意义的意义”(idea of ideas in things)。此外,受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物的性质如何为人类的存在提供稳定而恒久的感觉等研究的启发,布朗认为通过同样的物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物处于同样的位置或许可以创造出一种连续统一的感觉,用以帮助克服生活结构无序和现实的复杂变化。但布朗同时指出,习惯的打破包括原有模式的改变以及物的误用也可能唤起对于物的“纯粹物质性”(brute physicality)的关注。
在小说中,当上校和庞德烈先生先后离开,就连孩子也被接走时,家里就只有埃德娜一个人。然而,独自一个人时,埃德娜体会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平静,“一种不熟悉但美好的感觉向她袭来”[5]。她开始检查整栋房子,走遍每一个房间,“仿佛她以前从未见识过一样”[5]。埃德娜独自用餐,她感到无比舒服。之后,她走进书房,看起书来,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书了,于是决定多读点书,因为“现在她的时间完全可以凭她爱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了”[5]。然后,埃德娜洗澡,休息,“一种从未有过的安逸感向她袭来”[5]。随着丈夫的出门,家中原有的秩序被打破,物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埃德娜进而意识到周围物质环境中各种各样的物品的存在,而在与物的互动之中,埃德娜重新注意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这时,人物的缺席凸显了物品的在场,而物品的在场又进一步凸显人物的存在,人物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与存在。
四、结语
真实的物是无限撤回(withdrawn)的,物与物的本质之间存在着张力,真正的物“总是不断从人们对物的认知意图中撤回”[8]。可以看到,文学物(literary object)与作者试图表达的物的本质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作者间接而非直接地呈现出文学物的本质。进一步而言,语言虽然具有充满悖论的“无物质的物质性”(materiality without matter)的特点,但是在造成其自身与物质分离的同时,语言本身也是物质的、具体的。也就是说,尽管新物质主义源于对“语言学转向”主导下语言冗余(language excess)的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语言的忽视,而是希望可以重新关注到语言的物质性以及作为物质的语言所具有的力量。
从新物质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学文本的物质性持续不断地塑造着人们的情感、性格乃至身份意识。《觉醒》中物的出现不仅仅成为人物情感表达传递的媒介,同时也在反映甚至影响着人物主体身份的特征及其转变。埃德娜自我意识的不断转变不仅仅体现在其行动上,更体现在她与周围物质环境的不断互动上。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物的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具有流动性和多重性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物的意义指向是不一致的,甚至物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物的存在本身不仅仅只是作为文本对象出现,而是参与到文本组织架构乃至小说审美建构中去,实现了从文本指向的物到作为文本的物的转变,从而折射出作者对物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Durham:Duke UP,2007.
[2] Frédéric Neyrat.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M].London:Routledge, 2020.
[3] 陈海容.新物质主义“新”在何处——评《文学与唯物主义》[J].外国文学, 2022(1).
[4] Bill Brown.A Sense of Things: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M].Chicago:U of Chicago P,2003.
[5] 肖邦.凯特·肖邦作品选[M].岳峰,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
[6]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 韩启群.布朗新物质主义批评话语研究[J].外国文学,2019(6).
[8] Graham Harman.The Well-Wrought Broken Hammer:Object-Oriented Literary Criticism[J].New Literary History,2012(2).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方传杰,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