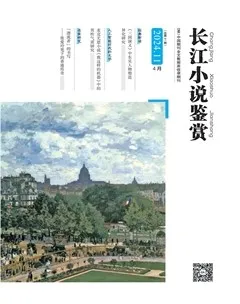《云影·古堡·湖光》中纳博科夫的飞散意识
[摘要]纳博科夫是20世纪最重要的俄裔美国作家。《云影·古堡·湖光》写于1937年,其语言艺术与飞散意识备受评论界关注。本文试图从弗洛伊德暗恐理论的角度解读《云影·古堡·湖光》中纳博科夫的飞散意识。小说展现了主人公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非家幻觉的原因、症状、治愈,以及最后的精神崩溃。在这一过程中,瓦西里作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俄国士兵的复影,一系列俄国田园风景被建构为衔接空间。纳博科夫从瓦西里的个人危机介入对俄裔飞散群体的集体创伤的思考,描述他们所患有的集体病症,即因被迫远离家园而形成的暗恐心理。通过暗恐式书写,纳博科夫展现了俄裔飞散群体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境,传达了他作为俄裔飞散作家因非家幻觉而无法抵御的失落感与文化焦虑。
[关键词] 纳博科夫 飞散意识 暗恐 复影 衔接空间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11-0063-04
一、引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是20世纪最重要的俄裔美国作家,在俄罗斯文学和美国文学中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云影·古堡·湖光》写于1937年,是纳博科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年轻的代理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从柏林到俄国的火车之旅。在1936年或1937年,瓦西里在俄国流亡人士举办的慈善舞会上意外获得一张旅游券。尽管他试图通过多种手段退掉这张突如其来的邀请函,结果都不尽人意。无奈之下,瓦西里只好踏上这辆从柏林开往俄国的列车。《云影·古堡·湖光》自发表后广受学界关注,国内外批评界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多从不同维度分析小说中的艺术特色和微观主题。然而,目前鲜有论文从心理分析视角出发探讨这位俄裔飞散作家的创作意图。本文试图借助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分析暗恐/非家幻觉,即压抑复现在主人公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身上的体现,探究瓦西里暗恐心理的成因、症状、治愈,及最后的精神崩溃,并解析纳博科夫暗恐书写背后的飞散意识。
二、瓦西里的压抑复现
在《云影·古堡·湖光》中,纳博科夫以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俄裔飞散者形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是一名飞散在柏林的俄国年轻人,一日在俄国流亡人士举办的慈善舞会上偶然中了一张旅游券。从瓦西里收到这张从柏林到俄国的旅游券开始,战死的俄国士兵作为瓦西里被压抑的恐惧的象征,在瓦西里的生活中多次复现,揭示了其暗恐的原因和症状。
首先,瓦西里的暗恐来源于他对死亡和远离家园的恐惧。弗洛伊德指出:“暗恐是一种恐惧情绪,源于很久以前就认识和熟悉的事物。”[1]在小说中,瓦西里在旅途中不自觉地将当前陌生的俄国与记忆中所熟悉的故乡进行比较。暗恐就建构在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家与非家的二律背反中[2]。每到一个车站,瓦西里总会观察一些毫无意义的小东西,辨认其外观特征。瓦西里的视线聚焦在等车的小孩子中,他竭尽全力去寻找一些非同寻常的命运轨迹。透过这些孩子们,他仿佛看到了一张旧照片。在照片右排最后,一个男孩子的脸上被打了个小白叉,并写着 “一个英雄的童年” [3]。在这里,小说使用了暗恐式的复现。瓦西里突如其来的看似陌生的惊恐经验,实质可以追溯到他心理历程上的某个源头,也就是当他听到这位俄国士兵死讯时的负面情绪,确切地说是瓦西里自己对于被迫离开家园和死亡的恐惧。在这个意义上,在战争中牺牲的俄国同学成为瓦西里内心恐惧的隐喻,进入瓦西里的无意识,成为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当瓦西里在陌生的孩子们身上寻找熟悉的踪迹时,他曾忘却的、压抑在无意识中的恐惧开始在意识中重复。
其次,瓦西里的暗恐心理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被唤醒的。瓦西里多次复现俄国士兵的经历,这种重复的冲动来源于他看似已经忘却的创伤记忆。弗洛伊德将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遗忘的那些印象命名为创伤[4]。瓦西里所受的巨大创伤已在他心中形成心理历史,被压抑的事情并未真正忘却,而是在忘记状态下的记忆留存。在故事伊始,瓦西里与俄国士兵经历了相似的事件,都是被迫登上列车离开家园前往俄德边境。士兵无法摆脱被征召入伍的命运,背井离乡参加战争。而瓦西里想尽办法也无法取消这张开往俄国的旅行票,正如瓦西里心中所念,这趟旅行是命运女神强塞给他的[3]。在这一移置的时刻,当瓦西里察觉到记忆中俄国士兵的踪迹时,无意识中的压抑在相似的情景下被唤醒,以不自觉的方式复现,即瓦西里被迫离开柏林的经历复现了记忆中俄国士兵的遭遇。因此,当他登上开往俄国的列车时,一股荒唐感和恐怖感开始在心中暗暗萦绕。
再次,在故事的开头,瓦西里曾试图通过家的踪迹压抑自己的非家幻觉。瓦西里在无意识中将这次旅行与曾给他带来幸福、象征着俄国故乡的各种形象联系在一起,他沉思这场旅行是否能给他带来快乐。这种快乐的源头类似于“他的童年”“俄国抒情诗”“梦中傍晚的天际线”,抑或“他暗恋了七年的那位女士”。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位女士已然成为他人生奋斗的目标[3]。在小说中,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可以解读为俄罗斯的象征,即远方的家园。这是作为在德国的俄国难民无法接近的实际的地缘所在,也是瓦西里心中所向往的舒适美好的想象空间。
最后,战死的俄国士兵作为被压抑的恐惧的象征,在瓦西里的生活中并非以原有形式复现,而是以其他的、非家的方式复现家的某些痕迹。瓦西里的暗恐具有再创造的特点。火车上同旅的8个德国人本来同瓦西里的过去无关,但是由于“恐惧”这个母题,瓦西里在从柏林开往俄国的火车上所遭受的苦难,成为俄国士兵在俄德战场上经历的复现。在这个意义上,瓦西里成为照片中牺牲的俄国士兵的复影,同行的8个德国人则是战场上德国士兵的复影。瓦西里将压抑的关于俄国士兵的记忆,在无意识间不自觉地演了出来。此外,弗洛伊德强调复影在压抑复现过程中的暗恐作用[1]。小说中,瓦西里连续不断出现的惊恐情绪表明瓦西里作为受害者被创伤的经历反复折磨,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和性格塑造。因此,以另一种形式亲身经历士兵的人生后,瓦西里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他再也无法控制这股反复出现的恐怖情绪。
三、非家的俄国田园风景
纳博科夫采用飞散的视角,抛弃二元对立,将俄国田园风景作为衔接空间。小说中的田园风景应被视为俄国的缩影,它既是超越时空的衔接空间,也是治愈瓦西里暗恐的心理空间。小说通过虚构的风景揭示了纳博科夫作为精神流亡者的非家幻觉。
根据霍米巴巴所言,“衔接空间”是一个“移动的瞬间”,它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接纳着古往今来的各种复杂意象,从而营造出一种家与非家之间的暧昧感[5]。在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中,风景的想象无异于衔接空间的建构[6]。《云影·古堡·湖光》通过巴巴意义上的衔接空间并列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当下经历的,一个是记忆中经历的,两者奇妙交融。根据弗洛伊德所说,当想象和现实的界限消失,恐怖情绪应运而生[1]。当瓦西里进入田园风景中时,记忆与现实相重叠,熟悉与不熟悉相并列,家与非家相关联。随着隐蔽的、私密的记忆暴露出来,瓦西里的非家幻觉油然而生。
在小说中,衔接空间也被建构为治愈瓦西里暗恐的心理空间。火车沿途的俄国田园风景形成了一系列的衔接空间。火车之旅伊始,当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恐惧感袭上心头,瓦西里立即说服自己从飞驰的火车窗口欣赏沿途的风景。花草覆盖的河岸、树林、峡谷和云朵治愈了他的心灵[3]。在这片由云影、城堡、湖光构成的俄国田园风景中,湖边小旅馆里隐约像是俄国老兵的店主成为死去的俄国士兵的复影。俄国老兵与瓦西里在衔接空间的共存,让瓦西里陷入一种幻想,幻想自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俄国同学的身边。虽然衔接空间只是关于当下的,但只有在这个转瞬即逝的时刻,瓦西里接近理想家园的迫切愿望才能得以实现。瓦西里告诉他的同伴,他宁愿将来留在这里,也不愿回到柏林[3]。
俄国田园风景建构的衔接空间将瓦西里与俄国士兵、陌生与熟悉、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从而将压抑的恐惧逆转回意识中。因此,离开衔接空间的痛苦放大了瓦西里的不安全感,当他被迫远离田园风景,回程中被同行的德国旅客毒打,他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虚构的俄国田园风景背后承载的也是作者纳博科夫隐秘的非家幻觉。这个由陌生元素虚构的异乡实质建立在记忆中所熟悉的故乡之上。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家与非家相辅相依,故土成了纳博科夫心中难以释怀的束缚[6],同时田园风景成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俄罗斯文化的记忆之场。对纳博科夫这样的现代飞散作家来说,家园不仅是自己离开的地缘空间,也是在跨民族关联中为自己定位,为政治反抗,为建构文化身份而依属的心理空间。在小说中,纳博科夫以建构俄国田园风景式的衔接空间,给予俄裔飞散群体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故事结尾,当瓦西里被驱逐出连接家与非家的衔接空间时,他无法再次接近理想化的家园,也难以在未来的柏林生存下去。
四、纳博科夫暗恐式书写背后的飞散意识
在《云影·古堡·湖光》中,纳博科夫以居住在德国的俄国侨民生活为题材,通过瓦西里的个人危机将小说文本同俄裔飞散群体的历史相关联。纳博科夫通过在放逐中对俄罗斯和欧洲的再造,展现了他文学创作中独特的飞散特性[7]。小说描写了瓦西里暗恐的成因、症状、治愈,及最后的精神崩溃,展现了纳博科夫作为俄裔飞散作家,因与家园隔绝引起的无法抵御的失落感。同时,在小说中,通过展现德国主流文化对俄裔飞散群体文化的冲击,纳博科夫批判了隐含着同化概念的国家意识,表达了自己作为俄裔飞散作家的文化焦虑。
纳博科夫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从揭露瓦西里所代表的个体的危机进入对俄裔飞散群体和文化的思考。在小说中,主人公瓦西里与“我”互为复影。弗洛伊德认为,互为复影的两者拥有“心灵感应”,共享知识、情感和经验,进而产生身份认同,从而将异质的自我代替真正的自我[1]。在小说中,暗恐的心理过程在瓦西里和“我”之间转移,类似的境遇和命运也在当中出现。瓦西里和叙述者的身份相同,都是生活在德国柏林的俄国侨民,压抑着远离家园的惊恐情绪,将云、堡、湖组成的俄国田园风景作为治愈主体暗恐心理的衔接空间。“我”和瓦西里之间复影关系的实质是自我主体中的自我与他者,小说中表达意义的创伤并非直接作用于“我”,而是来自作为他者的瓦西里。瓦西里的声音作为他者的声音代表着自我主体中的他者,这种他者通过心灵感应拥有自我主体创伤的记忆[8]。在这个意义上,瓦西里与纳博科夫互为复影,小说的暗恐式书写承载着作者本人的飞散意识。纳博科夫通过隐喻的形式将自己本人的流亡经历植入他流亡生活早期的文学虚构中,形成他对创伤的记忆和情感表述[9]。在小说中,瓦西里念念不忘的那位女士与瓦西里的关系也折射出作者本人与俄罗斯故土之间的关系。正如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中所言:“我第一次自觉的返回……不是绝不会发生的庄严的还乡,而是在我长年的流亡中它永不终止的梦。”[10]想象的家园概念在此涵盖的不仅是客观所在,更多的是纳博科夫对历史和创伤记忆的隐喻,而这张去往俄国的旅行票正是承载纳博科夫创伤记忆的变体。
纳博科夫的暗恐美学不局限于个人心理层面,它能够指向更大的范畴。恐惧不安元素一旦出现,就会形成心理历史。这种元素既存在于个人,也存在于文化[2]。小说使用暗恐的叙述方法,个体的负面情绪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通过回溯历史,纳博科夫揭露了俄国侨民的创伤经历,指出瓦西里所患有的暗恐心理是一种集体病症。作为俄裔飞散作家,纳博科夫责无旁贷去描写俄裔飞散群体的流亡现实,延续他们被切断的历史,从而延续他们共同体的生活[11]。在小说中,纳博科夫通过揭露个人的、私密的惊恐经验,指向历史和文化的危机与冲突。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显然是反对集体暴力。在整个旅程中,瓦西里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集体暴力。纳博科夫批判以群体规范来衡量个体价值的集体暴力给人们带来的创伤[12]。同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集体暴力则表现为德国主流文化与俄裔飞散群体的边缘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纳博科夫采用飞散视角,客观地观察生活在文化移位状态的俄裔飞散群体。瓦西里精神上受到的暴力正是源于文化差异,这体现在饮食、文学、娱乐方式等众多方面。瓦西里在旅途中不断被要求抛弃俄国传统,接受德国流行的享乐方式。纳博科夫试图从飞散视角挑战某些以同化意识为目的的国家文化界限,小说揭露了侨民文化不断被主流文化改变和同化的现实,传达了纳博科夫作为俄裔飞散作家的文化焦虑。
五、结语
纳博科夫作品中展现的精妙的语言技巧和飞散意识一直以来广受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在《云影·古堡·湖光》中,纳博科夫将本人的流亡经历以一种隐喻的形式置于文学虚构中,形成了他对创伤的记忆和情感表述。小说系统展现了瓦西里暗恐的原因、症状、治愈,及最后的精神崩溃,其中瓦西里作为在战争中死去的俄国士兵的复影,一系列俄国田园风景被建构为衔接空间。小说从人类社会的心理机制出发,解读了以瓦西里为代表的俄裔飞散群体的创伤经历,描述了他们所患有的集体病症,即因被迫远离家园而形成的暗恐心理。纳博科夫通过暗恐书写,描述了俄裔飞散群体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境,传达了他作为俄裔飞散作家因非家幻觉而无法抵御的失落感与文化焦虑。
参考文献
[1] Freud S.The Uncanny[A]//David H.Richter.The Critical Tradition:Classical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C].Boston:Bedford/St.Martins,2007.
[2] 童明.暗恐/非家幻觉[J].外国文学,2011(4).
[3] Nabokov V.Could,Castle,Lake[A]//Dmitri Nabokov.The Stories of Vladimir Nabokov[C].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
[4]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11:图腾与禁忌[M].邵迎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5] 何畅.“非家”的风景——纳博科夫笔下的风景想象[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6).
[6] 吴迪等.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第八卷)当代卷(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7] 童明.飞散[A]//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8] 王卉.创伤小说的伦理意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9] 韩悦.创伤与文化记忆:纳博科夫早期流亡小说的俄罗斯主题书写[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5).
[10] 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陈东飙,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11] 纳博科夫.菲亚尔塔的春天[M].石枕川,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12] Assa P F.Nabokov the Psychologist[J].Nabokov Studies,2017(1).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何韶婷,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