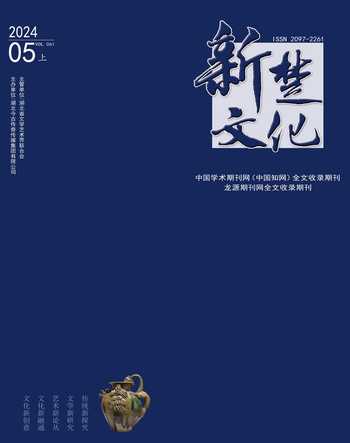论加缪《戒严》中的共同体思想
【摘要】加缪在戏剧《戒严》中,将共同体思想作为其反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并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以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为背景,阐述了在暴力面前,封建政治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的脆弱和崩解;其次,加缪揭示了极权主义的逻辑和荒诞本质;最后,通过对爱与自由的论述,证明了借此所激发勇气和责任,并由此进行的群体反抗是面对荒诞世界的解决路径,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实现抵抗,从而为我们理解加缪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关键词】《戒严》;荒诞;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565.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4)13-0029-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3.009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论加缪作品中的瘟疫书写”(项目编号:YCX23052)的阶段性成果。
加缪的戏剧《戒严》因为与《鼠疫》描写的故事背景相似,情节大体一致,故而常常被看成是《鼠疫》的续篇或注脚。但加缪再三申明,“《戒严》根本不是根据我的小说《鼠疫》改编的剧本”,并且“我始终认为,《戒严》也许是我的作品中最像我的一部”[1]758。戏剧《戒严》讲述的是一位经历了觉醒的年轻人狄埃戈带领市民反抗“瘟神”,最后牺牲自己,拯救爱人的故事。故事延续了加缪一贯的风格,将“荒诞”和“反抗”的命题记入时代的预言中。“戒严”是瘟神统治城市之后宣布的“政令”,它代表着城市原本秩序的破碎、荒诞的填充和匮乏的蔓延。随之而来的极权主义统治加速了对人的消耗和对世界的破坏,剧中对爱与自由的讨论彰显了“向死而生”的反抗姿态。狄埃戈对维克多丽雅的爱拯救了他,他对人民的爱与人民对自由的渴求结合在一起拯救了所有人。这种存在主义式的激情饱含着个人与集体的互动关系,既表现出个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又表现出集体对个人的塑造,主体和集体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相互依存性,从而形成了一种责任共同体。
一、两种共同体的崩解
“戒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和生存境况,能够迟滞时间的流动,维持空间的不变,放大紧张、恐惧、焦虑、无助、厌恶的感觉,以一种理性到冷酷的技术手段来观察人的变化。剧中早已暗示出戒严之前早已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治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封建共同体的崩解体现在三个方面:统治者对人民的愚弄、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和最高长官的出卖。
首先,在疫病肆虐城市之际,剧中描写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场景:首席治安法官表面上声称“好的政府就是不出任何事情的政府”,背地里却在和众人商量如何掩饰当前局面,还十分庆幸重病只在贫民街区出现,俨然将人民当成了灾难的“隔离墙”。
其次,面对来势汹汹的疫病,行政长官仍在考虑不要误了出门打猎的行程,为的是让全城人了解:即使在逆境中,他的神态能显得平静安适;法官告诫妻子不要在乎别人,就算是自己的女儿,同时要学会囤积居奇。
再次,行政长官为了保命,以保护人民为由与瘟神签订了契约,彻底抛弃了人民。总体而言,封建共同体的解体早有端倪的。卢梭认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是:“假使一切情况都相同……而在它的统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得最多的,就确切无疑的是最好的政府。”[2]83而该统治者的行为恰好与其背道而驰。同时,即使是封建的政治共同体,其核心仍旧是立法权和行政权。“行政权是国家的心脏,立法权是国家的大脑”[2]86,失去大脑和心脏,没有谁能安然无恙。况且洛克也早有预言,握有最高执行权的人放弃职责会导致政治共同体的解体,统治者的背叛是压垮封建共同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世界有“世俗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的区分,前者统摄于后者之中,信仰的“失灵”或“崩塌”对西方人造成的毁坏不亚于政治性的死亡。占星术士一边哄骗人们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边借着人们的恐慌大肆敛财。就连以慈悲为怀、以拯救为责的神父在危难之时也选择逃走,留下了不知所措的穷人和农民,将他们随意扔在荒诞和虚无之中,承诺中的应许之地并未向他们敞开。加缪被认为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哲学上的自杀,信仰是一种“跳跃”,是毫无缘由地对世界作出解释。非理性借由至高无上者来否定人的理性,从而使得荒诞成了“智力的牺牲”。而“荒诞是人有意识的一种形而上的状态,不会指引人走向上帝”[1]50。他将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如此冒险而又大胆地讲出来,为的就是抗议信仰共同体对荒诞的驱逐,所以也就理解了莫尔索为何拒绝神父的救赎。两种共同体的崩解革除了人的双重身份,两种“管人心”的力量并未发挥作用,反而进一步把民众推进了深渊。
二、疾病——极权主义的深层隐喻
在《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中,加缪强调由于纳粹造成了“四分五裂的欧洲”,而“我们从未忘记过一个思想和一种希望,它永远和我们同在,那就是一个欧洲的思想和希望”[3]16。所谓的“一个欧洲”并不是法西斯在地图上勾画出来的布满彩点的欧洲,它在根本上无法使得人们聚合在一起,不会让人感到振奋。而加缪所倡导的“一个欧洲”是一种基于智慧和勇气的传统,承载着所有人民心灵深处呼声的欧洲,是“将继续进行下去的、共同的冒险活动”。但如果因此就仅仅将这部剧作看成是《鼠疫》的补充,或将瘟疫看作是法西斯的统治这样的表层隐喻,这样并不足以理解加缪政治立场。《戒严》和《鼠疫》的根本区别在于,《鼠疫》交代了纳粹统治的事实,而《戒严》揭橥了纳粹极权统治与现代性的关系。
首先,瘟神的统治是要所有人都按照同样的死法,并且严格按照名单的顺序。他将其称之为“沉默的、秩序的、绝对公正的逻辑”;分批将所有人进行放逐或者关押进集中营里,要使得清白的人向有罪的方面转化;教给民众口号,“直到他们能自动地没完没了地重复同一件事,直到他们终于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好公民”[1]161。阿甘本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主体是人的身体,也就是说通过控制人的身体来实施政令。在此处,身体并非成为自由的载体,而是被宰治的象征,被控制的人进入“例外状态”。“例外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戒严”状态,是一种打破稳定,现有法律无所适从,因而对国家现存法律进行悬置的状态。在阿甘本看来,现代最典型的例外状态便是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西方政府以政治决断取代法律,俨然已经成为惯用的手段。
其次,这其实是一种生命政治化的管理技术,其最大优点便在于管理。福柯发现,自古典时期人们就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4]146,属于技术—政治领域。其中心观念在于人的“驯顺性”,这代表着不仅肉体是可以驯服的,同样也是一部政治机器,借助严明的纪律完整掌握住这个庞大的机器。所以女秘书手中的“死亡表格”是用来管理市民的最大依仗。剧中还描写了一段女秘书和渔民的对话,二者围绕着“生存证”和“健康证”的矛盾展开,到底是先办生存证才能办健康证,还是先办健康证才有生存证。先给出一个可以开店铺的权利,随后又取消这个权利。看似矛盾的做法在彰显荒诞性的同时也暗示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造成人们虽然说着同样的语言,但却相互不理解的状况。
再次,瘟神简单粗暴的做法本应引起市民的反抗和斗争,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城市似乎按照这个“井然有序”的方式运行着。在鲍曼看来,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官僚制度的作用。在分析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关系时,鲍曼指出,正是拥有“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度,制造出非理性到极端的大屠杀。因为现代性孕育下的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使其可以用纯粹“技术性”、道德中立的方式来对待身处其中的普通民众。非人化使得大屠杀行为成为被分解开的流水线工作。人们普遍性地保持道德中立,甚至道德冷漠的态度对待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瘟神留下了最高行政长官以及法官众人,它需要借助既有制度的惯性和动力以及市民习以为常的“服从感”来完成大屠杀行动。就像女秘书说的那样:“一个秘密:一台完善的机器。您就瞧着吧。”
所以,从本质上将极权主义是“反共同体”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体现,这种集体意识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个体意识为导向的,个体是绝对的、孤立的、没有存在感的。如果个体没有被接纳或者没有被认可的话,那么个体就会被剥夺其存在价值。因此,纳粹通过对个体进行排斥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这也为暴力统治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三、责任共同体的形塑
剧中有值得关注的人物,就是女秘书。她既是瘟神的帮凶,也是撬动“大厦”的第一股力量。她告诉狄埃戈,瘟神所创造的机器有个缺陷:“只要有一个人战胜恐惧心理,起而反抗,就足以使他们的机器吱格作响。”而且她仍进一步“提示”他,这个摩擦作响的声音代表着机器真的要卡住了。事实上,正是女秘书“帮凶”和“启示”的双重性质,促成了为狄埃戈的成长。在加缪看来,20世纪初,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共同生活”转变为“共同劳动”,进而进入“共同消费”时代。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纯粹的自然联系,而是必然要通过各种社会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正处于一种新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个历史转折期中,责任共同体作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开始形成。罗尔斯强调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责任。个人需要借助集体的支持和保护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和发展,而集体也需要依靠个人的参与和奉献来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责任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促进的。
所以责任共同体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首先,它是一种集体责任。加缪曾说:“我不认为,为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可以奴役一切。有些理由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我要既热爱自己的国家,同时又热爱正义。我不愿使自己的国家伟大而毫无顾忌,不论这种伟大属于血统的伟大还是虚幻的伟大。我愿我的国家与正义同在。”[3]5这正是鲍曼所强调的集体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在狄埃戈的带领下,民众开始萌生希望,他们扔掉口衔,抹除掉关于瘟疫的标记,打开窗户,集中患者,与瘟神展开决斗。在戏剧中,合唱队和渔民是加缪经常借用的意象。他借合唱队之口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借渔民之口抒发民众的心声和改变,二者相得益彰。尽管狄埃戈牺牲了,但他们领悟到了共同反抗的真谛:“让瘟疫来吧,战争来吧!所有的城门都关闭,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共同守卫到底!那么,你们就不会胡思乱想,不会沉迷于空话。”[1]193
其次,它是一种特殊的个人责任。剧中的纳达仿佛永远处在“局外”的角色,他目空一切,否定一切,当彗星刚刚出现,他便高呼“处死这个世界!”他藐视世间一切,认为自己超越一切,对任何事情不抱希望。等到瘟神统治世间,他又对所有人说,“瘟神还是行政长官,反正是国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虚无万岁,既然虚无是唯一存在的东西”。纳达,在拉丁语中代表NO,在西班牙语中意涵为Nothing。可以看出,纳达是一个彻头彻尾虚无主义者。他排斥各种道德准则和责任义务,缺乏自我负责和对他人负责的精神,结局也和科塔尔一样早已注定。
只有狄埃戈实现了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统一。他也曾是一个追求荣誉的热血青年,经历,也有痛苦、恐惧和彷徨,维克多丽雅的爱给了他莫大的勇气。剧中描写了三次狄埃戈和维克多丽雅定情的场面,可以看到,狄埃戈从充满激情到受到挫败再到充满信心的变化过程。同时起作用的,除了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还有他对自由的理解。他呼喊所有人:既不害怕,也不仇恨,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如今是自由人的时代,自由属于每一个人,没有人有理由被赋予绝对权力,以暴制暴的逻辑在如今是无法成立的。并且,他并不是在单枪匹马的战斗,“他们总跟我在一起”。瘟神总是不理解狄埃戈为何要为别人操劳,狄埃戈却认为说:“我知道他们并不纯洁,我也不纯洁。而且,我一出世就在他们中间。我为我的城市和我的时代而生,”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维克多丽雅和整个城市的自由。体现出一种“救世英雄”的崇高感,但这与里厄身上的“反崇高”并不矛盾,里厄是具有崇高精神的,正如加缪谈论荒诞是在别人止步的地方起步一样,加缪也并不否认崇高,他认为,应当把英雄主义和勇气看成次的价值——在证明过自己的勇气之后。也正因为如此,狄埃戈实现了从个体到集体的飞跃。
四、结语
苏珊·桑格塔曾这样评论加缪:“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正是在加缪孜孜不倦对爱与自由的追求上,使这部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给予我们抵抗灾难的勇气。
参考文献:
[1]阿尔贝·加缪.加缪全集·戏剧卷[M].李玉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阿尔贝·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Ⅱ[M].杨荣甲,王殿忠,李玉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5]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神话[M].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
[6]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第2卷[M].黄馨慧,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8]郑文涛.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J].世界哲学,2018(02):110-117+161.
[9]王丁莹.荒谬中的求索:《鼠疫》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其现实意义[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7(06):115-118.
[10]华丽娜.生命技术——对戏剧《戒严》的存在性解读[J].名作欣赏,2020,(12):73-75.
[11]刘妍.加缪生命伦理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6.
[12]李贺.困境·选择·超越——加缪戏剧人物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4.
作者简介:
高振凯(1996-),男,汉族,陕西汉中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