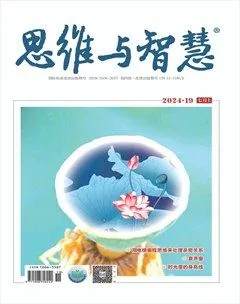说“垛”
戚舟
草木或者石土,堆成“几”状,就是活灵活现的“垛”字。但我猜想造这字的人未见过雪,否则高低得加上“雪”的元素。一入了冬,西北的雪跟不要钱似的,落得大街小巷无处安置,只好在林荫道旁砌成一个个白生生的雪垛子。它被铁锨敲打得坚不可摧,就是顽皮的孩子站在上面蹦跳都不会塌陷,且等着迟来的春天慢慢消融这冬天的特殊馈赠。
三月半,春阳升温,雪垛子被无孔不入的阳光渐渐攻占,先是表层变得湿淋淋、软塌塌,再是原本坚固的一角轰然崩塌。到四月初,雪垛子在某一个艳阳高照的早晨彻底消失,只留下许多混着春泥的水洼。我踮着脚尖走过黑白混杂的泥水,突然有些怀念犹如宝藏的雪垛子——它可是西北荒芜冬日里的游园,孩子们乐此不疲地蹦来蹦去,站得高就能望得远,有了雪垛的助力,谁都盼着快快长大呢。家家小院也有雪垛,是大人们藏食的天然冰箱,日日都能掏出美味的肉、馍和红薯,殊不知小孩子眼尖又嘴馋,早把家里的“老底”摸了个遍,雪垛成了他们偷嘴的秘密基地。
等冬天的美味被吃干净,雪垛子也全化成了春水,就意味着新一年的忙碌开始。雪垛之后,村庄又出现新的垛景。女人们将小院翻土、规整之后,从养牛的人家拉来一独轮车的粪,齐齐码在屋后,等粪垛发酵好后,四月半正好施肥、耕种。接着收拾二十亩自留地,去岁的玉米秆大部分就地粉碎,余少部分拉回家堆成垛,或用来引火,或当作蒸馒头的燃料,恰好补了煤炭的缺。这里的男人们多在工地上做活,无论是修河坝、开路还是盖房、建牛棚,都少不了砖土,谁家都有些剩下来的边角料,却不舍得扔,捡回家堆成砖垛,没准自家修屋顶、院墙就用得上呢。我很喜欢站在砖垛上假装将军,叉着腰指点江山,长大后才发觉这是自己向往远方山海的潜意识——边陲戈壁无山,这砖垛就成了我的第一座山。
跳下砖垛,一眨眼就是五谷丰登的秋天。田间万物经过悠悠长夏的生长,到了金秋,犹如菜码般齐齐垛在屋前屋后,谁看了都喜欢。先是收割后晒干的苜蓿垛,西北多苜蓿,一半被碾碎为鸡鸭猪羊的草料,一半成了人们冬天的干菜。每个秋后清晨,我总在窗后混着露气和苜蓿草的清香里醒来,那气息十分提神醒脑。
苜蓿垛阴上几日就得收起来,给西北最为隆重登场的向日葵让位,百亩地就有七十亩种植向日葵。多数向日葵的收割、敲籽都在地里完成,只有在小院附近种的向日葵要收回家来——屋后堆满了向日葵盘子,高高成垛,全家老小坐在上头,人手一根粗棍子敲得梆梆响,像是同奏一场丰收的交响乐。悉数敲出的葵花子们被装进麻袋,堆成垛放在杂物间里,到了冬天就有吃不完的香喷喷的炒瓜子!新收下的葵花子生吃也好吃,我和小妹爬到垛顶,撕开个小口摸葵花子吃,撒下一地的皮,常叫母亲怀疑老鼠会登高了。种地讲究一年一作物,待次年的苞谷丰收,黄澄澄的玉米棒子也堆成垛,冬日的零嘴就从瓜子变成了爆米花,别有风味。
冬天的食物储藏得差不多后,就要准备取暖的燃料了。除煤炭外,家家户户都要在晚秋进林子捡柴火,这时候的树枝开始“更新换代”,脆弱堪折的断枝就成了最好的柴火。一般是杨树、沙枣树和红柳,被父亲锯成一截截的圆木,齐齐码在灶房门外的铁皮屋檐下,再拿塑料布盖上,既不叫雪淋湿,又显得小院丰盈。等初雪落下,柴火垛披着洁白的长衫,又待衣衫层层加厚,我便知道趣味十足的雪垛子将要堆起来了。
春去冬来,冬再走向春,时间飞逝,却被一个个内容丰富的“垛”留下了足迹。小院虽小,亦被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垛”撑起一片天。“垛”是四时万物的回忆,更是浓浓郁郁的乡愁。
(编辑 兔咪/图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