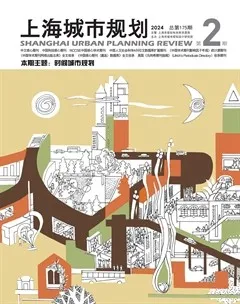基于多尺度价值链接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系统组构
肖竞 张芮珠 刘环宁 张晴晴 曹珂



关键词:城市遗产;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统筹保护;人本视角;文化生境;历史场景
0 引言
在城市文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发展和从快速城市化时期向后城市化时期转型的过程中,城乡遗产保护的核心矛盾逐渐从扩张性建设冲击导致的历史建成环境“空间孤岛化”问题转变为全球化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渗透引生的本土文化异化和“价值孤岛化”问题。其保护行动逻辑也相应地从防范扩张建设冲击的物质空间登录、保存、修复转向抵御外来文化挤替的历史文化价值识别、活化、传承[1]。在此背景下,将保护和发展置于对立关系的“历史遗产”对象范畴和桎梏于冻结保存目标的“物质保控”范式方法逐渐难以适应当代城乡遗产资源活化与价值传承的现实需求。
与此同时,伴随全国遗产资源普查工作的持续推进和地方遗产保护台账的全面建立,当前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已进入“资源渐控,价值未彰”的新阶段。其工作重点在于通过建立各类城乡历史文化空间与当代城市功能空间及人本经验主体的“价值链接”,促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乡发展建设的协同和与公众日常生活的融合。围绕上述目标,学界开展了广泛的城乡遗产价值传承研究探索[2-6],但多局限于“历史遗产”的概念桎梏和对单类遗产对象的本体分析,缺乏对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城乡遗产空间价值链接路径及其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链接机理的系统研究。为此,本文以面向发展、人本化导向的“文化空间”概念切入信息时代与后城市化时期城市遗产的价值认知和保护传承研究,以期为我国城市遗产的保护、活化和价值传承实践提供参考。
1 理论辨析:城乡遗产的“文化空间”属性与“价值链接”需求
城乡遗产的对象认知与保护逻辑受时代背景和发展观影响,在不同文明时期和不同城市化阶段,城乡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不尽相同。本节拟通过对世界遗产保护思想衍化历程的理论辨析,明确当前我国城乡遗产保护的实践方向。
1.1 对象认知:从“历史遗产”到“文化空间”
在世界遗产保护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学界对于城乡遗产的对象认知与概念界定经历了不断拓展、深入的辩证发展:在人文与自然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文化、自然遗产泾渭分明体系架构到“人化自然”(文化—自然复合遗产)登录标准确立的范畴拓展;在文化遗产类型方面,经历了从古迹单体到建筑群体、历史园林,再到历史地段、历史城区的要素与规模拓展;在遗产价值载体方面,经历了从物质遗产到非物质遗产的维度扩展;在对象时间界域方面,经历了从“源点锚定”的历史遗产(强调对特定历史时期原真信息的证据价值)到“线性发展”的文化景观、城市历史景观(强调对人化自然和城市发展过程的见证、记录价值)的概念衍化[7-10]。
综上,人类社会对于遗产对象的概念界定受到“当代”视角与人本视角的影响。而在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和城市建设从快速城市化时期向后城市化时期转型的新阶段,将城乡遗产理解为记录、传承历史文化信息的文化空间场域,是一种符合当代人本价值观的认知方式[11]。与桎梏于过去、将保护与发展置于对立关系的“历史遗产”概念相比,“文化空间”的对象范畴面向未来且更加包容,其可通过赋予遗产对象当代价值和发展属性的方式消解其保护与发展的二元矛盾,使城市历史空间与城市居住、商务、产业、交通等其他功能空间一样具备现实意义,契合“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的指导思想[12]。
1.2 实践逻辑:从“物质保控”到“价值链接”
实践方面,经过30余年探索总结,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基于空间调查评估和类型学、形态学分析的遗产分级分类保护管控制度范式和风貌修复设计规程,对各类城乡遗产保护实践起到关键指导作用[13]。但上述方法体系主要针对物质空间的保控修复,是快速城市化时期应对扩张性建设冲击的产物,在遗产价值识别、价值挖掘和价值链接方面缺乏有效手段[14-16]。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后城市化时期,随着空间生产的动力衰减和遗产资源的全面登录,以及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挤替、异化,城乡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矛盾与行动逻辑逐渐转变,从历史建成环境“空间孤岛化”问题及其物质保控逻辑转变为地域遗产资源“价值孤岛化”问题及其价值传承逻辑[17]。而实现价值传承的关键在于建立“价值链接”,即建立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与其自身系统要素、其他城市功能空间和各类价值媒介的多元链接,并最终建立城乡遗产客体与人本经验主体的“价值链接”(见图1)。
2 方法建构: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多尺度价值链接与统筹保护路径
本文以城市地区为研究范围,探索其历史文化空间多尺度价值链接路径与系统组构方法,以此实现对城市遗产的统筹保护。
2.1 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多尺度价值链接路径
价值链接即从价值维度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城市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链接”即建立历史文化空间与自身系统要素、城市其他功能空间以及各类价值媒介之间的多元价值关联。作为在城市持续发展进程中不断层叠累积的空间对象,城市历史文化空间具有多重维度的价值属性;同时,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其价值载体与价值呈现方式亦不尽相同,进而决定其价值链接的对象与路径差异。为此,本文从城市与城区、片区与地段、建筑与场所三重空间尺度进行梳理和讨论。
2.1.1 城市与城区尺度:孤岛文化空间历史价值链接
城市与城区尺度即城市全域和集中建设区的宏观空间尺度。其中,历史文化名城有对应的历史城区范围[18]。在该尺度下,城市遗产以历史文化空间要素与结构的形式存在,作用于主体对城市历史文脉的抽象结构认知,无法触发人本主体的具体空间经验。为此,该尺度下的历史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的重点在于梳理各空间遗产要素的文脉关联,建立孤岛文化空间的历史价值链接,以文化价值脉络统领遗产空间结构,建立散点遗产对象的整体保护逻辑[19-20]。
在此方面,既有的分类分级保控体系在处理遗产空间与价值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操作逻辑。即根据遗产对象的空间特征定义保护类型,再根据其价值重要性划分保护等级。上述保控思路可有效指导遗产保护实践中的空间差异化管控和对象优先级决策问题,但不利于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链接,进而影响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人本主体的文化信息感知。为此,本文提出城建历史脉络考据、建成环境“层积剥离”①[21]、同源文化空间识别的分析方法,以指导城市历史文化空间自身要素系统的价值链接。具体通过历史文献、舆图、影像考据划分城市历史营建周期;以不同年代周期为时间截面,剥离城市既存建成环境,识别层积各类遗产资源在不同历史周期中的空间价值与关联关系;根据“层积剥离”结果,将相同历史周期中存在价值关联的遗产空间作为“同源文化空间”,在层积建成环境中识别其空间—时间关联。
2.1.2 片区与地段尺度:历史文化空间当代价值链接
片区与地段尺度即城市中局部功能片区/地段的中观空间尺度。其包含遗产资源分布集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地段等保护对象。该尺度下的城市遗产以功能空间和文化场域的形式存在,作用于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人本主体发生经验关联[22]112。因此,该尺度下的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的重点在于建立其与邻近城市当代空间的功能价值关联,进而整体促进片区、地段遗产资源价值活化和文化活力提升。
在此方面,早期保护理论对于遗产对象的价值认知偏重于历史纪念、科学艺术和事件证据价值,忽略了遗产作为实存物质空间所兼具的功能价值和实用价值,导致其被冻结保存,陷入“价值孤岛”衰退陷阱,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的整体发展和自身功能与品质提升[23-24]。为此,本文提出遗产空间兼容性探查、当代功能需求预测、地段供需关系链接的分析方法,以指导城市历史文化空间与邻近当代空间的功能价值链接[25]141-142。首先,通过对片区内各遗产资源要素的交通区位、空间尺度、保存情况、价值主题、价值重要性的系统分析,梳理其历史与当代价值的兼容与活化方向②。其次,结合片区与地段人口规模、土地价格、功能关系综合调查,预测其整体发展导向与功能业态需求。最后,基于对片区、地段的历史文化空间兼容性与功能供需关系的判别,建立历史与当代空间的价值链接,明确其活化更新功能定位。
2.1.3 建筑与场所尺度:小微文化空间价值媒介链接
建筑与场所尺度即建筑遗产与历史文化场所的微观空间尺度。在该尺度下,城市遗产以具体的文化空间媒介形式存在,直接作用于主体文化感知经验的过程。其价值链接重点在于建立历史文化空间与实物、文献、影像、布景、活动等其他文化媒介要素价值表征与价值内涵的链接,使不同媒介要素在历史文化信息的阐释、解说上相得益彰,以促进人本主体对文化信息的感知和接收。
在此方面,传统保护理论将遗产对象的价值呈显媒介锁定于物质空间,关注其物质形态特征的保控延续。建立了以形态学、类型学为理论基础的遗产空间形态、风貌保控修复范式[26]。相关方法虽有效促进了各类遗产空间形态表征的保存延续,但在文化信息呈显和价值传播方面却缺少有效手段,难以将遗产对象的文化内涵切实转化为公众主体的文化认知[27-29]。为此,本文提出价值内涵识别、价值载体梳理、价值媒介关联的分析方法,以指导城市小微文化空间多元价值媒介的要素链接。具体通过历史学、文化学分析,考据、识别各小微文化空间的文化价值内涵。继而从空间形态、陈设布景、文献影像、历史实物、行为活动等方面梳理相应价值信息的媒介载体。最后,以文化价值主题为线索,建立相关媒介载体的要素链接。
2.2 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组构方法
“统筹保护”即对遗产保护相关对象、事务的通盘组织和整体筹划。其与“孤立保护”概念相对,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公共文化质效提升为统筹目标,以不同空间尺度、类型城市遗产资源和当代文化资源为统筹要素,以城市遗产保护、活化、展示等不同工作事务为统筹内容,涉及多目标、多要素、多维度的统筹工作[30]。在具体操作中,以多尺度的历史文化空间价值链接、组构为实施路径。
2.2.1 城市与城区尺度:遗产同源要素统筹与文化空间网络建构
城市与城区尺度下,统筹零散分布的遗产资源要素,建立城市历史价值脉络的整体阐释逻辑和与之适配的文化空间叙事结构。在城市建成环境不断重构演替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价值同源性的遗产对象会逐渐失去其与原生空间的关联,以碎片化、散点化的方式分布于现代城市空间,沦为“孤岛遗产”[31],进而导致城市历史文脉整体价值逻辑在文化空间结构表征层面的线索模糊、不易阅读。因此,可借鉴区域遗产廊道保护模式,通过文化廊道/线路对具有价值同源性的遗产要素进行统筹组织,建构易于主体阅读的历史文化空间网络结构(见图2a)。
具体以点状(历史地标、历史场所)、线性(历史街巷、文化轴线)、面域(历史街区、历史地段)3种空间形态的历史文化空间为结构要素,通过要素等级判别、文化线路串联、节点标识强化的步骤统筹建构。首先,梳理各类遗产要素的价值关联性、价值重要性,确立城市文化空间网络的价值脉络和要素等级(主次轴线/廊道、一级/二级节点等)。其次,根据各类遗产要素的空间分布,结合现代城市交通路网,将具有价值同源性的历史文化空间链接为具有集群展示度的主题文化线路,形成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展示的网络结构③。最后,根据各文化空间轴线、节点的价值属性和价值等级,配设相应文化标识、解说和公共交通设施,以提升文化节点空间的价值关联性和空间可达性,为居民、游客提供城市文脉认知的系统性空间结构与阅读路径。
2.2.2 片区与地段尺度:遗产文化生境统筹与文化空间功能组织
片区与地段尺度下,统筹遗产对象所在区段的文化生境,组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融合的城市文化空间。伴随邻近片区、地段的功能重构,冻结保控的历史文化空间与周边现代城市空间在环境品质和活力质效方面的差距日益显著,进而引生功能、效用边缘化问题,不利于其空间活化与价值传承[25]140。因此,需加强历史文化空间与当代功能空间的要素统筹,组构融历史文化传承与日常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生境,以提升片区、地段的整体空间活力和公共文化质效(见图2b)。
具体以历史文化空间、当代功能空间和公共游憩空间3类空间对象为统筹要素,通过交通衔接、功能协同、设施共享的方式统筹组织。首先,结合3类空间要素的价值联系与位置分布,以点、轴连接方式,建立片区文化空间慢行系统,提升片区文化空间步行环境品质。其次,建立历史文化空间与当代功能空间的功能链接,提升其在城市公共生活中的触媒价值。最后,增强片区空间新质公共服务设施配设,以共享设施驱动各类空间单元在日常生活服务与公共文化组织方面的关联性。
2.2.3 建筑与场所尺度:遗产价值媒介统筹与文化空间场景营造
建筑与场所尺度下,统筹历史建筑、场所中各类价值媒介要素,营建易于历史文化传承和主体经验感知的文化空间场景。建筑遗产的历史信息潜藏于其多元文化空间的多维场景特征中[22]117,单一的物质空间表征制约了主体感知接收历史信息的质效,不利于历史文化传承。因此,需加强对各类价值媒介要素的统筹,营造利于主体感知的小微文化场景,提升公众文化体验品质和信息接收质效(见图2c)。
具体以空间陈设、文献影像、历史实物、行为活动为媒介要素,通过历史场景再现、生活场景植入、数字场景拓展3种方式统筹营造。(1)历史场景再现即对场所空间中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传统仪俗和历史人物行为场景的演绎呈现。基于文献考据,其可通过历史布景复原、历史实物陈列、历史影像比照、历史雕塑点睛等综合手段建立现实空间与历史场景的时空关联,使参观者产生“历史在场”经验。(2)生活场景植入即通过遗产功能活化、公共活动组织等方式,将当代日常行为植入历史文化空间。其通过实用职能延续、公共化更新方式促进历史文化空间使用频度提升,增强城市当代生活的文化沉浸感,使公众在日常状态中濡染城市文化和传承审美意趣。(3)数字场景拓展即通过数字化手段拓展遗产空间价值传导的场景媒介。其通过全息投影与增强现实技术在实体空间中叠加虚拟场景、通过历史档案数字化转译与数字孪生技术在虚拟空间中传播历史文化信息,更加契合当代信息传播途径和主体认知习惯,利于拓展遗产对象的文化传播广度和影响深度[32]。
3 重庆市近代遗产多尺度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组构
3.1 案例概况:重庆市中心城区近代建设情况
本文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为例,其近代发展以1891—1949年为起讫时间,先后经历开埠通商(1891—1920年)、设市建设(1921—1936年),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1937—1949年)3段历史时期。
开埠通商时期,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全球市场,城市建设围绕商埠、租界和富商宅园营造等线索展开,于渝中、江北、南岸、巴南等地建造海关、商会、洋行和富商园林。设市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建设以明清府城更新和新市区拓展为重点,完成了现代道路、轮船码头、市政工程建设,并在李子坝、上清寺、枇杷山、七星岗等地修建了大量公馆。同时期,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北碚兴建公园、图书馆、体育馆、医院、学校等现代公共建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带动工商企业、机关团体、文教组织内迁,促进了重庆渝中、沙坪坝、北碚等区的城市建设,于上清寺、李子坝、歌乐山等地建造了行政及军事机构,于黄山、山洞、南泉、鹅岭等地建造了一批政要宅园和外交领馆建筑,于渝中、南岸、沙坪坝、九龙坡等区构筑了200余处防空工事。与此同时,1938—1946年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分别在红岩村、曾家岩、中山三路和民生路等地设立办事机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斗争工作,留下了大量历史见证(见图3)。
3.2 孤岛遗产要素串联与城市文化空间网络建构
城市与城区尺度下,对各时期城建遗产资源进行梳理串联。考虑开埠与设市时期遗产资源数量较少,且在空间、功能与文化方面具有一定关联,故将两阶段资源要素整合,梳理出开埠、设市期区段遗产6处、建筑遗产124处、景观遗产9处和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区段遗产5处、建筑遗产301处、景观遗产30处(见图4a)[34]。结合上述历史遗存的保存、分布情况,在资源集中的渝中、南岸、北碚、沙坪坝四区内,分别梳理出以开埠通商历史见证、市政建设历史见证、中西文化交流纪念、民族实业家及名人纪念为价值线索的开埠设市文化线路4条;以革命先烈斗争纪念、抗战机构职能见证、抗战历史事件纪念、抗战历史人物纪念为价值线索的革命、抗战文化线路8条(见图4b),系统建构重庆市近代历史文化空间网络[35]17-21。
3.3 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与片区文化空间功能组织
片区与地段尺度下,结合城市各行政辖区内历史文化空间和其他公共文化空间分布,梳理组织片区/地段公共文化生境系统。在渝中区,统筹张治中公馆和重庆谈判旧址等历史文化空间,重庆市委办公楼、三峡博物馆、人民广场等当代功能空间,形成中山四路抗战文化展示与行政办公生境系统;在南岸区,统筹卜内门洋行、意大利使馆旧址等历史文化空间,南滨路文化产业园、开埠遗址公园等当代文娱空间,形成滨江开埠历史纪念与文旅游憩生境系统;在北碚区,统筹惠宇楼、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等历史文化空间,北碚体育场、北滨文创街区等当代公共空间,形成三峡乡建纪念与旧城人居生境系统;在沙坪坝区,统筹“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孔祥熙公馆等历史文化空间,四川外国语大学、康明斯文创园等文教科创空间,形成红岩精神纪念与文教科创生境系统[35]41-48(见图5)。
3.4 多维价值媒介呈显与小微文化空间场景营造
建筑与场所尺度下,通过多元遗产媒介要素统筹与文化空间场景营造实现各区近代遗产历史文化信息的多维呈显。其中,《新华日报》与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渣滓洞监狱、蒋介石黄山官邸等历史建筑转作文博建筑对公众开放,并通过前述多元场景营造手段全面复现了重要的历史场景。川康银行、美丰银行、罗斯福图书馆、法国水师兵营、安达森洋行仓库等建筑则采取实用职能延续和公共化更新方式,为相应历史空间植入公共生活场景。宋庆龄旧居、《新华日报》办事处旧址、三峡博物馆、重庆市规划展览馆、重庆时空大数据展示中心等通过全息投影、增强现实、历史档案数字化集成、历史空间数字孪生等技术拓展了重庆市近代历史文化空间的数字化展示场景(见图6)。
4 结语
本文基于信息时代与后城市化时期城乡遗产保护矛盾从“空间孤岛化”向“价值孤岛化”转变的现实背景,以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当代城市发展协同为目标,提出基于多尺度价值链接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与文化空间系统组构方法,主要创新与贡献如下:
(1)基于人本价值视角,系统地辨析了城乡遗产保护从“历史遗存”到“文化空间”的对象范畴转变和从“物质保控”到“价值链接”的实践逻辑转变。
(2)系统界定了城市遗产“统筹保护”概念,厘清其统筹目标、统筹要素、统筹内容和统筹尺度;提出城区遗产同源要素统筹、地段遗产文化生境统筹、建筑遗产价值媒介统筹三重空间尺度的城市遗产统筹保护模式。
(3)提出以孤岛文化空间历史价值链接、历史文化空间当代价值链接和小微文化空间价值媒介链接3种价值链接机制为组构逻辑的城市文化空间系统组构方法,包括:①通过对点状、线性、面域3种历史文化空间要素的等级判别、资源串联和节点强化,建构城市文化空间网络。②以交通优化、功能协同、设施共享为统筹手段,结合旧城人居、行政办公、文旅游憩、文教科创4类当代功能,组织地段空间文化生境。③通过历史场景再现、生活场景植入、数字场景拓展3种场景营建路径,营造小微空间文化场景。
上述内容和方法可在遗产价值认知、价值链接和价值传承方面丰富既有保护理论,以期为我国城市遗产保护活化和价值传承工作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