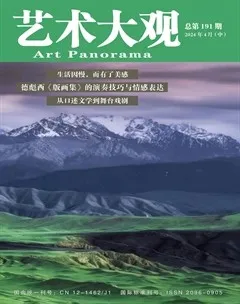从口述文学到舞台戏剧
摘 要:音乐剧《妈妈的女儿》改编自彝族传统抒情长诗《阿嫫妮惹》,通过舞台艺术成功地将文学转化为戏剧,展现了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该剧在西昌市金鹰大剧院上演,成为民族音乐周的重要剧目。音乐剧保留了彝族语言的使用,通过音乐、舞蹈、舞台设计等元素,创造出深刻的意境美,同时对原诗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增强了戏剧性和观众的沉浸感。本文通过对《妈妈的女儿》的创作进行浅谈,从而分析其创作的优点及不足,进而希望为推广民族音乐剧发展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提供些许有利的启示。
关键词:音乐剧《妈妈的女儿》;彝族文化;意境美;民族性;戏剧改编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4)11-00-03
2023年12月29日,民族音乐剧《妈妈的女儿》在西昌市金鹰大剧院上演,成为“听见绿水青山”2023中国(四川)首届民族音乐周民族音乐剧目展演的重要剧目之一。该剧由彝族传统抒情长诗《阿嫫妮惹》改编而成,故事通过讲述在遥远的过去一个名叫“阿妞”的“阿嫫妮惹”(汉语意为“妈妈的女儿”)从出生到嫁人的人生轨迹,形象生动又可歌可泣地展示了古代彝族女性在婚恋伦理上的悲欢与离合。独具特色的是,除剧中角色——“讲述人”(现代阿妞)以外,所有演员均用彝语演出,演出效果可谓轰动一时。
一、彝族长诗《阿嫫妮惹》
彝族传统抒情长诗《阿嫫妮惹》是彝族民间口传文学的一件瑰宝,是一部古代彝族妇女在特定时期由集体创作而成的口传文学作品。它不仅是彝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组成部分,其产生背景和深远影响无不体现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可以说,《阿嫫妮惹》的创作背景深刻地根植于彝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阿嫫妮惹》的产生与彝族的口头传统紧密相关,其在早期的创作和流传均通过口头形式进行。这种口传性是古代受传播形式所限的多种民间性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其表现往往是通过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和口头流传的方式保存下来的。《阿嫫妮惹》在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它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彝族人民特别是彝族妇女的社会生活和婚嫁细节,同时也表达出当时彝族妇女的一种对于“婚嫁”行为的集体情绪和感情。可以说,《阿嫫妮惹》不仅是一部在彝族文化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彝族文化代代传承的重要载体[1]。
在这样深刻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长诗《阿嫫妮惹》,曾对彝族的文化生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体现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首先,《阿嫫妮惹》的出现使得彝族民间文学体式形成了一种抒情、叙事的传统。其次,长诗在口传过程中自带吟唱效果,因此其具有一定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的节奏和韵律对彝族音乐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它还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口传长诗通过叙事和抒情的方式,传达出彝族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彝族社会共同体生活中的群体行为和道德意识的反映起到了调节作用。
《阿嫫妮惹》作为彝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它不仅在彝族地区广为流传,而且被编入了多所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科书中,成为研究彝族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二、舞台上的意境美
众所周知,音乐剧是一种融合了戏剧、音乐、舞蹈、视觉艺术等多种艺术元素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形式,它往往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本、旋律、编舞以及舞台布景,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意境美。虽然《阿嫫妮惹》有着上述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影响,但由此改编成的音乐剧《妈妈的女儿》却没有被原诗的文学性和社会性所束缚,而是将情节、音乐和视觉进行完美结合,将观众带入一个既是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艺术空间中,由此使观众深入地体验到剧中人物的情感波动和故事的深层含义,使其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磅礴且优美的戏剧性的“意境美”。
这样的“意境美”,首先,体现在其波澜壮阔又流连婉转的音乐上。
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歌曲《我曾有梦》(I Dreamed a Dream)通过深沉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展现了主人公芳汀的绝望与希望交织的复杂情感。《妈妈的女儿》一剧中的音乐所达到的效果同样如此,作为由形容妇女婚嫁苦难的长诗改编而成的音乐剧,剧中的音乐不仅有表达哀怨体现悲伤无助的部分,同样还根据不同的人物和剧情需要,充满了令人振奋谓之壮阔的内容。这些旋律不仅悦耳动听,而且能够深刻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同时还极大地丰富了剧中存在的人物情感,其中的音乐旋律、节奏和和声还与剧情紧密结合,既可以共同推动剧情发展,又有效地增强了戏剧的表现力[2]。
其次,本剧的“意境美”还体现在其舞蹈设计上。
舞蹈作为音乐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身体语言的变化来传达和表现人物的情感及故事的动态变化。例如,在音乐剧《西贡小姐》中那场著名的“直升机逃离”场景,就是通过舞蹈和舞台技术的结合,营造出了在战争背景下,人物内心的紧张、混乱与无助。《妈妈的女儿》同样如此,通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动作与音乐节奏的相得益彰,创造出富有视觉冲击力的舞台效果。特别是其中的女子群舞和男子摔跤群舞两段,女性的柔美和男性的阳刚无不通过精致的舞蹈动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样的舞蹈,不仅强调了此时此刻主人公阿妞和兄长们的内心感情,同时还强化了性别不同所带来的不同情境,观众看后无不震撼且印象深刻。
除了音乐和舞蹈,本剧的舞台设计及其带来的视觉效果也为其“意境美”添了一抹亮色。
作为现代戏剧舞台上的重要组成元素,舞台美术一直起着其他舞台元素所无法代替的重要作用。舞台设计师利用灯光、布景、道具等元素,创造出符合剧情需要的视觉效果,增强了音乐剧的沉浸感。著名音乐剧《歌剧魅影》中,就曾依靠舞美的光影效果营造出该剧特有的神秘和悬疑氛围。而在《妈妈的女儿》一剧中,舞台美术设计也是可圈可点的。其中,灯光的变化很好地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场景的转换,同时也如同许多优秀的音乐剧一样外化出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3]。
最后,本剧的意境美还体现在其整体的叙事结构上。
一部优秀的音乐剧通常具有清晰的叙事线索,编导利用这些叙事线索,通过把音乐、歌曲、对话和舞蹈等元素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讲述一个完整精彩的故事。《妈妈的女儿》中的叙事线索虽然基本来自原诗《阿嫫妮惹》,但是由于原诗的篇幅和文学性等因素,要将其由文学作品变成戏剧作品的编导必然对其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压缩和删减。可喜的是,这样的压缩和删减很好地保留了原诗作品的主旨和氛围外,并没有因为戏剧性的改编而对原诗的文学性产生破坏和消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除了压缩和删减,编导还在原诗的基础上适时地进行了增加,这样的增加首先体现在人物上,原诗中的叙述者只有“妈妈的女儿”,而编导为了让其适应舞台改编的需求,增设了“现代阿妞”这一角色。这样的增设,不仅可以让本来以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阿嫫妮惹”从角色中跳脱出来并产生一定的间离效果,同时还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让观众在观赏时能清晰地分清戏剧叙事的不同阶段。除此之外,本剧的编导者在原诗基础上的增设还包括“现代阿妞”的最后一段独白:
因为有妈妈披过荆棘
女儿们才能安然地长大
因为有妈妈采集果实
女儿们才能品尝甘霖
因为有妈妈矗立前方
我们才能坚定方向
因为有妈妈的坚实臂膀
我们才能自由成长
岁月流转,山海变迁
何其有幸生于此时
用火把照亮前方
何其有幸生于此刻
女儿们的微笑迎着朝阳
这样的独白,按照原诗的体例和韵律,不是单纯的自我情感的抒发,而是一种不脱离原诗的有机改编,因此在增添戏剧情感之外,不会给人以不和谐之感。如此看来,《妈妈的女儿》一剧的叙事方式清晰明了又不脱离原诗的文学性,在使观众能够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故事的情感深度和思想内涵。
综上所述,音乐剧《妈妈的女儿》的意境美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体验,它通过音乐的旋律、舞蹈的动态、舞台的视觉效果以及叙事的结构设计,共同创造出一个充满情感和想象的艺术世界,给观众带来深刻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
三、那些仍旧值得讨论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虽然能够看出《妈妈的女儿》是一部各方面都相对优秀精彩的作品,但称赞的自由与批评的自由是平等的,一部无论如何上乘的佳作都会在一些不易察觉的隐秘角落中存在着瑕疵。当然,用瑕疵一词也并非对好作品吹毛求疵地“贬”,更多的应该是笔者对于这样一部优秀作品存在精益求精的希望和期盼。
前文笔者曾经赞扬过本剧音乐的运用,然而,这些音乐中的某些部分,在笔者看来也存在着些许上述的“瑕疵”。
音乐在音乐剧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同时还极大地丰富了剧中存在的人物情感。然而,剧中关于“丑角”——媒人克里扎拉的音乐描述在笔者看来是存在问题的。克里扎拉作为本剧中唯一的“非正面”角色,其本身可以用“戏谑”“搞怪”来形容,但绝不应该是“邪恶”。如果这一观点大家认同的话,那么本剧中所有关于克里扎拉的音乐部分就显得有些“放肆”了。每当克里扎拉出场时,音乐氛围就会显得格外消沉与恐怖,似乎在刻意地告诉我们,克里扎拉是反派是恶人。但很显然,作为丑角出现的克里扎拉肯定不是那种典型的“反派”,他的各种行为和做派也是在特定历史文化下的正常反应,这样的角色根本让人恨不起来,似乎全剧中唯一“恨”他的只有诡异的灯光和刻意渲染“邪恶性”的音乐。既然让人恨不起来,那又何必给他如此“邪恶”的人物配乐呢?这样的音乐,不仅影响了克里扎拉,同时还波及了阿妞的父亲。剧中当媒人和阿妞的父亲在一起商议阿妞婚事的时候,前面明显是正面的父亲形象,突然在音乐的渲染下由“和蔼”变为“狰狞”。除此之外,在阿妞出嫁前的戏中,阿妞的母亲用哀怨的语调表达着自己的心碎,而此时展示父亲的音乐突然又同母亲一样变得哀怨婉转,与前面相比又似乎良心发现一般,这不免让笔者感觉到一种错位和割裂,也不免让笔者觉得父亲的人物塑造突然变得不准确了。诚然,并非说音乐不能成为塑造正与反的手段,但哪怕作为一部“音乐剧”,音乐这一元素也只能是为塑造人物而存在的手段。既然是手段,那么如何运用音乐,一定要符合人物本身的性格和背景设定。显然,从本剧一开始,父亲这一角色的设定同克里扎拉一样就不是“邪恶”的,因此就目前的音乐段落来看,每当克里扎拉单独出现或者和阿妞父亲一起出现时,其渲染人物的音乐段落之情调,是不太符合人物设定的[4]。
除了音乐在塑造人物上有一定问题外,剧中的舞台设定同样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在母亲为阿妞因婚嫁离去而哀怨的段落中,舞台的右后侧突然出现一个白衣女子,该女子在原地以舞蹈动作旋转了一段时间后就随着灯光的变化下场,这样的设计不免让观众在当时产生疑惑。当然,我们可以在事后把这样的设计理解成一种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也可以用评论的思维解释成一种形容人物命运的闭环。但是戏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它既要经得起观众的推敲,又不能让观众在观赏时太需要推敲才能看懂,因此,这样的设计笔者认为在戏剧作品中应该少有甚至不要有。
四、结束语
音乐剧《妈妈的女儿》作为一部深刻反映彝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戏剧作品,不仅在艺术表现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在文化交流和民族音乐剧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彝族传统抒情长诗《阿嫫妮惹》搬上舞台,该剧成功地将文学与戏剧、音乐与舞蹈、传统与现代进行了有机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艺术世界。此外,《妈妈的女儿》的创作和演出,为民族音乐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平衡民族性与现代性、传统与创新之间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它鼓励我们继续挖掘和利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创新的艺术形式,让世界了解和欣赏中国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
虽然作为一部带有鲜明“民族性的”音乐剧,《妈妈的女儿》无论艺术上还是演出现场效果上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且成功的作品。然而,任何艺术作品都有其局限性,本剧在音乐塑造和舞台设计上的某些处理仍有改进空间,正如前文所讲,若瑕不掩瑜,则玉不避瑕。这些不足之处提示我们在追求艺术完美的道路上还需继续前行。这样的前行,即使有着“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艰苦,大力发展具有民族性的音乐剧及其他舞台作品依旧是值得我们所有戏剧人奋力“上下求索”的事业。就如同本剧中台词表达的那样——哪怕道路坎坷,“阴雨绵绵也要走,银霜遍地也要走”,即使挡在前面的是连绵的高山,“冰雪漫山也要走,暴雨弥漫也要走”!
参考文献:
[1]方弘毅.基于口传故事的艺术学评价范式探讨[J].民族艺术,2023(02):26-37.
[2]孙子呷呷.凉山彝族民间叙事诗《妈妈的女儿》口传程式解读[J].贵州民族研究,2014,35(03):84-88.
[3]范嘉琴.如泣如诉的《阿莫尼惹》——凉山彝族叙事长诗《阿莫尼惹》的初步探析[J].北方音乐,2020(12):99-100.
[4]孙宏年.中国边疆学发展趋势前瞻的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01):29-35.
作者简介:高尚(1990-),男,山东淄博人,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话剧史论、编剧理论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