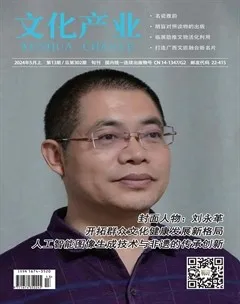文化自信与中国图书馆文化传统的哲理思考
韦晓冰

中国藏书和管理活动源远流长,这是中华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和历史依据。在数千年的图书馆建设历程中,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建设理念,并由此提炼为中国哲学与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建设应当接纳、吸收中国传统图书馆文化的优秀内容并将其发扬光大,为世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源泉,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深厚沃土。中国历史上有着久远的图书馆建设发展史,因而图书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体现。中国图书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渠道,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在文化自信的视角下对中国图书馆建设的研究成果不少。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还聚焦在图书馆人员设置、项目推广、技术研发等“术”的层面,对于中国图书馆建设与文化自信的哲理思考和文化关联等“道”层面则关注不足。在数千年的图书馆建设历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建设理念并上升为中国哲学与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故而,要持续发扬中国图书馆文化传统的优秀内容,为世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本文将从中国源远流长的图书馆传统与文化自信的历史来源展开论述,为世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源泉。
中国图书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与依据
19世纪60年代,部分西方传教士、商人与外交官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开设西方意义上的图书馆,曾有个别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有图书馆之开始,这一论点因为缺乏历史根据而被摈弃[1]。中国有三千多年的图书馆历史,虽然在近代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令中国图书馆的制度与文化遭到干扰,但保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仍旧传承了下来。
中国图书馆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
有考古与文献资料证明的中国图书馆文化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在河南安阳商都殷墟中,考古发掘出大量的甲骨文和简册,其内容不仅与占卜相关,还包含大量的商朝军事政治与皇室活动记录,说明商朝已经存在图书馆及管理甲骨文的工作人员,其典籍至春秋时期仍有流传[2]。此后历朝历代皆延续藏书传统,周朝有收藏典籍的“盟府”;秦代官方图书馆地位崇高;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后又于宫中昆明池上建“石渠阁”,以石为屋,且建于水中,具有良好的防火功能,专门用于保存图书典籍,是典型的专业国家图书馆;至隋朝,隋炀帝于东都洛阳建观文殿,藏书37万卷;以后历经唐宋元明清,不仅有皇家和官方藏书机构,还发展出大量的民间藏书馆,形成中国特有的藏书楼文化。
繁荣的民间藏书楼文化凸显中国社会的自由度
传统的中国图书馆藏书除了王家与官府之外,还有民间藏书,包括寺庙藏书与书院藏书[3]。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始于北魏,北宋时期湖南岳麓书院的“御书阁”中藏有唐太宗、宋太宗、宋真宗的御书;明清时期藏书楼多在民间发展,明朝浙江天一阁号称“天下第一藏书楼”;清朝更是兴盛之极,仅知名度较高的藏书楼就有五百多处,据统计共有数千座之多。中国古代众多的民间藏书楼通常是开放的,供大众阅读与传抄,并促进了中国古代出版、校勘、写作等事业的繁荣,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藏书楼文化,即强调藏用结合、以书会友、以馆传道、经世致用的目的。
中国图书馆兼容并蓄,尊重多元文明
中国古代藏书体现出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人民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中国藏书传统一向重视外来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文明的典籍,将其纳入收藏整理的范围。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前朝的经典图册,如汉代萧何收集秦朝图书史册被传为历史美谈。此后虽朝代变迁、最高统治者身份有异,但都十分重视历代文化、政治遗产,体现了对中华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认同感。
中国图书馆保障了社会公平与活力
中国藏书传统和图书馆文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化交流具有重要影响。从周朝开始,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阶层就以图书为中介,相互交流沟通,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王室藏书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开放的。孔子作为普通士人成为图书编辑、馆藏工作者;老子出生于楚国平民家庭,却可以担任周王室的守藏吏,为王室掌管图书典册;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太学、隋炀帝设立国子监等,都是当时的“国立最高学府”。同时民间也出现大量书院,招收各地学子,这些书院中都收藏了大量书籍供学子学习,“凿壁偷光”等成语的出现说明当时图书的流通与收藏,为底层平民提供了读书识字、参加科举,改变自身命运、为国家服务的机会及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场所。中国图书馆传统也为科举制、读书仕宦制提供了文化土壤与知识背景,体现人文精神与社会公正。可见,中国古代图书馆文化一向有寓藏于用、服务大众的传统,将书籍及其中记载的知识作为天下公器来看待。
中国图书馆建设理念的哲理意义
梁启超、章太炎等先贤都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应体现文化特色。梁启超早在百年前就指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词,但这个学问却是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读书治学过程中,大多涉及图书的馆藏、校勘、编辑、编目保存等具体事务,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图书馆(藏书楼)建设理念,常常会被应用到治国安邦、学问写作等相关领域中。因此,藏书之道往往体现了治国之道、学术之道、思想之道,具体表现以下几方面。
书即道、道即书:强调书籍的主体性地位
南宋学者包恢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中国图书馆传统命题:“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同时代人周敦熙称“文以载道”,具体而言即“书以载道”,书不仅是文的载体,同时也是道的载体,道在书中,方得以长久的传承下去。不论是古代的藏书楼或图册馆阁还是现代的图书馆体系,都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即书籍永远是图书馆存在的目的与对象,图书馆是藏书、传书之所在,也是为了书籍的流传和保存才得以产生与存在。对文字与书籍的重视与热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令书籍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图书馆建设思想中占据宝贵的主体性地位。
图书馆建设的功能论思想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称有好书“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壁,什袭而藏,於予又何稗?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中国藏书传统中一向强调以传为藏的美德,尽管确实有爱书以至于吝书的藏书家存在,将藏书秘而不发,虽是爱物的体现,但古人更强调不以物喜的“仁人”精神,将其视为思想品德崇高的体现。如果书籍不流通,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以传为藏,通过将书籍流通起来,令书籍的价值得到广泛的承认,在流传过程中令其不至于散佚,从而实现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治书即治国的图书馆建设本体论思想
清代乾隆皇帝下令纂修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对中国数千年历史所留下的典籍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部分研究认为,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历代中央王朝进行的国家图书馆建设,尤其是大百科全书性质的纂书工程是古代的国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构建文化大一统观相契合。由此可见,古代国家纂书与修书工程往往蕴含着统一疆域各地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历史记忆等,统一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信仰与文化。这对于促进国家统一、保护多元文明、促进社会化交流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治理书册是治理国家的行为之一,治书即治国,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思想价值。
图书馆馆阁之职的存在论认识
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建设成为国家治理、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国家管理者队伍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馆阁之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知识、书籍的重视,“书以载道”“朝问道夕死可矣”,在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中书籍与理念具有本体论上的纯粹价值,而知识则被视为道德的体现,这也对从事图书编修、撰写与管理的人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中国图书馆文化的伟大价值
现代图书馆学可以溯源至欧洲中世纪图书典籍的抄写、收藏、编目与考证等活动,而西方图书馆体系为人类的科技进步、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文化根砥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西方古典时期的图书馆往往具有排外性和保持神秘主义立场。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民间藏书楼文化的兴盛体现了中国社会学术自由,且更具有开放性和平等的意识,使社会更具活力。中国图书馆这一传统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历史的延续性,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可忽视。
现代图书馆学的诞生,是以现代主义、人文主义思想为学理基础的。与中世纪相比,固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秉承传统的图书馆从业者与普通大众的划分。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书)以载道”“人文化成”“有教无类”等与图书相关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更符合当代世界多元文明并存、尊重人文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平等发展的思想,蕴含在中国传统图书馆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对于当代世界的和平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引领作用[4]。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其创作与生活也多受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影响,曾经说过“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式的图书馆也往往以人间天堂、世外桃源般的美丽景色存在。这既是一种物理空间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心态的存在。中国图书馆传统中书即道、书以传道、治书即治国、书馆清贵的图书馆学理念以及尊重多元文明、促进国家与社会治理、保护自由与公平,对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部分。
国家哲社基金项目“中古志怪故事与丝路文明研究”(课题编号:21BZW16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