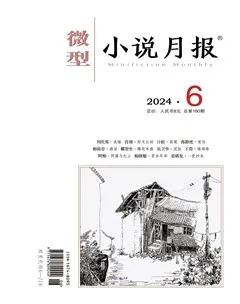小说家之死
杨小玲
独孤君住在C市,是个写小说的。许多年前我就认识他,那时他的新作刚在新华书店上架,他来到我居住的县城签名售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留着长发,穿着一身白色棉麻唐装,大功率的鼓风机每半分钟就要吹向他一次,他端坐在书案前滔滔不绝地演讲,可谓春风得意。作为他的粉丝,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但这次见面会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我们仅是通过互联网联络交流而已。
他很勤奋,然而真正发表的作品不多,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他仍在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重功利轻才华的年代。也罢,也罢!”
我说:“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他说:“发光的总是藏在墓穴里头的。”
五月的一天,他给我发来一个稿件,是一个长篇,叫《小说家之死》。故事讲的是一个过气的小说家暗无天日地写着没人愿意读的文字,孤独和失望中他寄出他最后一部作品,一年后他的小说意外获得国内知名大奖,当他们想将证书送给他时,发现他早已郁郁而死……
“他应该享受成功给他带来的喜悦才对。可不可以让他不要死?”我乞求独孤君。
“他必须死!”
“为什么?”
“他已经等不了了。”
他的态度很坚决,冷酷得像是一个掌握别人生死的刽子手。窗前,初夏的凌霄花探到矮墙之外,我冒出一身冷汗。
许多个平静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很快忘了独孤君的小说,我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是不会为了谁谁谁而轻易改变决定的。
我有些天没有和独孤君联络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打开电脑想查阅他是否给我发来邮件时,我的手机响了,号码有些陌生却来自C市。“我是C市警察局小罗,你认识独孤君吗?”
“他怎么了?”
“昨日他被人发现在自己的出租屋内死亡,尸检报告显示他的胃液里有大量安眠药的成分残余,我们暂时排除他杀的可能,但我们还侦查到,他最后联络的人是你,所以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调查。”
“独孤君死了?独孤君死在自己的小说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如果死亡是为了让小说更加好看,那么独孤君没有必要成为自己小说的牺牲品!这个世界不可能有那么多巧合,除非它们是被设计好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感到震惊,我只是有些懊悔,懊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看出端倪,阻止这场阴谋。
“作为他的朋友,你清楚他可以不用死?”罗警官又继续问。
“他必须死!”
“为什么?”
“他已经等不了了。”
罗警官觉得我在胡言乱语,他让我马上到C市接受调查。
案情已经非常明了,我在警局待了不到一刻钟他们就放我走了,罗警官也觉得有些无趣,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决定带我到独孤君的住所看看。
这是一个待拆迁的城中村,低矮的房子,斜斜的电线杆子仿佛随时会被风刮倒。一个胖女人立在小屋前,她听说我是独孤君的朋友,立马拿出像雪花一样多的账单。
独孤君起码有六个月没有交低廉的房租了。
独孤君的水费、电费、煤气费、宽带费都欠费了。
独孤君赊下巷子拐角的一间小饭馆数千元的菜金……
我不觉眼睛有些发酸,我摔开胖女人拦在门前的手说:“独孤君从来视金钱如粪土,他欠着的我会全部替他埋单!”
我闯进独孤君的小屋,屋内还算整洁,除一床、一桌、两个书架外别无他物。我在他书桌旁坐下,桌上堆满了退稿的信件,像一沓无力飞翔的蝴蝶贴伏在地面上。我打开独孤君的电脑,他的邮箱中依旧塞满了众多的退稿邮件,而在草稿箱里,我找到了孤零零躺着的一封信,闪烁着像萤火虫一样的绿光,那是他写给我的,我不知道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寄出。
在那封邮件里,他简单地向我交代两件事,仿佛只是出趟远门。其一,他让我帮他整理所有的稿件,该烧的烧了,该留的留下。其二,他恳求我以“独孤君”为笔名继续写作。
独孤君为什么会选择我?我只是每天为了蝇头小利忙得焦头烂额的俗人,我不再年轻,我是否还有梦想?
那一晚我没有走,我端坐在独孤君的书桌前,我的手指飞快地敲打着键盘,那样急促的嗒嗒声仿佛是山涧奔向早春的河流,我抬起头看到窗外飞出无数点如萤火虫的亮片,它们向我围绕……
原来独孤君并没有离开。
选自《小说月刊》
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