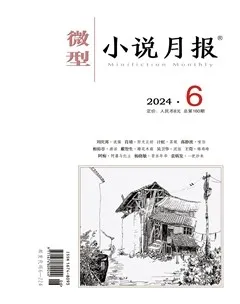我的太阳
李春华
邻居吴叔是音乐学院的博导,每逢星期天就在家里吊嗓练歌,即便是清唱,且门窗紧闭,那些雄浑、高亢的音符,也能打着滚钻进吕彪的耳朵,就像钻进了毛毛虫,不光耳朵痒,心里也痒痒。
吕彪试探着轻轻敲吴叔家门。嗒嗒嗒!
进来!吴叔磁性的声音入耳,他进门,吴叔侧身歪着头问他,喜欢美声?吕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拨浪鼓似的摇摇头。再看吴叔的装扮:一身黑色燕尾服、白色双翼衬衣,扎白色领花,锃亮的皮鞋能照见人。呵,绅士啊。吕彪咧着嘴,摸摸后脑勺,在边上傻笑。
刚才您唱的啥歌?
帕瓦罗蒂唱过,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
哦,听着真提精神!
嗯,美声是声乐的阳春白雪……
吴叔上下打量吕彪,说,嗯,长相端正,气质不错,个头够高,压得住台。
吕彪心里像装个太阳,暖暖的,有空就跟吴叔咪咪嘛嘛地开嗓练功,成了吴家的常客。不出吴叔所料,他天生是这块料,得过不少声乐奖项。
高考前夕,艺术类考生提前报志愿,初试专业课。老妈听说吕彪报考音乐学院,陡然像头母狮,戳着他的鼻尖吼,玩玩得了,穿个屁股帘咪咪嘛嘛唱一辈子?扭脸看儿子,她的话分明就是耳边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初试日期已定,吕彪要去北京考点应试。他反倒沉着脸,心里怦怦直打鼓。吴叔安慰说,你的专业课过硬,正常发挥就成。
许是家里暖气温度高,白天开窗户,潲进冷风,夜里,吕彪高烧直说胡话,嘴唇干裂,暴一层皮。一早,老妈叫来厂医,确诊是急性肺炎……冰凉的液体缓缓流进血管,吕彪的心也凉了半截,或许跟美声有缘无分吧。
师徒二人,在剧院同台演唱《我的太阳》,台下的座位空着。曲终人散,吕彪冲着吴叔的背影,深鞠一躬。
吕彪从综合大学导游专业毕业,想去国外当导游。可是老妈要做急性阑尾炎手术,怎能这会儿出国带团?何况,他从小到大,老爸都在矿上忙,不见人影。老妈在服装厂,整天不住闲地蹬缝纫机,喊着腰酸背疼,还给他洗衣做饭。娘儿俩像秤离不开秤砣,哪头重哪头轻呀。按老妈的想法,先在矿上干,不行再辞职呗。
吕彪的师傅老余黑脸膛,一对眼珠贼亮,瘦削的骨架支棱着松垮的卡其色工装——吕彪猛然想到螳螂,差点笑场,顺势弯腰鞠躬。老余斜楞着眼,像见到了怪物。呵,长发飘飘,牛仔裤筒有几个甩着飞边的洞。老余眉头一皱,跟老吕的秉性满拧呀。这范儿干安全检查?老余脸一沉,赶明儿剪寸头,把裤腿的窟窿堵上。吕彪点头,暗自嘀咕,又不是工装。
起初,吕彪坐着矿井升降机下井,身体急速下坠,一阵心悸,轰隆隆的噪声,震得耳朵嗡嗡地响,他权当是歌剧前奏慢慢适应。
工作间附近的巷道,有条洗煤留下的溪流,整日哗哗地流。吕彪拎着矿灯蹲下,一缕光柱里有一团小虾,江米粒大,通体透明,在水里游得可欢实了。他探身再看,咦!地面上的河虾,有两个鼓鼓的黑豆眼睛。它们的眼睛竟是俩小白点!
吕彪问老余,巷道溪流里的小虾没眼睛,咋游得那么欢实?
老余指指心口窝说,它们心里有光啊……
哦。
吕彪检查完通风设备,记停当了台账,咬几口馒头,倚着木料堆晕晕乎乎……恍惚中,他站在舞台上投入地唱《我的太阳》……
老余悄声来复检,见吕彪打瞌睡,手里还捏着馒头。看他穿藏蓝色棉工装,外披狗皮马甲,脚穿黑色长筒胶鞋。老余咧咧嘴,这打扮像模像样,倒像老吕几分。
谁知,老鼠冷不丁叼走吕彪手中的馒头,吕彪打个激灵醒了。工友们追打老鼠。或许,阴冷潮湿的巷道适合老鼠生存,它们体形肥硕,瞪着血红的眼睛,四下踅摸。工友们习惯把馒头放变压器上加热,被老鼠叼走馒头是常事。
吕彪想老鼠好歹是活物,巷道里有它们活泛哪。
吕彪两臂伸开,横在中间,说,留个喘气的吧!
工友们哈哈一笑散去。老鼠哧溜钻进鼠洞。老余心一动,在一边抿嘴笑,嗯,彪子心善,着实像他爸。
矿务局有歌咏大赛参加不?半晌没人吱声。老余瞄了眼吕彪和其他徒弟,从牙缝挤出一句话:一群废物!
师傅,我唱美声!
哈哈!一阵哄笑,众人像受惊的麻雀呼啦散了。
吕彪忙完,躲在巷道旮旯,清唱《我的太阳》。歌声像长了翅膀,飞到巷道角落;木桩上艳丽的蘑菇似乎都在颤悠;老鼠哧溜哧溜来回跑,像在给他伴舞。
那天,老余和徒弟们半信半疑地坐在前排。吕彪穿着燕尾服,扎白色领花,蹬黑色皮鞋,优雅地上场。前奏响起,他一开腔,雄浑金属般的男高音响彻全场,掌声如潮。
台下的老余使劲儿鼓掌,小声嘀咕,咱整天在巷道干活,见不着个阳光。听彪子唱的《我的太阳》,身子里咋像装着太阳,忒热乎!
徒弟们拍着巴掌点头。
结果毫无悬念,吕彪得第一。
一日,老余接完厂部电话,像中了大奖,小跑到工作间,扯着嗓门喊,彪子,明天去矿务局文工团报到!
选自《安徽文学》
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