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复乐古器古曲》中的音乐思想探析
潘娜 严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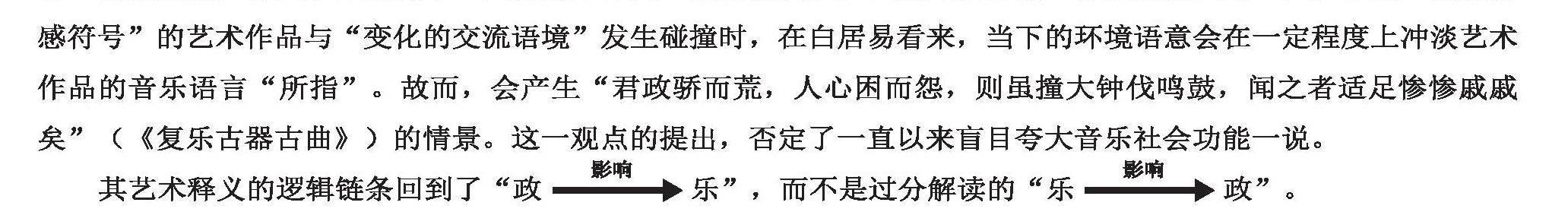
摘要:本文以白居易《复乐古器古曲》文本为基础,探析了其音乐思想中对“雅郑”关系、古今关系的认识。通过对文本中“正始之声”“乐教”“乐不可伪”等理念的分析,笔者认为白居易在此文中所表现的音乐美学逻辑具有儒家文化特有的空间布局,通过对“乐与政”耦合关系阐释,完成了其音乐实践审美体验的多重性构建。
关键词:乐教 乐与政 审美主体
白居易作为唐代最为著名的大诗人之一,不仅诗文出众,还一生与琴为伴,与音乐为伴,常“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①。在寄情于音乐的同时,他也将音乐寄于诗文之中,言乐论乐。公元806年,白居易为参加制举考试,独自拟作75篇试策,合为《策林》。在《策林》中,白居易从君道、施政、选贤、吏治、慎刑、御兵、恤民、文教等八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策林》被视为“策论”中的典范,成为唐代科考的圭臬。贯穿于其中的以“民为本”的家国理念核心,辩证地展现了白居易的政治抱负和礼乐文教观点,是研究其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
《复乐古器古曲》(下文也简称为《复乐》)正是《策林》中的一篇。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虽与儒家《礼记》中的某些观点有附和,但亦提出了对音乐的不同认识。文中对音乐的雅郑关系、古今关系进行了阐释,进而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辨析。以白居易的文本为基础,可以看出早期他对礼乐文教较为辩证和客观的理性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音乐的实际赏析中,白居易对于音乐中古今关系的认识常受到自身好恶左右。本文仅从《复乐古器古曲》一文的文本出发,讨论白居易在这一策论中的音乐思想。
一、对儒家思想中“正始之声”与“乐教”理念的认同
“乐教”一直是儒家音乐理念中非常重要的观点。西周礼乐制度伊始,音乐为政治、德行服务成为了国家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为儒家再次设立系统的乐教思想提供了平台。儒家代表荀子曾在《乐论》篇中根据音乐的特征剖析音乐的功能,其中涉及“审一定和”的观念,“故乐者……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②按蔡仲德先生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中的解释:“音乐既足以表现先王之道,又足以表现千变万化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使之最终合于先王之道。”③“夫声音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④荀子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将音乐“养耳”“道志”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地阐述,从而基本搭建了儒家乐教理念的思维模型。在这一模型内部形成了三层空间布局,即:
“礼”“乐”的表象实践 “养耳”“道志”文化内涵的输出 “正始之声”观念的社会认同
这一布局以音乐实践为基础,音乐的“他律性”为美学根基,完成了儒家音乐意识中“教化”功能的最终实现。同时,也开启了我国正统礼乐思想的深入化构建。虽然魏晋之后乐教思想曾一度被打破。但其植根于中国文人思想中的核心影响力却如暗流涌动,深刻于文化源流的隐性基因之中。故,至唐代后,随着统治阶级对音乐文化的重视,这一隐性基因无疑会以更为强化的意识,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特征化表现。
白居易在《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中提到“正始之音”一词。何谓“正始之音”,在《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一诗中他曾有如下表述:“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谈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⑤蔡仲德先生在其《中国音乐美学史》一书中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分析,认为白居易的“正始之音”代表的是“礼乐”“雅颂之乐”⑥。如果以这一释义为基础,则可以剖析出白居易乐教理念中深层的思维逻辑:即以“礼乐雅颂之乐”作为社会音乐思想的底层逻辑,以此构建起他认同的“正统乐教”体系。音乐在这里有了标准的审美规范,并且以此规范为基础,对社会音乐生活完成多维度的历史搭建。“在音乐中,存在着对价值与意义、以及世界观与概念等方面的解释。”⑦这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民族音乐学家洛马克斯,针对“文化中的音乐”这一论题提出的观点。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音乐实践表象下的逻辑意识才是音乐得以发展的动力。而在一个社会环境、群体范围以及文化思维惯性的形成过程中,建立主流的文化意识观念和标准成为了历代中国文人下意识的社会举动。究其根源,则是西周至春秋以来构建起的“士文化”理念的辐射式发展。白居易的音乐观念,毫无疑问,是与这一理念相吻合的。这种吻合首先基于对“士”阶层身份的认同。作为唐代中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白居易自小有较深的家学渊源,世敦儒业。这样的生活背景,必然会形成对“正声”和“乐教”理念的认同。《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作于其科举之前,此时正为其意气风发之时。强调为维护“正始之音”的重要性,为白居易的音乐观念奠定了思维底色。从这一底色出发,音乐实践描述和音乐理论的构建都会形成特有的价值反馈和文化内涵。
因此,笔者认为,以《复乐古器古曲》为分析文本解析白居易的音乐思想时,将“儒学”“正教”理念作为前提,是客观认识其音乐理论观念的根本。即使在某些文字的描述中我们会看到其受到魏晋思想和唐开元年间唐太宗和魏征音乐理念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学正统的观念仍然是其认识和考察音乐的基本逻辑。
二、从“古器”“今曲”中审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
儒家自始以来重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且一直认为“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复乐古器古曲》)。音乐是对政治、德行的表现。《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中多次提到“正始之音”,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白居易的音乐观承袭了对这一表现的认识,其音乐审美的基本路径与儒家正统如出一辙。然而,在阐释政与乐的逻辑链条时,白居易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其他儒家学者的论述往往仅对音乐泛泛地进行定义,而白居易则不同。他认识到音乐实践中的多重性,即包括了创作、表演、欣赏三个层面的审美体系。在文中,他的审美触角拓展到了对音乐演奏、表演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古器”“古曲”“今器”“今曲”的概念。
首先,他提出:“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也。”(《复乐古器古曲》)可见,在白居易看来,声音的“邪正”与“器”的“今古”无关,不会因为演奏乐器的古老与否而改变;乐曲的“哀乐”与“曲”无关,亦不会因为乐曲演奏时代的转换而消失。音乐所表达的内涵与当时创作中所感受、理解的情感有关。因此,笔者认为白居易对音乐中“一度创作”所奠定的音乐基调是持肯定观点的,且认为在整个音乐发展的历程中,创作者所奠定的情绪认知、内容铺垫,对音乐的流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进而,他又提出了对“若废今器,用古器,则哀淫之音息矣;若舍今曲,奏古曲,则正始之音兴矣。”(《复乐古器古曲》)这一观点的质疑。《复乐》一文中提到,在“政荒”“人怨”的社会环境下,即使采用古代先王所用的“古器”奏乐,其“哀淫之声”也不会散去。“古器”“古曲”中的“正始之音”表现的是“古时”的“清正”,而若“哀淫”的社会环境发生在“今时”,这种“清正”是无法完全转变社会风气的。因此,在白居易此文的思维逻辑中,政治、情感、音乐的关系,所形成对的图谱应为:
政和 情和 乐和(强调政治对音乐的作用)
而非一直以来儒家所强调的逆循环亦成立的关系。
乐和 情和 政和(过度夸大音乐对政治的作用)
这一观点的提出,恰好与唐太宗李世民对音乐的认识相似。李世民曾与太常少卿祖孝孙讨论音乐,说“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乐在人和,不由音调”⑧。剖析其内核会发现,其焦点在于反对企图通过音乐完全改变现实社会的“清”“浊”。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由政入乐”的关系,反之则未必成立。“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复乐古器古曲》)“今器”“古器”只是音乐的表现手段,政治导致的“哀淫之声”,不会因为使用了先贤所用的乐器而有所消散。在白居易看来,这三者之间从属于两个不同的认知层面。
以此为基础,文中提出了对“郑卫之音”的认识——“善其政,和其情”(《复乐古器古曲》)。从其表述中,笔者大胆猜测“郑卫之音”在文中的意义,有可能不再是特指某种音乐类型,而是成为了一种配合社会心理的实践行为。在《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中白居易多次提出了对“正始之音”的推崇。并通过《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一诗对“正始之音”进行了解释,认为其形式应为“曲澹”而“声稀”,最终达到的情感效果是“心平和”。而在《复乐》一文中,更是提出真正使人心“平和”的是“政和”。从表面上看这两个论述似有相悖,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儒家在论述“郑卫之声”时,一直关联的是对社会政治的认知,并非从音乐具体的形式来阐述。因此,回归到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中,是否亦可以认为,此时所说的“郑卫之声”更多的是从“政”角度上的判断,而非对音乐本体内容的理解。因此,白居易才会说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在他看来只要君正和平、人心安乐,即使出现像“郑卫之声”中“援蒉桴击野壤”的音乐形式,听到的人也可感到“融融泄泄”(上述两句引文均见《复乐古器古曲》)。因此,即使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其“他律性”重要的特征,但在白居易的《复乐》一文中并不主张夸大其功能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跳出了大多数儒家学者对音乐狭隘的认知。
三、对“乐者不可以伪”的认识
音乐除了在“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中会被赋予意义以外,作为艺术作品审美的讫点——听众,其特有的审美心境和欣赏语境,也会成为音乐作品审美意义末端的赋予者。因此白居易在《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中所提到的“乐者不可以伪”,此处的“伪”兼有创作中的心境表达和审美过程中的心境表达之双层意义。谢嘉幸在其《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野》一文中提道:“音乐文本都是针对处于特定语境范畴的人——主体而存在的。因此,音乐文本所体现的价值视其与不同交流语境的关系而定。相同的音乐文本在不同的交流语境(含共时与历时的不同语境)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价值。”⑨音乐审美过程中主体语境的改变条件是多元的,最常见的是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而艺术作品文本一旦形成即有其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所谓的“特定语境范畴”。当作为“特定情感符号”的艺术作品与“变化的交流语境”发生碰撞时,在白居易看来,当下的环境语意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艺术作品的音乐语言“所指”。故而,会产生“君政骄而荒,人心困而怨,则虽撞大钟伐鸣鼓,闻之者适足惨惨戚戚矣”(《复乐古器古曲》)的情景。这一观点的提出,否定了一直以来盲目夸大音乐社会功能一说。
其艺术释义的逻辑链条回到了“政 乐”,而不是过分解读的“乐 政”。
“乐者不可以伪”一说中,乐者的含义,从以上解读中也逐渐清晰,他不仅包括了创作者、表演者,同时也包括了赏乐者。艺术审美的多层结构中都具有人的意识参与,当创作者和表演者将艺术理念客观化、外在化呈现后,赏乐者的审美主体意识(除了部分会受到客观艺术语境的影响外),必然也会受到自身真实体验和情感的左右。因此在《复乐古器古曲》一文中,所提到的“不可以伪”,笔者认为应该是指通过“善其政和其情”最终达到“乐和”的境界,而不是单纯地“改其器易其曲”完成的“乐和”假象。音乐欣赏的过程中包含了主体的创造性⑩,而这种创造性基于音乐的非语意性特征。在不同社会政治环境和不同语境理解下最终完成艺术内容的变迁。仅从对此篇散文的文本解读上看,白居易的音乐理念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这种理念的闪现是不具备稳定性的,从白居易的其他文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策论中的思想并没有得到系统式的阐释。
结语
作为唐代以乐入诗的重要代表人物,白居易对音乐的认识以创作和表演实践为着眼点,进而形成了特有的音乐美学价值理念。其中,对“乐与政通”,以及“正声”“乐教”理念的认同,承继了儒家礼乐观念,即重视和强调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但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颖的视角和思想。如,他在《复乐古器古曲》中提出,“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和而平,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对儒家一直以来强调音乐之于政治的教化作用进行了论辩和反思。此外,通过“不可以伪”的视角对乐与政的关系进行论述,表达了一个刚刚步入仕途的青年人对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清醒认识。这种反思和批判在白居易的音乐文论中是具有特殊性的,也是极其珍贵的。
《策林》虽是白居易为应制举而作的时事对策,却满怀济世热情和政治倾诉,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对政治时事的思考认知和勇敢无畏的批评态度。因此,文中那些新视角、新思想有时也变成他自相矛盾的痛点,但正是这些“痛点”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完整丰满、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达济天下,穷修其身”,为实现理想抱负积极作为的青年乐天形象,为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白居易提供了路径和例证。
注释:
①[宋]李昉辑:《文苑英华》(1000卷),明刻本,第4页。
②[东周]荀况撰,[唐]杨倞注,[清]卢文弨校補:《荀子》(20卷),清乾隆嘉庆间嘉善谢氏刻抱经堂丛书本,第1页。
③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④[东周]荀况撰,[唐]杨倞注,[清]卢文弨校補:《荀子》(20卷),清乾隆嘉庆间嘉善谢氏刻抱经堂丛书本,第2页。
⑤[唐]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71卷),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日本元和间活字本),第16页。
⑥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614页。
⑦张伯瑜:《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⑧[唐]吴兢撰,[元]戈直集论:《贞观政要》(十卷),清康熙潜江朱氏大易阁大字刻本,第23页。
⑨谢嘉幸:《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野》,《中国音乐》,2005年,第2期,第50-51页。
⑩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2年,第177页。
参考文献:
[1]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75-178页。
[2]秦序:《崇雅与爱俗的矛盾组合——多层面的白居易音乐美学观及其变化发展》,《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6-18页。
[3]葛蓁蓁:《白居易音乐思想中的三重身份交织特征探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81-91页。
作者简介:潘娜,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音乐表演系讲师
严薇,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日本现存唐乐曲研究”(19BD061)阶段性成果。
——长春市第一中学学校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