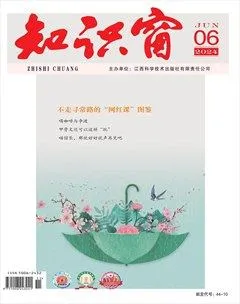鸟叫与鸟鸣
韩钦明
鸟鸣是伴随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挤进窗棂的,它清脆、婉转,愉悦着我的耳朵。我疑心是在梦中,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怕稍一翻身,会惊飞这天籁。
鸟鸣是从院子墙边的洋槐树上传来的,树长在隔壁人家的老院子里。因久未住人,院子里老屋的青砖黛瓦已显陈旧,如同岁月剥蚀的古董。院子不大,却冒出许多植物。除了这棵洋槐树,还长出了椿、榆、楮等树木,每棵树都无拘无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长着,显示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这里成了鸟儿的乐园。
我没留意过那些鸟儿的种类,许多鸟儿我也叫不上名字,四季里总有它们的声音和身影。鸟儿三五成群、七八只一伙的,叽叽喳喳,有时争吵,有时嬉戏,有时似乎在比赛唱歌,有时在枝头蹦来跳去,如树之精灵。我听不懂它们鸣叫的内容,但我能感受到它们自由舒展的快乐,以及自然且发自内心的歌声。
那天去拜访亲戚,我看到房间里悬挂着许多鸟笼子,形状各异,琳琅满目。有的笼子还用厚厚的黑布罩着,很神秘的样子。几只红嘴黄鸟在笼子里蹦来跳去,不知道是在跳舞还是在挣扎。亲戚看我对他的鸟笼感兴趣,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他的这些宠物:“这个是鹦鹉,那个是画眉,黑色的是八哥,黄色的是黄鹂。”他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亲戚说,在每天清晨,他都要担着这些鸟笼去另一个地方遛鸟。我问:“有必要跑这么远吗?”他说:“这里没有树木,空气也不好,车来人往的,会惊着鸟儿。”
这是一处新建的住宅区,到处是水泥建筑,道路两旁的树木细细的,无精打采,显出营养不良的窘相。天空中看不到鸟,更听不到鸟的鸣叫,只有几片灰白的云,如同破败的棉絮,在灰蒙蒙的天际懒懒地缩成一团。
我期望有鸟儿掠过,但没有一只鸟飞翔的影子。
鸟都在亲戚的笼子里吗?
亲戚并没有留意我在仰望天空,他打开鸟笼的黑罩子,一只褐色的鸟惊恐地在笼子里上蹿下跳。亲戚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嘘声,似乎在安抚鸟儿。待鸟儿安静下来,我和亲戚都期望它叫几声,可是鸟儿好像不屑一顾,蹲在笼子的细棍上东张西望。亲戚又是添食,又是引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鸟儿也没给亲戚一点点面子。
“早上遛鸟的时候,它叫得可好听了。”亲戚讪讪地说。我说:“也许它倦了。”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挂满鸟笼的房间,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的耳边或是脑海里蓦然就闪过《囚鸟》这首歌曲:“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人类从山林里进化出来之前,与其他生物共生共存,应该具备一种天地自然的情结吧。而现今,建筑越来越密,道路越修越宽,楼房越盖越高;而河道越来越窄,树木越来越稀,植被越来越少。人类一步步挤压着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周遭充斥的不是天籁,而是车的噪声、机械的喧嚣和人群的吵闹。
人为了能欣赏到悦耳的鸣叫,将本来属于自然的、属于天空的生灵囚禁于笼,逼着它们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献媚讨好。
所幸,我还有窗外这座小小的绿岛,还有一群群鸟儿翩然飞来,每天都唱着悦耳的歌谣。这是鸟鸣——一种自由的吟咏、无拘无束的发自内心的灵魂引吭,它不同于囚在笼子里的鸟叫,无奈、机械与哀怨。
这种天籁常常让我激动不已,只有飞翔在天空的鸟儿才能“声生不息”。
鸟叫与鸟鸣,绝对是两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