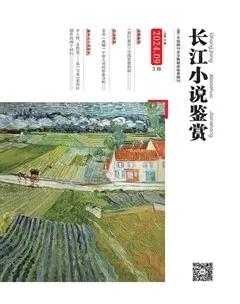穿越苍凉的人生
崔云红
[摘 要] 张爱玲是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家,她的作品不仅充满了对女性命运及其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对于人性尤其是对于大变动时代微不足道的普遍生命一直予以深情的关注。张爱玲由于自身特殊的成长经历,导致她笔下塑造出的女性形象或多或少都带有不同苍凉色调的悲剧命运。她思想中的现代哲学视角切入,使她对生命规律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穿越张爱玲给读者制造的苍凉人生,可以洞悉她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对女性出路、命运的不懈探索;通过特有的历史书写方式,在苍凉故事背后展现对现实世界深切的痛悼。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 苍凉 悲剧
[中图分类号] I2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7-2881(2024)09-0074-04
张爱玲,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如彗星骤然降临,带来一片炫目的奇光,与此同时,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研究热。但只是短短的几年,又如彗星般转瞬即逝。直到后来,她带着一段苍凉的爱情故事,留居美国,悄然离世,她又一次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之后又归于沉寂。这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这样一位传奇般的女子,留下了传奇般的作品,吸引了无数好奇的人去研究,而且硕果颇丰。尽管研究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称她的作品“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对于她作品的苍凉基调,对人生的悲观情绪已达成共识。
在笔者看来张爱玲的作品绝不仅仅止于展示苍凉的人生,或像有人说的:演绎都市中饮食男女的小悲欢,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内蕴,需要进一步解读。杰姆逊在比较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文化形式差异时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式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1]他还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杰姆逊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当代第三世界文化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也即西方文化的渗透而产生困惑与焦虑的分析上的。故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很难成为纯个人化的文本,相反,它常常是“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对整个整体的艰难叙述”以此精辟的分析作为指引,我们就能穿越张爱玲给我们制造的苍凉人生,而去洞悉作家深刻的思想内蕴。
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注首先基于她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出路、命运,她一直在做着不懈的探索。首先,她在文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幸的女人:有套在黄金枷锁中的七巧与银娣;有清醒的堕落者,葛薇龙;有放纵欲望,依靠色相的霓喜;更有一批“美丽而绝望的夫人”,如:娄太太、匡太太、白老太太等等。作者极为冷酷地展示了她们苍凉的人生,并对造成这苍凉人生的旧时代做了一次大扫除,席卷了所有隐藏在死角里的梦魇与黑幕,给那个黑暗苍凉的时代做了一次健康检查,告诉我们此路不通。就像唐文标先生所言的“她一再替我们点出这条不能再走下去的死亡之路,使我们踏上正途”[2]。
张爱玲对女性独立自主意识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就有了体现。最典型的是在历史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可以看作是她的一篇宣言。文中,她改写了代代沿袭的英雄美人模式,否定了传统的美人伴英雄或美人甘心为英雄殉情的女性生存价值,以惊世骇俗的笔把“霸王别姬”写成了“姬别霸王”。在传统的女权封建文化中,女性是毫无主体性可言的,因此便有“女人是月亮,是依赖他人而生存,借别人的光而生辉的,有着病人一般苍白面孔的月亮”[3]之说。而她笔下的虞姬,却否定了“太阳和月亮”这一传统两性关系模式,她开始思索自己的生存目的和意义:“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英雄的呼啸中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如果项王成功:“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者贤穆贵妃的谥号……”她看清楚了无论他成功与否,她只能是承受和反射太阳光的月亮。她作为人的女性生存权利和愿望是被男权主义所剥夺和淹没了的。她要按照自己的愿望认真地活一回或者死一回,于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比较喜欢的收场”,在项王突围之前拔刀自刎。
虞姬在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决绝惨烈的死去了,难道女性的命运注定如此苍凉没有一条出路吗?不,透过一个个曲折、幽怨、悲切的故事,我们看到张爱玲在她的笔下也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女性——顾曼桢。她比《创世纪》中的虞家茵乐观、开朗、向上。“她的脚踝是那样纤细而又坚强,正如她的为人。”一个人支撑着全家人的生活。她是一个走出家的女性。对爱情纯情又多情:“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等着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样一个人”。她是高尚的,对助纣为虐的曼璐,感情是复杂的,认识到制造曼璐悲剧的是罪恶的社会。她深恶痛绝祝鸿才,可是为了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的儿子,她妥协了,这是她的母性的最光辉的表现。后来,她毅然决然与祝鸿才离了婚,走向光明,走向幸福。“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4]顾曼桢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女人。
在中国女性作家里,还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那样孜孜于女性凄惨、悲凉的命运的写生。她对她笔下的女性无不呈现出一种同情,可以说“她的同情心无所不包”[5]。但这并没有遮蔽她锐利的眼睛,她对女性进行了“人性恶”的剖视,打开了对女人自我负面认识的锁头,这是她的独特贡献。
张爱玲笔下最能体现“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的无孔不入”的莫过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了。她先是以自己的青春换取黄金枷锁,满足了黄金欲,然后情欲复燃,二者畸形地结合,成为一种疯狂的变态心理。常言道,虎毒不食子,而她却在自己得不到幸福和爱情的情况下,在儿女身上报复情欲对自己的折磨,吞噬了亲生儿女的幸福和爱情。作者那冷酷的笔调,让人读来脊背发凉:世间竟还有这样的母亲?作者毫不留情的展示了一个在黄金枷锁下丧失了母性和妻性女人的“丑史”。张爱玲有着极为冷静的理性思维,透过女人种种不幸的遭遇展示了女性内心阴冷、残酷的一面,拓展了女性自我认知的空间。
“女人在为男人活着,对于大多数的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现代人多是疲惫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可以说是女性文学最大的母题,在她笔下几乎没有一桩完美的婚姻。但这些文章背后恰恰表现了她对于理想两性关系降临的祈望。女性对于永恒爱情的宿命般的追求才是张爱玲作品真正表现的主题。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学生葛薇龙,出演的就是一出女性为了爱情毁灭自身的悲剧。她爱上了一个根本不值得她爱的浮浪子弟——乔琪乔。可一个女人陷入爱情之后是根本不可理喻的。薇龙笑着:“我爱你,关你什么事儿?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此时她爱的已不是面前的这个男人,而是她心中已经理想化了的那份爱情的幻影。女人永远是女人,为感情而活,为爱而生,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张爱玲笔下还有许多为了自己的爱情而执着追求的女性。虞家茵、宝滟身上似乎有着更多的理性色彩,她们追求的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爱情。而在这一系列追求爱情的女性中,迈出更超前一步的是王娇蕊。“她的一技之长是玩弄男人。”婚前如此,婚后亦然。可当她遇到佟振保时,就结束了这种游戏的态度。因为她真心真意的爱上了这个男人,无条件的付出她的情感。她忠实于自己,也学会了接受别人。我们不能不承认,王娇蕊是一个有女性觉醒意义的光辉形象,这也是张爱玲对女性意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是一位极具女性意识的作家,她描写了女性种种悲惨的命运,对女性充满了同情与宽容。但这并不妨碍她以凌厉的笔触解剖女性内心深处“恶”的方面,她是一个真诚的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少有美满的婚姻,但是她却描写出了女性对爱情宿命般地追求,她是一位深刻的作家;她对女性的出路进行着自觉的孜孜不倦的思考与探索,这也是至今困扰女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她又是一位女性主义的先行者;她总是不动声色,隐自己于一个个苍凉的故事背后,故她又是一位冷静的智者。
然而,张爱玲仅是一位女性主义的作家吗?恐怕我们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张爱玲追求的是人生永恒的东西,而她又把这一永恒归为“妇人性”,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柱上。”由这两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更加关注的是具有永恒意味的普遍人生。而她对人生的关怀是从女性入手,以女性为基础的。她们充满生命的热情和活力,有着蓬勃的爱欲和广博的同情与慈悲,代表了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永恒,健康的人生。
二、对人生人性的普遍关注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深刻变迁的时代,但是她并没有像丁玲们那样选取人生飞扬的一面,写“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在轰轰烈烈的新旧冲突中表现作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她甚至只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她认为,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男女之情的朴素和放恣无疑是渗透于人生全面的,负载着更深刻的现实内容。前文,我们已经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进行了分析。作为完整的人生还应有另一半的天空,那就是男性世界。张爱玲还塑造了一系列男性形象,对他们张爱玲有着同对女性一样深刻的洞察与思考,这构成了张爱玲对整个人生,人性的普遍关注。
张爱玲笔下塑造了两类男性形象。一类是一批终日无所事事,袖着手到处打秋风的遗老遗少。他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偏又架子十足在坐吃山空的情况下还要撑门面。张爱玲对他们做了最尖锐的批判,说他们是“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对他们最辛辣的讽刺是:“他们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在他们身上显示的是人性的怯懦、虚伪、懒惰与生命力日渐萎缩。另一类是新生时代中的都市浪子,如乔琪乔、范柳原、长安、姚三爷等等也不外是金钱的俘虏,小奸小滑、自私自利的花花公子,诱良为娼,专吃软饭的地痞流氓。故事里这些人代表了人性的自私、贪欲、残狠、沉迷以及社会道德沦丧的堕落。作者写来从容不迫,确实又令人触目惊心、齿根发冷。张爱玲就是这样冷静地解剖人性,让我们来正视现实,“张爱玲是这个没落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无怪乎大家对她笔调的苍凉是众口一词。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作品再仔细品味一下,按我们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理论来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她只是在运用了深度的观察力,洞察世情后冷冷静静地替这现实开了一次刀,做了一个切片。她的世界确实有些苍凉、黑暗,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作品让读者“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相反的“是她的一颗敏感悲悯的心与一支呼风唤雨的巧笔,领导着五四以来日益光大的中国文坛,一级一级地走进了光风霁月,光明灿烂的领域!”
传统道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受到了严峻挑战,面对斑斓的沪港洋场,张爱玲把尘世的喧嚣恼人,人生的惨伤沉落,生命的琐屑卑微化成一阵阵失落感、苍凉感、娓娓道来。她所执着揭示的正是都市人性的现代意义。她打碎了古朴的“善”、“恶”观念,将其掺和起来,重新塑造,在苦苦求生存时,会有无数的内因或外因,诱使人显露本性——那里就有着惊心动魄的善恶在殊死搏杀。在搏杀中给人以求生存的亮色,从中显示着张爱玲对人生普遍关怀的独特视角。
人与环境抗衡最激烈的要数《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遗少父亲,绣在屏风上褪毛鸟似地母亲,态度冷酷的后母,弥漫着鸦片烟香的家。这就是聂传庆的生活环境。无可指责地形成了他衰颓的、无能的、变态的性格。又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然而张爱玲并没有让他一步步就此扼杀,而是给予了他反抗的性格和渴望正常生活的灵魂。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不多见,却也表达了她对现实不满背后,对生命的热情。
聂传庆不愿意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憎恨厌恶他的父亲和家庭,而又无能为力。人的最大也最持久的痛苦在于:“他处在一个蔑视他作为人存在的地方,仍然不能完全忘怀自己是一个‘人”。当代表着健康生活的言子夜教授和她的女儿丹朱出现后,聂传庆昏睡的心灵被震醒了,宁可毁了自己也要去冲那囚禁人性的牢笼,做了最后绝望的反抗。虽然这牺牲盲目甚至病态,但我们在他心理扭曲导致的变态行为背后,却明显感到自然之子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壮,传达了人性觉醒的新信息。
她强调生命,懂得生命之奇特,也懂得生命之短暂不易,尤其对于大变动时代微不足道的普遍生命予以深情的关注。她执着于人性的真实、畸形、变态尽收眼底,“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她在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历史的重构。她的历史由一些“不相干”的事组成。这些“不相干”的苍凉故事背后有深切的痛悼与凄怨,更有默默无声的誓言:这种惨状再不能容忍继续下去了。
张爱玲的小说内容是清一色的琐碎人生。人物是一些彻底或不彻底的真实人物“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6]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启示呢?这是解读张爱玲创作深层意蕴的一把钥匙。可以这样理解:张爱玲的这些小说不是时代生活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部分,但它们像一个视窗,可以透视人生百态,他们是这重要时代风潮的灰色背景。如果没有这些灰色的人生背景,便聚不成带有亮色的生活主流和时代风云;也就是说,那些带有鲜明色彩的生活主流和时代风云正是为了改造这灰色的人生背景。从此意义上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它与那些写生活主流,时代色彩浓厚的小说在价值指向上是相同的。他们不仅仅是止于苍凉,相反是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
三、总结
在解读作品时,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水平绝不等于作家的思想水平,二者应区别对待;同时,也不能局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环境,而是应透过文本的表层,对隐匿其后作者的深层叙述进行挖掘。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中西合璧”的女作家更应如此。她思想中的现代哲学视角的切入,使她具备了更高的眼光,能够看到文学史所忽视的东西,并且作为女性作家,她对生命规律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因而,她的作品也就具有了更深的思想内蕴,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和思索。本文就是笔者的一点尝试。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 唐文标.张爱玲杂碎[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
[3] (日)富士谷笃子主编,张萍译.女性学入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
[4] 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特约编辑 范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