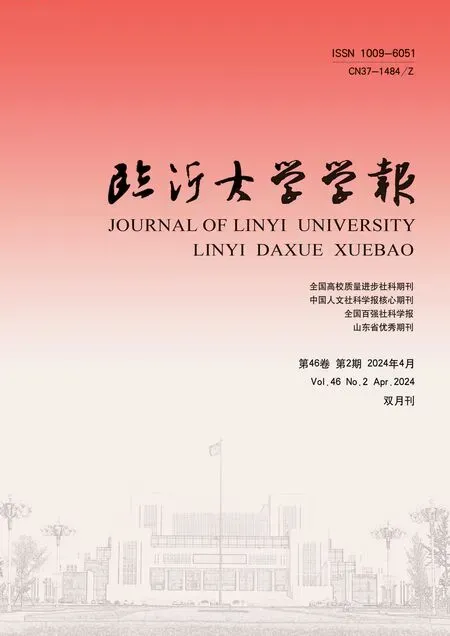直而已矣,然是否真?
——也论儒家观念中的“亲隐”问题
周建漳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由2002 年第2 期《哲学研究》发表刘清平先生《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肇其端,围绕其关于儒家文化内涵“徇情枉法”腐败基因的批判性论点,持赞同与反对意见的双方基本以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为分野展开了声量颇高的理论论争,主要文稿分别见于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邓晓芒的《儒家伦理新批判》和郭齐勇主编的针对邓说的《〈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三本集子中。2019 年第6 期《中原文化研究》发表的刘清平《再谈“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与韩东屏教授商榷》一文是目前所见最后一篇与此相关的文字。①
论争的焦点是关于“亲亲相隐”的正反伦理及文化评价,其中涉及《论语》与《孟子》中三段话的文本解读,旁涉相关法律规定、儒家传统的整体阐释与评价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古今之辩”等。这一讨论为我们理解儒家思想及其正负方面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切入点,启人思考,是必要和有益的。笔者在上述两派立场间无单面取向——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儒家文化本身无立场倾向,但对于这一道德选择的两难问题非此即彼的理论取态不以为然。我希望在新视角下给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以此就教于学界尤其是这场讨论中的各位先进。
一、文本解读
依我浅见,这场围绕孔、孟三个文本的争论最大的特点与不足,是双方对于原始文本的解读有欠细致和理论阐释上陈义过高的“宏大叙事”倾向,这两点互为表里,于此不难觉察其背后“启蒙心态”与“传统立场”对双方论者的影响。
不妨指出的是,刘清平最初文章也许因为强调“美德还是腐败”论点的缘故,直接列举了《孟子》中公职人员舜的例子,只是在后来的论述中以“例如,孔子曾指出”的方式引出《论语·子路》,而郭齐勇与之商榷的文章中则首列“子路篇”,同时列出《孟子》中“桃应”与“万章”两则对话,事实上,尔后的讨论同样集中于孔子而非孟子。总体上说,孔孟语录均事关亲情与公义(包括法律)的张力乃至冲突,并且其强调前者而非后者的倾向亦一以贯之,但在细部上则有若干不同。其一,二者的论主分别为孔圣与后来的亚圣,其在儒家系统中的权威性不同。孔子之言在前,孟子之言包括后来朱熹等皆其流,因此,不论追根溯源或正本清源,主要由孔子入手有其合理性。其二,“子路篇”中对话中人物似无《孟子》中所举舜的公职身份,此中公私冲突是隐在而非显在因素,这对刘清平的“腐败”批评有避其锋芒的意思。其三,更重要的是孔子关于父子关系的提法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与舜只是“子为父孝”在理论上隐含有微妙的平等与不平等之别,在这一观照下,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副标题特别拈出“亲亲互隐”而不取对方刘清平“子为父隐”的提法,显然有避开后者隐含的人际关系上不平等等级因素的考虑。然而,由于儒家伦理思想明显以“孝”为本,因此,在我们所讨论问题的语境中,“子为父隐”显然是更为中肯的表达。
回到原始文本。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有关上述对话的语义人们之间基本无歧义②,而在理论层面上,今天与孔子观点“异于是”者由此读出亲情压倒公义的意味,并进而得出关于儒家“血亲情理”原则的理论概括,认为这是儒家思想糟粕所在。而持为孔子辩护立场者认可其中蕴含的孝亲原则,但在默认隐父之恶不报者有欠公道的同时拈出所谓“深度伦理学”的解读,认为“子为父隐”乃人类基本道德情感的直下天然呈现,而叶公式的“直躬”进行到底则可能导致亲人“相互告发、相互残杀”③大逆不道的社会后果。应该指出,双方对孔子在上述对话中所表露思想倾向的理解基本无误,尤其是证之以儒家后进的相关言论,“以孝为本”而不宜“证父攘羊”的确反映了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想脉络与伦理原则。奇怪的是,人们热衷于在普遍理论和道德层面上相互辩难,对这段对话内含的实际含义和微妙之处缺乏细加琢磨的耐心,不能不说有情绪压倒理智和立场先行之嫌。
论争双方对文本本身“掉以轻心”的集中表现是斤斤计较于“隐”,而对其中真正的核心概念“直”缺乏应有的学术敏感,满足于从一般语义上将之疏解为人原始情感的天然呈现,却似乎不注意叶公与孔子言下“直”的概念意义不同。叶公言下所谓“直躬”说的是公义上不徇私情的“正直”,孔子言下“异于是”的“直”的确说的是一般都注意到的亲情之直。正是因为这是与叶公所说的“正直(躬)”不同的“情直”,孔子才在拈出父子之隐时要说其实“直在其中矣”。关于这一点,后世大儒朱熹的解读亦隐含此意。他在论及“子为父隐”案例时称此为“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1]。“子为父隐”作为人情之常的自然流露怎么可以说“不求其直”?在此,可以说得通的解释只能是不求正直而情直恰在其中。
当叶公赞叹其乡党中直躬者证父攘羊之行,孔子提出情直与之对质,其对后者的强调不言而喻,但仅从这则对话看,孔子在此不过“有事说事”,其言“抬杠”或有之,却并未否定叶公所言之直,至多可以说是“道不同”,却无碍二者“并行不悖”。这与后来孔子的非直接引言以为叶公所说的直躬者有“求名”之嫌的话尚有距离,证诸文本,并推不出所谓“血缘亲情至上”的结论。顺便指出,“求名”云云属于质疑动机,有人身攻击、转移视线之嫌,更重要的是,此疑即便坐实,终究不能抹杀证父行为的正当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此,理论上任何一边倒的阐释其实缺乏确切文本支持。
按照孔子及其所形塑的儒家关于“言辩”的态度,其对“讷于言”与“巧言”间“仁”与“言”及“君子”“小人” 之辨十分值得注意,孟子作为辩才亦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护,“予岂好辩哉!”这与西方传统对修辞学作为公共演说与论辩术一脉相承的推重形成甚具思想意义的比较。[2]在“子路”篇中,孔子积极扮演“反方辩手”角色,想来亦是因为兹事体大而“不得已尔”。不过,在本段文本中,孔子虽于叶公其党之外另行拈出“吾党”之直,倒真没有党同伐异的意思,其所显现的除了孔子思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特色,主要是他在人事体察与评价上推重“质直”的理论态度,这既可以从他对言语拙巧的褒贬中得到印证,更直接形诸其相关言论,孔子关于“孰谓微生高直?”(《论语·公冶长》第24)的质疑即为此例。微生高有直名,但孔子却不以为然,他举例道,邻居跟他讨醋,他没有但不说,却为此到另一邻居处找来给那人。孔子认为,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品德甚高的行为并不足以称道,因为这样的行事方式非人的本心呈现,透出矫揉造作(“孰谓直?”)之态,有沽名钓誉之嫌。
就人情世故言,孔子关于微生非直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符合我们关于伪君子的某些直觉,但实际上却也未必如此,由此而判定虚伪乃至居心不良恐怕言之过甚。顺便指出,这里所说的微生有可能即尾生——二者音近,如果此说无误,则微(尾)生为信守约定于洪水到来之际不惜“抱柱”而亡,实为真君子。不过,我们在此关注的不是孔子这一人事判断的具体正误,有意义的是如何从理论上理解人的自然本性与文化教养间“直”与“伪”的关系。依荀子的观点,伪在字面上有后天“人为”之义,既可能有言不由衷之虚(伪),也可能有德性修为之差异。因此,如果一味强调“直”,那我们将如何看待“真小人”?其实,孔子在此对直的强调和他自己关于质“野”文“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18)之说在理论上亦相抵牾。
也许还可以指出的是,孔子怼叶公虽有其“直”的理由,其实亦不妨从他苏格拉底式穷究事理的哲学气质与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处去理解,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之洞见。此处所谓“女子”并非泛指女人,而是特指家中“女眷”,与之并提的“小人”则是家中“下人”,这两种人与一家之主(当然是男人)之间固然有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但二者作为身边人与主人间还有一般权力关系中所没有的个体密切乃至亲密接触这层关系,从而人与人之间关系被注入了某种“平起平坐”的内涵。正因如此,彼此分际从而相互关系中远近亲疏的分寸殊难把握:“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西方人也说仆人眼中无英雄)如果将女子与小人径直以阶级观点视之,那么所谓的“怨”与“不逊”就没有着落了。诚然,孔子时代男女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孔子之为圣人亦未能免俗,由此引申出其歧视妇女的意思似乎顺理成章,实际上却是过度引申,言不及义。总之,孔子在叶公所言“直躬”外另立一解,固有其一以贯之的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重情底色,但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传统对原则性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在意与固执,而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亦不必作过度理论概括与引申。
二、伦理两难
依我之见,孔孟与叶公、桃应和万章间三段与“亲隐”有关的言说实质上给出的是一个类似于西方伦理学“电车难题”思想实验的中式版本,可以在伦理困境的框架下加以理解与分析。与西方背景下功利语义、后果论与道义论的理论对峙不同,孔孟们面对的是独特的亲情与公义的两难选择,儒家思想的特色表现出在二者之间以亲情为主的倾向,但对于其与公义之间的张力未尝掉以轻心。孔子在叶公赞赏的公义之外另立一说,其与“直躬”在逻辑上并无非此即彼的排中关系,事实上亦无党同伐异的动机。《孟子》中的两段对话分别涉及由舜与其父、其弟之间关系引出的孝亲、孝悌主题,由于舜的公职人员身份,忠孝问题隐约包含其中。
在《孟子》的文本呈现中,作为儒家所推崇的上三代圣贤,舜面对身负杀人重罪之父与“日以杀舜为事”的不义之弟象均不取大义灭亲之策,而是在事亲与从义之间偏向前者:对杀人之父,舜选择“欣然”放弃天子之位,“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对曾加害于己的兄弟象,他成为天子后没有如“流共工于幽州,放骈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颈稣于羽山”那样“诛不仁”,而是“以德报怨”,封其弟于有庳之地,如假包换的“双重标准”。
在上述两种描述下舜对父兄的行为显然表现出一以贯之的明确以维护亲情为重的倾向,但未必可以说是“亲情至上”,换言之,亲情在此并不具有排他单一优先性。因为,如果以亲情为单一标准且理直气壮,那他以天子之尊,其徇私枉法的手段应该是运用权力直接或间接为其父脱罪,相反,他的做法是牺牲权位,携其父于“法外之地”,这本身即透露出知庇亲行为于理有亏的意味,其选择是在保全其父性命的同时保全自身名节。这一举动从德性上看是自我牺牲的至孝,与后世二十四孝中所宣扬的欲感天动地的牺牲行为如“割股疗伤”“卧冰求鲤”相比毫无二致,而就行为设计看,通过放弃公职携父外逃,他似乎脱去了社会责任,在公义与私情间“分而治之”,似乎为两全其美之策。然而,公义立场所要求的是大义灭亲,舜以弃天下而逃法网虽因其个人的巨大牺牲而可以获得某种理解,但原则上显然于正义有亏,即便将之解释为通过代父受罚而维护公义仍是不成立的。当然,由于亲情在人类情感中的独特地位,舜的行为虽无法通过公义或法律的审视,但的确可以获得某种同情的理解,正因如此,东西方法律基本有亲属罪嫌无强制举证义务的条款,不过,这只是某种特设安排,是宽容而非正义,换言之,对亲隐的容忍并非基于任何应然之理由,因此,大义灭亲是更高的道德——应然的反面是不然,在道德上是负面的。
伦理困境的特征是两难,就像康德所揭示的理性二律背反,其中任何一方各自皆有理由,但任何一方对对方皆无压倒性排他理由,因此,一旦陷入这样的处境,怎么样的反应都有其不如意处,谁都没法全身而退。以舜对其不仁之弟象的处置,公义的要求是一视同仁,而不是不罚而封或轻罚而放,但依儒家伦理,对兄弟如对众人本身即属伤仁,如此说来,舜之所为未尝没有可以同情理解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象对舜甚至有害命之举,舜这样做似乎与兄弟情义没啥关系,毋宁具有以德报怨的道德意味。
伦理困境无完满解决,或者说无黑白分明一刀切的真理性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存在理性或道德真空。其实,妨碍问题最终解决的不是抽象地说其认知或实践的复杂性,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利益主体价值角度的分歧难以两全:举证攘羊之子伤及其父,这种事摊到谁身上——即便是理念上强调公义者——恐怕也难免纠结踌躇,但是,对于失羊者来说,即便他原则上是主张亲情优先的,对为攘羊者隐的行为亦不以为然,若要公道,打个颠倒,诚哉斯言。但如此说来,岂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理”“婆理”无所适从?其实不然。在表层逻辑上,不论是亲情还是公义皆有其理,但“两直相冲”背景下真理是否可能?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对“亲亲相隐”者诚然可以有某种“同情的理解”,法律上对亲人举证义务的容隐就表明了这一点,但同情不等于认同,从社会公义的角度看,对恶的隐瞒无论如何都违反了正义原则,不能想象直斥“乡愿,德之贼也”的孔子会“世故”到昧于嫉恶如仇、大义灭亲之理,上述文本事实上也不支持这样的想象。在此,“亲亲相隐”与“官官相护”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相对于亲亲相隐,大义灭亲是远为艰难的良知选择,就人性的崇高论,二者显然高下可判,后者在道德排序上远高于前者,那些责之以不孝,甚而随意加诸“沽名钓誉”之类的轻浮联想实不可取。在此,福斯特(Rainer Forst)关于“伦理”与“道德”私人维度与公共维度之间关系的论述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福斯特指出,在“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的冲突中,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对善过于僵化的、道德说教的解释”[3]83,另一方面,亦要避免“有可能否认道德的绝对有效性”[3]83,“人情世故”与“天理良心”如能兼及诚然皆大欢喜,如无可能——通常如此,原则上“道德论据比伦理论据拥有更重的分量”[3]80,具有价值优先性。
首先,道德应然与事实实然在“可普遍化”(康德)方面存在原则区别。亲情在人类社会中有事实的普遍性,却并不具有道义的普遍性。为其攘羊之父隐者固然出自亲情之直,那被攘羊者“痛不欲生”,则其情何以堪,其亲情之直何以安顿?!因此,道德之为公道必须超越私利,唯此方可成为可普遍化的法度,因而在功利上亦是最终令所有人皆受益的公共之善。此外,血亲之情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身上“卑之无甚高论”的动物性本能,而道德作为人性必须具足超越性,就此而论,公义与私情相比显然处于更高的道德水位,即便我们“行”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黄裕生从人的本相存在与现实生活中关系角色如父子兄弟的角度切入问题,一针见血,见解深刻。[4]对于务实有余、超越不足的中华民族来说,意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其次,道德属于公义,亲情显系私情,就此而论,道德的要义在于“把自己看成对他人负有义务”[3]67。退一步说,即便除去利他的因素,“相互性和普遍性是道德情境中关键的辩护标准”[3]19,在此,关键不在于两造皆私我,此中之公在于满足相互性和普遍性的要求,这意味着对本我之直的约束与超越,在某种意义上亦真君子与真小人之分际,同时亦超越个体视角最终众人即每个人之善得以更大化的有利策略。
最后,实践理性不但非本能之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本能反向而行的,这就涉及“直”与“真”的关系,在这方面,美国海德格尔研究者、哲学家哥文(Michael Gelven)关于“母亲”之义的思辨对我们思考当下论题富有启发。母亲在事实上为“女性家长”,而关于母亲意义的理解则远为复杂。母亲的本质在母爱,母爱除了意味着为子女无保留的付出,常常还意味着对子女无条件即无原则的袒护,一个平常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母亲眼里如蚌含珠般包容的那粒沙子就是她的孩子!对某一妇人匪夷所思的特定言行,只要说一声她是那人的母亲,则一切似乎皆不言而喻,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母亲之为母亲。现在的问题是,母爱之直是否即母亲的真谛?恐怕不能这样说。一个教会孩子如何立身行事的母亲难道不是比护犊的母亲更明智、更称职?比如,许多人都听过一个故事:小时候拿人家根针母亲不加训诫,长大后偷金杀人的儿子在刑场上说要让母亲再哺乳最后一回,结果却咬下母亲的乳头。子不教,母之过,包括这个人不反躬自责,有恨无悔的泄愤行为都昭示了那位母亲有悖母亲真义的失败。现实中,有犹太血统的上海人沙拉关于亲子教育真谛的深刻领悟由其书名即可窥其一端:《特别狠心特别爱》,前者非母性本能之直,但唯其如此才是真正的母爱。由此可见,人情之直固为人心之实,却并不构成理性之真,即便从实践后果的角度考虑,亦欠明智,因此,虽可以理解,但不足为训。
总之,围绕“亲隐”的是非曲直具有伦理问题的两难性特征,要求对之有非单面性的辩证思考从而简单明了的解决方案,但总体上看,仅仅以人情之直为“子为父隐(互隐)”“兄为弟赦”辩护并不充分,反之,大义灭亲不但因其艰难而可贵,更以其正直而合乎道义之真。相反,关于直躬者想必父子关系有问题或好名之甚的各种臆测实属节外生枝的曲为之辩之举,没有必要。
三、文化反思
就事论事,我关于儒家“亲隐”的理论思考俱见于上,在此尝试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进一步对与传统文化及思想方法有关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纵观这场持续时间不短、热度不低的儒家伦理攻防战,“控辩”双方都有较为明显地将问题上纲上线的倾向。刘清平文标题大书“是腐败还是美德”,指儒家关于亲情与孝的观念为贪腐的文化基因,似是而非。至于“美德”云云亦有焦点失实之嫌——“直”而已矣,无论是原始儒家还是所谓新儒家,似乎并没有谁将之赞誉为美德。就此而论,韩东屏认为亲亲相隐只是可以容忍但不涉善恶的观点倒是更为中肯、通达。[5]反观辩方,将亲情上升到“抗拒皇权专制主义与法家效率主义”[6]序言8 和保护“私领域”[6]21的“人权”高度,并从反面将曾经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父子相残、夫妻反目的悲剧与亲情不彰挂钩,由此解读出控方立场包含的可能危害,引喻失义,过甚其词。由此观之,这场论争实非“五十年来国内最有深度的中国伦理争鸣”[7]。
在理性思考层面上,见微知著,由点到面是当然之事,但这与抽象思考,任意联想之间有明确的思想界限。即以“亲隐”行为论,亲情因素或许是其中大多数情况下的原因,但其实仍未必尽然,面子观念、利益考虑如“一损倶损”等有时候也许是其中更为关键的因素。至于亲情为上的观念与徇私枉法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在不同文化传统下后者均可能发生,而前者则未必是各民族一致的观念。反之,重视家族亲情就其善者言之,显然亦有其正面社会意义,因此,重要的不是强调某种文化观念可能的积极或消极表现形式,其发生作用的机制显然不是由观点到行为或反之点对点径情直遂的因果关联,从而简单“对症下药”式的思考不但有急功近利之嫌,实际上也是无效的。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的现实功能不应离开特定体制孤立地加以考虑,某种观念之流行有时不过是已然现实的背书,而非简单的观念为因现实为果关系,也就是说,观念对现实的影响不但是在复杂的思想脉络中成立的,并且,在观念与现实之间,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看法是中肯的,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意义的腐败,罪魁祸首都是特定权力的制度现实而非观念——一定要说到观念,那首当其冲的也是“贪”,轮不到“亲情”。
儒家“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亲隐”观念既非刘文所谓“腐败”即徇私枉法行为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将二者联系起来实属牵强,但此一观念包括围绕它的讨论倒的确折射出传统文化的某些深层逻辑与精神特征,值得在理论上细加剖析和深入反思。
其一,“亲隐”及其辩护透露出中华文明重情甚于论理的情本位④思想逻辑,这不但表现在亲隐者发乎父子、兄弟之情的动机层面,更重要的是,亲情是自孔子始为“亲隐”辩护者的基本理由,反之,直躬之为公义的背后是公理而非私情。情本位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有广泛的表现,孔子的核心概念“仁”具有明确的情感内核,孟子进一步发明的作为仁之四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皆诉诸情感,唯“是非之心”涉及公义。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拈出的不只是现代文学的抒情性主旋律,其折射的是历史进程内在的情感主线。而就文学论,何止现代,一部《红楼梦》,在叙事手法上固然出之以将“真事隐去”(甄士隐)的“假语村言”(贾雨村),而从主题到主角都是货真价实的“情文”(晴雯)。今天,我们关于道德模范的阐扬,其着眼点依然是“感动中国”。关于情感思维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存在,诸如“合情合理”“通情达理”“准情酌理”这样一些成语在日常语言中的流行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语词的明面内容,而是隐含在句法性结构背后的集体无意识。上述三个成语的语词顺序均“情”在“理”先,这代表情重于理的内涵,在相反语词构成的词组中,语词的先后排列顺序如“善恶”“是非”“真假”“正邪”“好坏”不但皆遵循前正后反的规则,尤其意味深长的是,依索绪尔之洞见,当我们将上述语词纵向排列或者在口语中一一读出,当最后一个词组“男女”出现,男尊女卑的意味不言而喻!⑤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当然是人所共有,但依理性还是情感为评断标准,中西方思维显示出明确的不同:“合情合理”之英译为“fair and reasonable”,“情”在此杳无踪影。这当然不是因为英文中无“情”字,而是因为思维上理本位与情本体的深刻区别导致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这不是语法上不可能,而是语言或者说修辞上不成立,也就是理解上成问题。
与理相比,情或许是人性中更基础和直接的东西,一事当前,人心中首先发动的往往是情感。例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等明显都是情心,而非理思,后者按休谟的说法是在情感基础上进一步地考虑且服务于情感的。就此而论,诉诸情有其务实性的一面,这与儒家所说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由近及远是同样的思路。但是,虽人人有情,但在人与人关系上情具有特殊性、私人性,不仅爱情是高度排他的,亲情、友情、乡情都有远近亲疏之别,与之相比,理无远弗届,只有对所有人都“说得通”或“说得过去”才“言之成理”。因此,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理性是我们安排与处理问题时具有可通约性的规范,亲情因素非不能被理解,但作为准则只能停留在私人关系层面。总之,可以同情,但只能共理。否则公义何以确立?法律在举证义务方面对亲人“网开一面”是在可能情况下人性化的宽大表现,却非理之必然。
其二,在更抽象的层面上,情本位可以从超越性角度加以理解,意思是,情感性思维务实性的一面暗示着超越性方面的某种缺失。
超越性有横向与纵向、个体性与群体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西方式与中国式的不同。总体上看,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人自我超越的横向历史性通道,在此,进入历史、慎终追远包含生物学基因方式(子子孙孙)和语言文化方式(正史、地方志、族谱等)。西方文化最为触目的是宗教层面上的纵向超越,但除此之外,基督教出现之前,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已然成型的学术上“究虚理”及其背后的“自由”精神同样代表超越性追求,而与此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文化“重实用”的“实用理性”倾向。前者最终结出现代科学发现的理论花果,后者则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及作为“四大文化”的“兵农医艺”[8]304名闻遐迩。
人生天地间,中西方“重实用”与“究虚理”的文化精神于天地之间各得其半,中华先祖于“忧患”中脚踏实地,务实生存,希腊人则于“闲暇”际有心“忧天”⑥,各自发展出一番文明胜景。在哲学理论方面,人们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8]304,所谓“修齐治平”“经世济用”的“道术”⑦。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不是表象的,而是履行的和参与的;它不是推论的,作为关于道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实际技巧”[9]。“实用主义”是挑战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美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实用主义精神毋宁是当行本色。美国汉学家孟旦说:“在儒家思想中,不导致行为结果的‘知’是没有的。”[10]冯友兰早就指出,除名家之外,“中国哲学史中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之学说极少”[11]。
宗教之外,西方文化对超越性价值的精神性追求对中华文化来说极具“他者”性,这里借裴多菲《自由与爱情》一诗稍加分析。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此诗郭译可以说脍炙人口,但其内含的深刻文化信息却未必为人所真知。诗中三个关键词无疑是“生命”“爱情”及“自由”,且三者在价值上呈由低到高的排列,在此,生命是纯物质性的,爱情是精神(灵)与物质(肉)的统一,高于爱的自由代表纯粹精神性价值,这里显示出由明显由实到虚的倾向。站在务实的唯物立场,显然生命最不可抛,命都没了,爱情及自由何所依附?但这显然与此诗之精神不合。那么,西方人难道不知道死生事大吗?或许是特定的宗教救赎观念在此发挥作用?非也,诗人在此并没有说为“上帝”或“天堂”故尘世生命、爱情不足惜,其实,即便在宗教背景下,贪生怕死仍然是人的本能。据实而论,现实中能“抛二者”的西方人未必比东方中国人多。因此,此诗并不是面对死亡的慷慨陈词,其要义不是勇气,而是对自由作为精神性存在在价值上高于非精神性存在的理解和判断,此中传递的是人性中向上超越的理念,其更直白的意思是,“灵魂”高于“肉体”,虽然现实中前者物理地“随附”于后者。这些思想我们今天或许不难理解,中国文化中亦不乏舍生取义的勇士,而内中义理与此仍迥然有别。我们有为道义死的烈士、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但罕有因自由而献身的个人。
关于中国文化务实的“在地”性格,有两位文化人各自给出了独特然而彼此高度一致的观察。台湾学人汉宝德⑧判断中国文化“是一个经过包装的原始文化”,“所谓原始文化就是人类在原始时代以本能为求生存所产生的文化。其基本的性格就是生存”,与此不同,“文明社会则是在生存之外,肯定精神的价值”,甚至在生命之上。[12]20他并不是荒谬到宣称中华文明没有精神价值,而是说它本质上是“唯物”的,未能实现精神上的整体超越。以“性”为例,西方文明发展出以爱情升华性欲的精神化方式,“将爱、欲相提并论”,中国文化对性有很通达的看法,“食色,性也”表现出对人生物本性的尊重,同时以繁复的礼仪加以约束,以孝加以包装,但并未发展出精神性的“爱”的观念,比如没有发展出与爱的专一性相匹配的一夫一妻制。[12]20-22中国文化的世俗化、物质化倾向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找到痕迹:中国建筑重风水、重功能,但不赋予建筑独立的精神性价值如纪念性,这是中国人选择木材而非石材建房的根本原因,而非通常似是而非地解释为石材与木材在经济成本上的不同。[12]27-28
无独有偶,关于中国文化的世俗化、物质化倾向,小说家阿城有同样的观察:“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上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13]29商周甲骨文的内容满是各种实际问题,“牛跑了是什么意思?”“往哪个方向能找?”“女人怀孕了,会不会难产?”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所谓群经之首的《易经》,其文字似乎玄之又玄,其形上外衣之下说穿了无非吉凶祸福。反观西方,庞贝遗址上发掘出来的古图书馆泥板书的内容被释读出来,“全部是哲学。吓了我一跳”[13]31。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中国人憎尼姑、回教、耶教,唯独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14],对此阿城曾“很久不能懂”,但“说穿了”,其实也简单,“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13]42,包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实用理性的另一个含义,是在成败与是非之间向前者倾斜,试看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通篇关注皆吉凶祸福而非是非,功利重于原则,小说家张大春于史迁“究天人,通古今”的抱负中见出其背后“岂有只字而及于‘存旦夕之真’乎”[15]的阙失。与我们当下论说直接相关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真理高于师恩⑨,此一道理在父子间——在“天地君亲师”的语境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亦是一样的。
和任何文化一样,中华文化精神的养成有其现实和复杂的历史因缘与脉络,务实忌虚自有其通达合理的一面,孤立地看本身并不必然为弊,即无先验之善恶,但由此在精神性超越方面或有不足亦不争之事。本“反者道之动”之旨,“避实就虚”对于积实有余、虚有不足的我们来说未尝不是负反馈纠偏之道。至于西人或“虚火上炎”,则无须我们代为操心,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或许即西人一药。
注释:
①为简直计,本文提及各位学者时直接出之以姓名而不加尊称如“先生”“教授”,非不敬也。如果一定要加,我属意的倒是“君”,各位也许不妨依此自行脑补之。
②至于有论者在“隐”字上作文章以为隐者行为辩护,不过是曲为之辩,不足为训!
③郭齐勇:《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兼与刘清平先生商榷》,载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13 页。
④李泽厚关于中国文化有“情本体”的论述(见《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及《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与本文观点有交集,不一样。
⑤这是1990 年代德国美因茲大学哲学系主任西博姆教授(Thomas M.Seebohm)来系访问讲座最后提到的,当时我担任口译,印象深刻。
⑥问天是人类最初的科学之问,传说泰勒斯曾因顾天不顾地坠坑而遭女仆嘲笑,其中文版正是“杞人忧天”。
⑦中国哲学区分“道”“器”,却未见严别“学”“术”,倒是“道术”并用。《庄子·天下》称诸子为“天下治方术者”,谓“百家争鸣”为“道术将为天下裂”。
⑧汉宝德先生兼具建筑学教授、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建筑师等多重跨界身份,尤其是他中西文化的素养和比较眼光为一般专业人士所不及。
⑨其原话大意是“老师固然可贵,但更高贵的是真理”,此言通常转述为“吾爱吾师”云云。另外,《论语》中的“当仁不让”亦涉及师生,但与西人观念仍有微妙差别,强调的只是在追求仁的时候不必礼让,并无亚里士多德语蕴含的“批判性思维”的意味。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