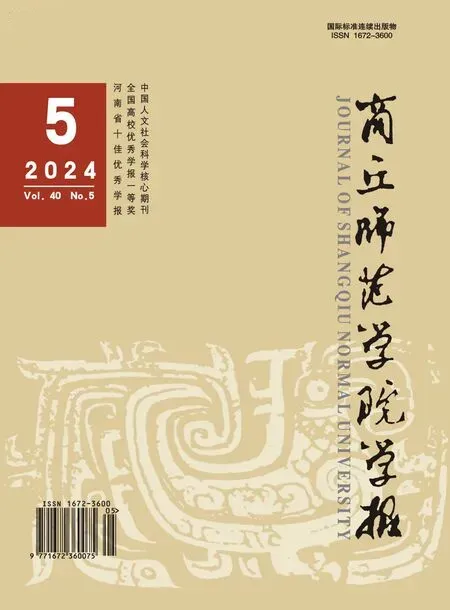明代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塑造
——以《明实录》丘濬传记为中心
刘 小 龙
(广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320)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深菴,谥文庄,广东琼山县(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他是明代中期的理学名臣,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在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过巨大影响,学界历来重视对其人其事的研究(1)陈敏《丘濬研究述评》(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孔维劲《2008—2021年丘濬研究综述》(《潍坊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梳理了相关研究论著,张朔人《丘濬研究新进展》(《海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介绍了丘濬诞辰六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一方面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丘濬及其相关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相关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研究参考、引用《明实录》中的史料,却很少深入探讨实录对丘濬的记载。
因此,需要重视对那些我们“日用”而未必“真知”的基本史料进行研究。本文拟以实录中丘濬传记为主要分析文本,结合年谱、墓志铭、碑传、笔记、文集、方志、正史等其他不同性质的文献,考察作为当朝国史的《明实录》[1]16对丘濬传记的编纂情况,探讨其中的史实遮蔽和形象塑造。
一、《明实录》中的丘濬传记
实录并非通常认识的那样只是编年体史书,它的确以时间为轴线记载历史,却适时(历史人物首次出现或最后一次出现时)地插入传记。于是,《明实录》中存在两千多个传记(2)李国祥等主编《明实录类纂 (人物传记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凡例”,第7页)辑录统计的结果是2 350个传记。据考察,这一统计数据存在不少遗漏。《明实录》中的传记应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实录应该被称为编年附传体史书[2]152—153。丘濬去世后,实录按照惯例为之立传,即孝宗实录中的丘濬传记[3]1775—1777。
实录丘濬传记,约计476字,涉及以下事宜:1.基本履历,包括姓名、表字、籍贯、科举经历、仕宦升迁、卒世、赠官赠谥;2.参与编修寰宇通志、实录、续通鉴纲目;3.上呈《大学衍义补》;4.恩荫孙子;5.早慧;6.上奏两广用兵疏;7.在国子监祭酒任上、主考乡试和会试时,整顿士风学风;8.入阁上疏言事,指陈时弊,求访遗书;9.太医刘文泰弹劾王恕事件被牵连;10.博洽多闻,著述情况;11.奇论苏轼、秦桧;12.时人评论。
通过上述记载,实录传记塑造出丘濬的正面形象。一是天纵英才的形象。他早慧,天资聪明,少时即享有重名。与明代其他士子一样,丘氏为科举努力拼搏,尽管其中同样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但结果很不错:正统九年(1444)考中广东乡试解元、景泰五年(1454)考中进士、后改选为明代培养高级官员的翰林院庶吉士。二是当世名臣的形象。他为官恪尽职守,屡次升迁,弘治时期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成为朝廷重臣。丘氏直言敢谏,多次上疏言事,深受皇帝嘉许。三是学术大家的形象。他多次受命编修官史,特别是英宗、宪宗两朝实录的编修,这是当时文人知识分子的莫大荣耀[1]21。丘氏博洽多闻,文章雄浑畅达,编著的《大学衍义补》受到明孝宗赞许,其《家礼仪节》《世史正纲》也盛行于当世。四是经世致用的形象。他积极参与实际事务的谋划和运作,为明朝廷用兵两广上疏、建议访求当时的遗书、积极整顿士风学风、为治国理政编纂《大学衍义补》、为重振礼仪世风编撰《家礼仪节》《世史正纲》。
可见,实录传记塑造的丘濬形象是多重性的、复杂的。如果扩大视野,将实录中涉及丘濬的记载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在丘濬生前,负面记载仅见孝宗实录中的两则史料(详见下文),且都属于科道官的风闻言事,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在其生后,除了传记之外,孝宗到神宗等多部实录均没有负面记载。因此,关于传记所载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时人和后世一直流传着史实遮蔽和形象塑造厚诬的说法。那么,相关史料在编纂过程中的史实遮蔽和形象塑造情况究竟如何呢?
二、《明实录》记载丘濬的史实遮蔽
在论述丘濬不畏强权、敢于坚持正义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举出两个事例:一是丘濬编修英宗实录时,他虽然仅为纂修官,但是敢于为政治敏感人物于谦辩白,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是明代史权复苏的例证之一[4];二是在宦官李广等人的影响下,弘治元年(1488)孝宗皇帝沉溺祷祠,贵戚又都“希旨用事”,京畿地区惊现罕见的天变预警——彗星孛三垣、地震天鸣、异鸟三鸣于宫中,五年(1492)丘濬不惜冒着激怒孝宗、得罪宦官和贵戚的危险,上疏指陈时弊,借以弥灾。翻检实录,却找不到这两件事清晰完整的记载。前者没有只言片语,后者含糊其词,只有“及入阁,上二十余事,陈时政之弊”[3]1776的记述,根本看不出丘濬的正直敢言。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是否真如以往认识和理解的那样都是史官的有意遮蔽呢?
(一)实录不载丘濬为于谦辩白
关于这件事,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大概是丘濬生前的好友何乔新写于弘治八年(1495)的墓志铭。他在《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墓志铭》中有云:“修英庙实录,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迹。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实书之。”[5]457何乔新的这一记载,出自蒋冕撰写的丘濬行状,还是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见闻?由于流传至今的蒋冕文集《湘皋集》没有收录那篇行状,且没有在其他史籍中找到此行状的踪迹,所以这一问题难以确考。之后,明代郑晓《皇明吾学编》[6]563、《广东通志初稿》(嘉靖)[7]263、雷礼《内阁行实》[8]492、明末清初傅维麟《明书》[9]500、张岱《石匮书》[10]286、查继佐《罪惟录》[11]2178、清代官方编修的正史《明史》[12]4810、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13]703、《广东通志》(雍正)[14]225等文献均沿袭这种说法。以此观之,丘濬甘冒风险为于谦辩白似乎是历史的真实。那么,实录为何隐而不载呢?要回答前面的疑问,恐怕先要弄清楚一个关键性前提,即英宗实录编修时,于谦是否还是钦定的“奸臣”。
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在成化元年(1465)二月己丑,监察御史赵敔上疏宪宗皇帝,乞请为于谦等人平反昭雪,其言:
往年尚书于谦等为石亨等设诬陷害,榜示天下,冤抑无伸。其后亨等不一二年亦皆败露,实天道好还之明验。今陈循、俞士悦等前后遇蒙恩宥,天理已明,无俟臣言。独正统十四年虏犯京城,赖于谦一人保固,其功不小,而已冤死矣,余亦可悯。伏乞收回前榜。凡死者赠官遣祭,存者复职、致仕,或择其可用者取用。[15]317—318
奏疏明确地说于谦在正统十四年(1449)北京保卫战有着巨大的功劳,却被陷害冤死。鉴于真相已大白天下,且当时与于谦一起被陷害的陈循、俞士悦等人已经先后平反昭雪,赵敔请求明宪宗为其他没有沉冤昭雪的人平反。宪宗皇帝积极肯定赵敔所奏的正确性,而且动情地说道:“朕在青宫,稔闻〔于〕谦冤。盖谦实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15]318可见明宪宗早就认为于谦是功臣和忠臣,应该予以平反。于是,宪宗皇帝让有关部门按照赵敔的意见马上办理。史书中“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15]318一语,用“悉”“亟”两个字展现出明宪宗为于谦平反昭雪的立场和态度。可见,于谦在当时已经由最高统治者平反昭雪,也就是说于谦从那以后不再是钦定的“奸臣”。
次年(1466)八月,明朝廷谕祭于谦,翰林院奉命撰写祭文,并由行人前往祭墓。于谦之子于冕也官复原职,为府军前卫副千户[15]669。如果说前一年二月在庙堂之上为于谦平反,其影响还局限于明朝廷的官僚士大夫之间,那么这一次的公开谕祭于谦墓,则是在向普通民众郑重宣布为于谦平反,其影响可以说远超前者。在当时,相比于皇帝的一纸榜文,普通民众更容易受到具有视觉和听觉效应的这场谕祭仪式之影响。人们在围观、感受这场谕祭仪式的同时,获得的信息是明朝廷已为于谦平反昭雪;他们在谈论这场谕祭仪式时,传递的同样是明朝廷已为于谦平反昭雪的信息。可以说,这场谕祭仪式以后,于谦已经平反昭雪已成为天下人所共知的事情。
独立设课后的实验教学,必须以特色突出、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强、吸引力强的实验教学教科书为基本保障。在内容和篇章结构上应主要由“导论篇”和“指导篇”两部分构成。
据研究,英宗实录编修于天顺八年(1464)八月到成化三年(1467)八月[1]109—110。结合上文的讨论,可知成化元年二月在明朝廷庙堂之上就已为于谦平反。在英宗实录成书的前一年,为于谦平反的信息通过那场谕祭仪式更是广为传播。换言之,在成化元年二月时,明朝廷官僚士大夫就应该知道于谦不是奸臣,而是有功于明朝江山社稷的重臣。这一官方的新认识在次年八月更是为天下所共知。另,根据实录编修的流程[1]87和工作量(正统、天顺共计22年史事,加之初期史官们因政治忌讳而消极怠工[1]178)来讲,成化元年二月(英宗实录编修刚好六个月)的修史进度难以达到编纂天顺元年(1457)于谦被陷害、下狱、冤死等事件[16]5792,5806,史官们自然不会讨论如何书写相关历史。因此,即便真发生丘濬为于谦辩白的事,也应是在成化元年二月之后。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明朝廷为于谦平反后,还会有人像何乔新在墓志铭里所写那样,提出“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迹”吗?揆诸情理,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人,因为这既不符合当朝最高统治者的意愿,又违背了历史事实,也与天下正义的舆论为敌。那么,丘濬坚持正义为于谦辩白的言论“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和事情的结局“众以为然,功过皆实书之”云云,则不能不令人生疑。遗憾的是,前引郑晓《皇明吾学编》等明清文献(包括极具严肃性的清代官修正史《明史》)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疑点,进而沿袭了何乔新的说法。
明清时期的墓志铭,与中古时期相比,已有诸多不同,其中之一便是它们不只是埋在地下,同时也可以传抄、刊刻,在当时社会上流传,收入撰写者的文集,流传后世。孝宗实录编修的时间为正德元年(1506)到四年(1509)四月[1]114—115,编撰丘濬传记时,史官们理应可以参考行状、墓志铭之类的碑传材料(3)在明代,官员家属向朝廷请谥时提交的行状、墓志铭等材料,会很自然地成为《明实录》附传的史料来源之一。参见刘小龙《〈明实录〉科举史料的价值探析——基于文献学和史学史双重视角的考察》,《南都学坛》2023年第1期。。史官们之所以没有记载丘濬为于谦辩白,大概也是因为发现此事存在疑点。因此,这非但不能成为实录有意遮蔽史实的例证,相反,它反映出史官们的谨慎态度。
(二)实录含糊记载丘濬因灾异上疏
前文已述,实录关于丘濬在弘治五年因灾异上疏的记载,可谓含糊其词,以至于根本读不出因灾异上疏这一层最基本的意思。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史官们也应该了解到这份奏疏的具体内容,故而他们才煞费苦心地作了模糊化处理。探寻这份奏疏的内容和事情的原委,将成为解开谜团的钥匙。
明代官史中没有奏疏的相关记载,丘濬的文集《丘文庄公集》也没有收录。幸运的是《重编琼台稿》收录有这份奏疏,题名为《论厘革时政疏》,时间为弘治壬子(即弘治五年,1492)四月十日[17]134—144。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份奏疏,还需要借助其他相关记载,进而了解丘濬此次上疏的来龙去脉。明人的私家著述很多都为丘濬立传,它们不仅节录有这份奏疏的部分内容,而且也记载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廖道南《殿阁词林记》[18]119—120、焦竑《国朝献征录》[19]467—468、何乔远《名山藏》[20]1942、尹守衡《皇明史窃》[21]380—387等文献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结合这些文献,可以探知丘濬此次上疏的原委。
深受儒家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丘濬,在京畿地区出现天变灾异的情况下,针对当时明孝宗沉溺于祷祠而权贵们争相迎合的事件,他上疏规谏孝宗皇帝。奏疏中使用“天变莫大于彗孛,而侵三垣、台斗,尤为重;地变莫大于震动,而在京师、边防,尤急……变不虚生,必有其应……故其咎征之应,深可畏也……天之示警乃如此,夫岂无其故哉?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7]135等字词来描述当时的天变灾异,对于彼时的人们来讲自然是异常敏感和尖锐的。类似的,奏疏规谏明孝宗的用语“将否之运而使之转为泰,其斡旋之机,政在皇上今日,失此时而不为,踵其后者纵欲有所为,无及矣。……臣愿皇上体上天仁爱之深,念祖宗基业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应天下之务。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伏望皇上怜其憨直之愚,赦其干冒之罪”[17]135—136,144云云,言辞同样非常尖锐,几乎是变相地批评孝宗皇帝的失政、失德行为导致天怒人怨。何乔远根据奏疏内容,提纲挈领地概括出谏议的22事[20]1942,也都是针对当时的弊政。
据研究,孝宗实录为彰显明孝宗“虚怀纳谏之广阔胸怀”,收录了不少臣下劝谏的奏疏。但是,史官对这类奏疏极其注意节制,特别是对待言辞激烈者,或是不予收录,或是虽然收录却对其中的激烈言词加以删除[22]。诚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丘濬弘治五年因灾异上疏,其言辞可谓尖锐、激烈。当然,这不利于维护明孝宗光辉伟大的形象。正是这个原因,史官们才必须含糊其词,对这件事情作了模糊化处理。如此,既不损孝宗皇帝的正面形象,也没有回避事实、完全淹没丘濬因灾异上疏这件事情,可谓是煞费苦心。
如果说实录不载丘濬为于谦辩白,体现的是史官们谨慎的修史态度,尚不构成有意遮蔽史实,那么,含糊记载丘濬因灾异上疏,将其言辞激烈、正直敢言(不惜得罪孝宗皇帝和宦官贵戚)模糊处理为云淡风轻的记述,则明显地表现出史官刻意遮蔽史实。
三、《明实录》厚诬丘濬形象
丘濬是明代中期的理学名臣,在大多数人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信奉者眼中,他自然是正面人物。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明实录》在记载丘濬事迹时,却恰恰存在几则负面记载。以故,时人和后世一直有实录厚诬丘濬形象的说法。那么,实录建构的丘濬形象果真存在厚诬吗?
实录关于丘濬的负面记载,主要涉及两件事情:一是成化二十三年(1486)十月言官弹劾丘濬昏庸误事、奔竞无耻、为人臣不忠[3]94;二是弘治六年(1493)七月南京工科给事中毛珵等人弹劾[3]1503—1504和弘治八年二月丘濬传记[3]1776共同提到的刘文泰攻击陷害重臣王恕,时人多谓丘濬是幕后主使。关于这两件事的是非曲直,下文分述之。
御史、六科给事中之类的言官们指控丘濬昏庸误事、“自入内阁以来,所为多不满人意”。这些指控,多为他们风闻言事,没有事实根据。相反,丘濬自进入仕途,在成化、弘治两朝参与经筵日讲、多次参与编修官史、参与科举考试、整顿士风学风、上两广用兵疏、因灾异上疏言事等,可谓勤勤恳恳,“昏庸误事”和“自入内阁以来,所为多不满人意”显然与事实不符。正因为如此,后世文献也很少沿袭此类记载。
言官们指责丘濬“奔竞无耻”,明人笔记倒是有些许记载。王鏊在《守溪长语》中有云:“李广幸于上,因之得入内阁。”[23]286其意为丘濬能够进入内阁,依靠的是攀附宦官李广。陈洪谟《治世余闻》更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丘濬“奔竞”的事件——“阁老饼”。他亲自做饼,托宦官进呈给明孝宗,孝宗吃后非常赞赏,进而命令尚膳监制作。司膳者向丘濬求教制作之法,后者害怕因此失去独宠,竟然不愿告知。丘濬的这一行为,甚至连宦官也鄙夷说:“以饮食服饰车马器用进上取宠,此吾内臣供奉之职,非宰相事也。”[24]40于是,“阁老饼”的称呼便在京师不胫而走。尽管这两则记载被诸多明清文献引用(4)如雷礼《内阁行实》(《明代传记丛刊》第27册,第499—500页)、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誊印本,1997年,第1553页下)、邓球《皇明泳化类编》(《明代传记丛刊》第81册,第241页)、傅维鳞《明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9册,第501页上)、徐乾学《徐本明史列传》(《明代传记丛刊》第91册,第575页)等明清文献都有征引。,影响较大,但是皆非事实,经不起推敲。第一,如果丘濬果真是攀附宦官李广进入内阁,那么前文讨论的弘治五年因灾异上疏似乎就不应该发生(5)或曰丘濬攀附宦官入阁后抨击后者,这有违明代的情况,因为正统以后明朝廷中枢决策是皇权、内阁和司礼监三者协作(参见王剑《明中后期中枢决策机制的嬗变》,《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阁臣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谋求宦官的协助,特别是攀附宦官入阁者更是如此,比如武宗时焦芳与刘瑾、熹宗时顾秉谦与魏忠贤。,毕竟奏疏针对的就是宦官李广“渐进左道,亲近用事”[20]1942。第二,丘濬入阁后,屡次乞请致仕,仅实录就记载8次之多(6)参见《明孝宗实录》卷65弘治五年七月癸巳“疾乞致仕”(第1248页)、卷66弘治五年八月辛丑“复两疏乞致仕”(第1257页)、卷78弘治六年七月甲寅“乞休致”(第1506页)、卷78弘治六年七月壬戌“再乞致仕”(第1509页)、卷79弘治六年八月庚辰“复以老疾乞致仕”(第1515页)、卷85弘治七年二月辛未“再乞致仕”(第1598页)、卷85弘治七年二月庚辰“再乞致仕”(第1591页)、卷96弘治八年正月壬寅“乞致仕”(第1765页)。,这与攀附宦官进入内阁、贪恋权位完全背道而驰。第三,时人黄瑜曾称赞丘濬一生“不可及者有三”,其中便有“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做,其介慎二也”[25]221。黄氏为丘濬同时代的史家,其《双槐岁钞》成书早于王鏊《守溪长语》、陈洪谟《治世余闻》,当时人记当世事比后人的追述,更有信服力。黄氏的言论也说明丘濬不是攀附宦官的“奔竞”之人。另外,丘濬是当时全国泰斗级的理学大家,他信奉和倡导的程朱理学特别重视气节等纲常伦理,也与这种攀附宦官的“奔竞”行为格格不入。
在刘文泰攻劾王恕的事件中,丘濬是幕后主使吗?他对这件事负有怎样的责任呢?锦衣卫镇抚司通过调查、审理,认为案件的经过大致如此:太医院院判刘文泰因私怨想要弹劾王恕,他与后军都督府带俸都事关昶一起商议,以王恕擅作威福等事为理由,写好了弹劾奏稿。之后,都御史吴祯以王恕编刊的自传涉嫌诋毁明宪宗为据,写了一份奏稿,并将之留在刘文泰家中。刘氏将吴祯奏稿中部分内容写入自己的奏稿中,后来吴祯又润色刘稿。此外,刘文泰招供奏稿中部分内容受到丘濬言论的影响,在拜访丘濬时,丘濬曾对刘文泰谈论王恕传记,认为不应该刊刻,有“沽直谤君”之嫌[3]1437—1438。锦衣卫镇抚司的这份报告,相比于涉事者的言辞,自然更令人信服。显然,即便按照刘文泰的供词所言,丘濬也构不成幕后主使,最多算议论失当、被人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皇帝本应按照锦衣卫镇抚司的建议,让刘文泰、王恕、丘濬三人当面对质,弄清事情原委。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明孝宗竟然拒绝了锦衣卫镇抚司的合理建议,而是以惩罚刘文泰草草结案。这就使得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在此之前,王恕上疏自辩时,提出过一个疑问:“文泰无赖小人,其造此机巧深刻之词,非老于文学阴谋诡计者不能。乞敕法司执文泰于午门前,会官追问及究主使之人,明正其罪,以警将来。”[3]1406—1407据文意可知,王恕认为刘文泰只是事件的表面人物,其背后有着主使之人。尽管王恕没有指名道姓地说事件幕后指使之人是谁,然而其言辞中“老于文学阴谋诡计者”具有极强的导向性,极容易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到丘濬身上。因为丘濬既有能力也有动机成为事件的幕后主使。他不仅是“老于文学”者,而且与王恕也多有不睦。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丘濬在弘治六年五月上疏自辩所言那样:“臣与王恕素无间隙。朝班之中,惟臣二人最老。班列序立,每相推让,且官皆极品,文学政事各有所司。于名于利皆无所争,虽其职任不同,而皆叨居百僚之首。”[3]1444其实,两人之间非但没有“每相推让……于名于利皆无所争”,相反在公开场合多次争斗,如内宴上争座次、罢黜官员问题上也争论[21]387。可见,王恕的言论,导向性很强,对于当时社会舆论也有很强的引导性。
正因为如此,前有王恕言论的引导,后有刘文泰供词的牵连,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自然会将丘濬视作事件的幕后主使。显然,实录传记的编纂者也受到舆论影响,“时议汹汹,谓濬嗾之,文泰下狱,词果连及濬”云云,特别是一个“果”字,近于定性的文字[26],其引导性甚于王恕言论。这表现出实录传记编撰者明显的情感倾向,相关记载的导向性十分强烈,甚至存在误导读者的可能性——认为丘濬是陷害同僚王恕的幕后主使。但是,实录编修毕竟是一项严肃的官方修史活动,只能采用“时议”“人自是皆不直濬矣”等字词来营造编纂者希望的导向性氛围,却不能罔顾事实,直接厚诬丘濬是幕后主使。可见,实录在记载这一事情的时候,既有编纂者情感倾向的渗透,同时也保持着一份谨慎态度。
如果将视线从实录转向其他文献,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形。前引明人王鏊《守溪长语》和陈洪谟《治世余闻》尽管在攀附中官问题上厚诬丘濬,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也与实录传记类似,只是用“或以为濬嗾之”[23]286和“人谓阴主刘文泰攻王恕”[24]39云云,却非断言丘濬是幕后主使。明人徐咸《近代名臣言行录》、郑晓《皇明吾学编》同样用“或以为公嗾之”[27]310和“众皆疑刘医官疏出公意”[6]564等类似言语,也不曾断定丘濬为幕后主使。这些文献均成书于正德、嘉靖时期,早于实录大规模流向民间的万历十六年(1588)[1]37,故而它们无法直接参阅实录传记的相关记载。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同于实录的另外一类叙事系统。两类不同的叙事系统,关于此事却有着类似的记载,即虽然渗透着史家明显的情感倾向,同时也保持着一份谨慎态度。因此,实录传记的相关记载应不是编撰者的刻意厚诬,而是当时社会舆论的投射。
总之,“丘濬是刘文泰攻劾王恕的幕后主使”的说法存在疑点。明人雷礼引用《理学明臣录》(7)按:雷礼《内阁行实》成书当在嘉靖四十年(1561)以前,所引《理学名臣录》绝非万历崇祯时期辛全《理学名臣录》,今已难寻,或已散佚。认为“丘密授风旨”[8]503、李贽《续藏书》以史论的方式发出疑问“非丘嗾之,医官敢讦奏冢宰哉”[28]258只是推测之词,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清人徐乾学[29]575、王鸿绪[30]24甚至错误地认为丘濬为刘文泰奏稿润色,更是有违事实(前文已述润色者应是吴祯)。但是,由于丘濬与王恕多有不睦,加上丘濬性格迂直、多次当面批评人,使得人们怀疑其为幕后主使。至于丘濬言论偏激、奇论范仲淹和秦桧,也当是其迂直的表现。明人何乔远评论:“丘濬立朝,有险谲之名。读书宿儒,亦岂宜尔?若迂与亢,疑有之矣!”[20]1944诚为不易之论。
四、结语
丘濬是明代中期的经世致用理学名臣,他在实录中的传记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前文比勘不同性质的文献,以实录传记为主要分析文本,从史实遮蔽和形象塑造两个点切入,讨论了实录丘濬传记的编撰及其意涵。
为了维护明孝宗的光辉伟大形象,实录的确遮蔽了丘濬在弘治五年因灾异上疏的史实。这本为实录惯常的编撰策略,并非只是针对丘濬一人。历来饱受诟病的实录不载丘濬为于谦辩白,非但不是实录遮蔽史实的例证,相反,因其真实性存在疑点,实录不载此事,恰恰体现出实录编修的严肃性、严谨性,反映出史官们谨慎的修史态度。因此,实录刻意遮蔽丘濬正面形象的史实,这种认识需要重新审视。
同时,实录对丘濬形象的塑造以正面为主,也存在少许的负面记载。言官们可以风闻奏事,他们对丘濬的诸多指控,都没有事实依据,甚至与事实截然相反。这自然是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的厚诬行为。与之不同的是,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实录厚诬丘濬是刘文泰攻劾王恕事件的幕后主使,却非中肯之论。不可否认,实录在相关记载中渗透着编撰者的情感倾向,表现出明显的导向性,可是实录并没有断言丘濬是幕后主使,而是以推测口吻记载时人的看法。与实录不同的叙事系统,也以类似方式记载此事,这更加说明实录并非刻意厚诬丘濬,它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之常态。
这例个案的考察,说明史书编撰和历史书写的复杂性。实录丘濬传记不足500字,然而它展现出的史实遮蔽和形象塑造问题则相当复杂,断难以“厚诬”二字一概而论。以往认为编撰者刻意遮蔽的史实(如“丘濬为于谦辩白”)、人物形象塑造的厚诬问题(如“丘濬是刘文泰攻劾王恕事件的幕后主使”),经过分析,却需要重新认识。反之,之前忽视的某些细节(如“丘濬在弘治五年因灾异上疏”“奔竞”),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史实遮蔽、人物形象塑造厚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