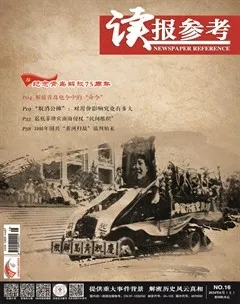“配享太庙”难于上青天
金陵小岱
所谓“太庙”,是古代皇帝用于供奉先祖神位的宗庙。早在夏朝时期,太庙被称为“世室”,象征着世代相传的家族纽带;至商朝,它被改称为“重屋”;周代叫“明堂”;一直到了秦汉以后,才被定名为“太庙”。
太庙是皇家祭祖的专有场所,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不过在最初,太庙仅用于供奉皇帝的直系先祖,其他的皇亲贵族压根没有资格进太庙。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太庙的供奉范围开始扩大。皇家在祭祀主神时,会将副神作为陪同一并祭祀,这个行为叫“配享”。那么在皇帝的特许下,皇后、宗室成员以及有着卓越功勋的大臣们被允许供奉于太庙,也就被称为“配享太庙”。
“配享太庙”有多难
配享太庙,指的是大臣凭借生前的勋业,去世后得以祔祀于帝王宗庙。在讲究“敬天法祖”的古代社会,能够“配享太庙”是朝廷给大臣的最高礼遇,对大臣来说是无上恩荣,能够得此殊荣者皆为朝廷的股肱之臣。同时,这份殊荣还能给整个家族带来声誉,对后代更是有着积极的影響。
早在先秦时期,《周礼》就有关于功臣配享太庙的记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凡有功劳的人,就书写他的名字和功劳在王的大常旗上,死后就在冬季祭祀宗庙时让他配食,司勋向神报告他的功劳。不过在商王武丁以后的甲骨文中,仅记载着伊尹配享先公、先王,至武乙以后,并没有出现有关于功臣配享的记载,说明这一时期功臣配享太庙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
到了三国时期的曹魏,功臣配享太庙这一制度开始相对稳定。据《魏书》记载:“昔先王之礼,于功臣存则显其爵禄,没则祭于大烝,故汉氏功臣,祀于庙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魏明帝曹叡登基后,于229年将曹操在邺城建立的宗庙迁至洛阳,并下诏将太祖曹操、高祖曹丕以及他自己(烈祖)的三祖之庙定为“万世不毁”。至233年,魏明帝曹叡正式实施配享太庙制度。《三国志·明帝纪》记载:“夏五月壬申,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
纵观历代配享太庙情况,能够配享太庙的功臣极为有限,大多为建立功勋的开国功臣,多数朝代配享功臣以武臣为主,明代甚至有“太庙专以武臣配享”之制,历代配享太庙的功臣总数不足两百人。
配享太庙的“另类组合”
古人若是能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或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也可以配享太庙,名垂青史,比如西晋的裴秀、唐代的安金藏。
据《晋书》记载,裴秀是西晋的名臣,少年时就颇有名气,好学多思,有风度节操。在魏晋朝代更迭之际,他能总括群臣进言的要领,他所裁定的事情,都不违背礼制。但单凭这些就想配享太庙,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裴秀这个人非常敬业,当时他任地官,这个官职可以掌管全国的土地、人口以及地图等事务。裴秀研究了一下,认为《禹贡》中的山川地名,沿用久远,后世多有改变,有些解说看着牵强附会,让人混淆不清。于是,裴秀采集甄别旧有文献,有疑问的先空着,古代有其名而当今不用的,也根据事实作出注解,作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皇帝,收藏于秘府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即地图绘制上的比例尺、方位、距离,及逢高取下、逢方取斜、逢迂取直,即把人行道路变为水平直线距离等原则。一直到了明末,都为中国制图者所遵循,在世界地图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有着如此突出贡献的“地图达人”,必须“配享太庙”!咸宁初年(275-280年),裴秀与石苞(西晋开国功臣)等并列王公之位,配于太庙享祭。
裴秀得以配享太庙,可以说是另辟“赛道”,但唐代的安金藏就显得有些惨烈。安金藏是唐代太常寺的乐工,当时的皇位继承人是睿宗李旦,原本这俩人完全不会有什么联系,但某天有个人跑去跟武则天告状,诬告睿宗暗地里有谋反意图。武则天一听,立刻就命来俊臣严查此事。来俊臣可是酷吏,睿宗的侍从落入他手里后,纷纷受不了酷刑,只好承认自己与睿宗共同谋反。谁知,安金藏忽然站起身来对来俊臣大声喊道,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我就只能剖开自己的心来表明皇嗣确实没有谋反!说完,他立刻举起佩刀将自己的胸膛割开,血洒了一地,他的五脏都快流了出来。
武则天听说后都被震惊了,赶紧命人将他抬进皇宫,让御医将他的五脏再纳进腹膛内,然后用桑白皮缝合,涂药。没想到过了一夜,安金藏居然苏醒过来了。武则天随后就下令停止追查此事,睿宗也因此避祸。这段故事被记载于《大唐新语》,世人皆为安金藏的忠烈之气而感动。安金藏去世后,配享睿宗李旦的庙庭。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