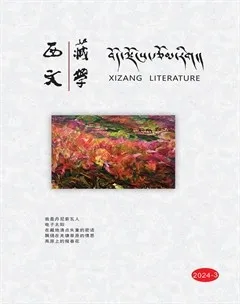高原上的报春花

格松卓玛,西藏大学2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藏当代文学。
青年与青春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杨沫的《青春之歌》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学者许子东曾评价:“《青春之歌》的特别,是把‘知识分子寻找道路与 ‘女人寻找爱情这两个选择无缝重叠。”①由此,理想与爱情这两大部分便成为青春文学中有力书写的重要内容。
在梳理西藏当代文学脉络时,发现每个时期都有作家创作出青春题材的作品。他们不仅写出了形态各异的青年,更是深入描摹了西藏青年对于理想和爱情的迷惘与艰难探索,尽管他们作为个体意义的作家,运用了不同的方式诠释爱情和理想,但其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20世纪50年代,徐怀中创作的经典作品《我们播种爱情》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评论界称《我们播种爱情》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②小说的内蕴十分丰富,不仅描写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日常,也书写了这片土地上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和远大理想,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气息。小说着重书写了青年们远赴边疆建设的远大理想,主人公倪慧聪起初是因为寻觅爱情来到祖国的边疆,但在认清爱情的虚伪本质后,依然选择为了理想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青春和理想“播种爱情”。
20世纪80年代,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江那边》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藏族青年面对理想和爱情的抉择呈现得淋漓尽致。书中的卓玛和单增都因失去爱情而感伤,但他们并不绝望。卓玛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甚至成为“三八红旗手”,单增也开上了机帆船,他们都在不断地向他们的理想与爱情靠近。扎西达娃早期的短篇小说正如李佳俊所说:“都是写藏族青年的,特别是城市下层青少年。”③扎西达娃时刻关注新时代新青年的现实生活,写出他们在新旧交替时,面对新鲜的生活内心所产生的微妙变化。
2004年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中,在小说中因迷惘而放纵的城市青年女性,成为她的主要关照对象——她们在新旧交替的商品经济时代不断挣扎又不断迷失。“白玛娜珍用细腻、忧伤和悲悯的情怀书写了女性的困顿人生,并将其放在历史进程和民族现代化的视野中,由此将对女性的观照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思考紧密相连。通过雅玛的爱情追求写出了女性在尘世中的惆怅与自我寻找的过程。”①
同样,由青年作家央吉次仁创作的,于2019年出版的《赤辛梅朵》,却显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质与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赤辛梅朵》是尤为特别的。在这本书中,央吉次仁别出心裁地将基层藏族大学生作为描写重心,不仅深入描摹了西藏波密基层人民的生活景观,更塑造出西藏当代文学中一批新的艺术形象——基层寻梦者。作家对他们真实而复杂的各种情愫与困惑进行了深刻阐述,更将他们放置在时代裂变的社会大潮之中,让个体与时代共振。为此,评论家魏春春曾做出过这样的评论:“《赤辛梅朵》展现的是藏族大学生在基层工作的生活景观,书写了以桑吉为代表的大学生们对基层的认知经历陌生、熟悉、依恋的过程,洋溢着青春激情、奉献基层的昂扬气息。这是近年来西藏小说创作中少见的文学气质。”②
《赤辛梅朵》是一部讲述藏族大学生在基层成长、抉擇、追梦和蜕变的励志小说。作者以桑吉的视角讲述了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工作的桑吉、其美、央宗及其同伴等人的职业变化、情感选择以及各自的心路历程以及具体到每一个个体上,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选择与取舍。
一、人物形象分析
“基层寻梦者”是央吉次仁在《赤辛梅朵》中重点关照的对象。他们有着丰富敏感的内心和鲜明的自我意识,面对爱情和理想等巨大命题时有着各自的考量与坚持。这一群大学生迷惘并困惑于自己的生活、感情和价值追求,形成了一组基层寻梦者群像——他们努力在探索、追求着自己认为更有意义的“未来”,有的想方设法逃离基层去寻梦,有的脚踏实地扎根基层,在基层工作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有的在安逸与挣扎中逐渐迷失自我。
(一)江白: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作为青年干部,江白是西藏基层生活真正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他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热爱文学,更热爱这片养育他的土地。毕业后,他回到松宗乡工作,由于表现出色,他本有机会高升而移调县城,但他不为所动,执意留在基层工作。许多同事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他是“极品”。而在老百姓的眼中,他却是“活菩萨”——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村民,建设乡村。从这个角度而言,江白是基层干部中的坚定理想主义者,他认定了在基层工作的价值,并愿意为之付出一生。
江白是清醒的、严肃的。他始终坚定、真诚而又极富力量感。当谈及抉择时,他说“这个世界能轻易干扰你,易如反掌。在命运的手下,你就是个玩偶。可恰恰因为这样,你就应该只管负责走你自己的路,就像……我想一个人,只有在内心没有方向时才会依赖外在的选择。如果心有所属,就不会有选择困难症,即便是面对命运的捉弄,也在所不惜地走到底。”①他并不困惑于自己的理想追求,对自己的道路也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对自己的生命高度负责,但当面对死亡时,他又极其豁达地认为它只是一场暖曲——死亡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所以在小说的末端,我们看到江白为了拯救朋友与集体而葬身火海。
但江白也有弱点。在爱情上,他同样多疑、自卑、胆怯。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说《一个人的小镇》中叙述的一样:“他爱上了一个姑娘,但她是一个路人。”他自认为桑吉对他而言只会是生命的过客,所以他十分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情感。而在得知桑吉要去拉萨见诺杰后,他生硬且艰难地向她送出了祝福,却在接下来做出了“因为白珍需要我,所以我要娶她”的愚蠢行径。
江白之外,默默无闻的扎西乡长是另一位坚守在基层的乡村干部,留在基层工作是他们共同远大的理想。作为第一批内地西藏班毕业的大学生,他原本有机会留在拉萨平步青云,但他却选择扎根在基层、并努力为当地的民众谋利益。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甘愿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层。幸运的是,多年以后,他与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央宗结识,并在相互的交往交流中情投意合而最终喜结连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整部小说中最完美的结局,也是作者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的最美好的祝福。
(二)桑吉:因爱成长,坚定理想
江白和扎西乡长是基层工作的坚守者,他们代表着身处落后乡村却能忍受艰苦环境的优秀乡镇干部。在他们的影响与感召下,一批新人在逐渐成长。从刚开始的懵懂、无知、犹豫与困惑,到定位自己、坚定理想信念,他们最终都成为坚守基层工作的接班人。这其中桑吉和央宗最具代表性。
桑吉是在内地求学10年之久后回到故乡——毕业后她被分配回了原籍工作。对此,她既感到不甘心又无能为力。“到底要去多远的地方啊?路途遥远……她所热爱的电视专业和他,该如何在一个偏僻之地得以继续呢?”②从一开始,桑吉似乎就显得十分犹豫与困惑。作为一个见过大千世界的人,她的抱负似乎绝不是一辈子留在乡村,所以初到松宗乡的她总是有着最复杂的情感与思绪。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试图规划自己的未来,并追问自己的方向——我将走向何处?幸运的是,在经历了并不漫长的思想挣扎后,她逐渐被松宗乡宁静的环境所吸引,自己也在日常琐碎却极充实的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在深入结识江白和扎西乡长等人之后,她更是被他们坚定扎根在基层的精神所感动。最终,通过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考量,桑吉迅速成长为新一批的基层追梦者。她自己也将成为一朵生在无名山间的赤辛梅朵,并和江白等基层坚守者一道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奉献自己、无怨无悔。
而当面对爱情时,桑吉则把女性的复杂性体现淋漓尽致。约·福特说:“爱情是心中的暴君;它使理智不明,判断不清;它不听劝告,径直朝痴狂的方向奔去。”①在困于诺杰和江白之间时,桑吉也曾丧失过理智。她很苦恼、疑虑,许多时候不知所措。直至前往拉萨与诺杰会面时,桑吉才终于听清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她必须坦诚接受自己已喜欢上江白的事实。所以她告别了诺杰,并在休假结束后很快回到松宗乡,也由此真正走向了江白。“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便意味着一次尽管残缺却无憾的人生……因爱而获救的不仅是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不仅是爱者和被爱者,而且是一处精神家园。”②桑吉和江白后来的爱情便是如此,尽管他们的最终结局因为江白离世看似是一个悲剧,但他们却因彼此的存在找到了自我价值的意义,并因心灵的相通寻求到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除桑吉外,央宗也是基层成长者的另一代表。即便她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更多时候只存在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但她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与桑吉一样,央宗同样经历了抵达基层之初的疑虑、困惑甚至恐惧。当她获悉自己被分到最艰苦的康玉时,她的脸便开始扭曲和抽搐,最后甚至半跪在县委书记前抽泣,“求您了,我不去那里。……”③但就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央宗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变得自信而优雅,眉宇间还透着一股干劲。一如她自己所言:“很好,我工作得很卖力……我觉得实现了自我价值……感觉自己正在熊熊燃烧……”④
作为初到基层的青年,央宗同样是在扎西乡长等人的关怀和鼓励下迅速成长。最终,这些基层迷茫者都完成了蜕变,她们不再畏惧或疑惑,而是在工作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她们是基层坚守者的追随者,最终也成了基层工作的坚守者,他们都是有远大理想的人,而基层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一个广阔空间。
(三)其美:追求优越的物质生活
基層寻梦者是多元的,在其内部,同样遍布着时刻考虑离开基层的人。这其中,其美是最典型的代表。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也见过繁华世界的大学生,其美一直都在追求一种相对富足而又闲适舒服的生活。因此,当她得知自己被分到松宗乡时,她便谋划自己离开乡镇的道路。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她便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他人。当领导来视察的时候,她抓住机会谎称自己有播音才能,后来她得以顺利调去县上,又开始计划继续依附男人前往更繁华的拉萨。从这个角度而言,其美的理想对应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她非常清楚这一点,但她并不为自己感到有任何不齿,因为她并没有太崇高或太远大的理想和价值要去实现,她只是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生活里过得更舒坦一些。
所以,当她的这种生活追求与其他事物发生冲突时,后者便不得不被摆在相对次要的位置,比如爱情。总体上说,其美的爱情观是实用主义的,本质上需要服务于她摆在首要位置的富足生活。她也曾相信过爱情,但过往的情感经历却让她无法找到切实的依靠。所以当多吉向她表达出热烈的爱意时,她却认为“男人到后面都会变化。”尽管如此,她也无法掩饰自己内心对多吉同样产生的好感。所以在县城和桑吉相聚时,她并不忘让桑吉也给多吉带回一盒肥皂。另一方面,她又始终留出足够的空间去对待那些有更大机率带她走向拉萨的其他男人。到了最后,其美完全放弃了和多吉的感情,选择与一位中年干部结婚。面对桑吉的提问,她说:“还算喜欢吧,有前途,有房子和车子,还能帮我调到地区呢。”① 由此可见,其美之所以愿意嫁给中年干部,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能帮助她实现离开基层、走向繁华都市的愿望。
(四)旺杰:迷失自我的青年
除此之外,在基层寻梦者群像中,作者还塑造了一类在基层工作中的迷失者,而旺杰是其中的代表。
同桑吉、其美等人一样,旺杰也被分配到了松宗乡。他毕业于四川大学的通信专业,长得高大俊俏。刚抵达基层时,面对书记提出的“与全乡电视有关的工作”,他非常积极地高举右手,并且抢先获得这份工作。但当他真正去从事这份他本以为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时,他发现这无非就是每天爬到后山坡进行最简单的开、关闭路电视。因此,不出几天后,他便很快对这份“事业”感到深恶痛绝。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才能终究无法在这个落后的小地方得以施展——他也不愿改变自己积极去适应环境,所以旺杰很快失去了在工作上的干劲。
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漂亮姑娘身上。由此,他的生活重心也慢慢倾向简单的享乐主义。他喜欢社交,也喜欢结交年轻姑娘。按照他本人的想法,他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万人迷”,所以在他们这个群体中,他最像一位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至于对待感情,他玩乐的意味似乎更大。久而久之,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旺杰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志向,他变得随遇而安。而到了最后,因为自己和村长的女儿好上了,他便选择入赘到他们家。对此,其美对他的评价是:“旺杰怕是要永远留在波密了,当人家女婿嘛,玩过火了。半推半就地就要结婚了。”②
起初,旺杰也是有抱负的,但当身边的环境与条件不允许他施展自己的才能时,他便很快放弃了自己在事业上的追求。同其美、桑吉和江白等人不一样,旺杰既不考虑要如何提升自己,也不积极改变自己去适应基层的需要。他变得随波逐流,慢慢走向了自我迷失。
这一群基层寻梦者是多样的,他们的道路不尽相同,在对他们进行的描述中,作家比较明显地带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即“离开基层可以被理解,但真正热爱基层、甘愿奉献基层,并能从中找到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却显得尤为可贵。”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象征是文学表达法的较高级模式”③,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常用的艺术手法。它使文学作品增加了暗示性与多义性,并给文学接受者带来克服“艺术困难”的审美体验。在《赤辛梅朵》中,央吉次仁大量运用了这一方法。小说中的许多象征不重视事实的描摹,更在意具象到抽象的提炼,并表达出表层和情节之外的哲理。
(一)赤辛梅朵:无私奉献
首先,小说题目是最显而易见的第一象征。赤辛梅朵原本是一种花,中文名为报春花,有两种颜色,味道很香,根部笔直,长在干净的溪边。小说中,作家前后共7次谈及赤辛梅朵。第一次出现是在《秋日麦浪》这一章节,“我老家在热振。我幼年在那里,那里有松柏、寺庙和赤辛梅朵。我只知道它很香,杆子笔直,长在最干净的清泉边。”①在这里,赤辛梅朵就是一种花,并没有使用象征意义;而第二、第三次出现则是桑吉在形容江白,“我接触过许多人,很多好人,很多善谈的、礼貌的、优秀的、有钱的,可是没有见过他那样的男人。尽管别人不理解他,但我觉得他是一 个……怎么说呢,像赤辛梅朵那样的人。”②也是从这里开始,赤辛梅朵和江白联系在了一起,而其象征义也随即诞生——赤辛梅朵指的就是江白,江白就是赤辛梅朵,他们同样纯洁、坦诚而又坚韧。进一步说,赤辛梅朵还象征着像江白和桑吉一样奋斗在基层的所有追梦者,他们坚守初心,甘愿留在基层,并且遍及西藏的每一个小角落,一如生在僻静山溪间的赤辛梅朵。尽管少有人问津,但它们亭亭玉立,并成为那一方水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死亡:艰难困苦
江白的死也颇具深意,在小说末段,桑吉和江白即将举办婚礼,此时两人的爱情与事业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融合,但就在这看似最圆满的时刻,作者却为江白安排了一场有关扑灭山火的意外死亡——为了拯救集体财产和多吉的生命,江白最终牺牲了自己。由此,松宗乡最挺拔的赤辛梅朵倒下了,获悉的桑吉悲痛欲绝,一时难以接受。对于这样的情节设置,作者似乎是有意为之,她似乎是想告诉读者:追梦者在追寻理想时绝非一帆风顺,因为前方的道路从来都是崎岖而充满险阻的,而江白之死便象征着追梦路上沉重的受挫与失去。但让读者又感到一丝宽慰的是,作家在最后又为悲剧的发生增添了一丝亮色——桑吉怀孕了。
(三)新生:希望
事实上,桑吉的怀孕可以看成第三个重要象征——她肚子里的新生儿不仅是桑吉和江白的爱情结晶,更象征着新的生命与希望。也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江白似乎从来没有彻底离开,赤辛梅朵依旧挺拔在原处——不仅桑吉会继承他的意志,他还后继有人。一如桑吉在雪中恍惚看到的场景——“那个男子却转身不见了,消失的速度就像片片雪花,说消失可能不够确切,似乎更像是消融了,消融进了温润疏松的黑土地里。”③
相似的情节还有三个石头的溺亡,事实上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另一悲剧,但正如最后一章的标题设为“重生”一样,小说的最终色调并不阴冷,因为自三个石头离世之后,他那消失多年的妻子玉珍却回来了——一切仿佛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死亡看似是终结,但它又孕育了新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江白和桑吉从来都不是在孤军奋战,小说的结尾用一辆大巴车驶进院内作为全书最后的场景。这意味着又一批“新人”来到了松宗乡,意味着又一批“新江白”和“新桑吉”会逐渐成为像赤辛梅朵一样的人。传承从不停息,理想从未消失,希望永不断绝。
三、人物塑造的得与失
客观而言,在对这群基层寻梦者进行形象塑造时,央吉次仁较好地完成了不同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但对个别人物的描写则多少显得有些单薄。如央宗,她很多时候只存在于人们的只言片语中,因此央宗的性格特征不鲜明、不丰满。除此之外,江白的出场也有一些不够自然与和谐,尤其是在突出江白的不一样与特别性部分,如第四章《初来乍到》中,江白一出现就自带主人公光芒,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作家的叙述语调与用词多少显得有些刻意。如在第五章《极品江白》中大家一致认为江白是奇葩,在和桑吉交往过程中江白也一直扮演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文艺书生的形象,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均和别人不同。与此同时,纯情而固执的多吉代表着一类较为典型而特别的爱情观,但关于他的篇幅和刻画则较少,不论是在形象塑造上还是在个人性格方面,他都不突出。
尽管如此,作为青年作家的央吉次仁却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当对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塑造时,她并没有为了谋求差异而选择极端化或脸谱化的写作手法,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其美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作者即写出了其美在现实生活中对物质的追求,也写出了其美真诚、善良的一面,如为桑吉准备生活用品,陪伴在她身边,真诚地安慰与劝诫她。事实上,《赤辛梅朵》是一本价值观鲜明的作品,其美在小说中选择的道路赋予了作者的批判。因此,作家其实完全可以将其塑造成丑角,但央吉次仁没有这样做。她放弃了对比性更大的两元对立写法,因而在塑造其美这一人物形象时,她始终对她抱有深刻的同情与理解。在作品中尽管我们看到其美通过撒谎调到县里,后来又通过嫁给老干部彻底离开了基层,但读者就是很难对她憎恨起来。
谢有顺说:“好的作家,总是能够通过生活现象和世事变化,看到人心万象,看到生活背后始终存在的各种疑难,文学就是对精神疑难的探询,这个精神疑难,可能是永远也解答不了的,文学对这些问题的苦苦追问,就是为了使人類不断地自我反省。”①同样央吉次仁关注到了藏族大学生这一群体,并观察到他们对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困惑。因此站在青年人的立场创作了一部“以寻梦为题的青春之歌”。在小说中,央吉次仁一直在试图告诉读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追求,无所谓对错。松宗乡是作为其中一部分人实现理想的平台,作者不仅颂扬了在基层实现理想的大学生们,同样也没有丑化走向灯火阑珊的城市去追寻理想的大学生。拥有一颗友爱之心,积极向上地追梦是这部小说的主旋律。
作为西藏当代青春文学的一部分,《赤辛梅朵》具备特别的品质。央吉次仁立足当下,在时代的呼唤中独到地将目光聚焦在藏族大学毕业生的身上,她抛开二元对立与脸谱化的写作方式,成功塑造出一群形象较为丰满的基层寻梦者。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