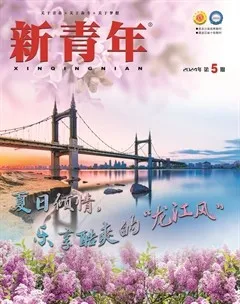义学书声琅
石红许
在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横街镇,玉琊溪畔,我去寻访桑田古庙,去聆听隔着时空飘来的琅琅书声。
桑田古庙,始建于唐末宋初,到了南宋时,当地一位乡贤刘允迪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隆兴元年的进士,最初办义学的场所,正是桑田古庙。
所谓义学,也称“义塾”,旧时一种免费的学校,资金来源为地方公益金或私人筹资。换句话说,义学就是招收一些贫寒人家的子弟,进行启蒙教育,教授《三字经》之类的内容,让人学会识文断字。
而今,桑田古庙就在镇政府内,是刘氏义学的遗址。走进桑田古庙,已看不出寺庙的模样。阳光洒在地面上,泛出斑驳的光影,增添了历史厚重的色彩。桑田古庙里面横卧的一块石碑引起了我的兴致,但石碑风化严重,加上人为损坏,几乎辨认不出一个字来。多么希望着能在上面读出一些关于义学的文字来,哪怕是一鳞半爪也好。横街还生活着刘氏后人,他们的家谱上对义学有着详细记载。桑田古庙,也与大儒朱熹有缘,曾题诗《桑田登云》《梅峡清溪》《黄山万松》等八首。
当年,朱熹与刘允迪的交情不同一般。一个在南康军(星子县)任职,一个在邻县德安任知县,彼此来往密切,甚至朱熹还前往探访取经。那时,刘允迪就十分重视教育,“淳熙八年(1181)县学圮于水,知县刘允迪为之重修。”朱子很是欣赏刘允迪的才学,尤其欣赏他归隐田园后自筹银两兴办义学之举,“捐养廉银以建义学,聘知名之士以教宗族子弟及乡人之愿学者,割田八百亩以供义学师生食宿开支”。一个封建士大夫,不为名利,舍得付出,真是了不起。
为此,朱熹又来横街拜访刘允迪,并主动请缨,亲自讲学,且留下了墨宝《讲学至言》《刘氏义学碑记》《义学堂八景诗》等,其中“八景”指的是:梅峡清流、古池跃锦、团村高桥、石壁钓潭、梅坡墟市、黄山万松、桑田登云、花山逸庵。岁月嬗变,时过境迁,而今有些景点早已不存,但我还是沿着玉琊溪去寻找那“梅溪八景”。在古代,玉琊溪又称梅溪,调查访寻,一一比照,在似是非是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去感受、去仰慕刘允迪的义薄云天。
不但重视义学,刘允迪治县也很有建树,在德安任职,他政绩突出。德安的名宦祠里,列有刘允迪之位,百姓常来祭祀,就是明证。当年,德安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刘允迪冒着丢官的危险,上书要求减免税赋,并提出开仓赈灾。经过刘允迪的再三请求,终于得到朝廷批准,德安的社会也慢慢走向稳定。刘允迪又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恢复生产、發展生产,德安人民渐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千百年来,刘允迪“以德安民”的故事一直在德安大地上广为传颂。
朱熹还撰写了《允迪公行谊》,概述了刘允迪一生,存于刘氏家谱。文中“人材赖以造就者众,而科第不乏人”算是点睛之笔,然刘氏义学,前后究竟培养了多少学子,或已不可考。横街当地有心人统计过,在刘氏义学读过书的乡族子弟有24人中举登科,贤才辈出,入仕者众,这是非常喜人的成果,正应了那句话“凡乡里义学兴盛的地方,其科举必盛”。
庆元元年(1195),刘允迪之孙刘麟将桑田古庙改为“登云社”。至明正德六年(1511),又改为“登云义学”,并于中堂挂朱熹和刘允迪的画像,以此激励、训导学子。桑田古庙,自南宋后,历朝历代一直扮演着义学场所的角色。侧耳倾听,那穿透岁月的琅琅书声正随风缓缓飘来。
早些年,横街建了行政大楼,竣工交付使用时,当地政府却毅然把大楼用作学校,而自己却悄悄地搬进了破旧的桑田古庙办公,这里面难道没有刘氏义学所折射的光芒吗?
一段义学佳话,光耀史册,映照着桑田古庙,也映照着横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