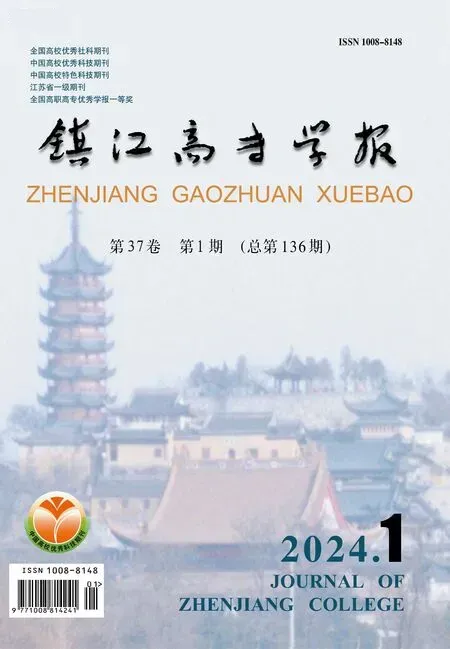论郁达夫《毁家诗纪》中自传体诗文的书写
杨仲友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不仅以小说闻名文坛,而且旧体诗也颇为时人所青睐。刘海粟认为郁达夫“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1]绪言。郭沫若也曾言:“他的旧诗词比他的新小说更好。他的小说笔调是条畅通达的,而每每一得无余;他的旧诗词却颇耐人寻味。”[2]454《毁家诗纪》作为郁达夫旧体诗的代表,创作于1936年至1938年,主要书写了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变过程,带有自传体性质,诗作凝练深沉、凄婉动人。在组诗发表前夕,郁达夫为诗作添上注文,使得“毁家”的来龙去脉更清晰具体。诗作与注文互补,不仅是了解郁达夫、王映霞两人婚变的第一手材料,还是了解郁达夫生平经历的重要文献资料。笔者探赜《毁家诗纪》自传体诗文的特色及其背后的成因,挖掘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以期进一步推动郁达夫相关研究。
1 自传体诗文的特色
1.1 诗文合璧,相得益彰
《毁家诗纪》共有19首诗、1阕词、19条注文(第5首诗没有注文),围绕“郁王婚变”书写了诗人“毁家”的心路历程,抒发了诗人痛苦与愤懑之情。诗作在表达方面较为含蓄凝练,而配之以晓畅直白的注文后,诗作与注文互有照应、相得益彰。
例如第8首诗写到:“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1]458在诗的前三联中,郁达夫借用“空台、碧落、横塘”等意象,营造了清冷孤寂的氛围。尾联一句“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不免让人心生疑惑,作者因妻子不在身边而伤心难过,这是人之常情,但武昌为何成为诗人记忆中痛苦的“伤心地”?用“侯门断肠”的典故又有何用意?结合注文提供的背景和细节,读者便能解开相关疑惑。注文写到:“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眠,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1]458原来诗人的妻子王映霞来武昌与诗人相聚后又隐藏不见,诗人在屋角寻得三封王映霞与“许君”的情书,才判断妻子恐怕是与别人私奔了。诗人的妻子在武昌席卷了所有东西后不辞而别,诗人非常伤心与痛苦,故而诗人在诗作中强调了武昌是伤心地。“侯门断肠”则化用了崔郊《赠婢》的诗句,暗示所爱者被劫夺。读者结合原诗与注文,可以更加眀晰这两句诗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与思想情感。郁达夫以悲痛婚变作为主题,配上详细的注文,“实则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文合璧形式,以前是文中镶嵌诗,他这里是以诗牵带文。其诗含蓄深沉,其文则畅快直白,诗文相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段恩爱情仇”[3]。
相较于《自述诗十八首》《青岛杂事》等组诗的注文,《毁家诗纪》的注文更丰赡翔实,自传体的风格也更明显。而郁达夫“毁家”奔赴星洲(新加坡的旧称)后,又撰写了《乱离杂诗》12首,却并未配上相应注文,其自传体特色因此就远没有《毁家诗纪》明显。
1.2 国难婚变,相互交织
《毁家诗纪》创作于1936到1938年,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处于战略防御之际,作为一介文人,郁达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关切民族命运,勇于担当时代使命。投身抗日救亡之际,遭遇爱人背叛,郁达夫将一腔悲愤付诸笔端,便有了国难婚变交织而成的“毁家”泣血之作。
在《毁家诗纪》中,既有“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1]464的豪情壮志,也有“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1]458的伤感哀叹;既有“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1]462的为国奔走,也有“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1]452的孤独落寞。其中的《贺新郎》将国难家愁相互交织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其词云: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1]471-472。
在该词中诗人将悲忆“毁家”之耻与痛定为国忍辱结合起来,发出暂忍“莺燕小丑”与“先逐寇,再驱雉”的悲愤之言。其愤懑凄切之情、沉郁哀怨之感,读后令人动容。郁达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4]613,牺牲后,墓碑上刻着“爱国诗人郁达夫之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5]162国家的不幸,使得郁达夫与妻子聚少离多,产生婚变,悲从中来,便有了这悲愤至极的《贺新郎》。郁达夫将婚变经历融入国家的抗日救亡,“从头到尾将国难家难交织在一起”[6],创作了一组情辞哀婉、凄恻动人的自传体诗篇。
2 自传体诗文的成因
2.1 “袒露自怜”的性格特点
“袒露自怜”[7]27一词出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对郁达创作风格的评价,编者认为郁达夫的作品呈现暴露自我、袒露内心、自伤自悼的特点。郁达夫生长在清末乱世,3岁丧父,两位哥哥比他大很多,他自小缺少玩伴,再加上家道中落,便养成了孤独害羞、顾影自怜的性格。郁达夫在自传中曾坦言:“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2]25-26到日本留学后,郁达夫受到日本“私小说”、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日本“私小说”侧重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合理欲求,认为“情欲”是人的自然天性。加上留日期间受到的民族屈辱与回国后经受的贫病煎熬,郁达夫内心充满苦闷、矛盾、痛苦、哀叹之情,想要解放却又不能彻底解放,不断抗争又不断妥协,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既袒露内在又自伤自怜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在其早期文学作品中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小说《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的病态性欲描写以及结尾处发出的期望祖国强大的呐喊,都充分体现了他想要暴露内心、解放自我,却又深陷苦闷而自哀自怜的矛盾心理。“他的民族自尊、性苦闷和沉沦般的心底波澜,化为激愤控诉、大胆暴露及无顾忌的自虐自伤自悼的文字”[7]67,这些文字正是其“袒露自怜”性格的外在展现。
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通过大量详细的注文袒露自我,陈述他与王映霞的婚变私事,在陈述的同时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自伤自怜。在《毁家诗纪》第8首诗的注文中可知,诗人的妻子同他人私奔,诗人恼怒异常,拿妻子的衣物作发泄工具,但却束手无策。这种不光彩之事,旁人唯恐避之不及,他却公开发表,让天下人知晓,既暴露了夫妻双方的个人隐私,又陷妻子于不忠,而不反思自身原因。此外,在第15首诗的注文中他写到自己在酒楼上听流娼卖唱,百感交集、醉不成欢,又恐被人传为话柄,作离婚的讼词。虽然料想到最后可能对簿公堂,但是仍惧怕被传作话柄,可见诗人内心的矛盾和幼稚,在两性关系和人情世故方面不够成熟。郭沫若为了批判封建士大夫的虚仁假义对郁达夫诗文中“袒露自怜”的自我暴露书写曾如此评价:“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假的困难。”[2]76“露骨的真率”当然是指郁达夫真性情的自我流露,但他将闺房之事公告天下,除了感伤自怜、博取同情外,却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两人离婚的过程。
2.2 “骸骨迷恋”的心迹表达
“骸骨”指尸骨,引申为陈旧腐朽的事物,“骸骨迷恋”一词来自叶圣陶在1921年发表的文章《骸骨之迷恋》[8],叶圣陶在文中批评当时一些人提倡白话文学却还有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之后“骸骨迷恋”一词便常被用来形容守旧者留恋过去。郁达夫在散文《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中曾提到自己的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钟情用“骸骨迷恋”的旧体诗表情达意[2]202。郁达夫用旧体诗创作《毁家诗纪》,有以下3方面影响因素。
首先,作家成长环境的影响。郁达夫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富阳,耳濡目染古典文化,沉浸在旧体诗的环境氛围,自小便会吟诗作诗,郁达夫曾有诗云“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生小便聪明”[1]179。在《自述诗十八首》里,郁达夫也提到受李白、龚自珍、吴伟业诗作的影响而写诗,“删尽定公哀艳句,侬诗粉本出青莲”[1]176,“忽忆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1]183,还曾受清代诗人黄仲则的经历和诗作的影响写了一篇自传性小说《采石矶》。从“九岁题诗四座惊”到遇害前夕他均有相关诗作,“旧体诗写作依然是他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最本能的方式”[9]。
其次,旧体诗语言精炼,更便于含蓄隽永地表达诗人内心情感。郁达夫在散文《骸骨迷恋者的独语》中写到:“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的想头来了。目下在流行着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象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了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2]202诗人在文中特意作诗一首表明自己中年生病、生死皆难的窘境,“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2]202。如果用新诗来写,可能几十行字也难以详尽其中的窘况,但是用旧体诗,作家言简意赅地将自己人到中年两难的困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旧体诗相较于传统小说、新诗等文体,格律音韵要求很高,文字洗练、意蕴深刻,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优点,非常便于抒情。
第三,旧体诗可作自注。诗作用来抒情,注文用于叙事,诗作与注文结合,能很好地兼容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与展现的细节。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充分将诗词简约、注文晓畅这两种文体的特点结合起来,使得《毁家诗纪》简约而不单薄,详细又不冗长,二者相得益彰。例如第3首七言绝句,仅仅28个字,就写出了诗人夜醉江城,独自一人在渡口看明月潮生的情景,而注文有200字,详细记录了他的妻子因抱怨富阳生活太苦而随情人离去,他虽有耳闻却半信半疑的经过。诗作与注文,长短有节、相互配合,很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与其中的曲隐。
3 自传体诗文的价值
3.1 内容史料: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及婚变的有力佐证
叶舒宪在《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中提到四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和文字;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图像和实物。”[10]四重证据法对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及文学而言,均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加以借鉴参考。《毁家诗纪》可归入一重证据,其20首诗词及其注文,作为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代表,对研究其诗词写作、个人经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意义。而对了解夫妻二人从结合到解缡的曲隐过程,尤其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
郁达夫的旧体诗创作贯穿诗人整个文学生涯。按照写作的地域范围,目前存世的近600首诗作可分为“留学日本诗”“国内诗” “南洋诗”三类。写于1936到1938年的《毁家诗纪》风格哀婉深沉、凄楚动人,是其“国内诗”的代表,其中七绝有7首,七律有12首,外加词一首。《毁家诗纪》书写了诗人丰富的内心情感变化:有呈现羁旅他乡的寂寥孤苦,如第1首七绝有云“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1]449;有表达有家难回的落寞伤感,如第7首七律有云“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1]456;有表现诗人面对妻子出轨的愤懑悲痛,如第8首七律有云“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1]458;有抒发为国纾难解困的家国情怀,如第13首七律有云“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1]464。《毁家诗纪》内容丰富翔实,情感富于变化,同时灵活使用典故、借代、对偶、比喻等手法,增强了诗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是研究郁达夫旧体诗创作不可忽视的代表诗作。此外,“郁王婚变”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未了的公案,双方各执一词而未有定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扑朔迷离。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诗注本身,20首《毁家诗纪》的诗词及其注文,以诗人婚变作为主线贯穿全部组诗,既陈述了其妻王映霞出轨之事,又刻画了诗人发现妻子出轨后内心诸般痛苦的心境,还展现了诗人劝阻妻子回头是岸与其同渡南洋的凄婉经历,是了解和研究“郁王婚变”的重要史料。
3.2 形式文体:推动旧体诗自传体诗文的深化发展
学者吴承学在《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一书中写到:“中国古代的诗序有其独特的艺术功能,诗序可以弥补抒情短诗的某种缺陷,它扩大了诗歌的背景,增大了艺术含量,增加了诗歌的历史感。优秀的诗序与诗歌,宛如珠联璧合,不可或缺。而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诗序翔实的叙事,有益于诗人在诗中集中笔墨抒情言志,使诗歌兼叙事与抒情于一身,同时又保持凝练、含蓄之美。这其实是文体上的一种创造。”[11]82-83古人在创作诗歌时,往往会在诗歌前加上一段小序,像白居易的《琵琶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或阐述历史背景,或交代写作缘由。诗歌抒情,序文叙事,诗歌与序文相结合,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此外,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将进酒》等诗作,不在诗作前撰写序文,而将序文内容融入诗作,以长篇形式展现。郁达夫的《毁家诗纪》则不然,它既不以长篇取胜,也不在诗作前写序文以交代毁家之经历,而是以“婚变”作为主题进行创作,每首诗书写毁家时的某个方面、某种心境,事后统一添上注文,细化毁家的经过,加强“婚变”主题的同时,通过注文串联起不同诗作,使之成为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分散又集中的组诗整体。这在旧体诗的发展史上,可谓别具一格而自成一家。
郁达夫在旧体诗的创作方面,祧唐祢宋,转益多师,遵循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12]64的诗学之路,不局限于一家一人之言,而是采集百家之长后自出机杼。在自传式诗文的形式文体方面,他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不落窠臼,敢于推陈出新,诗作与注文并呈,抒情与叙事一体,不仅拓展了诗歌的表现范畴和呈现形式,还增强了诗作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诗注互补的文体形式,在现代作家的旧体诗创作中也时有出现,“如沈祖棻《涉江诗词集》中作于抗日战争与两年内战时期的部分作品在结集出版之时由其夫程千帆加以笺注,意在记述词作所对应的时事及作者之情思寄托;金克木晚年亦将所作旧体诗整理结集并自加注解,以发其‘隐情’”[13]。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诗作书写的内容与注文记录的内容,有时并不十分贴切,呈现“诗注错位”的现象。例如在第6首诗作中“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1]455两句诗书写诗人投身抗战的情形,但注文转而记叙妻子与第三者往来的经过。但这种 “诗注错位”的现象并不妨碍读者对整组诗作思想与情感的把握。诗人得知妻子的出轨对象有了新欢已疏远其妻后心情大好,与诗作中收到捷报飞传的高兴心情互有照应,读者可以借此加深对诗人收到捷报后心情的理解。与此同时,较为详尽的注文将碎片化的诗歌内容梳理出清晰的叙事脉络,使诗作在逻辑上浑然一体。
《毁家诗纪》发表前夕,郁达夫统一为诗作添上注文,诗作与注文互释、互证、互补,勾连出夫妻二人十来年的感情变化的详细过程,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学者许凤才在郁达夫遇难60周年之际写到:“《毁家诗纪》及其原注文字是血和泪的结晶,是郁达夫的一段自传式的诗史。”[14]郁达夫在《毁家诗纪》中的自传体诗文书写,推动了旧体诗自传式诗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