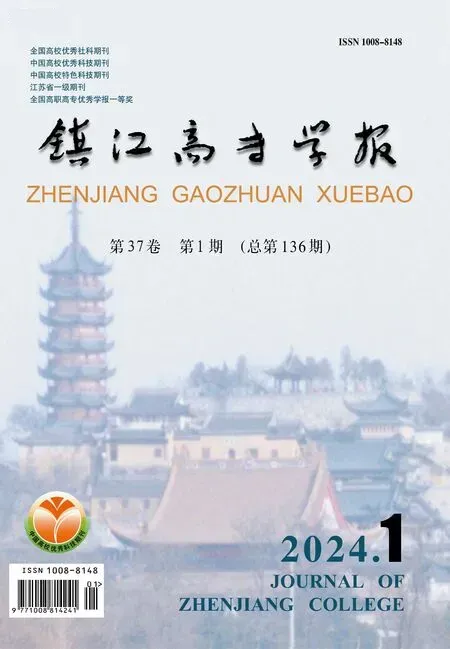赛珍珠在华教育实践与思想探析
李永卉,卢章平
(江苏大学 a. 法学院;b. 科技信息研究所,江苏 镇江 212013)
赛珍珠是一位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美国当代女作家,其描写20世纪初中国皖北等地农村生活的小说《大地三部曲》于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同年随传教士父母来到江苏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江浦区),后定居江苏镇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赛珍珠分别在中国和美国求学,毕业后在镇江、宿州、南京等地从事教学活动。她密切关注中国的民众教育,其在华教育实践和思想既与教会密切相关,又深受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影响,具有强烈的平民化倾向。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以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推行平民教育,赛珍珠返美后积极为之宣传与筹款[1]。目前关于赛珍珠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很少有人关注赛珍珠在华教育实践及其思想[2]。笔者拟在梳理赛珍珠在华教育实践基础上探索其教育思想以及该思想形成的原因,以期补充赛珍珠相关研究。
1 尊重社会现实:理性客观
赛珍珠在华教育活动始于大学毕业后。1914年赛珍珠从美国梅肯—伦道夫女子学院毕业[3],原拟留在美国,但因远在中国的母亲身染重病,遂决定回到母亲身边。虽然她对传教士职业并不感兴趣,但仍然给父母工作的长老会域外传道委员会写信,请求“立即派我到中国当教师”[4]105。回到镇江后,她一面照顾母亲,一面在教会学校从事教学活动。
赛珍珠在镇江任教,“在新建的男校教课和指导17至20个为参加其他学校的各种类型的工作而受训的中国年轻妇女”[4]110。她对教学较感兴趣,“因为我的学生并非小孩,而是高中生,远比他们这个年龄的西方学生成熟得多”[4]112。她很喜欢学生们,“我的学生在教室里既不懒散,又不贪玩,他们聪明好学,总想多学点东西”[4]138。这一时期国内正值辛亥鼎革之后,局势复杂,先是袁氏窃国引发护国运动,紧接着军阀割据混战、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在动荡的时局下各种思潮相当活跃,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十分关注。赛珍珠的学生也有人参与变革,虽然他们年纪不大,但是革命热情很高,他们守在城门,“看到留着辫子的人经过时,就让他坐在一张凳子上,给他上课,然后就减掉他的尾巴”[4]115。赛珍珠回忆说,虽然此时清朝已经灭亡,但是戊戌变法的影响依然存在,“对我的年轻中国朋友和学生来说,梁启超和康有为这时仍然是两个极具魅力的名字”[4]132。学生们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十分痛恨。“你们国家为何不给菲律宾自由?”虽然美国未在中国直接划分势力范围,但是学生们也经常在课堂上向赛珍珠发问,他们对美国享有在华治外法权和通商特权协定也十分不满。赛珍珠对学生的发难从不回避,而是直面问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行径感到羞愧[4]116。
在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进程中,教会学校培养的一些学生成为骨干力量。“最强大的力量来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坚决反对女学生裹脚,坚持讲授西方科学和数学而非中国学校讲的古代经典和文学”[4]130-131,而彼时“中国的新旧学者之间相互忌妒,相互轻视,积怨甚深”[4]131。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期,旧秩序并未完全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年轻的中国人,其中有许多是我的朋友的丈夫,甚至是我的学生,一心要缔造一个新中国”[4]136。赛珍珠对学生的精神钦佩有加,但对变法派和革命派照搬西方的做法则持保留意见,“他们办事不切合实际,不知道也不理解他们自己的人民有何想法,却试图照搬西方那一套”[4]136。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但是从对旧势力、旧思想的清算来说并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而是旧官僚、旧立宪派和革命党互相妥协的产物,真正从思想上进行变革还要等到新文化运动。赛珍珠对中国的变法与革命有清醒的认识,也认为辛亥革命并未触及思想文化领域,“在革命方面,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了。当中国为找不到适合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而苦苦挣扎时,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正在进行”[4]137。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一方面体现了她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力(赛珍珠对辛亥革命之后制度选择的判断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分析),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她对学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目标较为理性。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爱米尔·涂尔干曾经说过,教育的目标“根本上在于给孩子一种必要的推动力,让他能以正确的方向开始人生之旅”[5]49。赛珍珠对社会问题持相对客观和尊重的态度,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方向性指引,同时,正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对转型时期文化走向的理性观察,赛珍珠才能写出像《大地三部曲》那样反映中国底层社会生活的好作品。
2 深入底层百姓生活:博爱平等
1917年赛珍珠与美国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又译作卜凯)结婚,婚后两人搬至安徽宿县(今宿州市埇桥区)生活了5年时间[6]。在此期间,她在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任教,同时帮助丈夫从事农业相关研究,经常与丈夫一起去农村,深入体验中国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6]。在震惊于该地还存在弃杀女婴、女子裹脚等现象时,赛珍珠尽己所能帮助她们。
赛珍珠在宿县主要参与启秀女中的教学工作,“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我所负责的女子学校上”[4]161。启秀女中主要接收底层百姓家庭的女孩进行启蒙教育,赛珍珠希望她们能够打破命运的魔咒,不再重复母亲辈的命运。可以看出,赛珍珠在日常教学中已开始融入自己的理念,而不仅是“只是为培植善为布道传教的基督信徒”[7]。她的教学思想虽然承袭了博爱平等的教义,但并未将传教作为终极目标。其实在教化育人的目的方面,宗教与教育具有一致性,“宗教的对象是人,目的是感化人。教育的对象也是人,目的也是感化人”[8]。也就是说,虽然赛珍珠对布道不感兴趣,但对教会学校一视同仁的教学理念是认可的,因此她喜欢在这里教学,喜欢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底层百姓。后来返美以后,赛珍珠曾经高度赞扬晏阳初等人发起的平民运动,认为“尊重人类是任何和平方案的首要条件”[9]1。赛珍珠与晏阳初在平民教育方面取得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思想共识[10]。
赛珍珠还经常与丈夫奔走于乡间,进行农业调查。这些活动不仅使得日后卜凯成为一名著名的农学家,而且赛珍珠以后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也拥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在南徐州居住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了解那些住在城外村庄里的穷苦农民,而不是那些富人,……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己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4]156。但是这一时期的安徽北部并不太平,在1918年的秋天局势再次动荡,并且危及赛珍珠一家的安全,所以,当金陵大学邀请卜凯担任新成立的农学院农科主任时,卜凯欣然赴任,赛珍珠则受邀在金陵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教授英语。
3 正视不同思想:兼容并包
赛珍珠在南京教学期间,对学生的不同观点和思想相当宽容。当时金陵大学的学生多家境优越但思想趋于保守,中央大学的学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生气勃勃”,赛珍珠称“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些”“思想上颇受启发”“我与这些吃不饱穿不暖但却醉心学问的年轻人之间没有一点隔阂,他们什么都想谈论,我们也就无所不谈”[4]193。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军阀的混战割据,处于政治敏感地带的南京青年学生对于中国的未来颇为迷茫,他们认为根深蒂固的旧传统造成了中国目前落后挨打的局面,但是对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赛珍珠非常冷静地作了分析,“中国年轻一代中,有很多人的思想似乎尚未成熟,他们的表现让人感到惊愕。他们既然怀疑过去、抛弃传统,也就不可避免地抛弃旧中国那些无以伦比的艺术品,去抢购许多西方的粗陋的便宜货,挂在自己的屋里”[4]188。“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有些人对传统文化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赛珍珠对此满怀悲哀地发问:“中国的古典美谁来继承?盲目崇洋所带来的必然堕落怎样解决?难道说随着人们对传统的抛弃,我们也必须失掉庙宇的斗角飞檐吗?”[4]188-189看到日本学习西方经验后在一些方面获得成功,很多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开始全盘接受,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和摈弃的态度,这让赛珍珠觉得痛心和惋惜。
在教学之余赛珍珠继续协助丈夫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农业调查研究,她建议“首先查清中国农业经济这个课题,而教会大学的农学系又有许多来自各地的学生。我是在中国农村、在乡下人中长大的,知道有多少东西要学,也知道这些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距离他们自己国家的农村生活何其遥远”[4]205。“(我们)给中国学生发了农村生活调查表,他们便带着问题到农民中去”,完成后,“我们把资料集中起来,整理归纳一下,把调查成果写进了一本有关中国农业经济的小册子(1)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张履鸾,译.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这本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后,引起了太平洋关系学院的注意,从此,更为广泛、意义更为重大的中国农村生活研究就开始了”[4]206。这些调查资料使得卜凯成为农业经济学领域的杰出学者,根据调查资料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部著作成为该领域的经典。1927年3月,国民军进入南京,3月27日,军队开始破坏教堂、逮捕洋人,赛珍珠一家乘坐美国驱逐舰离开南京,经上海避居日本长崎[11]。
4 赛珍珠教育思想的生成原因
赛珍珠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有着强烈的平民化倾向,她关注民生、躬身基层,这些都与她自幼生长在中国、从小在双重文化环境下成长的经历有关。赛珍珠所接受的中西合璧式的青少年教育,使其思想经常处于既包容又矛盾的状态。她在回忆录中说:“我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着一堵墙。在中国人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思想感情也与他们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向另一世界的门。”[4]9
4.1 童蒙教育之启发
赛珍珠的孩提时代大部分在镇江度过,虽然父母“有自己的传教事业,他们为之忙碌而欣悦,无暇顾及他们的孩子”[4]15,但是赛珍珠在学业上很早就受到启蒙。童年的赛珍珠需要学习西方历史和文学,接受西方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训练,比如要学习“美国、英国、欧洲以及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4]15。每天上午由母亲凯丽按照美国的教材进行教学,“我阅读美国的教科书,学习母亲布置的功课。母亲完全是依照卡尔·弗特教育体系来教我的”[4]51。赛珍珠的父母是相当开明的人士,1902年他们为她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这是位饱读诗书的年老儒学士绅,“(他)在教我读书写字的同时,也向我灌输孔子的伦理思想,但看来我笃信基督教的父母没有因此而不快,……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孩子,我猜想孔夫子与我们所说的天堂里的上帝一样,是圣父”[4]46。这位中国家庭教师还经常给赛珍珠讲授一些中国人的人生处世哲学[4]47,以及诸如佛家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命运之不可变易仅仅是指某种原因必然产生某种结果,但是原因本身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不是一味无知,而有所作为,就可以开创自己的世界”[4]52。另外,童年的赛珍珠还对中国的俗文化特别是话本小说颇感兴趣,她曾提及“我们的厨师会给大家讲他从书本上读到的历史故事。他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红楼梦》”[4]58。她对西方文学也十分痴迷,“我父母已经有成套的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瓦尔特·司各特等人的书,还有英国诗集和一套版本很好的莎士比亚全集,装饰我们的房间。所有这些书籍,都是我童年充实生活的一部分”[4]65。成年后的赛珍珠对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推崇,认为“在中国社会里,等级观念全部来自教育。教育不仅旨在学有所成,还旨在道德修养。老师让我们理解并相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是一个修养好、品德高的人”[4]15。赛珍珠的童年启蒙教育来自完全没有交集的东西方知识体系,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教育除了带给她渊博的学识以外,也让她的思想得到解放。因此,童年教育的包容性对赛珍珠博爱、平等的价值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赛珍珠早年就认为,“在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绝对真理,有的只是人们眼中的真理,真理也许是,事实上也就是个多变的万花筒”[4]51。
4.2 家庭观念之影响
赛珍珠的父母都是传教士,他们同情中国社会底层百姓,认为无论他们的地位多卑微,都不应遭受歧视。教会传教的目标是使基督福音传遍全世界,而“中国的儒学在传教士眼中正是一种异端宗教,……是其必须予以打击破坏的”[12]。但是,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并不认为儒学和佛教是异端。赛珍珠曾提及:“我父母的思想是非正统的,认为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和我们是平等的,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中国文明值得尊重。”[4]69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甚至认为“耶稣既懂得孔子学说,又知道佛经,因为孔夫子和耶稣的圣训几乎同出一辙”[4]70。这种思想主要是基于对其他文明的尊重,“尽管父亲是保守派基督徒,但他得出结论:在亚洲,人类文明很早之前就在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方面登峰造极。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在稳定而深入地发展,对此,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作出了贡献”[4]70。赛珍珠的家庭环境宽松、民主,“我父母在我们面前从不以长者身份谈话,……遇到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参加讨论”[4]69。受家庭观念影响,赛珍珠认为“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耶稣很可能在年轻时访问过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王国”,但类似这样的观点却被教会学校校长朱厄尔小姐认为是离经叛道[4]69。赛珍始终对中国文化十分尊重和热爱,她对学生言论的宽容、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欣赏、对中国古老文明的赞叹,显示了长期的家庭观念浸润产生的深刻影响。
4.3 社会现实之驱动
赛珍珠小时候生活在镇江,镇江当时已经是一个通商口岸,当她看见很多外国人不愿与当地人为邻,都住在整洁、舒适、安全的租界内,现实与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赛珍珠一家依然住在租界外。关于她儿时的中国朋友、家里的中国仆人、婚后在宿州遇到的很多中国平民,赛珍珠在她的回忆录和小说中都以充满了友善、欢愉、慈悲的感情进行回忆与书写。可以看出,赛珍珠在教育实践中流露的质朴情感(或者说她的教学思想)是一种对中国人民怀有的强烈的认同感和悲悯情怀的自然流露,是在中国社会成长的切身经历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会后的反映,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近乎同胞之间的感情。但是,她成长的岁月也是中国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教会的在华境遇随着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教会教育遇到了难题。相较于庚子年义和团事件时期教会遇到的难关,辛亥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理性”时期,是“从前的传教士不曾梦想到的”[13]。胡适曾建议教会教育应该“抛弃传教,专办教育”[13]。1931年,当时的福建教育厅厅长在教会发表演讲,在肯定教会教育的同时,提出四点希望,即“要明了中国教育的方针”“要遵守中国教育的法令”“要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要以三民主义教育为中心”[14]。中国知识分子对教会学校的教育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们认为,虽然教会教育“对于我国的文化、人民的思想,影响颇大”,其实我国人民“大多迷梦未醒,以为外人本着人类互助的精神,帮助我们发展教育,开办学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对于中国前途有利无害,……殊不知他们代替华人发展教育,其用意并不在教育,而在实行其教会目的与计划”,而教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教育基督化”[15]。对于这些反思与批判,赛珍珠能够理解,因为她本来就对教会学校的诸多做法持保留态度。1927年离开中国后,赛珍珠依然关心中国民众、关心平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