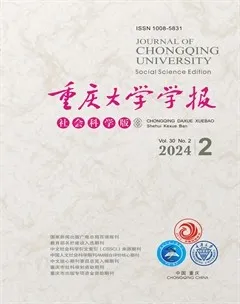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李燕 肖泽钰
摘要: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关键词:ESG;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双重重要性原则;单一重要性原则;绿色金融
中图分类号:D922.287;F27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2-0195-16
一、问题的引入
当前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即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简称ESG)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模式选择是学界与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强制性ESG信息披露标准与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标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重大性原则和法定披露事由两个方面。其一,ESG信息披露作为可持续性报告,在披露原则上包含单一重要性原则和双重重要性原则。单一重要性原则又称财务重要性原则,只考虑环境和社会议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双重重要性原则既要考虑环境和社会议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要考虑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后者称为影响重要性[1]。可见,双重重要性下可被纳入重大性范围的ESG信息数量远多于单一重要性原则。因此,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体现的监管力度要强于单一重要性原则。如一国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遵循双重重要性原则,则该制度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其二,法定披露事由,即监管部门是否列举了公司必须披露的ESG具体事项。法定披露事由可弥补重要性原则的抽象性。因此,即使在单一重要性原则下,监管部门如列出了较多的法定披露事由,也可认为该制度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
依据该标准,我国关于ESG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已形成了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体系。且呈现出社会、环境以及公司治理三类议题规制力度各不相同的特点。第一,我国环境信息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可视为半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监管部门并未对重大性标准进行修正,仍采取财务重要性这一单一重要性原则。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对重大性信息披露的认定采用价格敏感性测试与投资者决策测试(参见:《证券法》第19条,第80条。)。因此只有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或对股票及其衍生品价格产生重要影响ESG信息的才会被视为重要性信息。这表明我国ESG信息披露制度仍统领在财务重要性之下。但同时,监管部门增加了上市公司需披露的环境议题的法定事由。现证监会要求被环境部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单的上市公司应披露证监会规定的具体环境议题,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公司对于其规定的具体环境议题,应当遵守不披露就解释的规则(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第15号公告,2021年6月28日。)。而公司治理一直以来就是监管核心。公司治理议题在保证上市公司规范运作、降低财务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监管部门不仅列举了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公司治理的具体事项,还对其进行了强制要求。综上,依据前述论证的强制性与自愿性ESG信息披露的分野,我国环境信息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均可视为半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第二,监管部门对社会议题仍采取自愿立场,且建议披露事项也列举较少②。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规制体系契合了差异化的公司发展水平,也有助于绿色金融的建设。
但ESG信息披露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仍未取得良好效果。第一,信息披露缺乏可对比性。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公司会使用不同的术语和不同的衡量标准呈现ESG报告,使投资者难以比较各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报告[2]。即使部分自愿性ESG信息披露的支持者认为市场力量会推动公司采用類似的ESG信息披露模板[3],但反对者认为市场失灵也会导致披露失灵。从我国上市公司ESG报告名称看既有“ESG报告”,也有“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4]。且上市公司采用的披露指标也各不相同。第二,ESG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有待加强。当前大部分我国上市公司的ESG报告主要为价值陈述,无法验证其真实性。第三,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仍存在数量较少的问题。据统计,截至2022年上半年,沪深A市共有1 431家公司发布了ESG报告,虽然报告数量与发布比例在增量和增速上为过去5年最高,但仍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1.34%[5]。
据此,部分研究认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要优于自愿性ESG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保证ESG信息质量和数量、统一ESG发布标准等优点。监管部门应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强制性[6]。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确实有助于提升信息的真实性和数量。但前述问题的产生也可能基于制度构造本身的问题而非监管模式的偏差。现有研究仅聚焦于ESG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定位偏差,且在为何加强强制性以及如何加强的问题上论证不足。首先,未明确构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的实践基础,我国是否與欧盟一样有足够的政策与实践动因以支持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其次,并未回应以双重重要性为披露原则的强制披露模式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导向与商事法营利导向的冲突。最后,也并未协调《证券法》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的冲突。对此,本文不仅聚焦于监管模式的定位分析,也聚焦于监管模式定位下的制度优化,择机思考如下问题:第一,ESG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关系及其建构的法理基础。第二,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监管模式定位是否存在偏差。第三,监管模式定位下的制度优化。检视制度构造中的具体问题,对制度优化以及《证券法》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的协调提出建议。
二、ESG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模式评价
(一)强制性与自愿性二元融合关系证立
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相较于强制信息披露有两个特点:其一,信息披露具有灵活性。公司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经营状况选择需要披露的信息。其二,信息披露内容丰富。虽然存在信息过载的风险,但相较于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规定主题,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主题与内容往往更广泛更丰富。依据反身法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这两点使得ESG自愿性信息披露有着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讨论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优势不是为了否定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二者在制度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并且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相互配合。
1.ESG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制度优势
自愿性ESG信息披露制度可赋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自由裁量权,较好地平衡公司的营利性与社会性,更加适应反身法理念下复杂的社会现实模型。反身法理论以社会系统论为前提,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已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秩序,而是功能分化的子系统,例如科学、宗教等。这些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语言以及运行理性。例如法律与经济政治或科学都属于功能子系统,但又相互独立。因此,应清楚地认识到法律的有限理性与社会现实模型的复杂性。传统以形式平等为中心的“形式法”(formal law)与以结果为导向的“实质法”(substantive law)已无法适用当下功能分化的社会。形式法近似于民法形式平等的概念,是保证民事主体地位平等的法律,其正当性在于其对个人主义和自治的贡献。但形式法无法保障实质的结果公平,因此,随着时间的推进,实质法变得更为突出。实质法强调国家有目的的干预,侧重于通过规定和标准实现预定的结果。但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下,实质法的规制理念也面临着国家干涉主义的危机。一方面,实质法结果导向式的规制模式无法一一回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实体法的一一回应也会造成海量立法的问题,给执法机构执法以及民众认知都造成过量的负担[7]。因此,反身法理念提出了信息规制型策略。由于积极或负面的ESG信息都会影响公司形象与竞争地位,因此可通过要求公司收集和发布ESG信息对公司形成声誉激励,从而促使企业进行自我监管[8]。
不过具体到ESG领域,强制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虽然同属于信息规制型策略,但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更契合ESG多元化的价值要求。ESG的产生来自于社会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包括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以及公司应对社会与环境风险的现实要求。但是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以及公司面临的社会风险、环境风险都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赋能上市公司依据公司状况、行业状况等实际情况选择披露信息的自由裁量权[9]。除此以外,ESG信息披露也会给上市公司造成负担,过度的ESG信息披露也会造成公司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失衡。因此,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也赋能了上市公司披露或不披露的自由,可以较好地达成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平衡。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则存在实质法的特征,可能存在僵化、滞后以及过度立法的弊端。在规定法定披露事项的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中,监管部门一是无法确定哪些信息是上市公司所需披露的ESG信息;二是即使确定了相关信息,从确定到立法也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调整ESG信息披露。虽然双重重要性原则可以弥补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的灵活性,但双重重要性原则还未引入我国《证券法》。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具有僵化性、滞后性是可以确定的事实。
ESG自愿性信息披露还可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号。依据信号理论,自愿性信息披露更能形成有效的市场信号。信号理论是指企业通常会披露其独有的、其他企业很难模仿的信息,帮助投资者更易识别出优质公司,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10]。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领域,强制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不能作为投资者识别优质公司的甄别机制,无法有效传递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信号[11]。具体到ESG领域,上市公司依据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ESG信息往往单一、有限,投资者不能通过寥寥的强制披露信息了解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全貌;其次,如前述强制性披露信息具有僵化的特点,无法形成个性化的披露信息,因此,投资者无法仅借助强制性披露信息判断各公司ESG表现的区别。而自愿信息披露具有灵活性与供给充足的特征,因此可以实现信息的个性化和有效性,从而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号[12]。在投资者更愿意将ESG信息视为管理层向市场发出的积极信号,而非具体可解读的内容的前提下,自愿性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帮助更大[10]。
2.ESG强制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联性
论证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可替代的优势,并不是为了否认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相反,自愿性ESG信息披露制度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可割裂,二者具有关联性。第一,在制度功能上具有互补性。自愿性ESG信息披露内容具有广泛性,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内容具有有限性、法定性。因此,自愿性ESG信息披露可以弥补强制性信息披露内容的单一性,是对强制性披露的补充和延伸。另一方面,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强制性信息披露在信息类型上的单一性。ESG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主要功能在于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负面ESG信息,而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激励上市公司披露积极ESG信息,二者在信息披露类型上也具有互补性。第二,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市场实践或监管目标的变化使得某些信息的重要性提升,强制披露要求替代之前的自愿披露要求,自愿披露信息转变为强制披露信息[13]。第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为强制披露构建提供实践基础。监管部门可以通过梳理、统计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类型等信息,把握不同类型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偏好,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提供实践支撑。
综上,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信披与自愿性信披的相互配合,二者均不可偏废。将ESG信息披露制度的建构寄希望于单一的强制性或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相互转化表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为将那些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议题转变为强制性ESG信息披露议题。
(二)强制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构建基础
1.ESG的功能定位:公司长期价值与社会治理
ESG强调公司需应对环境、社会风险,从词义看与社会责任(CSR)、社会责任投资(SRI)相关联。因此,部分学者将其直接理解为CSR的下属概念。例如,有学者在梳理ESG发展源流时,将CSR视为ESG的前身[14];也有学者指出,ESG的法理基础在于不特定投资者以及不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公共利益[15]。诚然,ESG与公司道德、公司伦理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探究ESG一词的正式产生可以发现,ESG在产生之初是为了推动公司长期价值而存在,以公司利益为落脚点,与CSR并不属于种属概念,不过后期在实践中因其克服了CSR的缺陷,因此也被用作政府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要工具。因此,ESG可被视为统合营利至上与社会责任理念的新型可持续发展理念,既可促进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ESG产生于业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重视。ESG一词正式出现于联合国契约组织于2004年发布的报告《谁在乎胜利,将金融与不断变化的世界联系起来》(Who cares wins , 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a changing world),其产生是基于“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相互联系和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里,管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方式,是企业成功竞争所需的整体管理质量的一部分”[16]。即环境、社会风险都已基于声誉激励机制演变为可能切实影响公司短期价值与长期价值的因素。而后,公众及监管部门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追求使ESG在公司治理与投资领域逐渐占据重要地位。Martin Katz指出:“当前主要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均认识到短期主义和短期金融激进分子的攻击严重阻碍了长期经济繁荣。在此基础上提出创建一个促进可持续长期价值的‘新范式公司治理框架。在公司治理中将ESG纳入考量因素,将公司治理视为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之间的合作,共同努力实现长期价值、抵制短期主义。”[17]可见,ESG在产生时的价值目标与CSR并不相同。CSR产生之初着重于要求公司保护外部社会环境,而不是促进公司的长期发展。例如戴维斯“权力责任—模型”:公司的社会责任来自他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责任是权力的对等物[18]。因此,部分ESG支持者也认为ESG与股东长期价值相关联,就是股东价值而非利益相关者价值,与社会责任并不属于同源概念[19]。
不过ESG中包含了社会、环境因素,因此ESG在客观上具有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也被欧盟等国用作推进社会治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工具。ESG相较于CSR的优势有二:一方面,ESG使公司应对社会、环境风险的努力得到衡量[20],将CSR分解为环境与社会两个板块,并通过规定具体指标量化评价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另一方面,ESG相较于CSR增加了公司治理组件。联合国在其报告中认为,健全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制度是成功实施应对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关键先决条件 [16]。这也与有关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同,即改善公司治理可以有效改善公司CSR的承担质量,改变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两张皮”的现象。因此,ESG相较于CSR具有可量化和调整公司治理的优势,在客观上可被用作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责任的良好工具。
2.ESG功能定位與监管模式的因应性选择
实践中,监管部门对ESG功能的不同定位直接影响ESG信息披露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是公司自治范畴,监管部门对公司ESG信息披露往往持自愿态度,通过市场驱动等方式推动公司披露ESG,代表立法例如美国。监管部门如将ESG用作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代表立法例如欧盟。
当前美国ESG信息披露制度仍遵循财务重大性这一单一重要性原则。美国证券披露重大性标准建立于TSC案:“重大性是指一个理性投资者可能认为重要的所有事实。”(TSC Industries,Inc.v.Northway,Inc.,426 U.S.438(1976).)而通说认为对于理性投资者而言,重要的应该是与财务有关的事项,而不是关于人类普遍福利的政治观点[21]。因此,公司披露ESG也只需在与投资者利益相关这一原则下即可。其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公司必须披露的ESG具体事项也非常有限,主要体现在规则S-K中,例如在董事会提名中是否考虑性别多样性[9]。虽然SEC也在着手提高气候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于2022年发布了“气候信息披露标准草案”(Enhanc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2]。但自由派群体坚持认为,这是将政府部门无法解决的社会、环境议题强加到公司身上[24]。在自由派群体的激烈抗议下,美国SEC仍将ESG信息披露定义为与公司长期价值相关的披露制度,并未将其作为气候治理等社会治理的手段。欧盟则是将ESG用于社会治理的代表。为支持其绿色金融的建设,欧盟委员会于2014年就颁布了NFRD(Non-Financial Reporting Directive,非财务报告指引),要求员工达600人以上的公共企业都需要披露ESG信息,并在公司ESG信息披露原则中引入了双重重要性概念[23]。而后,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宣布了《欧盟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The EU Action Plan for financing Sustainable Growth)。该计划旨在将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联系起来,并提出了一项全面战略,其中就包括授权欧洲银行管理局将ESG风险纳入审查评估的原则和方法等[24]。在该行动计划的指导下,欧盟进一步提高了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新出台的CSRD(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公司可持续报告指引)取消了员工600人的限制,除微型企业外的所有企业都需要披露ESG信息[25]。
(三)我国ESG信息披露监管模式分析
结合前文对ESG功能定位与监管模式的分析,当下强制与自愿的二元监管模式契合我国对ESG的功能定位,具有合理性。
契合我国“双碳”治理、绿色金融的政策背景。2016年央行等七部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表明监管部门认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是实现绿色金融的重要工具。2021年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中指出证监会应当与生态环境部一起共同负责完善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形式等法治化建设。具体而言证监会需要将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纳入上市发行环节;并强化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强制性约束,禁止虚假陈述等“漂绿”现象(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环综合〔2021〕43号,2021年5月24日)。)。而关于整体ESG信息披露,监管部门并未做出立法规划与部署。表明监管部门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定义为社会治理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升级了其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将ESG信息披露制度整体作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手段。在市场端,我国ESG投资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ESG基金规模占全球比重不足2%[26]。个人投资的对ESG投资的了解与认知更不乐观,2022年《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显示,有77%的调查对象不了解责任投资,其中27%从未听说过“绿色金融”“责任投资”或ESG。虽然有84%的调查对象表示会在投资中考虑ESG因素,但58%为有时考虑,仅有26%为总是考虑[27]。因此,如在证券法律规范中不加区别地增强整体ESG信息披露制度的强制性,缺乏政策动因与实践动因。
可见,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数量不足、质量不够等问题并不是由监管模式定位造成的。除市场驱动有待发展外,监管模式定位下的制度构造也存在问题。
三、我国ESG信息披露制度的内生冲突
(一)环境强制性信息监管不足
1.单一重要性原则的局限性
单一重要性原则尊重企业的营利性,要求企业披露环境、社会议题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会对公司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是企业的声誉资产。因此,将环境与社会议题统领在财务重要性这一单一重要性原则之下,以公司长期利益为落脚点,尊重了公司自治,具有合理性。但如将其作为促进社会治理的工具,则在数量供给与应对“漂绿”现象上存在不足。
其一,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不足。依据上交所规定,上市公司只有在环境信息影响股票及其衍生品价格时才应当披露具体的环境议题。但环境信息作为非财务披露信息何以影响股票价格呢?除环境信息给公司经营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公司营利受到重大损失外,对公司经营并无显著影响的环境负面信息只有在ESG机构投资较为发达以及投资者普遍具有绿色、环保意识时,负面环境信息才可能影响股票价格。虽然大量的实证研究及实践案例已经显示,我国上市公司ESG表现与其股价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如前所述,我国ESG投资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这表明证券市场对于上市公司负面ESG信息事件的反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证券市场是否会对上市公司ESG信息产生负面反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以价格敏感性作为ESG信息是否属于重大事件的评判标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需要强制性披露的ESG信息不足,而在实践中则主要体现为负面性ESG信息披露不足。
其二,单一重大性无法良好地应对上市公司的“漂绿”(green-washing)现象。“漂绿”一词并无统一定义,最初起源于1986年,一位环保主义者将某家酒店对其服务误导性的环保宣传称为“漂绿”[28]。欧盟官方将“漂绿”定义为:不真实的或者以令人误导的方式呈现信息,这样的信息造成了该产品或企业是环保产品或环保企业的假象[29]。例如,公司往往会在新闻发布会中宣称他们为环境做了比实际更多的事情[30]。从欧盟定义可以看出,“漂绿”一般包含两种方式:一是公司隐瞒负面环境信息;二是公司夸大环境贡献,其目的都是公司为了塑造自身与实际并不相符的环保形象。当前,“漂绿”现象已从环境议题扩大至社会、公司治理领域,被称为ESG洗涤(ESG-washing),其目的都是公司为了塑造良好形象而夸大ESG表现。当前《证券法》关于信息披露虚假陈述的规制,均以重大性为前提,将财务重要性作为重要性判断的一般原则会导致公司对大量的ESG信息并无强制披露义务,也就无从构成虚假陈述。类似问题在美国也存在,是财务重要性原则下自愿ESG信息披露体系均会面临的问题[31]。当前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大量关于ESG“漂绿”的诉讼,但由于美国当前仍采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体系,因此投资者依据美国《证券法》10b-5提起的诉讼均会被法院依据公司没有披露义务抑或公司采用的模糊陈述不具有可诉性而驳回( Under Section 10(b) and Rule 10b-5, a duty to disclose may arise expressly pursuant to an independent statute or regulation, when there is corporate insider trading o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r a corporate statement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inaccurate, incomplete, or misleading. 15 U.S.C.§ 78j(b); 17 C.F.R. § 240.10b-5(b) (2022).)。我國ESG投资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无关于ESG洗涤问题的证券代表诉讼,证监会处罚也较为少见。但可以预见的是,单一重要性原则下以自愿信息披露为主的规制体系无法应对ESG洗涤问题。
2.法定环境信息披露规定标准不一
即使在单一重大性标准下,监管部门也可通过列举法定重大性事件以弥补缺陷。但当前证监会与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标准并不一致,导致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不一致,对投资者利益造成伤害,这其中的监管空隙也使得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不足,尤其是处罚类信息。
证监会衔接了环境法规定,列举了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环境信息;其余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必须披露环境处罚信息,对于其余信息遵循不披露就解释的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年修订)》第41条。)。交易所与证监会规定的区别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对于重点排污单位之外的上市公司,并未要求其不遵守就解释。第二,对于环境处罚信息规定不同。证监会规定下,上市公司无论环境处罚的金额大小、重大性程度如何均应披露环境处罚信息。而上交所对环境处罚的披露要求为:“公司因为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者被有关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决定限期治理或者停产、搬迁、关闭。”对于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或者其主要子公司,上交所规定的披露事由中也并不包含环境处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8.10,8.12条(上证发〔2022〕2号)。)。可见,在上交所规定下,无论是否是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重点排污单位,上市公司仅需披露符合重大性要求的环境处罚信息即可。深交所并无关于上市公司是否应该披露环境处罚的直接规定,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大污染事故;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重点排污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相关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8.8条(深证上〔2022〕13号)。)。依据体系解释,深交所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应当依据证监会规定,无论有无环境行政处罚的金额都应当披露环境处罚信息;其余上市公司仅需披露符合重大性要求的环境处罚信息。但在实践中,由于深交所对于环境处罚信息的披露并不清晰,上市公司也呈现出不一致的披露行为。综上,证监会与交易所对环境处罚信息规定的差异在于,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应当一律公开环境处罚信息,而交易所规定下,上市公司只需披露满足重大性的环境处罚信息即可。
实践中,上市公司对于环境处罚信息的披露依规定不同呈现出两种情形。部分上市公司依据证监会规定无论行政处罚金额大小均在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例如深交所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其因“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而受到的2万元行政处罚[32]。但部分上市公司会依据交易所规则,认为部分环境处罚不满足重大性标准,不予披露。例如,同属于深交所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傳化智联,其子公司因废气处理不达标而被处以18万的行政处罚( 参见:杭环罚〔2022〕第20000001号。)。但传化智联并未披露相关处罚,认为此次环境违法问题情节轻微,罚款金额较小且子公司已及时缴纳罚款并整改到位,未对公司业务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和风险[33-34]。再如,深交所上市公司贵州百灵公司子公司云南红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污水排放问题被处以10.5万元的罚款( 参见:红沪环罚字〔2022〕04号。),但是其作为环境部规定的重点排污单位,在年度报告中直接披露无环境处罚信息[35]。两类披露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但不一致的披露标准有可能对投资者造成误解,使其误认为上市公司如未在年报中披露环境信息,即无环境处罚事件。并且,从法定到重大性的监管错位,也为上市公司不披露某些环境信息提供了合法空间,使上市公司所必须披露的环境信息减少。
(二)ESG自愿性信息披露激励不足
积极的ESG信息披露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提供声誉激励,但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数量依旧低迷。据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数据统计,2022年我国已经披露ESG相关报告的上市公司占比仅约为30%[36]。这一现象除与上市公司ESG意识有待加强、ESG投资市场规模有待扩大外,与当前《证券法》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规定粗疏也有关联。
2019年《证券法》新增了关于自愿信息披露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不得误导投资者。”在《证券法》原则性规定的指引下,证监会及交易所均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进行了相应规定,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以消极义务为主,未规定免责事由。例如,避免选择性披露;对于预测性信息需附以警示性文字,提示相关风险因素;避免利用与市场热点不当关联的自愿披露,即“蹭热点”公告。第二,积极义务不明晰。相关规定关于ESG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为上市公司需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完整性、连续性和一致性( 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8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版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深证上〔2023〕702号)。)。其中上交所在关于《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自愿信息披露》(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中,对自愿捐赠的披露进行了示例,但也未明确提示自愿披露中哪些具体事项为应披露事项。第三,指引性披露粗疏。对于上市公司可披露的ESG信息议题列举较少。例如,《科创板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中,上交所对于公司治理披露的指引仅包括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关系及保护、信息披露透明度等信息,并未对上市公司如何建立利益相关者沟通机制、风险管控机制作出指引( 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自愿信息披露》(上证发〔2022〕14号)。)。
检索实践案例发现,虽然监管部门未详细规定上市公司的风险提示等义务,但上市公司ESG自愿信息披露仍有可能招致监管风险,主要与上市公司“踩热点”行为有关。具体包含以下两方面:第一,上市公司可能因未披露自愿捐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而遭受处罚。例如2020年联创股份在深交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互动易)中披露称“公司向湖北无偿赠送5吨次氯酸钠水溶液用于新冠疫情防控,而该水溶液属于联创股份公司子公司产品”。这是属于联创股份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行为的披露。但联创股份在此次披露中未能客观、完整地反映次氯酸钠水溶液对其股份业绩的影响情况,涉嫌通过互动蹭热点。鉴此,监管部门对联创股份予以通报批评处分(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联创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2020年3月8日)。)。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还有可能因为披露夸大描述而招致处罚。例如,海印股份披露其已开展成熟稳定的充电桩业务和物流城配业务,公司还将深度参与新能源、光伏等先导性和支柱性行业的分工,加速公司转型升级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但现实情况是,海印股份虽然于2016年开始打造新能源本土服务商,但其新能源业务对公司业绩影响依然很小。海印股份的股票因该披露大幅上涨,鉴此招致了深交所的监管问询,要求其说明新能源业务开展情况,是否具备深度参与新能源等行业的能力和自愿,是否已与他人达成意向性协定(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399号)。)。
上市公司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可能存在夸大性描述、披露不规范以及选择性披露等情形,这是将披露裁量权交给上市公司自由选择出现的正常现象[37]。证监会、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进行监管是出于对投资者的保护。且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相互转化的,如上市公司披露的ESG信息符合了重大性标准,自愿披露的ESG信息也有可能转化为强制性披露信息。因此,前述监管行为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当前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自愿性ESG信息披露的指引不清晰,这有损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积极性。第一,将价格敏感性测试作为单一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监管区分标准可能存在无法预测的问题。从上述存在的监管实例看,上市公司均是因为披露信息导致了股票异常波动招致证监会、交易所的监管。但价格敏感性是一个后验的概念,只有根据披露之后的市场反应才能得出判断,这可能会导致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监管陷入事后监管的真空状态。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作出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时也无法准确判断部分信息是否具有价格敏感性,可能无法准确调整披露行为[13]。第二,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只规定了义务,未规定免责事由,且义务规定也不甚清晰。除上交所发布了专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引外,《证券法》及深交所仅公布了关于义务的一般规定,这也是上市公司频频发生蹭热点行为的原因之一。如要发挥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赋能上市公司广泛披露ESG信息的功能,监管部门还需要在投资者保护与激励信息披露之间作出平衡。
四、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强化
(一)双重重要性原则引入的现实阻碍
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商事法的营利导向并不兼容,可能会给证券法乃至商事法律制度造成从价值到规则的原则性、体系性冲击。双重重要性原则下,上市公司不仅需要披露环境和社会议题对公司营利的影响,还需要披露自身行为对环境、社会的影响。因此双重重要性原则体现了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取向,这与我国证券法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主流价值取向并不兼容。且既有的证券市场执法机制与司法资源很难保证环境信息披露的威慑力[38]。另一方面,放眼整个商事法律制度,社会责任条款在商事法中,也仍属于倡导性、鼓励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例如《票据法》规定:“票据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票据法》第3条。)。《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商业银行法》第8条。)。即使是作为证券法基础的公司法,也并未将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位阶置于股东利益保护之前。因此,双重重要性原则与证券法乃至商事法律制度从价值导向上存在体系性不兼容。
(二)现阶段优化:修订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
修订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由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增列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而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需要协调证券法与环境法在环境信息公开上的冲突,也需要明确证券法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中之于环境法的特殊价值。
第一,对于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可以在证监会标准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正。一方面,对于属于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上市公司,证券法可对接环境法信息公开的规定,要求其在年度报告中对已在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公示的环境处罚等信息设置查询链接。既可避免立法重复,也满足了ESG投资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于环境保护部门名录以外的上市公司,除必须披露满足财务重大性标准的环境事由外,其余法定环境事由应采用不披露就解释的标准。如强行要求上市公司披露财务重大性以外的环境信息,在未引入双重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缺乏依据。且不披露就解释规则也可避免负面环境信息不足造成投资者无法选择的现象。与遵守或解釋规则类似,披露或解释规则为公司拒绝披露设置了障碍。这种障碍表现为,若公司不能为偏离最佳公司治理实践清单提供充足且正当的理由,这种偏离便不会被承认[39]。在市场机制下,ESG投资会倾向于选择有良好披露实践的公司。因此,不披露就解释原则更适合当下财务重大性原则下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
第二,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在环境法已对生态环境行政许可等企业环境管理信息、污染物产生等方面的信息公开作出规定后,证券法只需增加相应衔接即可;但可以增加对公司治理结构这类环境法无力直接规制引导的事项。虽在环境法以及ESG资本市场都会对上市公司保护环境形成外部压迫,但是环境法的三种规制模式:命令—控制模式、市场激励和经济激励以及以环境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反身法模式[40],都无从为上市公司转变经营发展方式、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方法论指引。仅有公司法、证券法可以承担指引上市公司切实转变经营方式的功能,改变信息披露与上市公司实践“两张皮”的情形。因此,证券法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也是证券法在环境信息公开中特殊价值的体现。当前,《深圳市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已设置了相应规定。例如,在深圳市注册的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层面设置与环境、绿色金融相关的委员会情况,以及其对环境、绿色金融相关议题的管理、监督与讨论情况。证监会与交易所可考虑将相关规定纳入年度报告要求与交易所自律规范。
五、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强化
自愿性ESG信息披露制度是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下的子制度。当前学界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激励研究主要集中于预测性信息的“安全港”规则。预测性信息安全港规则来源于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法案》(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 of 1995, PSLRA)。在该规则的保护下,善意和有合理基础的前瞻性声明将不具有可诉性( See 15 U.S.C. § 78u-5.)。美国证券监管实践表明,安全港规则有利于激励上市公司披露财务预测性信息。但如将预测性信息的安全港规则作为现阶段激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信息的法律手段,我国《证券法》需先体系化引入安全港规则,然后再研究安全港规则在ESG领域的适用,立法成本过高。因此,建议依照上交所出台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南,由证监会进一步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指引,让上市公司明确可为与不可为。如后续《证券法》引入了预测性信息的免责事由,再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ESG领域的适用。
(一)预测性信息安全港规则制定的现实阻碍
结合安全港规则的适用情形、ESG信息披露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我国法律制度环境,现阶段直接引入安全港规则以激励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ESG信息可能面临立法成本过高等现实阻碍。第一,我国《证券法》并无预测性信息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欠缺将免责事由适用于ESG信息披露领域的基础制度。当前随着美国国内投资者对ESG信息关注的增加,美国学界提出建议将安全港规则适用于ESG信息披露,以促进上市公司自愿披露ESG信息[41]。受此影响,美国SEC关于气候信息拟议规则中也提到,气候信息披露中的预测性规则可以适用安全港规则[44]。不过即使美国国内需要将安全港规则使用于ESG信息披露领域,也需要对安全港规则进行修订补充。一是二者内容不同。传统安全港规则针对的是财务预测性信息,例如对未来营利收入以及营利收入损失的预测,每股的收益增值或每股收益损失的预测,资本性支出,股息等财务事项。而ESG信息披露通常涉及风险管理或非财务价值的考虑。二是陈述方式不同。ESG信息披露可能相对具体,不符合推动安全港的基本规则。因此,美国也还在探寻将安全港规则适用于ESG信息披露的立法路径。而我国目前还并无预测性信息免责事由的具体规定。如将安全港规则作为激励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手段,还需要在引入安全港规则的基础上,再探讨适用于ESG信息披露的立法路径,立法成本过高,而且在短时间难以达成。第二,预测性信息安全港规则的引入也还需要依据国内司法制度进行改良。安全港规则对预测性信息进行免责的前提是该预测性信息负有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 See 15 U.S.C. § 78u-5.)。而何为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是由美国判例法进行解释定义的[42]。因此,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如要引进预测性信息规则,还需要研究如何改良其条文规定。
(二)现阶段优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指引细化
因此,现阶段可能较为合理的激励方法是参照上交所的自愿信息披露指引,由证监会或交易所在此基础上细化上市公司自愿性ESG信息披露的要求,为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提供行为指引。当前上交所在其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引中列举了上市公司可以自愿披露的ESG个性化信息,并举出了自愿披露对外捐赠公告的示例。但是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列举的具体议题过少,尤其是有关公司治理议题的列举过少。另一方面,即使是举出的对外捐赠示例,也未明确哪些陈述是必备披露要素。鉴此,可以作出如下改善。
第一,建议证监会或交易所增加列举事由,尤其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事由。如前述,公司治理对于上市公司应对ESG风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关于自愿披露的证券法律规范也并未对公司机关如何践行ESG提出立法指引。对此,可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中的规定:董事会应当披露对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的监督;董事会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方针及策略,包括评估、优次排列及管理重要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事宜(包括对发行人业务的风险)的过程;董事会如何按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目标配套进度,并解释它们如何与发行人业务相关联。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相关信息,通过透明化的方式鼓励上市公司实践最佳公司治理。
第二,在举出的示例或具体的ESG议题下,强调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重点。《上交所自愿信息披露指引》在“业务前瞻信息”“盈利预测信息”等章节均提示了上市公司应当重点提示的信息。因此,证监会或交易所在制定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指引时,也可根据上市公司近期被监管的自愿ESG信息披露类型,制定重点提示指引。例如,前文提到的上市公司对外捐赠披露,可规定上市公司应当重点提示以下信息:一是该捐赠有无经过公司正当决议程序;二是此次捐赠的资金来源;三是此次捐赠对公司生产经营以及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再如,在“双碳”背景下,上市公司容易发布减少碳排放的经营转型计划,以建立自身良好形象。为避免该行为因踩热点而招致监管风险,可规定上市公司应当重点提示以下信息:一是当前公司新能源业务占比;二是公司经营计划转型的现有投入资金与预期投入资金;三是转型可能失败的警示风险等。上市公司披露ESG信息以建立自身良好形象更易发生踩热点行为,监管部门应当对这类信息披露类型多加关注并制定相应的信息披露指引。
六、结语
ESG理念的兴起源于国际社会对气候风险与公司短期经营风险的忧思。在气候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及欧盟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在布鲁塞尔效应带来的制度趋同压力下,我国必须面对ESG信息披露制度对传统《证券法》的冲击。于《证券法》而言,ESG信息披露制度的引入实质上是非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对传统财务信息披露制度的全面挑战。二者在制度功能、披露理念、披露方式上都截然不同。
ESG信息披露制度的監管模式选择是制度构建的首要问题。学界研究大多囿于强制与自愿的二元对立模式,忽略了ESG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制度优势,以及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关联性。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因具有个性化与灵活性的特征,因此相较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赋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自由裁量权,更能适应反身法理论下复杂的社会现实模型。依据信号传递理论,个性化的信息更能形成有效的市场信号。因此,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不过这并不表明ESG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优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相反二者在制度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综上,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共同作用。结合域外立法例与ESG词源后,可以认为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是公司自治范畴,监管部门对公司ESG信息披露往往持自愿态度,通过市场驱动等方式推动公司披露ESG。监管部门如将ESG用作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在绿色金融建设目标下升级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社会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正当性。
虽监管模式具有正当性,但在制度构建上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监管不足和ESG自愿性信息激励不足的缺陷。在完善路径的选择上,环境信息监管的加强可以从重要性原则与强制性披露事由两个方面入手。但我国已经完成“双碳”治理现阶段的目标,且双重重要性原则与商事法的营利导向并不兼容。因此,当下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的实践动因与理论依据均不足,只需统合法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及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即可。学界关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法律激励主要围绕安全港规则的具体构建。但目前我国《证券法》中并无安全港规则的具体规定,且安全港规则本适用于预测性信息,如何适用于ESG信息还有待讨论。因此,监管部门现阶段较为合理的优化措施是细化ESG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引,后续再考虑安全港信息的引进。
参考文献:
[1] 黄世忠,叶丰滢.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双重重要性原则评述[J].财会月刊,2022(15):12-19.
[2] SEC proposes rules to enhance and standardize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 for investors[EB/OL].(2021-03-21)[2023-08-03].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2-46#.
[3]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 disclosures in proxy statements:Benchmarking the fortune 50[EB/OL].(2021-08-03)[2023-08-03].https://www.sidley.com/en/insights/newsupdates/2021/08/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disclosures-in-proxy.
[4] 郑丁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之审思与重构[J].金融与经济,2021(5):52-58,76.
[5]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ESG发展报告2022[EB/OL].(2023-01-17)[2023-08-03].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3-01-17/doc-imyansmn5843319.shtml.
[6] FRANK H E,Daniel R F.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J].Virginia Law Review,1984,70:669-716.
[7] TEUBNER G.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J].Law & Society Review,1983,17(2):239-286.
[8] DENNIS D.Hirsch.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News & Analysis[J].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News & Analysis,2012,42:10228-10241.
[9]FAIRFAX L M. Dynamicdisclosure:An expose on the mythical divide between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ESG disclosure[J].Texas Law Review,2022,101:273-337.
[10] 楊子绪,彭娟,唐清亮.强制性和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制度对比研究: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J].系统管理学报,2018(3):452-461.
[11] 方红星,楚有为.自愿披露、强制披露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J].经济管理,2019(1):156-173.
[12] 李有星,康琼梅.论证券信息自愿披露及免责事由[J].社会科学,2020(9):104-111.
[13] 北京大学法学院课题组,唐应茂.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比较研究[J].证券法苑,2021(3):163-194.
[14] 刘杰勇.论ESG投资与信义义务的冲突和协调[J].财经法学,2022(5):162-178.
[15] 刘俊海.论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保护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新视角[J].法律适用,2023(5):18-31.
[16] THE GLOBAL COMPACT.Who cares wins: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changing world[EB/OL].(2004-10-27)[2023-08-03].https://www.unepfi.org/fileadmin/events/2004/stocks/who_cares_wins_global_compact_2004.pdf.
[17] LIPTON M,LIPTON W,ROSEN, et al.Corporate governance:The new paradigm[EB/OL].(2017-01-11)[2023-08-03].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1/11/corporate-governance-the-new-paradigm/.
[18] 沈洪涛,沈艺峰.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8.
[19]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Punlic companies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B/OL].(2020-07-06)[2023-08-03] .https://www.gao.gov/products/gao-20-530.
[20] PURANIK S.Establishing long-term value and performance through ESG[J].Jus Corpus Law Journal,2022,2:653-662.
[21] MUSCIANO C B.Is your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 green or greedy? How a standard ESG disclosure framework can inform investors and prevent greenwashing[J].Georgia Law Review,2022,57:427-470.
[22] McHENRY P,CLAYTON J.The SECs Climate-Change overreach.[EB/OL].(2022-03-21)[2023-08-03].https://financialservices.house.gov/news/documentsingle.aspx?DocumentID=408294.
[23] Non-financial reporting rirective[EB/OL].(2014-10-22)[2023-08-03].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54213/EPRS_BRI(2021)654213_EN.pdf.
[24] Renewed sustainable financ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ion plan on financing sustainable growth[EB/OL].(2018-03-08)[2023-08-03].https://finance.ec.europa.eu/publications/renewed-sustainable-finance-strategy-and-implementation-action-plan-financing-sustainable-growth_en.
[25]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directive[EB/OL].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2/738177/EPRS_ATA(2022)738177_EN.pdf#:~:text=The%20legislation%20requires%20such%20companies%20to%20publish%20reports,anti-corruption%20and%20bribery%2C%20and%20diversity%20on%20company%20boards.
[26] 第一財经研究院.2022中国ESG投资报告—方兴之时,行而不辍[EB/OL].(2022-09-19)[2023-08-03].https://www.yicai.com/news/101540881.html.
[27]国责任投资论坛.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EB/OL].(2022-12-14)[2023-08-03].http://house.china.com.cn/uploads/20221220/202212201353221981.pdf.
[28] GENERALLY M A C.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eenwashing[J].UC Davis Business Law Journal,2013,14:281-304.
[29]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New consumer agenda:strengthening consumer resilience for sustainable recovery[EB/OL].(2020-11-3)[2023-08-03].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0DC0696.
[30] Screening of websites for ‘greenwashing:half of green claims lack evidence[EB/OL].(2021-01-28)[2023-08-03].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269.
[31] CHOI S.ESG metrics:Safeguard against greenwashing or safe harbor for greenwashing?[J].George Washington Journa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2023,14:27-41.
[32] 浙江本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EB/OL].(2023-04-27)[2023-08-03].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B_AllBulletinDetail.php?stockid=301065&id=9097049.
[33] 传化智联.2022年年度报告.[EB/OL].(2023-04-25)[2023-08-03].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B_AllBulletinDetail.php?stockid=002010&id=9057893.
[34] 每日经济新闻.A股绿色周报:49家上市公司暴露环境风险,国中水务子公司再因水污染物超标排放被罚[EB/OL].(2022-09-04)[2023-08-03].https://www.nbd.com.cn/articles/2022-09-04/2450958.html.
[35]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报告[EB/OL].(2023-04-29)[2023-08-03].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B_AllBulletinDetail.php?stockid=002424&id=9184383.
[36] 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产业研究: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情况分析[EB/OL].(2022-09-09)[2023-08-0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848851.
[37] 程茂军.试论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J].证券法苑,2017(2):176-201.
[38] 黄韬,乐清月.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规则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视角[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2):120-132.
[39] 楼秋然.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管模式选择:向“遵守或者解释”规则转变[J].证券市场导报,2017(1):63-70.
[40] 谭冰霖.环境规制的反身法路向[J].中外法学,2016(6):1512-1535.
[41] HAZEN T L.Corporate and securities Law Impact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purpose[J].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2021,62:851-904.
[42] 李先波,戴华丰.美国对有意义的警示性语言的规制[J].时代法学,2011(6):73-79.
Systematic improvement of ESG disclosure system of securities
law under the dual positioning of mandatory and voluntary
LI Yan, XIAO Zeyu
(Colleg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P.R.Ching)
Abstract:How to improv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SG disclosure is the primary goal of improving the ESG disclosure system. Based on the logic that mandatory ESG disclosure can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cy of voluntary regulation,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argue that mandatory ESG disclos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however, they ignore the value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and the insufficient arguments on why and how to strengthen mandatory disclosure. First of all, theoret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voluntary disclosure has the irreplaceable advantage of mandatory disclosure, and its flexibility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person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ESG disclos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re effective market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voluntary and mandatory disclosure are inseparable, and they are related and complementary in terms of system function, disclosure content and system construction.Secondly,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ESG directly affects the choice of regulatory model. If regulators position ESG as a tool to promote long-term corporate value,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corporate autonomy and adopts a voluntary stance; if they position ESG as a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y tend to enhance the mandatory nature of ESG letter approval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ocial governance. Accordingly, at this stage of Chinas dual-carbo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taining the voluntary nature of the remain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gitimacy. Again, although the positioning of the dual regulatory model is reasonable, there is still an endogenous conflict between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of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insufficient incentives for voluntary ESG disclos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ecific system. The current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still adopts a single materiality principle, which may result in insufficient supply of ESG disclosure as well as difficulty in coping with the phenomenon of greenwash; there is also the problem of varying standards in the matter of statuto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Voluntary disclosure, on the other hand, suffers from a lack of incentives. Listed companies may bear regulatory risks due to ESG disclosure, but there are no rules and exemptions to guide how to avoid them. Finally,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there are two paths for regulatory enhancement: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ouble materiality principle and the addition of mandatory disclosure.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the social public interest represented by the principle of double materiality and the investor protection interest of the securities law,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unify the legal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tandard at this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urities law can add environment-rel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disclosure matters to differentiate from environmental law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re are two paths to incentive enhancement:introducing a safe harbor for predictive information and refining the guidelines. However, considering that there is no domestic rule on predictive information safe harbor and the legislative cost is too high,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refine the voluntary ESG disclosure at this stage.
Key words:ESG;mandatory disclosure;voluntary disclosure;double materiality principle;single materiality principle; green finance
(責任编辑 胡志平)
基金项目:重庆市法学会第三期法学研究委托调研课题“金融法治护航乡村振兴问题研究”(CFH2022C02)
作者简介:李燕,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1002749738@qq.com;肖泽钰,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1552399675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