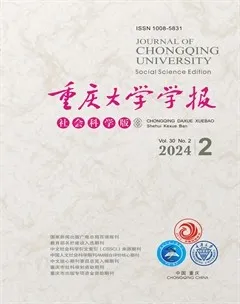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研究
摘要:《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但相关研究只注重其对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指导与借鉴意义。事实上,《长江保护法》对回答环境法治的三个问题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三个问题是: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自然区划法應如何立法?尤其是在强调立法节制的当下,为长江这一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而不是修正涉及长江环境保护的环境法律,背后更是具有深远的立法考量与丰富的研究价值。以《长江保护法》为素材,对三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长江保护法》未来的革新与发展,更能为新颁布的《黄河保护法》与《青藏高原保护法》等环境法律提供更为详备的理论支撑,进而最终作用于环境法治的发展与完善。《长江保护法》之所以被制定和颁布,缘于长江等自然区划的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存在不洽,并且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存在不洽,导致普适的环境法律无法满足自然区划特殊的环境保护需求,以及环境法治在自然区划上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出现了断裂。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然而却并非所有的自然区划都需要单独立法,长江流域为自然区划立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型样范。一方面,长江流域具备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具备环保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另一方面,长江流域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且又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此,只有具有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会产生与旧有环境法律的上述不洽,才具有单独立法的必要。为了让自然区划法适应于当前环境法律体系,且能更好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作用,需要将自然区划法置于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特殊法地位,在法律适用中予以优先适用。并且,自然区划法具有一项不同于现有环境法律的原则——完整性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自然区划法需要选择一种与当前环境法律有别的立法模式: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并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
关键词:自然区划;单独立法;长江保护法;特殊性;广域性;完整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2-0223-10
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下简称《长江保护法》)宣告实施,一时间全国上下关注环保的仁人志士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其是环境保护立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作为第一部全国性的自然区划单独立法,《长江保护法》不仅直接作用于未来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亦会对全国环境法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发挥《长江保护法》在环境法治领域的积极作用,环境法学界围绕其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并贡献出诸多富有见解的研究成果。
然而,丰硕成果的背后却留有一丝遗憾:学者在研究《长江保护法》更为系统的生态理念、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制之时,未能以其为突破口,在“自然区划单独立法”这一环保法治的重要议题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事实上,由于我国立法一贯秉承“宜精不宜多”的理念,在《长江保护法》颁布之前,学界与实务界曾围绕“是否需要在繁多的环境法律之外为自然区划的环境保护单独立法”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诚然,《长江保护法》的颁布为争论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回答,但这并不足以彻底消弭争论中提及的所有问题:为何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自然区划法应如何立法?尤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保护法》(以下简称《青藏高原保护法》)的颁布,上述有关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问题更是迫切地需要学界予以准确的回答。
基于此,本研究欲以《长江保护法》为例,回答有关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上述问题,不仅试图在学理上弥补相关研究的缺憾,更希望能为《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保护法》等法律的制定与革新提供更为详备的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长江流域应当进行单独立法”[1]。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抓紧制定一部长江保护法,联动修改水法航道法等,让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有法可依。2016年党中央印发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制定长江保护法。随后,中央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为此进行调研论证,在2018年9月发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长江保护法》被列为一类项目第41项。2020年12月26日,《长江保护法》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施行。毫无疑问,《长江保护法》是一部顺应万众期待的法律,是中央与众多关心长江环境保护的仁人志士长期努力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江流域单独立法是一项随着学理发展与实践演化而顺水推舟之举。相反,长江流域单独立法并不迎合学理上“立法节制”的理念与环境法治上“从分到合”的趋势。
我国立法学界一直秉承着“节制”这一理念,即部门立法“宜精不宜多”,解决社会新问题的法律思路应当是不断革新与完善法律设置与规制,确保既有立法的与时俱进,而非直接以新立法来予以应对,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法律法规的重叠与法律效力的疲怠[2]。并且,长期以来我国各个部门法领域都存在着立法过多、过杂、重叠的立法问题,上述问题也是法学界反思的重点所在。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等法律之外为长江流域单独立法,在直观上并不迎合学理上“立法节制”的理念。
此外,环境保护法并非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体系,我国最早的环境法律可以追溯到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197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某一特定环境情景下的保护法律。直到1979年我国才诞生出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但随着环境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不断整合零散的各类环境分支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主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为枝叶的系统性法律体系[3]。并且,模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制定并颁布环境保护法典,尽可能以“大而全”的法典统帅整个环境法律体系已成为学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与努力所向[4]。所以说,我国环境法治的发展路线是“从分到合”,且隐然出现“大一统”的趋势,《长江保护法》的颁布也并不迎合环境法治的上述趋势。
《长江保护法》自提出到正式实施历经二十余年,说明这是我国政府经过长期熟虑后做出的谨慎决定,它对学理和环境法治的“不迎合”不足以盖过长江流域单独立法之必要。但关注“不迎合”并不因此变得毫无价值,甚至比颁布前的关注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长江保护法》不只是一部长江法,更是首部自然区划立法。在它颁布之前,对“不迎合”的关注只是导向“应不应该为长江流域单独立法”的问题,而在它颁布之后,对“不迎合”的关注则演绎为更为复杂的 三个问题:一是更多的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是否有必要?二是什么样的自然区划应当被单独立法?三是自然区划法应当如何制定?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是对《长江保护法》的进一步巩固,更能为后续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的范式指导。遗憾的是,在《长江保护法》颁布之后,尽管学界对其充满了研究热情,但相关研究却多集中于该法对长江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长江保护法》以整体生态观保护长江环境[5];《长江保护法》中的生态流量保障制度等[6]。尽管也有提及《长江保护法》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7],或是《长江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的衔接问题[8],但也仅是就长江流域讨论《长江保护法》,而未能将其作为第一部自然区划法置于更为长远的视角之上,对后续立法的支撑与指导也就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将《长江保护法》置于第一部自然区划法的角色,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并以此贡献于未来的自然区划单独立法,应是环境法学当前研究的聚焦所在。
二、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必要性
颁布《长江保护法》的理由是“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9]。但从法律逻辑上说,这一理由仅能成为完善涉长江流域环境法律的理由,而不足以支撑起长江流域单独立法。因为这一理由无法排除以“完善现有环境法律”来实现“推动长江流域环境保护”这一方式。所以,探寻长江流域乃至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真正的必要性,应当着眼于二处“不洽”。
(一)自然区划环保特殊性与现有法律普适性的不洽
以《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环境法律强调对个体行为的规制,通过为个体行为设定禁令或是行为规则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10]。其针对的对象是虚指的个体(行为),而非特定的或是某一情境下的个体(行为)。因此,环境法律设置的禁令或是行为规则具有普适性,表现为设置较为原则的某类禁令而非明确某一行为的禁令,或是设置践行行为规则的程序而非直接可以使用的行为规则。并且,禁令只是禁止大概率产生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行为,或是行为规则的标准取污染程度适中的平均值。这里的“大概率”“较为严重”与“污染程度适中”是指相对于全国整体环境质量、污染排放水平、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水平等宏观情况而言。环境法律如此设置是基于其法律定位与效力范围的考量,过于直接或是过细的禁令或是行为规则都会阻碍其法律实践。
从法律传统上看,针对虚指的个体(行为)进行行为规制不会在具体情境的法律实践中造成法律设置与规制治理的脱节。因为绝大多数法律的调整对象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使是特定情境下的实体,其行为与法律关系一般不会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出现偏差。但在自然区划环境保护上却不能如此轻易地保持一致。尽管环境法律调整的依然是社会关系,但生态环境是该社会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一环,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会直接导致社会关系的特殊,进而使应当被规制的个体行为变得特殊[11]。例如长江流域面临的一个重要环境问题是生态流量过少,其直接后果是水质自净能力变差、渔业资源枯竭、水文环境恶劣等。但《环境保护法》对于涉水环境行为的规制只是要求达标污染排放、禁止过量捕捞等,《水法》也仅仅在第30条提到“應当注意维持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水位”,二者没能为长江流域生态流量的保护提供法律供给。此外,总磷是长江流域的首要污染物,防治总磷污染是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首要任务之一。但《环境保护法》与《水法》只是对一系列有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行为进行泛泛规制,未能突出总磷或是化学污染的防治要求。并且,《环境保护法》与《水法》也无法根据不同自然区划的客观情况来进行自身设置。例如二法很难单独根据长江流域的生态流量或是总磷污染的治理需求,在自身条款中单独设置相应规则。因为全国各河流与流域的客观情况不同,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需求也不相同,完全契合长江流域的个体行为规制未必适合其他河流与流域,故而二法只能在自身条款中取各流域需求的公约数——普适性的个体行为规制。
(二)自然区划环境法治与环保法法域链接的不洽
法域链接指的是法律实施的空间链接,这里的空间并非是法律效力覆盖的地区,而是指法律实施在空间意义上的过程与效果[12]。一般而言,法律的法域链接都保持着严密的因果关系,例如《刑法》在浙江省实施的过程是浙江省公检法部门对个体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产生的犯罪率下降的效果也发生于浙江省,呈现出前后的链接效应。法律的法域链接之所以保持严密的状态,缘于中国科层制体制下的行政区划良好地承载了法律的实施。换言之,法律的法域链接是建立于行政区划之上的链接。
但是,法域紧密的链接却在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上出现了裂痕。即实施环境法律在自然区划上的过程与效果出现了断裂。与其他部门法一样,环境法律的实施过程也依托于行政区划的行政单位,受规制的个体也集中于相应的行政区划之内,但其实施结果却并不完全发生于行政区划之内,可能延伸至自然区划中其他的行政区划之内。例如,在长江流域的上游对个体的污染行为进行规制,会产生净化空气、存活鱼类、净化水质等治理效果,但这些治理效果很可能通过风力吹拂、江水流淌、鱼类洄游等途径而发生于长江中游或下游地区。出现裂痕的法域链接会导致两大后果:一是规制个体的行政单位无法预测与享受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回馈;二是承受不良治理效果的行政区划无法通过对自身辖区内的个体行为规制来改变治疗效果。所以,考虑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就业之间短期内的互抑关系,承担实施法律这项职责的行政单位会基于性价比的理性,倾向于积极实施其他法域紧密链接的法律(比如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法律),而保守实施环境法律。
解决第一个不洽的方式应是围绕自然区划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立法设置,从而使法律切实且科学地满足自然区划的环境保护需要;而解决第二个不洽的方式应是将自然区划立法设置的层级上升到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层面,将多个行政区划置于一个自然区划之内进行环境法治,进而在一个自然区划之内消弭法域链接的裂痕。二者合一,解决自然区划环境保护与现有环境法律两大不洽的正确方式应是为自然区划环境保护进行单独立法。《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一方面,围绕长江流域的特殊性,《长江保护法》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置,建构了生态流量等为长江环境保护量身定做的制度;另一方面,《长江保护法》统辖了长江流经的11个省级行政区,将实施过程和效果扩展到长江流域这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之中,有效实现了各行政区划的规制合力。
三、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对象选择
(一)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需要具有特殊性
解决流域环境保护的特殊性与现有法律的普适性的不洽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必要的第一个理由,因而应当需要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首先应当具备特殊性。这里的特殊性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一是地理与人文的特殊性,二是环境保护需求与规制手段的特殊性。地理的特殊性是指自然区划在水文、地质、地貌、气象等地理特性上的特殊,是该自然区划区别于别的自然区划的客观标识,也是该自然区划可以单独立法的最基础条件。而人文的特殊性是指自然区划中或周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特性上的特殊,科学的法律应建立于多重因素的考量之上,只有将法律的实施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协同起来,才能确保其有效性。所以,自然区划人文特性上的特殊决定了自然区划在环境保护上需要考虑更多的协同,也意味着人文特性上越特殊的自然区划,越需要更“因地制宜”的环境法律。
环境保护需求的特殊性是指基于特殊的地理特性,自然区划相应地需要被予以特殊的环境保护。例如长江流域是水域采砂的重点,大规模、跨区域的过度采砂导致长江多段河体出现河道下沉等环境问题,《水法》第39条规定“影响河势稳定或者危及堤防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划定禁采区和规定禁采期”,但鉴于长江多段河体的脆弱性与连续性,长江流域的环境保护就需要法律进行更为精细与预见性的采砂治理[13]。规制手段的特殊性是指基于特殊的人文特性,法律为了实现自然区划环境保护的法律目的,需要量体裁衣地制定与实施对应的规制手段。例如长江是全国各省份重要的用水供应来源,保护长江水源应当考虑到沿江省份甚至全国的用水需求与调配。但《水法》没有也无法对此进行相应设置,因为绝大多数的河流在水源供应上都未如长江般重要。所以只有单独制定《长江保护法》,并规定“制定跨省河流水量分配方案”等方式来保障各行政区划的用水供给,才能更好地实现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区划的特殊性并非是一种绝对的特殊性,而是指相对的特殊性。绝对是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自然区划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使是一个小池塘或是一个小山坡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态系统。而自然区划支撑单独立法的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的特殊性,指相对于当前环境法律的普适性而言,既未能被其所涵盖又不无被其涵盖。这种相对的特殊性难以通过只言片语来进行直接界定,应以科学与法理的综合分析进行判断。这就对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前期论证要求,立法者需要以更为科学与细致的立法程序、更为广泛的专家与社会参与、更为系统的数据监测与前提调研来进行自然区划特殊性的判断。
(二)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需要具有广域性
解决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的法域链接的不洽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必要的第二个理由,因而需要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应当具备广域性。这里的广域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自然区划需要跨越多个行政区域,二是自然区划应当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之所以需要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是因为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的自然区划一般不会出现法域链接上的断裂,即使不同部门或者行政单位因为合作问题而出现“搭便车”的心理,也只需要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政府以行政规划或者命令的方式予以统合,而无需立法对其进行统辖与约束。只有当跨越行政区划时,法域链接出现了多处断裂且地方政府无法以一己之力来弥合这些断裂,甚至自身也在计算性价比之后消极地进行环境法治时,自然区划才需要单独立法。
单独立法的自然区划应当是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因为单独立法的目的是将原初断裂的法域链接弥补起来,将之重新变得紧密。而紧密的前提是承载法律实施的区域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承载传统法律实施的区域是行政区划,通过行政体制而聚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相应的,承载自然区划法实施的区域只能是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自然区划,它首先需要通过生态循环而自成一个生态系统,随后通过法律的实施而被注入各类社会关系,进而被连接为一个完整的法治系统。所谓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是指自然区划应是一个由内部相互作用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构成的、并可以在人类生产活动干预下形成的、具有整体功能的生態学功能单位[14]。倘若自然区划本身并非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则相应的法律实施就没有可以依附的框架与枝干。例如,依照温度及有关现象可以划分出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等自然区划,它们也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且跨越多个行政区划,但它们并非一个完整而聚合的生态系统,也就无从进行单独立法。
与自然区划的特殊性类似,自然区划的广域性也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因为行政区划是一个包含各个层级的概念,跨越多个行政区划的自然区划也就成了一个相对概念。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自然区划当然地具有广域性,而跨越多个市级行政区划或是更低级的行政区划是否算是具有广域性则需要“一事一议”。一般而言,省级地方政府可以行政规划或者命令的方式将多个行政区划的环境法治予以统合,但亦有可能因为某些客观因素(如特殊于省级行政区划内所有自然区划的特殊性)而需要单独立法。例如,浙江省钱塘江具有独一无二的潮汛这一地理特性,也就有了极为特殊的水域保护与水能开发需求,所以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钱塘江管理条例》,并围绕潮汐进行了相应的条款设置。当然,即使存在这样的例外,相应的单独立法也必然不会是狭义的法律,而应是地方性法规等,严格意义上说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内。
四、自然區划法的立法路径选择
(一)自然区划法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衔接
由于自然区划法与《环境保护法》《水法》等现有环境法律都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因而在法律效力上看属于平级。但从适用范围上看,自然区划法适用于特定的自然区划内,而现有环境法律适用于全国,因而自然区划法属于特殊法,现有环境法律属于一般法。进而在实践适用上,自然区划法应优先于现有环境法律。优先的地位决定了自然区划法应当比现有环境法律规定得更细、更严、更完善。
更细是指对于现有环境法律中许多指导与原则性的规定,自然区划法应结合自然区划的特殊性,设置更为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现有环境法律尤其是《环境保护法》设立了许多环境保护制度,如联合防治协调机制,但《环境保护法》就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的实施仅是规定“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以及“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或者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而《长江保护法》将之细化为“建立健全长江流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机制”、长江流域河道非法采砂联合执法工作、水工程联合调度、对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的联防联控、水陆有机衔接、江海直达联运、联合执法等。更严是指对于现有环境法律中已有的标准性规则(如排污标准),自然区划法应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型规则。《环境保护法》规定“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但在法律实践中,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理性缺乏制定更为严格标准的动力。因此,自然区划法应率先制定严于现有环境法律中已有标准的规则,为自然区划内的地方政府提供实施法律的技术性基础。更完善是指对于现有环境法律任何未规定的环境法治规定,自然区划法都应予以相应的补充和完善。补充和完善的对象不仅限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更包括现有环境法律未曾设计的制度与规制手段。
当自然区划法以更细致、更严谨、更完善的姿态成为一系列特殊法之后,其与现有环境法律这些一般法的衔接就自然地顺畅而不冲突了。在自然区划法治中,现有环境法律提供原则、引导与基础性规则,自然区划法提供细致、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只有在自然区划法未曾设置的方面(应当也是该自然区划中较为不重要的环境保护方面),才可以直接适用现有环境法律中的相关规则。
当然,就自然区划法与现有环境法律的本身立法而言,还应就无缝衔接作进一步的考虑与完善,尤其是《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兼具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两个目的的法,往往游走于经济法属性与环境法属性之间,容易与强调环境保护的自然区划法发生冲突。如《长江保护法》第23条强调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严格管控,而《水法》第26条侧重于鼓励开发、利用水能资源[15]。此时,《水法》等现有环境法律就需要对自身进行立法调整,以衔接自然区划法的相关规定。而除现有环境法律之外,《刑法》《民法典》等调整环境保护以外社会关系的法律,也需要就细节进行修正。如《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范畴涵盖不了《长江保护法》中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对“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程度性的司法解释无法契合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特殊性等[16]。只有比照《长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刑法》这些细节进行修正,才能实现《刑法》与《长江保护法》的更好衔接,进而确保长江流域环境法治的严密性。总的来说,现有环境法律与其他法律在与自然区划法进行衔接时,应着重关注现有法的修正,而不是自然区划法立法时对现有法的妥协。因为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诸多法律所追求的目的中,环境保护往往是最易被牺牲的那一个。
(二)自然区划法的原则与立法模式
自然区划法是针对整个自然区划、建立于自然区划特殊性与系统性之上的环境法律。除了承继现有环境保护的诸多原则(如环境保护优先原则、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等),还应具有自身独特的原则——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可以被定义为: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是基于其整个生态系统的考量,以系统且协调的法律体系实现自然区划的环境保护。具体而言,整体性原则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生态整体性、空间整体性、治理整体性与发展整体性[17]。生态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因为完整的生态系统而在法律关系中成为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上所有的环境治理活动都应当受统一的环境行政机构的统帅与管辖,所有的环境司法与执法活动都来源于统一的法律与行政权威。空间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环境法治虽然通过各行政区划的治理活动得以实现,但各行政区划应以统一的地理空间作为自身治理考量的前提,主动与其他行政区划合作与协同,履行联防联控等法律责任,并以整个空间的治理效果作为责任履行的评价标准。治理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的环境法治需要关注整体空间的环境质量,而非单一区划的个体规制或单一元素的环境保护。治理整体性缘于自然区划法生态整体性与空间整体性,同时又反馈于二者。同时,治理整体性又是整体性原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自然区划法衔接目标与规则的关键性要素,也是其立法应当坚持的首要原则。发展整体性是指自然区划法应当留意环境法治在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与现有环境法律“协调发展”原则不同的是,自然区划法并不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而是关注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来为环境保护提供充沛且永续的动能。因此,自然区划法的发展整体性是以环境保护的需求为衡量标准,希望通过经济与社会发展来反哺环境保护。典型例子是《长江保护法》第63条规定的“中下游地区在生态环境修复时应当对长江流域江河源头和上游地区予以支持”。
整体性原则是自然区划法特殊于现有环境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自然区划法选择立法模式所依托的基础。在诸多《长江保护法》的相关研究里,已有不少针对其整体性原则的研究,认为《长江保护法》实现了长江流域环境法治从“条块分割”到“统筹协调”的改变[18]。但这些研究只是关注了《长江保护法》贯彻整体性原则的表象,而忽视了《长江保护法》依托整体性原则在立法模式上的重大变革——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规制对象。纵观《长江保护法》中除第一章总则、第八章法律责任、第九章附则外,共计66条条款,其中有53条条款以各级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单纯规制个体或是要求中央政府进行引导与统辖的条款仅有13条。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环境保护法》《海洋保护法》等现有环境法律“重”规制个体而“轻”规制地方政府[19]。
《长江保护法》与现有环境法律在立法模式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其原因是《长江保护法》将现有环境法律的分散性转变为整体性。之所以说强调个体规制的现有环境法律是分散的,缘于规制个体在环境法治中的种种弊端。规制个体是提升环境质量的必要手段,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规制个体并不能必然提升环境质量[20]。但现有环境法律强调对个体的规制,意味着赋予地方政府只要实现了对个体的良好规制,就属于履行了法律赋予的责任。在这一立法模式下,地方政府只会关注行政区划内对个体违法行为的规制,而不会关注自然区划的整体环境质量。此时,可能没有个体违规(例如全部按照标准进行污染排放),但因个体数量过多而导致污染排放总量过大;也可能违规的个体全部受到法律惩罚,地方政府算是履行了法律责任,但已经排放的污染严重地损害了环境质量,产生了“合法”的权力寻租。并且,地方政府不会主动与其他地方政府进行治理合作,因为行政区划内的个体规制无需合作。所以说,现有环境法律的立法模式是分散的。
而《长江保护法》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要求地方政府为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而负责,实施“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建立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体系”,“补充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措施,实质上将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从个体规制转向了提升环境质量。此时,地方政府无法再通过个体规制来确保法律责任的履行,而必须通过完成《长江保护法》对地方政府的规制要求,并最终提升了长江流域环境质量这一结果来获得责任良好履行的评价。为此,地方政府不能再各自为战,因为完成《长江保护法》对地方政府的规制要求必须联动而非独立(如河流水量分配方案需要多个地方政府进行商定),履行责任是基于长江流域整体环境质量而非自身辖区的环境质量或是某一环境要素的评价。所以,《长江保护法》的立法模式是整体的。
《长江保护法》整体性的立法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成效,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21全年长江下游江苏段干流断面II类比例、支流断面优Ⅲ比例升至100%、98.3%,较2016年分别提高50个百分点和41.5个百分点,全面消除了劣V类,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新世纪以来最好[21]。借鉴《长江保护法》的科学范本与成功经验,自然区划法贯彻整体性原则必须从立法模式着手。只有将注重规制个体的立法模式转变为注重规制地方政府的立法模式,以系统的责任体系来确保地方政府为自然区划的环境质量负责,而不是为行政区划的个体规制负责,才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应有之道。
五、结语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自然区划法,它的颁布不仅是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的新福音,更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道路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研究《长江保护法》不仅需要对它进行赞美与期望,更应当从它身上发现未来自然区划单独立法的方向与路径。因为自然区划环境保护与现有环境法律的两大“不洽”,所以自然区划需要单独立法。而只有会产生“不洽”的自然区划,即具有特殊性与广域性的自然区划才需要单独立法。当为这些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时,《长江保护法》告诉我们,科学的法应当坚持整体性原则,并在该原则的指导下确立以地方政府为规制对象,围绕提升环境质量而非个体规制地赋予地方政府以法律责任。诚然,《长江保护法》并非一部完美无缺的法律,但它未来的每一步修缮都将是自然区划单独立法最好的借鉴与启迪。谨以此文抛砖引玉,希冀《长江保护法》与未来的自然区划法能为我国环境法治作出最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忠梅.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统一立法刻不容缓[J].内部文稿,2000(8):27-29.
[2] 顾爱平.节制是立法者的美德:兼论立法理念的错位与变革[J].江苏社会科学,2010(5):117-122.
[3] 徐以祥.论我国环境法律的体系化[J].现代法学,2019(3):83-95.
[4] 吕忠梅.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模式选择及其展开[J].东方法学,2021(6):70-82.
[5] 高中意.长江保护立法的理论建构:基于整体论的分析[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34-41.
[6] 徐海俊,秦鵬.流域立法视角下生态流量保障的制度供给:以长江流域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2):183-192.
[7] 吕忠梅.《长江保护法》适用的基础性问题[J].环境保护,2021(S1):23-29.
[8] 夏勇,范煜.论《长江保护法》与《刑法》的对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11-118,185-186.
[9]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研究课题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1999(2):39-47.
[10] 姜渊.探寻与建构中央和地方同时“在场”的环境质量目标制度:以环保督察常态化之争为切入点[J].政法论丛,2021(2):140-149.
[11] 张祥伟.环境法研究的未来指向:环境行为:以本位之争为视角[J].现代法学,2014(3):102-115.
[12] 徐祥民,宛佳欣.环境的自然空间规定性对环境立法的挑战[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4):105-115.
[13] 刘竹梅,孙茜,徐阳.《最高人民法院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2022(1):159-167.
[14] 马世骏.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J].环境保护,1978(2):9-11.
[15] 陈金木,谢浩然,汪贻飞.《长江保护法》实施后联动修订《水法》的思考和建议[J].水利发展研究,2021(3):11-15.
[16] 上海海事法院审判监督庭课题组,沈军,王岩,等.涉长江大保护海事行政审判疑难前瞻与规制路径[J].法律适用,2022(12):133-141.
[17] 王彬辉.从碎片化到整体性:长江流域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的立法建议[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6-29,111.
[18] 邱秋.多重流域统筹协调:《长江保护法》的流域管理体制创新[J].环境保护,2021(S1):30-35.
[19] 姜渊.政府环境法律责任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3-40.
[20] 徐祥民.环境质量目标主义:关于环境法直接规制目标的思考[J].中国法学,2015(6):116-135.
[21]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苏政办发〔2021〕84号)[J].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2022(1):5-33.
Study on separate legislation of natural regionalization: Taking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as an example
JIANG Yuan
(Law School,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P. R. China)
Abstract: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is the first independent law in China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natural zoning.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mainly emphasized it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hile neglecting its significance as a guide and reference for independent laws on natural zoning. In fact,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ree key question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why does natural zoning require separate legislation? What kind of natural zoning can be subject to independent laws? How should laws on natural zoning be formulated? Particularly in the current emphasis on legislative restraint, enacting a separate law for the Yangtze Rivers natural zoning instead of amending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s related to its protection reflects profound legislative considerations and rich research value.Using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as a basis, conducting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se three questions not only benefits future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is law but also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newly enacted environmental laws such as the Yellow River Protection Law and Qinghai-Tibet Plateau Protection Law. Ultimately, th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The reason why the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was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is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uniqueness of natural zoning areas such as the Yangtze River does not align with existing universal laws, and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natural zoning areas and the jurisdictional linkages of environmental laws. As a result, universal environmental laws cannot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atural zoning areas, leading to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se areas.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separate legislation for natural zoning, not all natural zones require individual legislation.The Yangtze River Basin provides a standard model for legislating on natural zones.On one h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possesse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uniqueness, which requires special measures for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On the other hand, it spans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while functioning as an integrated ecosystem.Therefore, only those natural zones that possess both uniqueness and broad coverage will experience mismatches with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s mentioned above and necessitate separate legislation.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legislation on natural zones can adapt to current legal frameworks concerning environment while better utilizing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and roles, it is necessary to grant special legal statu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law systems by prioritizing their application during legal proceedings.Furthermore, legislation on natural zones has a principle distinct from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s - integrity principle.Under this guiding principle, legislation on natural zones needs to adopt a legislative approach different from current ones by establishing local governments as regulatory target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regulation, and assign legal responsibilities to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natural regionalization; separate legislation; Yangtze River Protection Law; particularity; wide area; integrity principles
(責任编辑 胡志平)
基金项目: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优化研究”(22&ZD138)
作者简介:姜渊,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Email:1063940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