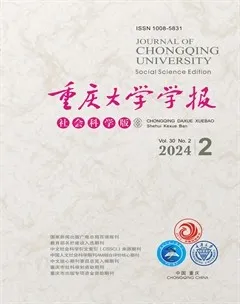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摘要:中国古代景观游赏经历了从自然景观走向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的过程。名胜景观作为景观之有“名”者,是无数文人士大夫、知名人士共同参与的自然与人共生的结果。“名胜”最初指“人物”,常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属于名流群体,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 “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逐渐成为知名景观,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发展为“景物”之“名胜”,“名胜”具有了“人”与“景”的双重含义,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集中体现了古代景观文化中的“慕古”与“述古”传统,这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具体表现在基于“名人”及“文献”的景观文化传承,具有层累的特征。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有效传播并保存了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士人游赏名胜,往往根据以往的诗文或志书追溯名胜的历史及相关人物,并以自己的创作或记述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地志类文献亦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考证并记述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形成丰富的景观记述体系。这一传承模式影响了古代名胜景观物质形态的复兴与遗产的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构建筑,其物质形态较难长期保存,古代名胜景观的复建,并非要完全恢复景观的物质形态,而是根据前贤诗文和文献中的景观叙述,进行文化和地点上的考证,重构描述或想象中的景观,表达追慕之情,传承景观文化。
关键词:名胜景观;景观文化;名人;文献
中图分类号:K928.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24)02-0133-14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空间、地点及景观的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学者们开始对空间、地点或景观的变迁作文化分析,其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涉及对景观的文化解释,注重景观的象征性,注重空间形式所表达的文化意义。在John Wylie看来,“景观”是人类、文化及创造性的领域,一方面,存在一个客观的、现象的、物质的“景观”,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主观的、感知的、想象的“景观”[1]。思考景观意味着考虑一个地区及那个地区所呈现的外观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 [2] 。学者们开始关注空间、地点、景观与文化记忆的关系,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虽然地点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3]344 。
在这种学术转向中,空间、地点、景观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鲁西奇认为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性的,它既是观念的反映,又是观念的形式,是想象的、阐释的和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思想“塑造”著其周围各种各样的“空间”,又处身于更复杂、广阔的“生产”出来的空间之中,空间与其创造者、使用者的各种思想、情感与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乃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和表现,在文化空间的生成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与主动性表现得最为突出[4]。 阿诺德·伯林特提出“参与”的环境美学,环境是由充满价值评判的有机体、观念和空间构成的浑然整体,美学的重要意义存在于一切人类关系、行为中,环境美学不只关注建筑、场所等空间形态,还处理整体环境下人们作为参与者所遇到的各种情境[5] 。在中国古代,环境与人之间具有双向的意义呈现,中国古人一直非常注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曾繁仁在探讨生态美学时,提到共生性是一个主要来自中国古代的生态美学范畴,意指人与自然生态相互促进、共生共荣、共同健康、共同旺盛[6]。吴欣认为任何熟悉中国式思维方式的人都会注意到世界同时意味着客观事物、我们的主观自我以及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天底下所有的事物、事件都是活生生的,并且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关系感知到。纵观历史,与自然诗意地交融是中国文化的特点[7]。
“名胜”作为中国古代景观文化的重要代表(随着山水文化研究日益兴盛,学界在诗文与山水书写、胜迹构建方面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研究时段多集中在东晋至唐宋,如莫道才《唐宋文人的游历与人文山水名胜的形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等等。),其文化历程正是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众多文化力量共同参与的自然景观与人共生的过程,是人与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是人与景之间的生命互动、性灵互感、内在心性上的交融和契合,并通过景作为媒介探寻与古人和历史的呼应,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美。《辞海》对“名胜”一词的解释为:(1)著名的风景地。如:名胜古迹;(2)犹名流[8]。大致可见“名胜”一词的语义主要有二:一为名景,二为名人。《现代汉语词典》“名胜”释义:“有古迹或优美风景的著名的地方。”[9]尽管现代汉语中“名胜”多用来指“名景”,但在古代,“名胜”一词最初是指“名人”,此后逐步过渡到“名人”与“名景”并用的状态,这一演进过程蕴涵了古代名胜景观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近年来,学者们提出“走向(或回到)历史现场”,“即研究者想象自己处身于其所研究的时间与空间中,努力站在所研究时代具体地方的人或人群的立场上,设想自己与‘古人处于同一种特定的地理、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境中,以‘古人的眼光,去观察、认识并描述所研究时空范围下的人与事及其世界,并做出分析和阐释”(鲁西奇《空间的历史与历史的空间》,《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1期,第18页),本文对中国古代“名胜”概念的探讨亦主要基于历史文献所见古人对“名胜”的认识和理解。)。 此外,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慕古、述古、怀古是其重要特征,而名胜景观的文化史正体现了这一特征。
一、从自然之胜到胜迹之胜:魏晋至唐“名胜”景观的孕育
魏晋之前,受制于交通、技术与文明的发展,人类对山林的探索有限,山林充满神秘色彩,常被视为神仙道教世界。尽管《诗经》《楚辞》中已有山水描写,如以山水自然为媒介传达情感,但山水景观尚未成为游赏和评价的主体。刘成纪提到“先秦两汉时期的圣王、权贵和士人,已多有山川壮游乃至风景雅赏的经历,但这些活动往往与认知或功利化的目的相混合,景观或风景并没有真正构成地理评价的价值主体”[10]。此时,国家祭祀系统里的“名山”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名”山。《四库全书总目》谓:“自古名山大泽,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闻品题名胜。逮典午而后,游迹始盛。六朝文士,无不托兴登临。”(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1《史部·地理类四·徐霞客游记十二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0页。)可见,在清人看来,作为景观的“名胜”应是具有游赏性质的,而这种游赏行为的起源,始自魏晋六朝。
魏晋之际战乱频仍,士人们逐渐以遁入山林为安身之法。“徜徉山林日久,却也在无意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于是,文士们便在歌咏黄老、诵吟松乔之余,也就有意或无意地将对山水的赞美夹杂其间。”[11]而晋室南渡,士人集中来到南方,离乡背井,且政局多变,常有郁愤之情,江南清丽的山水成为他们情感的寄托,参加兰亭雅集的孙绰言“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见《兰亭集校注》,李剑锋校注,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谢灵运称“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谢灵运《游名山志并序》,见《谢灵运集校注》,顾邵柏校注,里仁书局,2014年版第390页。)。江南的山,常与水相间,景色秀美,适合登临,士人们可以获得充分的山水游赏体验,他们的思想、知识和才华与江南山水相互作用,促进了山水诗文的兴盛,山水审美快速发展。葛晓音提到东晋永和年间玄言诗中开始出现了新的观念,“这就是将观赏山水视为体会自然之道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良辰美景中逍遥自在,以领悟人生取乐一时与追求永恒的关系”,“标志着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12]166-167。“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2《明诗第六》,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5页。),刘成纪指出这是当时山水观游成为风尚并成为纯粹审美形式的证明[10]。
山水的浸润,有助于士人群体更好地体悟宇宙自然之道、庄老及佛学思想,促进了对个人精神世界的追寻,士人山水诗文中常有一种时光易逝、生命短暂的感怀。“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房玄龄等《晋书》卷80《王羲之传》兰亭集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9页。),山水常在,而观览山水之人不能常在,山水之常得见生命之匆促。六朝文人流连山水,正在于山水得以映射人生之短促,并希望借山水而得人生之永恒。所谓寄情于山水,是以人生之情,托于山水之上。山水虽客观存在,然若无人情寄之,只是枯山冷水。因有人情,而有情景交融的“山水”。士人们流连于“山水景物之胜”,由此生发今昔之感,而诸名士参与过的“山水”又将成为后人慨叹吟咏的对象,正如王羲之所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晋书》卷80《王羲之传》,第2099页。)。
随着山水审美的兴起、魏晋时期交通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走入山林,尤其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丰富的山水资源逐渐得到开发。谢灵运身为门阀士族,尽管仕途坎坷,但仍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开发山林,满足寄情山水的需要。“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沈约《宋书》卷67《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5页。)同时,佛教东传、道教兴盛,山林成为寺观建设的重要场所。文士、名僧、道人走进山林,并通过诗文记述自然美景和游赏活动。伴着地理探索的热潮,魏晋南北朝时期诞生了以《水经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地理学著作。通过诗文和地理学著作的传播,许多山水景观在知识阶层中拥有了知名度,逐渐为人们所向往。
魏晋时期,“名胜”一词已频繁见诸文献,但最初“名胜”并非指胜景、胜地,而是指负有盛名的人士。《晋书·王导传》谓司马睿渡江,吴人不附,会三月上巳,睿亲往观禊,王敦、王导“及诸名胜皆骑从”(《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5页。)。其所说“诸名胜”,即当时名望高重、地位显达的达官贵人。北魏南安王元熙“既蕃王之贵,加有文学,好奇爱异,交结伟俊,风气甚高,名美当世,先达后进,多造其门”,因政治斗争,将死之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魏收《魏书》卷19下《景穆十二王列传·南安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3-504页。)邢卲“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李百药《北齐书》卷36《邢卲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75页。)。德高望重的高僧亦可被称为名胜,《续高僧传》载:“陈帝意欲面礼,将伸谒敬,顾问群臣:‘释门谁为名胜?陈暄奏曰:‘瓦官禅师德迈风霜,禅镜渊海。昔在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蔼。”(道宣《续高僧传》卷17《习禅篇之二·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顗传三》,郭绍林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28页。)又《长阿含经序》:“时集京夏名胜沙门于第校定。”(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9《长阿含经序第七》,苏晋仁、萧鍊子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6页。)其所谓“名胜沙门”,即指著名僧人。整体来说,见诸文献的名胜人物多有交游、赏景、文学、学问等特征,常具清高洒脱之意,属于名流群体,即可谓魏晋“名士”。因此,尽管“名胜”一词最初仅指人物,但这些人物与山水及景物游赏多是相关的。而山水景物因“名胜”人物的参与,也逐渐成为知名景观。
唐代作为大一统王朝,交通便达,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走向远方,旅行游览之风尤盛,诗人灿若星辰,诞生了非常丰富的山水诗文。随着宗教的发展,佛教和道教景观的建立,进一步促进山林开发和名山的形成。唐人山水景观记述中已出现较明显的慕古现象,例如,表达对魏晋风流的仰慕。魏晋时期山水文化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人物为唐代文人提供了追怀的对象。王羲之、谢灵运、谢安、谢朓、慧远等魏晋名士常常出现在唐人的山水诗文中,如,“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见《孟浩然诗集校注》卷1《五言古诗》,李景白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07-108页。)。“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孟浩然诗集校注》卷3《五言律诗》,第231页。),孟浩然基于晋代羊祜及岘山的故事生发的古今之感,成为景观怀古的一个主题,吸引众多后世文人参与其中。宇文所安提到“在人们的相互往来中,有人已经使得他们自己的某些东西同永恒的自然联结在一起,留下了孟浩然诗中所说的这种‘胜迹”[13]。景观中的“迹”或“胜迹”是与“人”和“事”相关的,巫鸿认为“迹”意味着追寻某人或某事的实迹,无始无终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再现,“迹”将自然转变成人为,亦将人为化为自然[14]。岘山怀古的情绪在史籍中亦有细致记载。《晋书·羊祜传》载西晋时羊祜借岘山感怀:“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猶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20页。) 西晋羊祜怀古时,贤达胜士湮灭无闻,而至唐代,诗文、史籍等将与此“胜迹”相关的“人物”和“故事”记录传播,并流传后世,羊祜亦得以“与此山俱传”。
魏晋至盛唐文本中的怀古情绪,往往是士人身处景观中生出的历史之感,这样的景观可为历史古迹,可为前贤故迹,也可为引发其追慕之情的其他风景。刘成纪提出怀古诗“是诗人在四方游历过程中对前人史迹的凭吊和观览,于此,前置性的历史知识变成了感性的历史现场,抽象的历史记忆被形象化、景观化了”[15]。不过魏晋士人在山水游赏中虽常生发时空古今之感,但追寻历史名迹并非游赏的主要目标。魏晋时期山水游赏以寻求自然之胜为主,且因战争及地理上的割据状态,当时人们往往只能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游赏风景、凭吊古迹,只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人才有机会走向远方,探访远方的古迹(田晓菲认为四至五世纪的军事远征为南方士人打开了新的视野,并被记录成文字,“征行赋对著名古迹和重大历史事件做出反思,在其中,地理的重要性被历史的重要性所取代”。见田晓菲《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76、87页。) 。唐代士人们的旅行不再有地域限制,一些山水景观因为魏晉名士的参与而成为胜迹,山水记述中出现了较明显的慕古情绪,但寻古同样不是唐代山水游赏的主要风尚;宋代之后,士人们继承了魏晋隋唐时期的山水游赏传统,并逐渐出现了一种好古现象,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
二、人景合一:宋至明清名胜景观的形成
葛兆光在论述8—9世纪思想史时说,在那个时代“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秩序的建立,从由外向内的约束转向了由内向外的自觉,这样,关于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终极依据就从‘宇宙天地转向了‘心灵性情”,溯史寻根成为韩愈以及9世纪初的士人重新建立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他们在原有的传统中发掘着历史记忆,在这种历史记忆中,他们凸显着历史时间、地理空间和民族群体的认同感”[16]。刘成纪亦提到从中晚唐对儒家抱有危机感的士人到北宋理学,“将天的问题复归于人的问题,将人的问题进一步复归于心性问题,人的主体地位和心性之于人的本体地位借此得以双重确立”[17]。这一转变逐渐影响士人们的心灵和生活。宋代以后,士人们对“人”的兴趣尤为凸显。吉川幸次郎认为:“宋诗是对于人之世界具有浓厚兴趣的诗。或许正因为如此,宋诗对于吟咏自然,显得既不热心,又乏善可陈。宋代以前,在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些偏于描写自然,特别是咏叹自然之美的诗人。如六朝有谢灵运,唐朝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可是在宋朝,像这样的‘山水诗人已不存在了。”[18]宋代之后,士人们在景观寻访与游赏时,屡屡借助景观诉说对前贤心灵、志趣的认同与仰慕。“何以娱嘉客,潭水洗君心。老守厌簿书,先生罢函丈。风流魏晋间,谈笑羲皇上。”(《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苏轼诗集》第三册,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37页。)苏轼仕途波折,辗转多地,他将前贤作为精神寄托,写作了大量追和陶渊明的诗,杨治宜认为追和陶潜的田园诗让受孤独、文化疏离感和物质贫乏折磨的衰老诗人与直接环境拉开距离,撤入一片居住着熟悉的伦理典范的文化风景,帮助他从大量古圣先贤中遴选自己的密友[19]。苏轼追慕魏晋风流及和陶渊明的诗并非基于与先贤所处的同一片景观,而是基于相似的心灵、性情、志趣或际遇,寻找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
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庶族士大夫成为影响景观记述和传播的重要力量,各类地理著述成为汇集景观诗文及掌故的重要载体,地图学及印刷术的发展,为景观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助力。宋代地理书“于郡县建置沿革、人口、赋税、风俗、山川、古迹、人物的记载详细而丰富,人文倾向日益显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人文内容日多,地方成为各种人物、历史事件、诗文、胜迹的丰富集合,充满了各种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知识与故事”[20]。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自序“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则未见其书,此纪胜之编所以不得不作也”[21],相较于此前的舆地类著作,该书开始侧重于对“山川胜景”的记述,搜集保存了大量景观相关的历史和诗文。“纪胜”已成为南宋地理类书籍的重要内容,《方舆胜览》亦将各郡“山川”“楼阁”“亭榭”“佛寺”“道观”“古迹”“名宦”“人物”“题咏”等作为记述的重要内容[22]1。同时,金石学迅速发展,“宋代金石学家通过自己的著述,为古代碑刻和其他文化遗物的理解提供了基本的历史框架,从而鼓励了‘古迹文化的发展”[15]。在这样的背景下,碑刻成为纪念过去的重要手段,崇古现象及刻石技术的发展,许多著名景观通过石刻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并成为新的景观点。潘晟提到,因各种幽思而广泛流行的石刻地图,将幽思凝固在碑碣之中,地图将各种胜迹作为自己的绘制对象,成为文人览胜之帮助[23]。
基于士人们的历史兴趣、地理文献景观文化记述之详备及“古迹”文化的发展,士人们出游时常依据图籍访问前人故迹,杨万里“随牒倦游,登九凝,探禹穴,航南海,望罗浮,渡鳄溪,盖太史公、韩退之、柳子厚、苏东坡之车辙马迹,今皆略至其地”(杨万里《诚斋集》卷81《诚斋朝天续集序》,宋集珍本丛刊第55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81页。),余靖言“予尝恨游观山川皆前贤所称、图籍所著耳,未能索幽访异舆音马迹之外,得古人所遗绝境,一寓其目,状其名物,与好事者传之无穷也”(余靖《武溪集》卷1《游大峒山诗并序》,宋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182页。)。可见,随着山水景观的进一步开发,许多胜景都已有前人足迹,士人景观游赏以“访古”为主,以致余靖觉得颇失趣味,希望能“索幽访异”“得古人所遗绝境”。
宋代文献中,“名胜”一词仍多用来指人物。南宋时临安府尹袁韶请建三贤堂,以安放原孤山竹阁白居易、林逋、苏轼三像,咸淳《临安志》称“本府三贤堂实为尊礼名胜之所”(潜说友纂修,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卷32《山川十一·湖上》,道光十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版第330页。)。周必大《跋郑景望诗卷》称南宋文士郑伯熊“见谓儒宗,而其诗句乃绰有晋唐名胜之遗风,胸中所养亦可知矣”(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8《题跋》,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第256页。)。宋人刘学箕言:“古之所谓画士,皆一时名胜,涵泳经史,见识高明,襟度洒落,望之飘然。”(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论画》,见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可见,宋代用来指代人物的“名胜”往往是那些学问深博、诗文卓越、胸怀开阔之士。宋代文献中使用“名胜”一词时,也常强调人物与“景”的紧密关系。《吴郡志》载臞庵“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范成大《吴郡志》卷14《园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范村菊谱》言名胜之士的品性之一是“爱菊”:“故名胜之士未有不爱菊者,至陶渊明尤甚爱之,而菊名益重。”(范成大《范村菊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7页。)宋代“名胜”人物重品性,而人之“性”借景之“性”得以彰显。
虽然宋代“名胜”依然主要指人物,但已出现用来指代景物的“名胜”,胡宿《文恭集》载:“金陵(今南京)故都,绪余六代,华人夏士,盛栖此土,虽一丘一壑之细,皆经高贤名辈尝所留连。茅、许世外之风,王、谢江表之德,山林皋壤,号为名胜。”(胡宿《文恭集》卷35《高斋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924页。 )可见,能被称为“名胜”的景物,不仅在于景物之“胜”,更重要的是“高贤名辈尝所留连”的名人之“胜”。元代,《至正金陵新志》提到“集庆(今南京)一路,旧称三吴都会,实为名胜之邦。古今纪载山川景物、英雄忠义之士,不一而足”(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279页。)。这里的“名胜”,包括了山川景物和英雄人物,有“人”和“景”的双重含义。元明之际,范理《天台要览序》:“并手疏游览郡邑名胜,大略分为山水、人物、词翰三志,名之曰天台要览。”(《浙江通志》卷263《艺文五·天台要览序》,嵇曾筠等纂修,沈翼机等编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6册,第147页。)在范理看来,供人游览的郡邑“名胜”,其核心要素应包括山水、人物及词翰。
明清时期,“名胜”一词用来指景物已是常见现象。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观江淮名胜图》,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诗名为《观江淮名山图》(参见: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1页;李云逸注《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仍作《观江淮名山图》(高棅编纂《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卷10,汪宗尼校订,葛景春、胡永杰点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45页。),陆时雍选评《诗镜》则作《观江淮名胜图》[24],明铜活字版《唐五十家诗集》亦作《观江淮名胜图》[25],明代中晚期诗名中的“名山”已逐渐替为“名胜”,也可见当时作为“景物”之“名胜”用法的流行。个人名胜著作也陆续涌现,如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名胜”已成为表述知名景观的常用词汇。明清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版业繁荣,伴随着旅游休闲文化的发展,名胜图册、名胜志流行,进一步促进名胜文化的传播。当然,此时“名胜”仍可用来指名人,表达“学问之士”“文人风流”之意。明张丑《清河书画舫》载:“右唐韩干所画二马,今藏松江一士人家,后有米元章、王尧臣、薛绍彭、苏子由、秦少游诸名胜题名,及东坡翁绝句。”[26]清王士禛曾言:“余少时官广陵,与诸名胜修禊红桥。”(王士禛《香祖笔记》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
整体来说,自魏晋至明清,“人物”之“名胜”的具体语义,往往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思想状况及推崇的文化性格有关,什么样的名人被称为“名胜”,有契合某个时代、某个地域或某个群体的审美标准,但这些人物与山水、景物多是相关的。而“景物”之“名胜”,起源于魏晋名士与山水之间的相互作用,伴随着魏晋至唐宋怀古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宋至明清时期,“前贤”影响下的“胜迹”逐步发展为“景物”之“名胜”,人景合一的“名胜”景观成为士人游赏追寻的目标。
三、“前贤故迹”: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
(一)古代名胜景观传承中的“慕古”传统
叶朗提到,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理世界之外构建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意象是美的本体[27]。中国古代文人对待景观的态度是重意而不重形,他们除了对风景名胜自身展露的意致和情态的追求外,亦会重视景观所蕴含的情感、文化和精神内涵,充满了对往日的“人”和“事”的向往,即景观游赏中的“慕古”现象。明徐有贞《云岩雅集志》介绍他与友人重阳虎丘登高雅集,可谓一次代表性的慕古行为。徐有贞隐居故里,非湖山之游不出门,闭门却扫三年,终在重阳节令之时,与夏昶、杜琼等诗社老友一行七人前往虎丘,登云岩寺,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门,笑咏以登”,“凡台殿亭馆之有名者,必造焉”,行酒作诗,赏菊品茗,“寻勾吴之遗迹,吊阖闾之玄宫,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风”(陈暐编《吴中金石新编》卷8《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第211-212页。) ,诸人皆着古装,探寻前代遗迹,吟咏各处景观,穷尽一山之名胜,充分展现了文人景观游赏对古意的追求。
景观文化中的“慕古”,是以人及与人相关的故事为核心的传统。此处的人可以是文人、帝王、官员、将领、僧人、道人,或具有特殊事迹的普通人,即此处的人是名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这一文化特征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名人传统。历代文人屡屡提到“人”与“景”的关系,即“胜景”的生成须借助“人”的参与: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 (白居易《白蘋洲五亭记》,《白居易集笺校》卷71《碑记铭吟偈》,朱金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9页。);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柳宗元《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柳宗元集校注》卷27,尹占华、韩文奇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95页。); 山之有景,即山之峦洞所标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校注·鸡山志略一》,朱惠荣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3页。);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才觉重西湖(袁枚《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小仓山房诗文集》卷26,周本淳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4页。)。
名胜景觀的传承与传播,须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或政治人物为景观增色增名,讲述名人与景观的故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夸胜迹”(《四库全书总目》卷187《集部·总集类二·二程文集》,第1695页。)。欧阳修《岘山亭记》言:“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欧阳修全集》卷40《岘山亭记》,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88页。)岘山本是小山,因羊祜、杜预的缘故而成为名山。明人张岳《信芳亭记》称:“盖凡湖山以胜名,则必带林麓,穷岩壑,有宫室亭榭之观,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传,如杭之西湖,越之鉴湖,然后其名始盛,而游者踵至。”(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32,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13页。) 因有“高人逸士”的故事,胜景得以名盛而游者众。
名胜也成为文人怀古的对象和媒介,怀古一般是怀思前贤的足迹、作品和故事,通过眼前的景观完成与古人的对话。清朱轼《陕西通志序》:“若夫二华、太白、朱圉、鸟鼠、崆峒之嵯峨,泾渭、涝潏、江源、汉脉之洸漾,古先帝王贤圣陵墓,以及韦杜曲江、华严石鼓、辋川诸胜迹,莫不凭眺徙倚,悠然动怀古之思。而幽岸绝壑、穴居野处之民,垂老不覩长吏之面,闻使者至往往扶杖牵袂,相与逢迎,于秦碑汉篆之间,为道山川溪谷之迁变,指示古人居处、游历之处……”(《陕西通志》卷93《艺文》,刘於义等监修、沈青崖等编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6册,第465页。)作为官员和学者的朱轼视学三辅,采风秦地,探访古迹名胜,感怀当地先代帝王及名贤之迹,即使乡野村民也如数家珍般为他指引“古人居处、游历之处”,可见“前贤故迹”在士大夫生命体验及地方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历史时期地域和景观开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景观游赏的序列来看,魏晋名士是早期先贤的代表,他们游赏过的景观为唐代士人所关注并传播,唐代山水诗人又通过文字和足迹,成为他们参访过的景观文化序列中的重要人物,丰富了景观文化体系。中晚唐以后,随着科举制推行,读书人日益增多,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一些偏远州县,取得功名后因做官、游历、贬谪、致仕、隐居等原因又奔向各个地方,进一步促进包括偏远地区在内的地域文化景观的开发。葛晓音指出:“中晚唐内外官的迁转状况以及文学之士吏道观的改变,导致大历以后文人任州县官的人数大大增加”,郡斋官员通过赏景写诗打发闲暇时光[12]124。这些官员到地方上一般会构筑或修缮衙署,衙署往往选在当地自然风光较为优美的地方,多呈园林式,颇有幽趣。游历地方景观也是地方官员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景观游赏的过程中,他们总要将感受诉诸文字,甚至会参与地方景观的营建、修缮,并叙之以诗文。宋至明清的地方官员亦承续了这一传统。因此,唐宋之后,地方官系统的官员及栖居在地方上的士人通过其景观实践和诗文,成为诸多地方景观营建、传播、传承的重要力量,成为后世追溯的源流或典范,形成地方上的“名胜”。
随着知名士人对各地景观的品题和开拓,逐渐形成王朝中晚期名胜文化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白居易、苏轼、欧阳修等。凡是他们居留、品题或参与过的景观,在后世层累的景观叙述中,他们往往成为故事的主角,而景观也因之尤为胜迹。王思任言:“滁阳诸山,视吾家岩壑,不啻数坡垞耳。有欧苏二老足目其间,遂与海内争千古,岂非人哉!”(王思任《王季重十种·历游记·游丰乐醉翁亭记》,任远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苏轼被贬黄州,成为黄州景观文化史的标志性人物,“仕宦而至黄者,每艳称子瞻雪堂、元之竹楼”(宋荦《筠廊偶笔》卷下,蒋文仙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杭州孤山六一泉,因是“欧(阳修)、苏(轼)、惠勤之胜迹”,“故以泉名于湖”(《咸淳临安志》卷78《寺观四》,第751页。)。苏轼追和陶渊明,自認是开创了追和古人的先例,“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卷21,陈宏天、高秀芳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0页。),而苏轼则成为后世景观诗文的重要追和对象,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南巡,其在杭州的诗文,常借景观与苏轼对话,进行诗歌唱和(高晋等初编,萨载等续编,阿桂等合编《钦定南巡盛典》卷9、卷13、卷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8册,第178、245、317页。)。《御题西湖志纂》:“表里江湖秀丽区,由来名胜擅三吴,谁宜作志传明圣,老沈今时白与苏。”(沈德潜、梁诗正等《西湖志纂》卷首《御题西湖志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3年版第337页。)亦可见苏轼、白居易在江南名胜文化史中地位之显著。一般认为苏轼未曾去过五台山,但写过与五台山相关的诗文,元好问《台山杂咏》述五台山景物之盛,特意提及东坡未来之憾:“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1160页。)可见,宋以后,苏轼已成为文人景观世界的一个重要符号,与之对话,是后世士大夫景观游赏的一大趣味。当然,因前代名人居留和游览轨迹不同,各地景观文化之名人序列也有差异,陕西乃汉唐文化最集中的地方,陕西一带的地方志在进行景观叙述与考证时,常用杜甫等人的作品,如“杜曲在启夏门外,向西即少陵原也。杜甫诗曰:杜曲花光浓似酒”(《陕西通志》卷73《古迹第二·府第园林郊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5册,第408页。)。
帝王故事也是各地景观叙述中非常重要的类别,以增加景观的文化影响力与传奇色彩。高士奇陪同康熙帝登五台山西台挂月峰,追溯魏文帝故事,提到“上有小石浮图,其量千计,即是魏文帝宏所立,石上人马迹宛然如新,即其地也”(《扈从西巡日录》,第1160页。)。清代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巡幸各地,皆六巡江南,对各地景观多有品题,成为清中后期巡幸过的地方宣扬景观身份与地位的重要符号。佛、道景观本身,除了帝王、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外,也有其宗教内部的名人序列,名僧、名道是寺观名胜传承中的重要人物。明人周召《双桥随笔》言:“有洞天福地、佛祖道场、神仙窟宅之说,于是一峰一峦之秀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聚而游也,一岩一洞之奇,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托而栖也,不但为之艳其事,而且为之像其形,不但为之撰其名,而且为之立其传。”(周召《双桥随笔》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432页。)佛、道景观的名人故事因要突出宗教的神秘性,也附会一些神仙传说,如纯阳宫“即柴扉道院,在州旧城东南隅,相传吕仙遗迹”,“吕纯阳、郭尚竈常栖遅于此,明永乐中大宗伯胡濙受命访仙人张三丰,题诗崖壁,太守郑福邂逅吕仙,自是遂为名胜矣”(《陕西通志》卷29《祠祀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2册,第537页。)。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并非基于对景观物质形态的保护,尽管历史时期确实有对建筑的修缮和维护,但名胜景观能跨越历史长河流传至今,主要依赖于景观文化的传承。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构建筑,建筑周边景观规划多以植物、石头及水为主要元素,其物质形态很难长期保存,而景观文化却可以通过各类记述一直保存下来。后人对景观的重新复建,并非要恢复先贤时期景观的物质之“形”,更多是根据先贤故事和文献中的景观叙述,来复建描述或想象中的景观,表达慕古之情。欧阳修言岘山亭:“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欧阳修全集》卷40《岘山亭记》,第589页。)“自古胜迹之传,皆以人重贤,士大夫有足表见于当世,其生平游辙所止一堂一亭,偶然而为之者,虽阅千载,人常求其址于荒烟蔓草间,或踵而作焉,以存其旧。”(《徐州府志》卷18上《古迹考》,清同治十三年刊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本第511页。)士大夫游赏某处景观,并记之以诗文,大多是偶然为之,但因“人重贤”,即使过了上千年,人们还是愿意在“荒烟蔓草间”,寻找曾经记述的景观,并寻找机会进行恢复。
阿莱达·阿斯曼提到废墟和残留物可能很长时间都以不为人注意的瓦砾堆的形式存在着,并由此变得不起眼或看不到,一旦内行的眼睛撞见了可见的遗留物,过去的精神遗产便变得可触可感,脱胎换骨的重生借助一个回忆的媒介发生了[3]357-358。中国古代的许多景观遗产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以复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在办差途中经过凤翔,见“名胜岁久就堙,旧有湖亭及轼祠宇亦多倾圮”,“饬为重加葺治,灌莽既辟,清流莹然,蒲稗因依,榆柳映蔚,庶几昔贤遗迹复还旧观”,名贤故迹得以恢复(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17《大川附水利》,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8册,第679页。) 。宋荦《黄州宋贤祠记》记述了其任职黄州时宋贤祠的兴建过程:
余董漕自淮归,簿书多暇,念先贤故迹久就芜,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责也。始从坡里坊求墨池旧址,得之颓垣败础间。于是芟榛莽,剔朽壤,决淤涂,甃以文石,周以栏槛,俯视一匊,浏然泓然。池故无桥,今则跨池为桥,翼桥为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既而曰:“池复矣,无堂曷祠?”乃建堂池东,祠子瞻,以张文潜、秦少游配。两先生固尝游黄,又苏门士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余材,建楼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楼”。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楼非其地而仍之者,从名也,合之为“宋贤祠”(《筠廊偶笔》卷下,第33页。) 。
可见,黄州宋贤祠的修建不在于物质形态仍其原貌,更重要的是景观文化的传承。士人们在任官、寓居、游历某地或致仕、回乡之际,游历当地名胜、寻访前贤故迹,进而在有力量的时候复兴这些文化遗迹。虽历经世事变迁,可能会再次毁坏,但在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名胜传承模式。
(二)古代名胜景观传承中的“述古”传统
正如顾颉刚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一样,名胜的文化史也一直处于不断叠加和层累中,历代地方文献都在前人撰述基础上记载景观文化的传承脉络。后人游赏或记述名胜,注重考证名胜的历史,并以自己的记述或创作继续丰富名胜的文化史。这是中国古代景观文化中的“述古”传统。“述古”主要依赖于历代诗文、志书等文献传承和丰富。诗文影响广泛深远,志书类文献进行学术性梳理和总结,二者有效传播并保存了中国古代景观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中国地理及景观著述的历史非常悠久,至宋代《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开“纪胜”传统,此后历代志书,记录“山川”“古迹”等各类名胜事物已是常态。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提出“山川”“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等项应记其历史沿革、旧有事迹,若有碑文亦须收录,“古今名公诗篇记序之类,其有关于政教风俗、题咏山川者,并收录之。浮文不醇正者,勿录”(《莘县志》卷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宁波天一阁藏明正德原刻嘉靖增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5年影印本。)。此次颁布的修志凡例是各州府县地方志修撰的参考范例,有助于促进各地整理收集景观相关掌故、诗文,且地理志一般附有绘制重要地理事物和景观的地图,如地方名胜图。每次编修地方志都是地方上一次大型地理及景观实勘与考古的过程,后世修志又往往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从都城到地方,各种类型的名胜在修志过程中被梳理,形成完善的名胜记述体系。除了官方志书,大量景观志、文人文集、游记、其他私人地理著述、石刻及绘画作品等也保留并传播了景观文化信息,成为官方修志或后世追溯景观文化史的重要参考。
宋代地理文献已非常注重古迹名胜考证。《舆地纪胜》李埴序提到:“然则天下郡县山川之精华,是真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在图经类多疎略、舛讹,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学者参伍考正,而勒为成书,然后可据也。”[22]13清人李之鼎说宋人“每于一邑之古迹,一区之名胜,往往各为一绝,或自注题下,不仅可使溪壑增色,且裨后人言地志者为考证之一助”(李之鼎《跋》,见许尚《华亭百咏》,宋集珍本丛刊第65册,第401页。)。对于后世而言,名胜遗产的存留情况各异,皆须从历史文献中详加考证,撰书以记之,方能在文献体系中继续留存下来,以为后人参考,尽管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未必准确全面,却为后人继续调研与考证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古人胜游之迹见于文章篇什者,历历可考,变迁以来盖有名存而实亡,有有其處而名不可知者”(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载《元代地理方志》下卷, 黄山书社,2012年影印四库全书本第81-82页。),李好文《长安志图原序》详载编制过程:“及来陕右,由潼关而西至长安,所过山川城邑或遇古迹必加询访。尝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故汉城,临渭水而归。数十里中举目萧然、瓦砾蔽野、荒基坏堞,莫可得究,稽诸地志徒见其名,终亦不敢质其所处。因求昔所见之图,久乃得之,于是取志所载宫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识了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长安志图》,第9页。)明吴之鲸撰《武林梵志》因“杭州梵刹盛于南宋,至明而残废者多,恐遗迹渐湮”,“乃博考乘牒,分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诸属县,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俱详志创置始末”(《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地理类三·武林梵志十二卷》,第621页。)。这些努力考证、勘察前人遗迹,记之以文、绘之以图、述之以册的做法,是古代士人寻古、探古、怀古、考古的成果,既保存了名胜的文化脉络,也为后世考察遗产位置,对遗产进行恢复提供了文献依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两江总督萨载、江苏巡抚杨魁奏言:“窃臣萨载于上年查勘栖霞工程,行至千佛岭以东,见石壁所刻隶书‘白乳泉试茶亭六字。臣等考之《江宁府志》,摄山中峰上天开岩为明征君故宅,宅后有白乳泉。又检阅明人盛时泰《摄山志》,白乳泉在栖霞寺千佛岭下,昔有伐木,见石壁上刻隶书六字曰‘白乳泉试茶亭,不知得名所自。又考唐人皇甫冉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黄居中有试茶亭诗,复阅盛时泰金陵泉品有‘白乳泉赞。是白乳泉之名,由来已久。今于其地构数椽,恭恳圣驾临幸栖霞时,顺道片时憩息,俾前人陈迹得邀睿览,山泽生辉,荣幸无极。”(《钦定南巡盛典》卷82《名胜》,第307页。)萨载偶见山上石刻六字,即考于《江宁府志》《摄山志》等历史文献,系统梳理“白乳泉”一景的文化史,根据相关文化故事,重新构置建筑,这也正是多数地方官员恢复或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做法。《日下旧闻考》载“燕京八景”之“金台夕照”,称“舆地名胜志云:在府东南十六里。又有小金台,相去一里。今朝阳门东南岿然土阜,好事者即以实之。所传古迹,大率类是”(于敏中主编《日下旧闻考》卷8《形胜·御制燕山八景诗叠旧作韵》,瞿宣颖、左笑鸿、于杰点校,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119页。 )。可见,名胜类志书成为后世寻找古迹遗产的重要参照,土阜未必真是小金台,但好事者愿意做此联想,这种现象成为许多古迹复建及被后世反复考证的原因之一。文献在记述或考证景观源流时也可能存在讹误,并可能造成后世错误地点的景观复建,然而这也成为古代景观文化史的一部分。
四、结语
魏晋之前,虽然已经有对高山流水的歌咏,但因技术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很少有人可以走进山林,人们对大自然更多是敬畏之情,山林充满神秘色彩。魏晋之后,山林逐渐得到开发,士人们开始惬意地欣赏山水自然之美,山水寻幽成为一种风尚,有了魏晋至隋唐山水审美的基础,许多景观故事得以流传,宋元以后“访古”才成为可能。山水景观从最初的神秘或仙道色彩走向“自然”再到“自然”与“人文”相结合,成为名胜。晚唐及宋之后科举的兴起,接受过丰富的知识性训练的庶族士大夫走上政治舞台,这些士人携带着他们积累的关于“往日”的知识,走向全国各地,也走进了各地的风景里,通过他们的文字、知识及实践为地方风景的发现与传承、地方名胜的开拓和形成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名胜”一词最初用来指那些喜爱交游的名流、名士,早期名士在交游的过程中常常与山水景物相接触,这也成就了名胜此后为人们熟知的含义,即经过名贤们游赏或品题过的山川胜景。魏晋以来,名士们寄情山水,以宣示其心性,表达其抱负,这一做法影响了此后历代文人士大夫。携三五好友,游赏名胜,成为古代士人重要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古代,名胜作为自然与人类共同的作品,其传承与中国古史一样,具有层累的特征,景观到名胜的过程往往叠加了很多名人故事和传说。这类故事的叠加,往往由各类地志、景观文献和诗文来完成,这种一代代的文化累积塑造了名胜景观的意义。
与一般的视觉作品不一样,名胜没有固定的作者,而是多个不同作者对其的书写,其作品创作的年代纵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创作方式多样,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所表达的丰富内涵并非某一作者所能控制和把握,却给予后世观者一些“共享的意义”。可能许多人都曾尝试在同一名胜上进行书写,但最容易保存也最利于传承的往往是那些名人的书写,并通过文献或诗文的方式,为后人谨记并时时提起,不断转述于后世的文献中。后世的士人,热衷于根据这些文献或诗文的记载, 回溯和考证名胜景观的历史文化, 寻觅和考察前贤足迹曾至的地方,并通过诗文等形式,与古代名士对话,表达一种怀古之思,一种身份认同,一种跨越百年或千年的文化共鸣。
名胜的物质形态在历史的荒烟中往往会慢慢消失,但后世的士人们总会根据各类记述在有力量的时候进行文化景观的复兴,呈现为一种“屡废、屡兴”的模式。景观和建筑的重构常常注重文化史的考证,重新恢复的景观并不追求与往日物质形态完全一致,更重视的是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WYLIE J.Landscap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7:1-10.
[2]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5.
[3]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 鲁西奇.空间的历史与历史的空间[J].澳门理工学报,2021(1):11-13.
[5]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1-13.
[6] 曾繁仁.美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4.
[7] 米歇尔·柯南.穿越岩石景观:贝尔纳·拉絮斯的景观言说方式[M].赵红梅,李悦盈,译.刘珂兰,陈李波,校.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5.
[8]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6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742.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912.
[10] 刘成纪.地理·地图·山水:中国美学空间呈现模式的递变[J].文艺争鸣,2020(6):64-77.
[11] 林文月.山水与古典[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6.
[12] 葛晓音.山水·审美·理趣[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
[13] 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2-33.
[14] 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M].梅枚,肖铁,施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5,77.
[15] 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时间、历史和记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41.
[16]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116,117,124.
[17] 刘成纪.论中国中古美学的“天人之际”(下)[J].文艺研究,2021(2):29-45.
[18] 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M].3版.郑清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58.
[19] 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91,194,197.
[20] 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07,411.
[21] 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19.
[22] 祝穆.方舆胜览[M].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23] 潘晟.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86-88.
[24] 陆时雍.詩镜[M].任文京,赵东岚,点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552.
[25] 唐五十家诗集(明铜活字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60.
[26] 张丑.清河书画舫[M].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93.
[27]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5.
The gener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scenic spots
HE Feng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Beijing 100048,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scenic spots(Mingsheng)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moving from natural landscape to the famous landscape. The famous landscape embodies extremel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symbiosis of nature and huma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countless literati and celebrities. “Mingsheng” originally referred to “characters”, often featuring features such as socializing, appreciating scenery,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They belong to the group of celebrities and are often related to landscape and scenic tours. “Mingsheng” of “scenery”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mous scholar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mountains and waters. With the further fermentation of nostalgia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mountain and water landscapes gradually became well-known landscapes du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Mingsheng” characters. During the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ll-known landscap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edecessors” developed into “Mingsheng” of scenery.“Mingsheng” has a dual meaning of “people” and “scenery”. “Mingsheng” that combines people and scenery became the goal pursued by literati during their travels. The inheritance of ancient Chinese scenic spots and landscapes reflects the tradition of “admiring and narrating the past” in ancient landscape culture. This is a tradition centered around people and stories related to them,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inheritance of landscape culture based on “celebrities” and “literature”, with a layered feature.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f ancient landscapes has been effectively disseminated and preserved through literature such as poetry, literature, and Geographical Records throughout history. Literati often trace the history and related figures of famous scenic spots based on past poems or historical records, and continue to enrich the cultural history through their own creations or descriptions.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also verifies and records the inheritance of landscape culture based on previous writings, forming a rich system of landscape description. This inheritance model has influenced the revival of the material form of ancient scenic spo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heritage. Many ancient Chinese buildings were made of wooden structures, and their material form was difficult to preserve for a long tim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landscapes in ancient times did not aim to completely restore the material “form” of the landscape from the past, but rather to conduct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landscape descriptions in the poet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past, reconstruct the described or imagined landscapes, express admiration, and inherit landscape culture.
Key words:scenic spots(Mingsheng); landscape culture; celebrities; documents
(责任编辑 周 沫)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西山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研究”(20LSA002);首都师范大学2020年度美育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何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博士,Email:hefeng95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