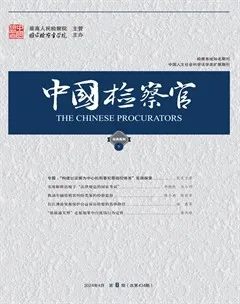“两卡”网络诈骗案件中帮助行为主观明知的级层化证明思路
谢文翼 高叶 向柯翰

摘 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帮助行为所涉帮信罪、掩隐罪、上游共犯三种罪名的主观明知之证明,应建立级层化的证明框架。以“犯罪行为客观存在”为第一层次帮信罪的明知,在此基础上若能吻合“在犯罪既遂后对资金性质明知”则上升到第二层次掩隐罪的明知,再若还能符合“在犯罪既遂前对共同性明知”则上升到第三层次上游共犯的明知。在具体证明思路上,对于帮信罪的明知若无直接证据则可以推定明知条款为核心进行证据搜集,对于第二层次掩隐罪的明知可以行为的“异常性”为方向结合推定条款进行证据收集,对于第三层次的共同犯罪,可以从一般共犯与片面共犯两种角度进行证据收集。
关键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共同犯罪 犯罪主观要件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两卡”犯罪帮助行为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以及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以下简称“上游共犯”)三罪的主观“明知”要素上的区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处理[1],导致了“明知”标准模糊化、证明思路混杂化的问题。[2]要解决“两卡”犯罪中所涉三类罪名主观要件的证明问题,就应从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中总结基本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解决思路。
(一)参考案例
[案例一]陈某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2022年7月13日至8月26日,陈某谊明知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仍将自己名下在本市某某区某某支行办理的交通银行卡及工商银行卡出借他人使用并进行转账操作。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陈某谊帮助不法分子转账时上游犯罪已既遂和其明知是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陈某谊构成帮信罪而非掩隐罪。[3]
[案例二]沈某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2021年6月,沈某某等人在上海市青浦区多处公寓据点非法从事跑分业务,使用沈某某2张银行卡、“卡头”王某某及其招揽而来的 “卡农”银行卡、支付宝或微信等支付账户用于收取、转移多人被骗资金。后在取保候审期间再次伙同他人进行跑分。法院认为沈某某与负责与上头对接的杨某某构成掩隐犯罪,而其余人构成帮信犯罪。[4]
[案例三]陈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2020年12月份左右,李某甲、李某乙组织陈某使用银行卡转移犯罪所得。陈某提供了自己的三张银行卡,并频繁将不同账户内的钱款转移到特定账户或者通过购买虚拟货币等方式参与转账,并通过李某甲等与上线组建的聊天群记对账。2021年2月20日,李某甲等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陈某仍旧组织他人使用银行卡转移犯罪所得,负责和上线联系、记账和找转账地点、接人。法院认为陈某转账、套现的“手续费”具有高度异常性,以此认定其构成掩隐犯罪。[5]
[案例四]李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2021年3月至11月间,被告人李某陆续购买大量未实名注册的手机卡,又安排王某、陈某等人对手机卡进行实名认证后注册微信账号,之后李某将采用前述方式获得的100余个微信账号以每个人民币170元出售给他人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致一名相关人员向虚假赌博网站投注,被电信诈骗受损100余万元。法院以李某交易行为的异常性为基础,认定其构成帮信犯罪。[6]
(二)司法活动中证明工作的基本特征与借鉴价值
1.对帮信罪与掩隐罪主观要素的区分呈现模块化与层次化特征
在案例一中,法院指出帮信罪的明知对象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存在,掩隐罪的明知则是知道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本案中的被告人虽明知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存在,但并不明知所涉金额属于犯罪所得,故被告人不构成掩隐犯罪。案例二中,法院指出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犯罪,其所经手的资金应系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仍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跑分”,构成掩隐犯罪。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仅向他人出租、出售银行卡用于“跑分”的,构成帮信犯罪,并以此对不同被告人区别定性。
可以看出,帮信罪与掩隐罪在“网络犯罪行为存在”这一点上具备相同之处。而掩隐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另有在犯罪既遂后对卡内资金性质的明知。这一观点也符合2020年12月21日“两高一部”《关于深入推进“断卡”行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中第5点将帮信罪“情节严重”定义为“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30万元,其中查证3000元系诈骗资金”,而掩隐罪则不存在对一般流水的规定,仅要求系犯罪所得或者掩隐次数达标。因此,掩隐罪的明知等同于帮信罪的明知加上行为人对犯罪既遂后资金性质的明知。这样的处理和区分方式体现出一种模块化、级层化的特征,能够指导司法实践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证据收集。
2.“异常性”证据和推定条款的积极运用
以掩隐罪为例,司法机关在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上较为强调对资金流动、交易方式、行为“异常性”的判断参考。[7]例如案例三中,法院就以行为人实施转账、套现等手续费的“异常性”为基础认定了明知。而在帮信犯罪里,案例四中法院對“异常性”证据的组合使用也是认定帮信罪明知要件的主要方法。
“异常性”的证明标准具备相关的法律依据。2019年10月“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帮信解释》)第11条第(三)(五)项规定,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督或者规避调查的可以明知认定。2009年11月最高法《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掩隐解释》)第1条第(二)到(五)项也指出,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转移财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收购财物、协助转换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价手续费、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在不同账户间频繁转划的,可以认定明知。
上述案件中在难以通过直接证据证明明知的前提下采用的以推定明知条款指导侦查并综合认定明知的方式,可以成为今后“两卡”犯罪中对主观“明知”证据收集的指导。
二、级层化证明框架的构建
我国的司法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以推定条款为指导的取证方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仍旧较为简陋和不成体系。例如,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明知认定虽存在一定的级层特征但尚不十分明确,上游共犯的明知也并未被纳入这一体系,且“异常性”证据在具体的适用方式上也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应当针对帮信罪、掩隐罪和上游共犯的明知构建级层化、模块化的判断框架,并针对不同级层、模块的明知要件提出具体的证明方法,从而扫清“两卡”案件帮助行为主观要件的认定窘境,规范司法实践的证据适用。
(一)对上游共犯主观要件的理论解构
要针对上游共犯、掩隐罪和帮信罪主观明知要件建立判断框架,具体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要成立上游共犯,行为人应当在主观要素上达成何种内容,二是如何将司法实践中级层化的区分思路运用到共同犯罪的明知要素中。
1.上游共犯主观要件具体内涵之释明
最高检在2018年发布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二部分第五款关于犯罪事前通谋审查中指出,对于共同犯罪也包括无共谋但明知他人实施犯罪提供帮助的情况。对于帮助者明知的内容和程度,并不要求其明知被帮助者实施诈骗行为的具体细节,其只要认识到对方实施诈骗犯罪即可。《指引》一方面强调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对犯罪存在的明知和帮助意志,另一方面并不要求行为人对上游犯罪具体细节进行了解,甚至并不要求行为人与上线犯罪者存在意思交流。从这一论述来看,《指引》采取了部分共同说的观点。
一方面,在认识因素上,不需要二人以上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只要行为人具有和他人共同实施行为的意思即可,即使二人的犯罪故意不同也不阻却共犯的成立。另一方面,虽不用和上游犯罪者的犯罪故意完全相同,但是也要求行为人明知行为的“共同性”与“犯罪性”,所谓“共同性”即是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前对自己和他人存在共同、分工、帮助的认识,所谓“犯罪性”即是对犯罪行为客观存在的认识。[8]
2.对上游共犯主观要素的模块化与级层化处理
首先,正如前文所举案例一、案例二法院的说理,掩隐罪与帮信罪在主观明知层面具有共通之处。而对上游共犯、掩隐罪和帮信罪三者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意志因素有所不同,但是其认识因素上具有共通性,即均有对犯罪行为客观存在的明知。掩隐则是在这基础上增设了在犯罪既遂后对获利性质的明知,共犯则是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在犯罪既遂前对行为“共同性”的明知。[9]
其次,分析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可以发现,掩隐罪与帮信罪在法律条文设定中均存在“实施本罪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处罚较重的定罪处罚”的规定,而帮信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掩隐罪则为7年以下,相较于帮信更高一级层。而对于上游共犯而言,以诈骗为例,诈骗罪最高法定刑为10年,明显高于掩隐罪和帮信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帮信罪还是掩隐罪,均存在“若有事前通谋就以共犯论”的规定,而“事前通谋”可以说是高精度地证明了行为人对“共同性”与“犯罪性”的明知。实际上,从立法原意上来看,帮信罪的设立是因为对于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往往无法查证共同故意,无法适用共同犯罪处理,才设立帮信加以处罚。[10]而对于掩隐犯罪而言,该罪同样是针对相关上游网络犯罪事后赃物处理的共犯认定不足而予以“兜底”性质的立法。[11]
最后,分析行为人主观认识可以发现,三者在主观认识难度上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在一般犯罪中,行为人对于帮信罪的明知是最容易也是最先达成的,无论是上游共犯还是掩隐罪的明知,都需要首先知晓上游犯罪客观存在,帮信罪的明知是后两者成立的基础。而相较于必须限定在犯罪既遂前,而且要求对行为“共同性”明知的上游共犯,在犯罪既遂后仅要求知晓资金性质即可的掩隐罪明知更加容易判断。需要指出的是,若掩隐的明知发生在犯罪既遂前,此时若足以明知“共同性”,则以上游共犯论处,若不足以达成共犯的明知,则以帮信罪处理,故掩隐的明知实际上是介入在帮信与共犯明知中间的。至此,可以发现三者的主观认识在证明难度和包容性上表现出一种以“帮信罪、掩隐罪、上游共犯”为顺序的层层递进、上层包容下层的逻辑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将上游共犯的明知解构为“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客观存在具备明知”和“行为人在犯罪既遂前对自己与他人的共同性存在明知”两个模块。而在级层设定上,应当高于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明知,这种处理方式也符合行为人的一般认识逻辑和法律适用规定。
(二)级层化判断框架的搭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以帮信罪、掩隐罪、上游共犯为基本顺序,建立级层化判断框架:
以帮信罪作为第一级层,考量“对犯罪行为客观存在的明知”这一模块,以掩隐罪作为第二级层,考察“犯罪既遂后对资金性质明知”这一模块,以上游共犯作为第三级层,考量“犯罪既遂前对共同性明知”这一模块。其中在判断完第一级层后,即使不符合第二级层中“资金性质的明知”模块,也应当考量第三级层中“共同性”的明知。在这种级层思路的指导下,也更能清晰地说明前文案例中法院的认定原理。
三、级层化判断框架中具体模块的证明方法
前文将帮信罪、掩隐罪和上游共犯的主观要素进行了模块化,并创设了级层化的判断框架。在此逻辑框架下,證据的收集审查就可以模块为中心进行组合考察。
(一)“对犯罪行为现实存在的明知”模块的具体证明思路
1.以“明知”推定条款为取证方向
《帮信解释》第11条第3、5款的规定应当着重考察行为人在上网方式、交易价格、虚假身份、逃避监管等客观表现上的异常性,从而综合推定行为人的明知,前文所举案例四中的法院便对交易活动的“异常”进行了具体认定。实际上,除了前述规定的情形外,其他条款也均可以作为证据收集的指导。例如本条第1、2款规定的告知、举报一般均在政府、相关机关单位的后台留有数据,行为人自身也无法消除,取证较为容易。除此之外,第4款的适用也较为重要,其规定为“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主要是针对“并非社会正常活动所需,而系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专门服务”的活动。[12]对于此类在规范意义上已经存在禁止性规定,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存在的某些特定的提供行为,若满足“非正常生活所需,并专为违法犯罪而生”的标准,则也可以使用第4款的规定推定明知。
综上所述,对于帮信罪明知模块的证明,在没有直接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可以《帮信解释》第11条各款的规定为指导,集中进行证据收集。
2.对推定条款适用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活动在符合《帮信解释》中某一款的情况下,往往还采取了其他足以证明“异常性”的要素进行补强,例如在前文所举案例三、案例四中,法院均是在证明其中一种推定条款的情况下,结合了其他能够进行相互印证、强化证明力的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对推定条款的适用进行限缩,一是不能仅符合《帮信解释》第11条中其中一款就直接予以推定,而应当在此基础上强调其他要素的综合性认定,二是对推定条款的适用必须建立在穷尽直接证据彻底无法证明的前提下,以恪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二)“对资金性质的明知”模块的证明思路
参考前文所举案例二、案例三的处理方式,对于掩隐罪中“对资金性质的明知”模块的证明思路则应当强调对资金流动、提示警告、行为方式等诸多因素“异常性”的考察。对于“异常性”的理解,一方面可以参考《掩隐解释》中“没有正当理由”的规定,主要考察针对于大额、大宗转账,畸高、畸低买入卖出行为,巨额现金散存等行为中行为人的辩解是否符合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逻辑,是否具有合法事由,能否在客观上加以印证等。另一方面可以参考金融机构的警示通知或者其他规范文件、国家反诈app短信信息等发送情况和银行交易、流水、转账时间、次数等能否与其他同案犯或者其他涉案财物相互印证。
另外,对于掩隐罪中推定条款的适用,一方面也应当受到如同帮信推定条款一样的限制,在符合其中一款的情况下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另一方面,应当将第二级层的明知产生时间严格限制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掩隐犯罪针对的行为是犯罪行为结束后对非法获利进行隐瞒、切割联系的行为,核心在于事后隐瞒。[13]关于这一点,前文所举案例一中的法院也提出了“帮助不法分子转账时上游犯罪已既遂”的要求。若这种明知产生在犯罪尚未既遂、非法获利尚未产生之前,则要么以上游共犯论、要么以帮信罪论。
(三)“对共同性的明知”模块的证明思路
对上游犯罪共犯中“共同性明知”证明的问题,应当以是否具备“事前联系”为标准区别为“事前共谋”和“片面共谋”,也就是一般共犯和片面共犯。而因“事前联系”形式标准的有无,对一般共犯和片面共犯中“共同性明知”的证明要求也不同。
1.一般共犯中“共同性明知”的证明
一般共犯要求“事前共谋”的存在,要求二人以上为了实施特定犯罪行为,以将各自的意思付诸实现为内容进行策划谋议,或者说各犯人就何种犯罪以及犯罪的目标、方法、时间进行了策划、商议。[14]行为人只需要在实施犯罪上具有共同故意即可,而进行的谋划商议也不需要完全知晓犯罪的全部细节,只需要针对犯罪行为存在分工、商量即可,即使仅透露商议了整体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只要这种沟通商议行为存在,且行为人具有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故意,则符合“事前共谋”的认定。
故对于一般共犯而言,一方面需要判断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者之间是否就犯罪的具体内容进行过联系沟通,另一方面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对犯罪行为客观存在、自身与他人之间的辅助分工或其他共同关系以及自身在整体犯罪中所起到的价值地位存在明知。级层判断思路中,则应当组合现有证据,一方面证明行为人知晓自己与他人实施犯罪行为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证明行为人对自己犯罪行为在他人犯罪行为中地位、价值存在明知。
2.片面共犯中“共同性明知”的证明
《指引》第二部分第五款认为,虽无共谋但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的情况,也应当认定为共犯。由此看来《指引》认可了片面共犯的存在,并认为此种行为应当以共犯定罪处罚。故有必要将片面共犯纳入“两卡”犯罪中共犯的成立范围。[15]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信罪之前,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单方明知的信息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几乎全部能够以被帮助的网络犯罪的共犯论处。[16]
片面的幫助,即正犯者没有认识到另一方对自己的帮助行为,但帮助者知道自己在帮助正犯实施构成要件行为。[17]片面共犯与一般共犯的区别在于缺乏“联系沟通”的形式,其并不存在双方行为人之间的交流合意,仅存在一方对于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认识,故有必要对片面共犯中“共同性明知”进行单独判断。
首先,片面共犯的明知应当在具体罪名上与上游犯罪一致。与前述一般共犯不同,上游的犯罪分子并不知道自己与行为人之间的共同关系,也并未与行为人进行谋划,并未就共同实施某一犯罪行为达成合意。[18]故对于片面共犯应当要求行为人准确地知晓上游犯罪所触犯的具体罪名,因为若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者对于行为罪名的认识不一致,加之二者之间并未对实施犯罪达成合意,那么行为人单方的帮助行为也就很难被评价为“帮助者知道自己在帮助正犯事实构成要件行为”。
其次,片面共犯中的行为人应当对上游犯罪的基本流程、行为模式具备明知。因为在片面共犯中帮助的犯意是行为人单方产生的,上游犯罪者不可能通过联系沟通帮助行为人知晓共同关系,故仅有在行为人原本就对上游犯罪的基本流程、行为模式具备明知的情况下,才可能了解与上游犯罪者之间的分工、共同、辅助关系以及自身在整体犯罪中的价值。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片面共犯中同样不需要行为人知晓上游犯罪的所有细节,只需要对犯罪性质、犯罪流程和模式具备明知即可。例如在提供信用卡型帮助行为中,在没有交流合意的情况下,行为人要成立片面共犯,则需要知晓上游在实施电信诈骗行为和上游诈骗犯罪的基本流程和行为模式,例如何时诈骗、取现、使用自己的信用卡等。而对于上游诈骗犯罪的具体细节,例如何人实施诈骗、采用何种理由实施诈骗、信用卡转账的钱将被用于何处等细节则并不需要明知。
故对于不具备“沟通联系”形式特征的“共同性明知”模块,应当考量如下内容:(1)行为人是否明知上游犯罪的具体罪名(2)行为人是否对上游犯罪的基本流程具备明知(3)行为人是否对上游犯罪的基本行为模式存在明知。
3.对“共同性明知”模块的阶段限制
我国并不存在事后共犯的問题,若行为人在上游犯罪结束后才与犯罪分子共谋,为其犯罪所得进行掩饰隐瞒,就不能以上游犯罪的共犯定罪处罚,而应当以掩隐罪定罪处罚。《指引》第二部分第五款也明确提及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应当在犯罪行为既遂之前。
四、结语
本文围绕“两卡”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帮助行为主观要件的认定困境,针对帮信罪、掩隐罪和上游共犯主观要件的区别与证明提出了级层化的判断框架,并将三罪复杂的主观要素模块化,从而对司法实践认定区分“两卡”相关罪名的活动进行指导,也为相关罪名的证据收集提供了基本引导。但不可忽视的是,级层化判断框架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补全和完善。
一方面,“级层化”判断逻辑框架仍旧停留在学理构架上,其对于证据的收集仅能提供方向性的指导,而对于证据具体内容、证明标准的把控仍旧会给司法者带来较大负担。另一方面,本文的探讨仅止步于相关犯罪的构成与否,如何把握入罪后处罚幅度的均衡,还有待于司法者进一步的研究。[19]
* 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一级主任科员[610213]
** 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610213]
***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201620]
[1] 参见曹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的异化与归正》,《青少年犯罪问题》2023年第3期。
[2] 参见莫洪宪、吕行:《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3] 参见《陈某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人民法院报》2023年12月14日。
[4]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2)沪02刑终607号。
[5] 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2)豫08刑终50号。
[6] 参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2)沪0106刑初118号。
[7] 参见李立众编:《刑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791页。
[8]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34页。
[9] 在网络犯罪语境下,帮信犯罪行为人与被帮助的对象(一般是上游犯罪的正犯或实行犯)之间往往缺少双向意思联络更不存在事先通谋,在实施犯罪前基本上没有接触互不认识。参见王聚涛:《准确把握涉“两卡”犯罪的罪名和罪数》,《检察日报》2023年4月26日。
[10] 参见喻海松:《网络犯罪二十讲》,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11] 参见赵拥军:《“断卡”行动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及其从犯的认定与限制》,《人民法院报》2023年3月16日。
[12] 参见喻海松:《网络犯罪黑灰产业链的样态与规制》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13] 参见谢栋、陈月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定性争议》,《人民法院报》2021年10月21日。
[14] 参见单成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共犯明知的认定》 ,《中国检察官》2022年第9期。
[15] 参见闫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技术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6期。
[16] 参见欧阳本祺、刘梦:《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方法:从本罪优先到共犯优先》,《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1期。
[17] 同前注[8] ,第597页。
[18] 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19] 参见喻海松:《涉非典型“两卡”案如何实现罚当其罪》,《检察日报》202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