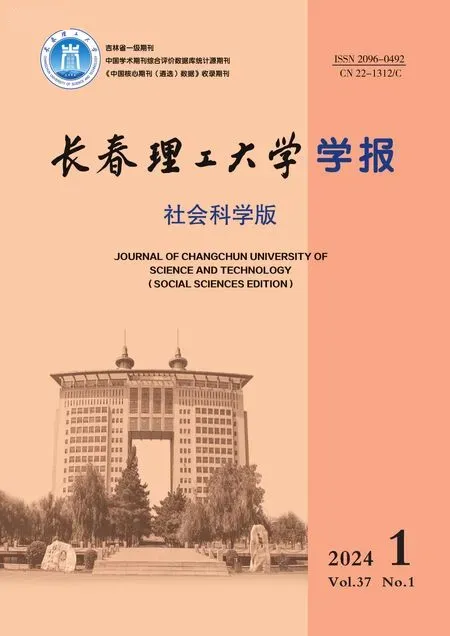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阐释学考察与重塑
杨德敏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德国刑法学者约亨·本克(Prof.Dr.Jochen Bung)教授认为当今刑法的五个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罪责的解释不清楚[1]。作为罪责的构成性要素,期待可能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重大,这在国内外已达成共识。但是其在德日和国内的争议,主要来源于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模糊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面临被滥用的危险,破坏法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在当下中国,期待可能性应当作为功能主义刑法观的义务规范边界,以限制一般预防目的的过度追求,限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审慎把握价值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尺度,规范法官的裁断权。因此,认真对待期待可能性,必然要明确期待可能性弱失的判断标准。
一、理论基础与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刑法理论界,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有行为人标准说,平均人标准说和国家规范标准说。马克昌教授、陈兴良教授、周光权教授等赞同行为人标准说①关于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理论观点及其评价,参见:马克昌.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5-11;陈兴良.本体法学[M].北京:商务书馆,2001:312;陈兴良.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J].法律科学,2006(3):72-81;谢望原,邹兵.论期待可能性之判断[J].法学家,2008(3):32-40;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秉承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初心,认为期待可能性在德国的产生就是立足于对人性弱点的关怀,且现代社会的责任是个人的责任,应当站在行为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虑其做出合法行为的选择能力,从而使归责更合乎情理。但是行为人标准说要回应行为人视角衍生的主观性与可信任性问题。因此随着责任认定的客观化趋势,平均人标准曾一度获得认同,并在日本获得通说地位[2]。另外还有学者给出了折中型或混合型标准,如以平均人为基础的类型人标准说,即以限缩的平均人为参照来判断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3]。还有学者从期待可能性的有无与强弱对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作出了区分,如有学者主张期待可能性是否阻却责任即有无的判断,应当兼采国家标准和平均人标准;是否减轻责任即程度的判断,应采用行为人标准[4]。当下刑法学界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仍然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标准,而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规范评价,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必然会影响期待可能性的理论价值,导致其实践功能不彰。此外,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要求遵从行为人的实践经验而予以规范性评价,所以应当是事实与规范的统一,而前述三种标准都是在二元分立的类型化思维之下所给出的相对片面的、具有先验性的判断标准。近年来,张明楷教授认为不应当将三个标准进行绝对分立,因为不同的标准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而应该“站在法益保护的立场,根据行为人当时的身体、心理条件等,通过和具有行为人特性的其他多数人进行比较,来判断能不能期待行为人在行为发生时通过发挥自己的能力不实施违法行为”[5]。这一主张彰显出判断标准的整体性思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以阐释学的方法“回到事情本身(zur sache selbst)”,即回到事实的本身分析此在行为时的存在样态,回到理论的本身分析期待可能性的正当性依据,尝试理解个体以及人类整个生存经验。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情境,每个人意识里的“正当性”与“可能性”就不同。因此,尝试理解行为人,如实地描绘出现在我们意识中的现象,立足于不法行为的原初样态,从期待可能性的原初意义把握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达成法学理论与哲学理论的智识互构。
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的学说论争
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目前在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
第一种是行为人标准说。这种标准主张期待可能性的有无应该以行为发生时的具体状况下的行为人的自身能力为标准。如果在行为时的具体情境下,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表明不具备期待可能性,因此也就不能谴责行为人。这是以行为人的视角来进行客观判断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第二种是平均人的标准说。这种学说将抽象的平均人置于行为人的状态下,如果平均人具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那么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就是值得谴责的。这种学说,是为了克服以行为人单一的视角判断期待可能性有无可能带来的狭隘和对法律秩序破坏的风险。但是这种学说以平均人视角替代行为人的视角,以抽象的理性人评判具象的行为人,存在事实与规范的断裂,存在“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同时这也违背了责任的个别化判断的要求。
第三种是法规范标准说,这种标准是站在国家或国家法律秩序的角度作出的具体要求。这种立场本身就已经背离了期待可能性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难以保证针对行为人的人性弱点而给予法律上救济和宽宥。究竟在什么场合下,国家或法律秩序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这种法规范标准说实际上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标准。
上述三种观点都是有各自的立足点,但是也都有各自的缺陷。三种标准学说都是基于一种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元思维下的判断。从生活实践整体来看,三种标准将行为人与社会群体以及政治权力进行了割裂。从每一种具体标准来看,行为人标准是将行为人主体与所处的关系向度进行了分立,平均人标准是将普通人与行为人进行了二元分立,法规范标准是将国家与行为人进行了分立。这种主客二元式的一阶思维是将除己身之外的存在都对象化的思维方式,所以强调分类视角的非此即彼,将主客观事实单一面化和理想化,其自身是具有局限性的。这种思维方式只能看到特定空间下的当下和在场因素,而忽视了当时当地不在场但是具有关联性、影响力的其他因素。只看到了此在的存在者,没有看到存在,最后陷入理想化的自我建构和自我辩护之中。在20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对法律的严密逻辑推理和形式理性主导下的司法产生了普遍怀疑,认为人的理性认知的有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实践是由多元的互动所决定和产生的。因此绝对的主客二元是一种理想的超验的存在。这种后现代的哲学思潮都是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为基础的。伽达默尔认为单纯的科学实证的方法并不能获取真理,尤其是对于人文学科,阐释学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
期待可能性是在形式逻辑理性边缘探索规范性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无法脱离人类现实的整体所衍生的应然要求。法律责任是个人的责任,但是责任的确认需要通过他人的归责来实现。所以期待可能性就是要将目光游离于行为人与他人之间,达成一个行为人与他人都能够接受的正义结果,这也是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根据。因此,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要奠基于可接受性正义的基础之上,在法律的边缘寻求一种权衡的技艺理性。这一目标的预设决定了判断标准的应然样态。
三、正义对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目的统摄
施米德霍伊泽:“一切刑罚,只要对同时是不道德和可罚的行为作出了公正回应,都发挥着社会教育的功能;它证实了道德判断,从而在社会意识中确认了规范的效力”①Schmidthäuser,Strafrecht,Algemeiner Teil,2.Aufl.1975,S.52.。刑罚的适用应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首先,行为是受到道德谴责的且可罚的;其次,刑罚必须是在具体案件中被感受为“公正的”[6]。作为一种制度的刑罚,当其对犯罪人人格的侵害进行正当性证成时,首要的就是要将其与责任原则联系起来,即具有实施合法行为的期待可能,这是法之合理性原则。司法体系的存在是为了公正,但是公正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内涵,一个健全的司法体系,必须根据社会观念和道德发展不断进行自我修正,让国民对公正的理解和期待能在司法活动中得以表达。
(一)权衡的公正塑造法律合理性内核
在马克思·韦伯的语境中,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体系是指依一般规则或原则的统治,强调在所有情况下,都可能借助于法律逻辑由抽象的法律判断得出判决,以法律体系的无隙可循塑造包容所有社会行为的无隙可循的“法律秩序”[7]。现实生活中,这种无隙可寻的法律体系只是一种理想型。在法律普世主义特征之下建立起的形式主义体系,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预期性,这是形式法治的内在要求,但是在宏大的法治图景之下,在边缘、细节处需要司法的细细描绘,这种宏大视角要转换成显微视角,因此司法在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时,要在立法的普遍主义之下细细考察每个个案的事实情形与特殊情境。海德格尔认为,边界不是停下的地方,而是存在开始的地方。边界作为居间-空间一次次重新定义差异,相应地也重新定义同一。在秩序边缘处发生的案件与在秩序核心处发生的案件同样地值得关注,边缘正义才真正决定了整个法治图景的轮廓与呈现。
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行为时的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相反,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就是没有期待可能性,不能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有责任,因而不能让他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不法性的行为,但是由于主客观情况而使其不具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则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5]。期待可能性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犯罪论否定机制,其主要适用于发生在边缘的“临界案件”“疑难案件”中。大多数有关公正与否的犯罪化决定的争议,都涉及边缘行为,而不是对行为的危害性存在深刻共识的明显危害行为。在边缘地带,难以确定边缘不良后果的可入罪性。英国刑法学者丹尼斯·J·贝克教授试图在当代背景下探讨刑罚何以正当化的问题,提出每个人都享有不被不公正定罪的权利,以合比例性与公平正义性要求司法者考虑到行为人行为的可责性程度[8]。法庭上的正义必须获得其与具体事例相结合的实践意义,抽象的正义是没有任何规制的信仰型的普遍原则。当将要援引刑法规定进行处罚之前,必须衡量一系列理由,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尽可能地运用合比例性限制,来推翻那些规定了不合比例罪刑的法律。
朱熹认为“常则守经,变则行权”(《朱子语类》卷三十七),即在常规的情况下,人们遵守法律的规则,但是在边缘的、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则要运用“权”来弥补“经”之不足,进而实现“经”之价值精神指向。就“权”的一系列含义为中国思想中的权利概念赋予了特殊的性质。中国思想中的权利概念不包括任何终极性、绝对性或恒定性,而只是包括了不同情境下的正确性(right)。“权”的最初含义是指可以在秤杆上来回移动的秤砣。因此,“权”在我国古代的初始意义就是称重和衡量。它没有固定、最终的位置,而是灵活的、可移动的,就像秤杆上的秤砣会根据称量对象的重量而改变自己的位置[9]。任何个人的立场都受制于他的各种社会关系强加给他的综合影响。因此,权利不具有主体性,而是情境性的,权利取决于所处的位置。期待可能性作为出罪的责任阻却事由,是以合法性对抗不合理的合法律性的秤砣,以衡量刑罚的正当性与正确性。其中期待可能性的目的就是责任平衡,以达到保障人权。称量对象就是不同的案件,以期待可能性不断权衡,达到对刑罚权的约束,而使正义之秤达到平衡。期待可能性回应了朱熹之“权”的思想,将相对性和情境性嵌入了中国的权利观念和人权概念中。期待可能性(“权”)的相对性和情境性解构了法律形式主义(“经”)的僵硬与滞后,给出了更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责任认定,权衡的公正塑造了法律合理性的内核。
(二)可接受性正义是判断的目标
2014 年以来,为加强刑法对人权的保障机能,实施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举措,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10]。这一感受性的正义对司法裁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法律就是一个以法律价值与法律理念为向导的规则现实。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的理念由安定性、正义性、合目的性构成。其中,拉德布鲁赫通过二战后的“告密者案”深刻分析了正义性与安定性之间的矛盾,认为在边缘的极端情形之下,“作为不正当法的法律必须向正义让步”[11]。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观念从相对主义转向自然法的观点实际上迎合了法院在解决处于道德困境中的案件的司法理念,社会主流的法的安定性的期待要求趋于要以一种正义且理性的方式得到裁决。所以通过期待可能性的责任归属是理性的要求和内容可接受性的要求,而内容可接受性是与正义的期待相关联的。法官的司法权威的基础在于其裁判的可接受性,而不是他可能拥有的权力的形式职位。因此对于裁决的做出,说理与证成的责任同样是促成法的安定性的理性基础,同时也创造了司法的可信赖性。从制度结构来看,既然裁定者的正当性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接受裁定,那么显然存在结构上的相对不稳定,也正是“不满的当事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将问题提到更广的层面”这一制度中的相对不稳定性,保证着审判的公正性。案件的无限个别性导致审判的个别主义,塑造了具象的个案正义。用罗宾逊教授的话来讲,犯罪的认定和刑罚的分配不是根据任何具有哲学基础的、清晰理性的体系,而是基于公众在评价应受谴责性时的原则,这不是超验意义上的正义,而是公众理解的正义[12]。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可理解的是可认识的、可接受的,可接受的正义应当是符合其生活逻辑的常识、常情、常理。而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规范性的证成概念,一个揆理准情的重要理念,是将民众的情理和正义直觉体现到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制度路径。期待可能性作为合理性的理性,是司法裁判重要的说理依据,在对不法行为规则存疑之时,则利用一定的非规则型法作为证成判决的法律解释而说服听众。法的效力概念基础并不能建立在实际接受之上,而是要建立在理性可接受性之上,这才符合我们的法律意识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法律经过理性的考量,根据主流的价值体系,它被普遍接受了,那么它就是有效的。通过期待可能性所达成的可接受性是法律秩序之合法性的测量尺,以用来评估和批判那些形式有效且有实效的法律规范的一个理想标准[13]。
总之,期待可能性追求的是一种可接受的正义,合乎事理的正义。这一标准要求责任归属应是合乎事理,合乎有待调整的生活关系并与之相匹配,其塑造的“得其应得、各得其所”的公正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均衡。
四、视域融合视角下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重塑
在可接受性正义的统摄之下,面对边缘的难办案件①苏力在《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中对于难办案件(hard case)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认为难办案件通常是事实清楚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或适用的结果明显不合情理甚或有悖天理人情(所谓自然法),法官因此面临艰难选择。与临界情形,应该脱离单一面向的视域局限,借助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方法,运用视域融合理论打通关于期待可能性判定标准三种学说之间的壁垒,建构应对难办案件的裁判规则。同时以康德的绝对律令作为期待可能性判断标准的核心要素,建构社会公众的行为规则,实现他者与自我主体相统一的理解和解释视域。这种基于绝对律令的视域融合是建立期待可能性的综合标准的理论依据,是达成责任认定之人权保障目的的根基。
(一)视域融合下的司法裁判
具有万全的预期,因此,司法权的本质是在难办案件情况下的决定权,可以称之为“剩余裁断权”,这种裁断权主要依据价值进行判断。法官的判断力,司法的能动性就是在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难以轮齿相合的情况下,以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剩余裁断权进行规训,以防止价值判断的主观化、恣意化。期待可能性是一种规范的价值判断或普遍的价值判断,需要运用阐释学的方法回应价值判断的理念。普遍的价值判断要以个体视野为基础,更要跳出个体视野,借助“理解”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来获取真理。“在理解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14]435,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和一致性,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是指用自己的视域和历史的视域一起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理解框架,这样才能达成一个更高的提升,克服个体视域的狭隘与偏颇,达成统一的实现形式和平衡状态。理解的方式能够超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局限性,不再以主体自身为中心俯视己身以外的事物,而是以想象的方式将己身置入已然发生的案件当中,贯通他者与自我的边界,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想象“我”是行为人,从行为规则指引的角度想象别人也是“我”,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历史(已发生的案件)和传统(行为应对惯习)的递嬗中,置身事内,通过与对象融为一体、彼此互动的体验进行理解,按照特定时空文化下的普遍的价值规范进行判断,从而阐明行为人的规范责任。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只有在游戏者失去自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的目的”[14]152。因此当事人、平均人、国家(的代理人)等在场和不在场的司法多元参与主体,都要将自己带入行为人的视野中,设身处地进入行为人行为时的情境中,成为与情境的互动人,通过平等的对话和沟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才能真正把握和理解当时行为人的行为逻辑,理解行为人特定情境中的不得已和无可奈何。具体来讲,在犯罪论体系中,责任的判断是个别的,因此期待可能性的判断应该首先是从行为人所处的客观情景与主体情况出发,依据其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主体进行理解,权衡不同的具体选择会带来的后果,而且有足够的依据能够自由地从一个充分宽广的角度来看待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现实,包括相关的主观责任感、行动支配能力以及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他的行为举动应该是考虑到各方面相关因素的“权衡结果”。
“一切理解必然包含某种前见”[14]385,因此如果行为人的这种主体性概念的本体论前提就是由社会群体所塑造的某种合理前见,那么这种前见自身主要是无时间性的具有规范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传统,行为人通过想象的情境式判断依据就是范例式的传统,是行为人和平均人/普通人共同分享的判断依据,这就达成行为人与平均人的一种通基于合理前见的视域融合,通过司法场域中的沟通与对话,转变对行为人的态度和定位,行为人不是二元思维下的客体,而应当作为参与沟通的主体一方,寻求行为人与平均人的视域融合。这种视域融合的路径,是以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的具有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形成一种同处一种境遇下行为的共同刑法意义,即对不得已和必然性支配下行为的人权保障。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于正确的立法艺术的理解,正是这种个体与一般人的共同认可的传统是将伦理的道德规范过渡到国家政治立法的重要推动力[15],这也是对于立法序言的核心阐释①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提出,给法律加上序言,解释制定法律条款的理由和意义,将城邦人当作可以与立法者平等交流的人来看待。,所谓“法者,缘人情而制”,刑法以规范人的行为为内容,只有尊重个体人性,符合社会公众之传统共识、人情常理才能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这是当下主流的进化理性主义的法治体系的建设进路。
(二)绝对律令的行为指引规则
基于多个主体的视域融合,其路径建构如下:在涉及责任认定的困难案件中,法律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因此,从道义论的角度需要借助一般性的道德原则来整合对案件的一般判断,以一种二阶视角审视行为人在特定时空的思考与判断,认真对待当事人的观点,达到罗尔斯所阐述的一种反思性平衡②罗尔斯认为“从道德哲学的立场看,对一个人正义感的最好解释并不是那种跟他在考察各种正义观之前就具有的判断相适应的解释,而是跟他的在反思的平衡中形成的判断相适应的解释。”这是一种针对特定情形的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和普遍道德原则与相关背景理论的反复比较,达致一种检验合理性的形式标准。。期待可能性作为个案正义的主要修正方式,要求行为人遵循公平正义的平等性意涵,即人们自愿并希望他人遵循规则,这是存在强有力的生物学基础的。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对于刑事法律的规范性指引应当关照到这一心理结构。儒家“仁”理念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规则,是历代中国正义体系的核心,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意义。这一理念在经过现代化和理性化之后,则跳出了“己所不欲”的个人视域,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方法论,升级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③赵汀阳针对传统的黄金道德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做了一个“最佳版本”的想象,以“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规定一种“绝对无懈可击的人际共识”,以更好地适用于今天社会的价值多元情况。,即包含所有可能眼界的人际共识和价值共识。这一合理形式的表达接近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因此,借用康德的伦理学理念修正对困难案件的判断,就要预设行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基于其前见的视域融合,应当是以一种康德的普遍立法的绝对律令的方式来做出行动,“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④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表述是:“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虽然是一种独白式的理性表征,是一种自己为自己立法的普遍形式,但是其心理路径是一种从个体来理解整体,又从整体来理解个体的双向诠释学的规范过程。即每一个主体都能够且必须让整体道德与法的原则在大脑中产生。虽然仍然是立足于主体性,但是主体的行动心理已经掺入了他者的视角,以求最终达成个体与整体的一致性。或许有学者会主张康德绝的普遍立法的普遍性天然排斥个人的特殊情况,但是我们不妨拉远焦距,将个体的特殊性以及所处的特殊情境,都结合在这个普遍性中进行审视,也就是说,当“子为父隐”而行动时,也愿意将来在同样的情况下“父为子隐”做出同样的行动,同样的特殊情境,同样的行动回应,是包含人性法则在内的普遍合乎道德规范的情理行动。特殊性与情境性本身就是一种更广阔的普遍性,这种普遍立法的道德律令是作为责任认定设置一个边界,以防止犯罪人脱罪。这一过程被李泽厚称之为是一种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性凝聚”,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人性能力和心理形式”[16]。基于此我们将个人意愿普遍化的道德哲学法理化,行为人依照此普遍立法的命令进行行动,就是遵循同一律和不矛盾律,确保了刑法中对于免责事由的不得已的判定,即任何一个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情境中都这样做且不能不这样做。即使是不法行为实施者也必然会运用这一标准,那么关于期待可能性所征表的罪责的判断于他而言就是可理解的。所以,这样就使得行为人和他者/一般公众的对特殊情境的行为反应实现了跨时空、跨历史、跨越主客二元的境遇的移用和理解的视域融合。因此,这种行动方式的存在本身是为“观看者而表现”,是存在于他者视域中,也正是因为以此绝对律令而行动,才获得一种自身行动的完全意义和正当性。行为者的行为与他者设身处地的可能行为达到了跨时间的统一性和同一性。这种共同性的存在,是一种分享性的共识,基于同的存在必然是抽象的,因此也是薄的共识,所以作为行为逻辑的绝对律令只能是一种形式法理(实证)①此处的概念借鉴了李泽厚关于将康德和黑格尔的伦理哲学定位为“形式”伦理和“内容”伦理的论述,认为康德普遍立法的绝对律令揭示了道德行为的心理形式结构,而黑格尔所探讨的内容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内在道德,这种形式法理的外壳包括的内容法理是视情况而变的,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现代的亲属拒证权等,所关照的是不能期待一个人抛弃人性情感和人际情理而实施法律规范所要求的行为。内容法理(非实证)是涉及家文化传统下的亲伦情感。再比如,紧急避险是不能期待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面对恐惧、紧迫而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其中内容法理是人性本能。总之是将人是目的、保障人权作为一种抵御集体主义的现代社会性道德内容。
(三)期待可能性判断的融合标准
法律规范是普遍性的,法律的生长是哈耶克所阐述的自生自发的,是遵循制度逻辑与生活逻辑,表现为与朴素的常识、常理、常情的沟通与互动而共同塑造了一般的制度理性,一种人类精神的集体业绩。而期待可能性体现了法的一个基本的内在规定性—法不强人所难,由此,行为者与一般社会公众与法律规范(国家)要求达到了一种统一。三者的统——性决定了其具有的不可谴责性,但是如果行为人超出了绝对律令的法理形式,那么就超出了三者的统一,这种存在者的行动方式就决定了其未来的存在模式,决定了其责任的承担,因此这是一种源始时间形式的作为未来的过去,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过去和未来的沟通。由此以绝对律令作为法理形式和规范期待,使其成为行为人的行动逻辑和标准,自然而然将此标准适用于普遍的社会公众的行为逻辑。这样就使得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成为行为人、平均人、法规范(国家)的共同标准。这正是符合中国人的整合性思维传统,强调主客融合,相融相通。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一种全面的、重视背景的世界观,强调从人与整体的关系来理解自我。因此,张明楷教授主张将三种学说放到一个整体中进行把握,将三者结合适用。不同的是,通过上文论述,期待可能性是责任阻却事由,因此这个整体的标准应该是站在国家人权保护的立场,根据行为人当时的身体、心理条件等,通过平行处于相同特定情境下他人的合法行为实施可能性的比较,来判断是否能够期待行为人通过发挥自己的能力不实施违法行为[5]。这种整体性标准强调三种要素的纵向历史主义的视域融合、横向空间的跨越与交叠。以康德普遍立法的绝对命令作为具体的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依据,达成历史主义的视域融合,做出符合传统法理内容的责任认定。法规范的学说代表国家的要求,平均人的学说即人民的学说,代表朴素的社会常理,行为人的标准代表了个体化特殊化的情境,法规范(国家)、平均人、行为人立场的视域融合,正是将国法、天理、人情融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应有之义,才能让公民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期待可能性作为当下我国犯罪论体系的重要出罪机制,承载了文化传统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是在形式法律的普遍性难以涵射之时,针对疑难案件中行为人的不得已而给出责任认定的基本框架和法理形式。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游离在刑法教义体系的边缘地带,通常情况下,并不需要出场审核。但是其重要性不可小觑,因为边缘正义(个案正义)的细致描绘决定了法治整体的图景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由边缘看核心,边缘正义的塑造,就是法治核心的塑造。现代国家的发展,国家权力偏向对秩序的强调,个人偏向对权利的强调。国家与个人仍然是生存于特定的关系中,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紧张关系的处理要以均衡为旨向,“于必要时,随有轩轾,伸缩自如”[17],具体来讲,遵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关系中的主体要有他者的视野,个人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为行动导向,因此裁判时,司法权力要以行为人权利保障为出发点,将国家视域融合于个人视域,以个人特定情境下的困顿与不得已为裁判基础,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以准确归责。行为人在行为时要以关系平衡、社会秩序为重,国家与个人互以对方为重,才能产生均衡,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本位蕴含的相对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