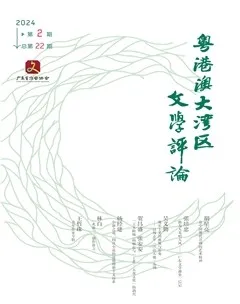抒情性叙事的探索及文学远景
陈银清 陈培浩
摘要:青年作家王哲珠的小说作品多与潮汕乡土关联,也有对城市的呈现,体现了浓厚的乡愁与对热烈的新乡土生活的展望。她的小说多采用抒情化的语言,形成一种诗化的叙事风格。王哲珠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将小说写得波澜婉转,饱含深情地述说时代与人、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表现了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变化,别具独特的审美意味。王哲珠的写作,自觉地赓续和转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其诗性叙事颇具特色。然而,有效的抒情化叙事不是叙事的悬置,而是情动对叙事的激活;抒情化叙事也需要与更宽广的文学观相连接,与叙事性与虚构性相统一,以打开更广阔的文学远景。这构成了当代小说待解的难题。
关键词:诗性叙事;抒情传统;叙事性;虚构性;王哲珠
潮汕作家王哲珠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玉色》,于202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老寨》《长河》《琉璃夏》《尘埃闪烁》《我的月亮》《姐姐的流年》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作为“80后”青年作家,王哲珠虽不如双雪涛、蔡东、王威廉、陈崇正、郑小驴、孙频等人受关注,但凭着勤奋和高产,王哲珠也收获了不少文学成果和荣誉。新近更是凭长篇小说《姐姐的流年》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值得追问的是,写作已有十多年,王哲珠的创作显示了怎样的阶段性和内在衍变?浓烈的抒情语言是王哲珠小说的重要特征,抒情性成了王哲珠小说的语言气质与风格类型。但小说的抒情性如何获得更高的文学远景?如何与叙事性、虚构性相统一,这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尝试通过王哲珠的小说对此有所回答。
一、王哲珠小说创作嬗变
王哲珠的写作是从书写乡土起步的。乡村是王哲珠最熟悉和依恋的地方,也是她持久回眸的对象。在乡村观察乡土,于城市回望乡村,斯土斯民成为王哲珠写作的重要题材。但王哲珠小说也不局限于乡土题材,也有多样的题材和多变的风格,曾引起社会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王哲珠的创作初期,乡土题材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此间,不但有出版于2013年的长篇小说《老寨》和出版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长河》,还有很多中短篇小说面世。这个时期的王哲珠,萦绕于怀的是中国农村为何逐渐失去新鲜血液,日渐衰微与空荡,那原本附着于乡村的生活方式、朴实无华的价值观、专属于乡村的味道都随时代的变化而渐渐消弭。乡村对于王哲珠来说,是小时候的家园,是纯真无邪的地方,是充满着童趣与故事的地方。在乡村所积累起来的童年经验,影响了王哲珠对生活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与艺术追求。但时代的高速发展,渐渐将乡村抛在现代生活的外面,乡土朴素可亲的面目也逐渐模糊了。于是,王哲珠想用饱满的细节再现一个寨子变迁中的点滴,以叙事复活乡土曾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理念、人伦关系,这便有了《老寨》。《老寨》以丰富的细节展现过去乡村生活的缓慢与柔美,以温暖细腻的笔触思考老寨的历史与未来,寄托着对传统乡村的凋零和没落的无限追忆与感伤。王哲珠创作的多部(篇)乡土题材小说,并非一成不变地描写乡村的凋零,也有别样的呈现,如长篇小说《长河》。《长河》通过冯家几代人的生活,书写了金溪寨与金溪河的命运,展现了人心在膨胀的欲望中的背叛与坚守。王哲珠感慨于:乡村想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却被时代越甩越远,直到失去它原有的生命力。与《老寨》不同,《长河》有乡村子民面对时代变迁的迷茫与挣扎,也有尝试跟上时代步伐的努力,体现了更强的主体性自觉。
王哲珠创作的第二阶段大约是在2016年至2019年。随着阅历的增加和视野的打开,王哲珠的小说不再局限于写乡村的盛衰兴替,而开始有了视角的切换,由此带来对生命“真实”的不同理解。此间,她更多从城市回眸乡村,尝试以丰满的日常细节挖掘生活更深的内里,写出生活的背面,表象世界底下的另一面。此阶段代表作有《琉璃夏》《纸上人生》《尘埃闪烁》《琴声落地》等。《琴声落地》,描写了乡村扬琴手老独与花旦映婵在潮剧兴盛时期结下的深厚感情,也展现了现代生活观念如何逐渐渗透并深深影响、改变了农村。年轻人不喜欢潮剧,传统乡土的文化生活方式已无人呼应,作者流露出一种怀旧的感伤和忧思。王哲珠意在描写现代城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入侵,乡土文化逐渐失去坚守者,这让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行进艰难。《纸上人生》思考的则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写的是一个离奇故事,小说中的人物高宇、杨木木、阎让东,自以为掌握了自己的生活,最后发现自己被生活掌控,这种“失控”的隐喻,让小说呈现出思想的厚度与深度。再如《尘埃闪烁》,主角是都市里的边缘人物,小说写出了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吸引与融合。来自乡村心灵纯净、珍视生命本真的丁丑原本与女朋友姚婉净一起摆烧烤摊谋生,但这无法满足姚婉净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最终她追随有钱人而去。在城里长大的高书意家境优越,但她的生活却很单调空虚,她被丁丑那丰富的内心与纯净的心灵所打动,最终与丁丑走在了一起。这篇小说写出了两种错位人生,乡村与城市有了交集与融合。这个时期王哲珠对乡土的描写更加扎实与厚重,有了更多层次。
王哲珠第三阶段的创作有了更大的推进,也更加注重对人物的刻画与表现。2020年至2023年的三年间,她发表了《我的月亮》《姐姐的流年》《玉色》等多部小说。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时期王哲珠笔下人物更加立体,有对人性更深入的探讨,叙述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如《我的月亮》,小说展现了生与死的纠缠,爱与人性的交汇。得了绝症的青年女歌手高灵音面对命运的戏弄意图自杀了结,但老天让她遇见了富二代肖一满,他阻止了高灵音的自杀。高灵音之后去了山村小学教孩子们唱歌,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圆满。又如《姐姐的流年》对“姐姐”的多视角描写,让“姐姐”的形象更加饱满。小说六个章节书写独立的故事,以不同的视角描写“姐姐”,还以诸如剧本体、日记体来结构全篇,且形式与内容形成内在的嵌合和呼应。“姐姐”也随着不同的视角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侧面,展示出“姐姐”的成长轨迹,以及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形象。
最新长篇小说《玉色》则以乡村振兴为主题,这是王哲珠以更加建设性的方式回望乡村。但她的书写比之以往有诸多不同。《玉色》中延续了《老寨》《长河》的乡土抒情叙事,但在精气神上与《老寨》《长河》不同,书写的是充满希望与奔头的乡村,是追求文化高度的乡村,是不甘于落寞的乡村。小说主要写: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以夏文达、欧阳立与林墨白等人为代表的乔阳人不懈努力,让乔阳成为全国重要的翡翠聚集地之一。小说既写村干部的精神成长与思想的进步,也写乔阳人创业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团结协作。围绕玉石交易和人性纠缠展开了颇具可读性的新时代乡建叙事。玉在中国的文化中,不仅意味着财富,也代表着美德。《玉色》在乡建叙事的背后,也内蕴了以“玉”为核心的德性呼吁。小说在语言上更加的克制与隐忍,也间以魔幻的元素,如“粉翠精灵”,以一种魔幻式的表达丰富了乔阳村的翡翠文化。这是王哲珠在长篇小说的又一次发力,也是她对乡土题材的再次呈现,但无论在写作手法、叙事技巧,还是抒情方式上,《玉色》都体现了一种新的气质。王哲珠正是在对生活的不倦挖掘与对日常细节的细腻展示中,呈现了对现实和时代新的诠释。
二、抒情化叙事:以情感为中心
抒情与叙事是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但就如陈世骧所说:“中国文学的传统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抒情的传统。”1“抒情精神在中国传统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正如史诗和戏剧兴致之于西方。”2那么,作为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小说的抒情与叙事该如何结合?然而,这里的抒情不局限于作为表达方式的抒情,更是指一种精神与韵味。王哲珠曾多次提到自己喜欢《红楼梦》,并在创作中受其影响。《红楼梦》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鼻祖,也是中国抒情传统的集大成者。受古典文学的教育与熏陶,王哲珠小说中有丰厚的感伤气质与浓郁的抒情性。王哲珠对第三人称内聚焦限制叙事颇有心得,能精微捕捉主人公意识流动;又以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使意识流叙事呈现出抒情化格调。谢有顺曾说:“抒情传统不仅是一种文学实践,也是一种生命实践。抒情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不把抒情、情感视为小道或仅仅局限于文本,而是表现为对一种生命意识、生活态度、情感结构的体认。”3王哲珠的小说也体现了这样的追求,其第一部长篇《老寨》,在开篇就奠定了一种抒情基调:
作为一个寨子,我的年岁不算大,但我老了。我这样说时,心平气和,无悲无喜。我很清楚,如今不比从前,人世间的一切都鼓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风,哗哗啦啦地飘。风呼呼呼地喊,快,快,快。人世间的脚步便啪啪啪地快了,往前赶,虽然不清楚那么快做什么,也不清楚这声音从何而来。4
《老寨》的语言很有黏性与表现力。读小说开篇的这段文字,我们感觉语言被拉长。重复的字词、深情的语调让语言节奏舒缓悠扬,又不乏灵动的变调,如从二字的“哗哗”“啦啦”到三字的“呼呼呼”“快,快,快”“啪啪啪”的转换。这里将老寨拟人化,以老寨为第一人称,以老寨之“眼”观乎世情,既蕴含对乡村的充沛情感,又带点伤感的气息。小说开篇的这种抒情性写法,并不合于一般的小说写法,那它没有小说叙事性吗?又不是的。小说接着便进入人的故事。《老寨》全篇分为三个部分,围绕着乡村的典型事件——丧事与喜事展开叙述,最后以“心事”来深入老寨的血肉记忆与沧桑岁月。《老寨》擅于抒情化叙述及在叙述中抒情,在叙事与抒情中呈现乡村的精神内核。如第一部分《丧事》中,进城务工的树春因工伤亡,而树春妻子此后却背叛树春,最后又感到愧疚。这一部分描写的多是乡村生活的琐细点滴,描写乡村人物如树春、秋柳、喜月、阿爸之间的关系缠绕,少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高潮与矛盾。小说用抒情的语言,浓墨重彩地书写人物内心的情感波澜。如树春因工受伤却得不到说法的无奈:
“所有的声音,都落进树春的那些黏稠的静里了。以后的岁月中,树春要不就在这团黏稠的静里沉默,要不就全身烘出一团火气,炙烤那团黏稠的静,烤得噼噼啪啪地响,那层静便一片一片地掉落,甚至飞溅,溅到身边某一双眼里,或某一张脸上,周围那双眼或那张脸就疼痛起来。” 1
树春因工受伤,却得不到老板相应的赔偿,将老板告上法庭也无济于事。树春陷入求告无门的痛苦中。这一段以第三人称内聚焦限制叙事的方式,呈现了树春受伤后身体的疼痛与精神的困苦。人物描写是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这里,王哲珠不用曲折的情节去凸显人物,而是通过表现人物情感与精神来表现人物。她的小说叙事结构单纯,文字直指人的苦难与疼痛。《老寨》的树春、《长河》的冯家人、《我的月亮》中的高灵音、《姐姐的流年》的姐姐等人物的人生在王哲珠笔下徐徐展开,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与严密的故事性,她只是细致入微地观察、平静如水地叙述。王哲珠小说的抒情性,即体现为将人物情感作为小说的内核。抒情的文字之下,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层层深入的人物情感。人物情感成为了叙事的中心。另一方面,尽管情节并不曲折,但故事也在抒情性的语言中得到铺呈和展开。因此,这并非一种静态的抒情,而是一种抒情化的叙事。
又如王哲珠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长河》里的抒情语言:
冯流夏在河边遇到叶子,准确地说,应当是先遇到叶子的歌声。当时,冯流夏坐在河边,手里扭着细长的草茎,他听到歌声,烟一样,渺渺而来,又极脆亮,像鱼翻起的水花声,因隔得远,声弱了,但仍感觉得到丁当的质感。2
这里对人物的感觉有多层的表现:冯流夏听到叶子的歌声,而叶子的“歌声”又如“烟一样”,又如“鱼翻起的水花声”,声弱后又有“丁当质感”。小说由单纯的叶子的歌声,串联起“烟”“水花”“丁当”几种事物,让一个事物的声音联系起多种声象,语言曼妙而生动。同时,人物自身的情思与心绪,也由语言的组合汇聚成一种抒情的氛围与情调。这样具有抒情意味与情调的语言,让我们不由想起废名、沈从文与汪曾祺等小说家的抒情化叙事。废名将自然美景和田园趣味引入小说,他写小说不重讲故事而重创造意境,并在此过程中写出对人生的理解;沈从文擅长在小说中铺展湘西边地的风土人情,创造氛围与意境在沈从文是与小说情节同样重要的事;汪曾祺常将风俗描写作为人物的背景与叙事契机,借以呈现人性之美。不难发现,王哲珠受到现代文学抒情化叙事的影响甚深。她眷恋和书写故乡的风景与人物,人物的行为在不同氛围的笼罩下不断发展,心理思绪也因之不断起伏变化。在小说中,作为作者的王哲珠也是潜在的抒情主体,其情思投射在小说人物的言行上,现实认知和省思遐想蕴于其中。
不能说王哲珠在抒情化叙事的方向上超越了前人。事实上,超越可能不是用来描述文学代际赓续的有效概念。对于科技而言,一代之兴必是上一代之废;但对艺术而言,承续不是在上一代的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是独辟蹊径和别开新境。几千年过去,《诗经》和荷马史诗依然是吸引后人的中外经典。这样说,不是说王哲珠已经可以和前面那些抒情小说家相提并论,而是说作为后辈小说家她同样拥有吸纳前人又另辟蹊径的可能。抒情化叙事,不重故事、淡化情节、深挖内心、重视氛围和意境的营造,这些都是共性。然则,什么决定了抒情化叙事的艺术高下?情感的独特性、技巧的创造性以及艺术上击中人心的效果,都是考量的要素。抒情化小说,归根到底必须有情。不仅是人物有情,更是写作者有情。写作者有情,其笔下人物才可能有情。文学的有情不是一般地指有感情、有良知,而是指其内心被某种情思所缠绕,甚至有所郁结,不吐不快。文学的有情也不仅是作者情感的宣泄,它必须是一种更丰富、更微妙、更高级,包含着更高价值内涵的情感。文学的有情,是指某种情思穿透了写作者的心灵结构,使其悸动,不可抑止;随后又把这种心灵波澜艺术化,投射到人物和叙事中去。所以,抒情化叙事的真正核心是情动,而不是叙事的缺位或隐匿。叙事隐匿并不会自动带来情感的凸显;没有情动而强行抒情,同样无法让人感动,反而容易令人反感。不管具体的展开方式如何,王哲珠的抒情化叙事,绝大部分把握住了由情动而生发叙事这一核心。
三、抒情化叙事与文学语言的更高追求
必须说,王哲珠的抒情性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王哲珠的小说语言清丽婉转,具有轻音乐般的和缓柔美,笔触细腻,情境冲淡平和,作者也力图将文学之美和哲理之思有所融合。如她在《尘埃闪烁》与《琴声落地》中的描写:
这两个多钟头里,周雪雅把城市一层一层掀起来,让姚婉净细细看,她一层一层,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抖搂开,经经脉脉理给姚婉净听。真正的城市其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得融进去,整个化进它独有的生活和方式、观念和意识。1
掂起琴竹,老独整个人变了,蜕皮般褪去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琴架前的他成了月下的烟,邈远、神秘,目光蒸腾,表情游离。琴竹敲出第一个音,余音袅袅。第二个音响起,曲子就起了,他蒸腾的目光收聚成点,闪烁在曲子深处,涣散的表情一扫而光,面皮浮起光彩,随曲子起落而明暗。2
以上两个文段,情与景交融互渗,运用具有灵动性的词语,如用“掀”“抖搂”“蒸腾”“游离”等词语自然地铺展叙述。无论是对乡村还是城市的描写,王哲珠常常挖掘出易被人忽视的情感体验。《尘埃闪烁》中的姚婉净向往城市的繁荣,却不通晓城市的经经脉脉。王哲珠于此处道出了城市的复杂及其生存方式,具有哲理性;《琴声落地》则写出了主人公老独只有面对着扬琴时,生命才焕发出了光亮。王哲珠用“月下的烟”来形容老独弹琴时的状态,营造了一种缥缈神秘的氛围。同时,也从侧面表达了以生命状态呈现的艺术之美。可见,王哲珠的小说具有语言的美与哲理之思。
但也要看到,这种比较理想的语言状态,是王哲珠不断追求和实践的结果。王哲珠创作初期的小说,抒情味较浓,在思想性与哲理性上还有发展空间。但到了后期,她的小说渐渐将抒情性与叙事性、思想性更好地结合了,如2020年发表的《姐姐的流年》:
母亲说姐姐背着我洗衣时,我偏偏爱撒尿,又偏偏总在冬天。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来,才意识到母亲语气里充满疼痛,而姐姐总是笑,手指在脸上划着羞我,我因为害羞,母亲说起这些时总想避开。
云淡风轻的语言背后,是人生的疼痛与无奈,是生存的艰难与困苦。王哲珠在这里写出了“姐姐”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姐姐生活之苦。这里交杂着命运与人性的主题,具有思想性,同时又没有消磨小说的故事性。从《老寨》到《玉色》,王哲珠擅长以日常的书写与充盈的细节,描写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记录对时代的感受与思考。她不断摸索着自己的创作风格,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抒情特色。如今,王哲珠在语言上有了更多的突破,她的最新长篇小说《玉色》就融入了对人物意识流的描写:
他感受到极端的亮,亮到无法睁开眼睛,但每一寸肌肤都打开了眼睛。他看见了光,光饱满浓稠到难以承受,灼热是在灵魂里的,热到极点,失去了灼热感。转瞬间,他从极亮跌入极暗,暗像水像空气,渗进林墨白的身体,他被融化,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刺骨的冷,不,是冷到感觉不到骨头,感觉不到自身,只有冷,巨石一样在压在身上,压得人无处可逃。1
这是小说里的人物林墨白见到粉翠精灵时的心理描写,同时也是一种感觉化的描写。从光、热、融化,到冷、刺骨,王哲珠熟稔地运用着感觉化的语言来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以具有陌生感的语言打破以往司空见惯的日常语言,让小说具有新的形态,带给读者独特的阅读体验。总的来说,王哲珠的小说语言在不断进步,也在不断挖掘自身的可能性,其抒情性小说也获得了文体意义上的合法性。
某种意义上,王哲珠的抒情性小说赓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学者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认为:“引‘诗骚入小说的艺术尝试,不单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抒情小说,而且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2他将现代抒情小说的出现视为一种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我们由此可以找到这条关于抒情性小说的“史的线索”,即从鲁迅《社戏》《故乡》开始的抒情乡土小说,到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萧》、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再到汪曾祺的《受戒》、迟子建的多部乡土抒情小说与魏微的创伤书写等。萧红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将对悲凉生命的迷惘与挣扎化作抒情性的文字,诉说孤独者的生命感受。迟子建以儿童般纯净的赤子之心,以不被世俗侵扰的眼光和观察力,记录乡村与城市的生灵日常,文字澄澈而空灵。“70后”作家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花城》2001年第5期),写的是一个城市女孩与农村男人之间的微妙感情,这篇小说同样不以情节取胜,而是将感情作为中心,推动叙事的行进,主导了小说的叙事方向。王哲珠小说中充溢的抒情性,让她的小说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抒情性小说创作,自觉转化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无疑是当代抒情小说的一朵浪花。
事实上,重语言、擅于抒情化叙事,这是大多数女作家的特点。女作家出色的感受力和细腻的表达力,往往使她们与抒情传统缔结了更亲密的关系。但是,抒情化叙事能否、又如何上升为上述那种语言与思想、内容与形式化合为一的更高的语言?这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又是一个对王哲珠这样的青年作家尤其重要的问题。抒情化叙事以及抒情传统,常是可以方便地加诸其身上的论述。这种论述固然敞开了作者的某种写作特质,却也搁置了更高的追问:即抒情化叙事内在有没有高下?抒情化叙事如何朝向更高的方向迈进?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1汪曾祺也有一句名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2他们都说明了语言的重要性。表面上看,这是指任何文学作品都以语言作为载体,文学效果的达成也有赖于语言的恰当运用。深层次看,则是指文学语言与叙事内容以及精神价值之间,不是简单的杯子与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创造和文学价值。将语言提升至文学本体的位置来讨论,并非否定其他诸如经验、内容、思想等文学要素的作用,而是说真正好的文学语言,必然蕴含着内容、思想和价值观等内容;而文学的思想和价值,也必形诸于语言之中。语言的内容和形式,都化合为一。所以,抒情化叙事,并非悬置叙事就够了。既必须以真正的情动使抒情化叙事获得有效性,又必须置身于更高的语言追求中,使抒情性获得更大的文学前景。此外,小说的抒情性还必须处理好与叙事性的共生关系。诗性或散文化的小说虽以抒情性为主导,但并非对叙事因素的全面拒绝和放弃。抒情也需要语言载体、故事模型的依傍。然而这需要作家以高超的功力去调节抒情与叙事的矛盾,达到抒情与叙事的平衡。从文体角度来看,小说主要还是一种叙事的艺术。虽然每个时期抒情性的小说的出现,都是一种超越主流叙事范式的努力,但它们往往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静态的抒情过盛,很可能伤害小说的故事性与虚构性。导致抒情性的失效。这些,都值得以抒情性为叙事追求的作家注意。
结语
小说由语言造就,某种意义上,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小说。抒情性叙事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脉,这一脉的小说更强调,“人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而且还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一种情感的存在。”3因此,重要的不是故事和叙事,而是通过小说对人的情感内在性进行不懈的勘探。王哲珠的写作有多个面向,但她显然更擅长抒情性小说,抒情性叙事随着她的写作探索、对世界认识的深化而发展和完善。她不断耕耘,也在不断收获。她的语言与思想经过时间的锤炼获得了发展,她小说中纯净婉转的抒情语言与颇有哲思的诗性叙事,吸纳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养分。王哲珠的写作,关联着抒情性叙事的探索和如何获得更大文学远景的理论难题,值得持续关注和探讨。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1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页。
2 [美]陈世骧著,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页。
3 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4 王哲珠:《老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 王哲珠:《老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2 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页。
1 王哲珠:《尘埃闪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
2 王哲珠:《琴声落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1 王哲珠:《玉色》,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49页。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2页。
1 [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6页。
2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见《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3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