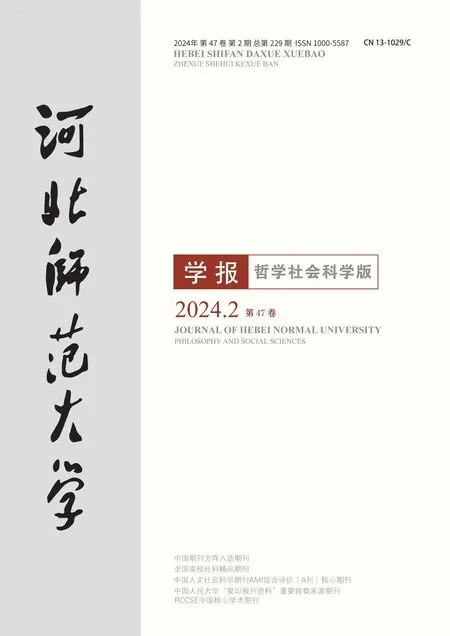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司新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70)
北宋中叶,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一股整合会通思潮,“诗画本一律”(1)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见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9,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5页。“书画文章同关纽”(2)黄庭坚:《题摹燕郭尚父图》,见黄庭坚著,白石点校:《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第42页。“文章书画固一理”(3)苏轼:《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合注引王仲至诗,见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8,第1427页。等说法大量出现,“诗书画一体”观成为士大夫群体的共识。元之后,“诗书画一体”的含义虽有发展、丰富和变迁,但作为称誉文人艺术的特定用法,则延续至今。对北宋诗书画如何走向深度结合,学者们主要从诗与画(4)例如钱钟书论“中国诗与中国画”,见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8页;徐复观:《论“中国画与诗的融合”》,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5页;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刘石:《“诗画一律”的内涵》,《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等。和书与画(5)参见顿子斌:《文人画的书法化倾向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陈思:《北宋绘画文人化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邱振中:《书法与绘画的相关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两方面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对文学与书法一体关系的探讨仍有待深入。(6)古代的“文学”观念比现代的文学观念宽泛得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学”,基本上相当于今天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即大致包含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广义的“文学”,在古代包括一切艺术性或非艺术性的文章典籍,是整个文化学术的总称。本文所称的“文学”取其广义,具体到苏轼,则包括诗、词、文、赋,但在具体论述中侧重于狭义“文学”中成就最高的诗歌。本文所称的“书法”,包含苏轼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两个方面。本文以“诗书画一体”观的先行者——苏轼展开讨论,在重点分析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的基础上,立足于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的不同揭示其机理和成因,为探讨我国“诗书一体”观的知识谱系提供学理依据和参考背景。
一、苏轼“诗书一体”观的内涵
纵观文学与书法的关系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可以转化为书写的艺术;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一旦成为书法艺术,更多的则是著名文学作品的反复书写,正所谓“书由文兴,文以义起”(7)赵孟頫:《阁帖跋》,见崔尔平编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大约在唐代已有文学与书法关系的论述,如张怀瓘所言的“字之与书,理亦归一,因文为用,相须而成”(8)张怀瓘:《文字论》,见张彦远著,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卷4,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但张氏仍限于从平行相须的角度进行描述。孙过庭《书谱》认识到作品的文意对书法具有一定的影响:“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9)孙过庭:《唐孙过庭书谱墨迹》,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页。不过,这里更多的也只是心理上的感觉而已,并没有对二者结合机理的认知。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则真正实现了文学与书法的深度融合。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云:“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10)苏轼:《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51页。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最为典型的表达。首先,在苏轼看来,诗书画都是“德”的表现,文同(字与可)之所以能在诗文书画诸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于其自身有“德”,“德”是文艺的根本和灵魂。“德”不仅仅是狭义上的“道德”,也包括个人的学养和品格,是“人”最本真的表现。不论其为文、为诗、为书,其所表现的无不以具有同一性的“德”而呈现出相似性。其次,在诗书画中,最能表现“德”的是诗文,次之为书画,不同的文艺门类虽都可以表现“德”,但又有表现方式上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第三,在诗书画的不同文艺门类中,书画为“诗”之余,是诗的变种和延展,是诗意的不同呈现形式,在表现“德”的程度上,书画不及诗文。总之,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诗书综合艺术论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基本内涵。在苏轼对文同诗文书画的评价中,不变的是“意”,变的是不同的文艺形式。
就文学而言,中唐以来,佛学心物关系论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传统的物我关系逐渐被颠覆,出现了一种超越感物兴情模式的“非感物”论。(11)萧驰:《佛法与诗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203页。在此指导下,宋代文学具有尚意的倾向,表现为对诗人主体超越性的重视,诗歌笔触所指,既不是外在的物色,也不是变幻的情感,而是主体独立不倚的识见。(12)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1页。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所秉持的这种超越性的人生态度,可谓尚意文学的精神内核。南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记载了一则苏轼写文章的故事:“坡常诲以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13)葛立方:《韵语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页。很明显,苏轼所谓“意”,主要指的就是自己的思想和识见。
苏轼论书也以“意”作为核心观念。与东晋“二王”书学观念中出现的“意”与“象”相对应不同,苏轼的“意”对应的是唐“法”。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14)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见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6,第235-236页。,“意造”旨在倡导书法的自主性和非功利性,不墨守陈规,不求先入为主,让书法成为体现人格精神的载体。“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蔡襄)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15)苏轼:《跋君谟飞白》,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第2181页。“通其意”才能使真、行、草、隶各得其所,而且可以实现各种书体技巧的综合变通,创造出“飞白”的艺术美体。“飞白”在文学修辞学上强调的是故意仿效明知是错的修辞方式,是一种文学与书法通显的艺术方法和效果。苏轼对飞白体的高超艺术造诣大加赞誉:“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始余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16)苏轼:《文与可飞白赞》,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1,第614-615页。在重“意”的意旨下,苏轼的“诗书一体”观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丰富的逻辑延展。
二、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机理
苏轼的书学理论和实践开创了书法“人格化”和“文学化”的道路,奠基了苏轼人文艺术理论开拓者的地位。此文风一开,遂传至千年,至今仍是文人从艺的理想范式。不同文体之间、书体之间的嵌入和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互生共融,构成了苏轼文学与书法的整体互动和内在机理。
1.破体为文——苏轼不同文体间的交融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用“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7)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见张健校笺:《沧浪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概括宋诗的特点实为击中要害。“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盖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18)赵翼:《瓯北诗话》卷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页。宋代文坛最擅长破体相参,而苏轼“遍悟文体”(19)柳宗元著,尹占华等校注:《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62页。,可谓最成功的文体改革家,正如宋人评云:“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20)曾季狸:《艇斋诗话》,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页。苏轼之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21)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乙编卷3《东坡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如苏轼主张“以诗为词”(22)陈师道:《后山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9页。,使宋“词”成为集表演性、音乐性与文学性于一体的悦耳、悦目、悦心的新的诗歌艺术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总之,苏轼一方面既“尊体”(23)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同时又能做到“出位之思”(24)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53页。,审慎把握各文体的“临界点”,不断进行“破体”(25)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第64页。试验,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文学面貌,遂成为一代文坛领袖。
2.体兼众妙——苏轼不同书体间的会通
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首先论及智永书法,苏轼认为智永书之所以能达到“骨气深稳,精能之至”,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体兼众妙”,融通了陶诗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6)爱新觉罗·弘历编:《唐宋诗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9页。的风格特点。任何单论一种书体自身的技艺或只从书艺本身出发论书,都是不全面的,难窥智永书法的全貌和艺术造诣。苏轼随后又对欧阳洵、褚遂良、张旭、柳公权、颜鲁公五位书家的师承和面貌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27)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第2206页。等诸多“艺心”与“人心”综合互融的论点,更以陶诗、杜诗的艺术风格来类比阐述五书家诗书共融的精深造诣,使人形象而又立体地体认了六家书艺的特点和精神风貌,这充分体现了苏轼从诗、书、人互融共通的视角综合论书的观念。
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提出了“兼百技”的书艺创造原则:“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28)苏轼:《跋秦少游书》,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第2194页。秦少游的草书之所以具有萧散简远的“东晋风味”,就是因为他能兼融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家的“百技”特长,也使他的诗作“增奇丽”,收到了诗书兼采众长的效果。虽然“兼百技”与“体兼众妙”并无太大区别,但是苏轼由此更上一层,认为秦少游“体兼众妙”的“百技”特长,能够结合自身的学识、趣味和精神,追求一种“技道两进”的艺术境界和人生目标,将创作的技术性与思想性相互结合,达到二者的完美统一,提出了艺术创作由技到人再到道的创造之路,这才是“体兼众妙”“兼百技”的真正目的所在。苏轼的这一观点道破了文学与书法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3.外部联系——苏轼诗书形式上的结合
文学与书法都源于中国独特的汉文字,许多书迹本身就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东坡的《赤壁赋》等;许多文学佳作也都是书家乐意书写的对象,如《洛神赋》《归去来兮辞》《赤壁赋》等;至于诗文辞赋与书艺的结合,更是中国书艺主要的表现形态,除了日本和我国一些现代书家单个汉字的书写,以及传统习俗中“寿”“福”等用于特定场合的单字书写外,书法作品很少单字书写。传统书家的题材不外乎儒释道三家之经典文句、流传广泛的诗文辞赋、自作诗文,以及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等传统启蒙儿童的文字。书法艺术是随着文学的载体——文字书写不断求美的取向而逐步出现和形成的。书法家的睿智和审美为文人开拓了描写范畴,提升了文学描写的效力;文人把观赏书法的感受吟而成文,书法亦因文章而日臻精妙,广为流布,二者共同促进了传统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方面,苏轼把自己在观书时的认知和情感作为诗歌的题材、对象加以咏叹而形成论书诗文、咏书诗文;另一方面,苏轼又常常以文学为对象进行书法创作。从苏轼的诗文集和留存于世的书迹中可以看出,苏轼有意抄写前人和自作诗文都是文辞优美的典范之作,如《归去来兮》、前后《赤壁赋》等,以此达到文字与书迹双美的最佳状态。《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自书书法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从书与文两个角度进行了品鉴:“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29)朱天曙主编:《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河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至于苏轼的自书文行楷体《前赤壁赋》,也是文书双雄、珠联交融之作。董其昌在观跋中写道:“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30)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教研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页。这同样又是把文体与书迹源流结合起来加以赏析和评论的例证。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却总是趋向综合,……书法何不然?挂在厅室里的条幅一般不会是无意义的汉字组合,而总兼有一定的文学的内容或观念的意义。人们不唯观其字,而且赏其文,而后者交织甚至渗透在前者之中,使这‘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获得更确定的观念意义,另方面又不失其形体结构势能动态的美。两者相得益彰,于是乎玩味流连,乐莫大焉。”(31)李泽厚:《略论书法》,《中国书法》1986年第1期。
4.书卷气息——苏轼诗书内容上的影响
程抱一在《中国诗画语言研究》一书中指出:“在书写过程中,文本的含义从未从书法家的脑际完全消失。因此对文本的选择并非毫无缘由和无足轻重。”(32)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程氏的这段话道出了诗文文本如何影响了书法的奥秘。就苏轼的“诗书一体”观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苏轼诗文对书法最大的影响是书法“书卷气”的提出和实践,对此,黄庭坚曾赞誉道:“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33)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见黄庭坚著,白石点校:《山谷题跋》,第77页。因此,一般书法史皆论苏黄下开文人意趣,至明末而极,也有学者认为清代别求碑派“美典”的运动或趋向,其最直接的来源恐怕还是苏轼“石文而丑”和黄庭坚“凡字要拙多于巧”的语论(34)龚鹏程:《龚鹏程说中国文人书法》,海南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可见苏黄文人意趣影响之深,诫如刘熙载所云“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35)刘熙载:《艺概·书概》,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教研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13页。。作为源于先秦和汉代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气”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天地万物的本体“元气”论转化为美学上的元气自然论,成为概括艺术本源、艺术家创造力和艺术生命的一个总括性范畴。(36)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25页。“士气”指的就是“书卷气”,或称“士夫气”,强调的是在书写中所体现出的遒劲流利、自由洒脱、笔致空灵的形式美感,多呈现在以行草书体书写的用于亲戚答问、友朋来往、抄写诗文等轻松随意的书写场合,体现出文人的品性、爱好、学养和情趣等。“书卷气”从何而来?苏轼道破了其中的奥秘:“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37)苏轼:《李太白碑阴记》,见《苏文忠公全集》卷33,明成化刻本。“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38)查慎行著,王友胜点校:《苏诗补注》卷21《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培植书法“书卷气”最好的办法,就是树立独立人格、饱读诗文辞赋,以及浸润临习法帖,以学养领字,以此去俗脱俗。黄庭坚在《跋法帖》中曰:“宋儋笔墨精劲,但文词芜秽,不足发其书。子瞻(苏轼)尝云:‘其人不解此狡狯,书便不足观。’”(39)黄庭坚:《跋法帖》,见黄庭坚著,白石点校:《山谷题跋》,第55页。这正是从艺术综合的视角指出了客观存在的以文发书现象。强调书法之于读书和学养的关系,在宋代蔚然成风,成为书法家创作的普遍心态。
第二,文风文气对书法章法的节奏和贯气有一定影响。苏轼善以“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40)苏轼:《自评文》,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6,第2069页。评文,又以“万斛泉源”(41)苏轼:《自评文》,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6,第2069页。自夸。读苏文总给人一种跌宕起伏的如潮气势,如云水般流动多变而又自然率真。苏轼在书写自作或抄写他人成熟的文学作品时,特别是在创作行、草书时,在无意识的日常书写中必然将这种文气贯穿在书作的笔法、结构和章法中,使作品从整体上一气呵成,文气氤氲,神形具备。从苏轼的存世墨迹看,无论是苏轼的题跋、笔记等小品文,还是苏轼的诗词如《黄州寒食诗》《梅花诗》《赤壁赋》等名作,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这种现象。这种书艺章法的诞生,除了书法形式本体的自律性功能外,文气的辅助作用不能忽视。在符号论美学中,苏姗·郎格认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符号。同时,作品中也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个别符号。如苏轼《黄州寒食诗帖》中的“年”“中”“苇”“纸”几个字的最后一竖直接与下一字相连,缓解了整幅作品结构字字紧密的压抑感,留出的空白增加了自然舒展的气氛,而又给人一种直刺心灵的触痛感。这些长竖没有丝毫突兀之感,所形成的节奏和气势恰与作品激愤、痛苦、屈辱而又不安、爆发、倾诉的整体情感和氛围相吻合。作为个别的艺术中的符号,与作品的整体形式有机结合,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而在总体风格上又能体现书与文同气共意的美学意味。
第三,文意对书法创作具有一定的唤情催兴作用。“兴”是中国艺术独特的创作美学范畴,强调的是外物对心灵的触发。兴到作书,中国一流书迹的创作完成,都是在一种特殊的兴发之下所展现的生命意趣。那么如何才能触发作书之“兴”起呢?孙过庭曾在《书谱》中提到心情、材料、纸墨、天气等可以触发创作状态,王羲之、苏轼等也都有借酒创作的经历。反映文学题材的文辞作为书者主观世界与艺术形式之间的纽带,贯穿整个创作过程,当然同抒情气氛的确立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42)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35页。作为内容的文意不但能促成书法创作的神思、气势和情感,而且还有可能形成书法创作时的书文“应感 ”现象。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提出的将“成竹在胸”(43)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65页。的审美意象,通过笔墨变“胸中之竹”(44)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65页。为“手中之竹”(45)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65页。的创作过程恰好可以说明在特定的创作条件下,书法家由于受书写所反映的文学题材及文辞内容的感染、启发和孕育,在“文—情”的触引下,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体现为书与文的相与浚发,最终达到“身与竹化”(46)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65页。,文境与书境浑然一体。《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至黄州的第三年所作,政治上的诬构和倾轧给苏轼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伤痛。由于文辞的孕育和激发效应而使苏轼产生了强烈而丰富的内心体验,此时苏轼利用先前习得的书写技巧写下了这两首诗,文辞作为中间物连接着作者的生活感受和书法构成形式,使书写的各种笔调和形式成为苏轼谪居黄州心境和情绪变化的反映,实际上文辞的作用是通过其背后的生活感受所呈现的。“从书家选择书写对象开始,直至书法作品最终完成,所书之文的文意对于书家的书写而言,一直会如影随形,书像、书意永运不会忘却字像、字义是它的源初和母本。”(47)赵宪章:《文学图像论》,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06页。通过书写之意来传颂、彰显文学之意,自然成了书法创作的不言自明之理。
第四,文意文风影响着书家书写作品的风格类型。书家经常书写的文学作品,最能体现书家的审美个性,这自然是由于书家与所书内容精神上的共鸣或与作者兴趣爱好、人格品行上一致的原因。如前所述,苏轼喜欢书写楚词、陶渊明和柳宗元的作品。他曾录陶渊明诗作并跋云:“予常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48)苏轼:《东坡题跋·录陶渊明诗》,见《丛书集成初编》第159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苏轼《和陶渊明诗引》曰:“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49)爱新觉罗·弘历编:《唐宋诗醇》,第1119页。“绮”“腴”既是陶渊明诗的特质,也是苏轼书法的特质。从1081年苏轼在黄州流放时第一次有意效仿陶渊明作《东坡八首》始,到1092年他任扬州太守时偶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再到1095年贬谪惠州时决定从《和陶归田园居》再始,尽和陶诗,终于在最终流放地儋州完成,并在1100年流放结束后将全部四卷本109首和陶诗面世,和陶诗使苏轼诗歌进一步转向平淡自然,然而苏轼的“平淡”是领悟了最高技巧之后的“灿烂至极”。(50)苏轼:《与二郎侄一首》,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佚文卷4,第2523页。至于促使苏轼多年效法陶渊明的内在动力,既有对其人格的仰慕,也有对其诗歌文学价值的认可,甚至也包含着与陶渊明刚拙性格和人生经历相类似的暗示。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多次书写《归去来兮辞》等陶渊明诗的缘由了。苏轼一生喜欢过的书家类型不拘一格,从杨凝式、徐浩到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其审美倾向变化较大。他早年追慕唐朝的丰腴厚重,晚年服膺魏晋的平淡天成,这和他的诗风一样日益趋向平淡自然。所以,苏轼爱书《归去来辞》《赤壁赋》等文学作品,都是由于所书文学作品的文意、文风和书家的情性、书风有着某种异质同构之处。正如刘熙载《艺概》所云:“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51)刘熙载:《艺概·书概》,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教研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06页。
上述文意对书法的影响虽不易言说,但绝不是臆造,是真实存在的现象。有宋以来,自成一格的诗人和书法家的姓常与“体”字结合起来,以此描述他们的个人风格,例如颜体(颜真卿书法的个人风格)、白体(白居易诗歌的个人风格)、苏体(苏轼诗文与书法的风格)等,艺术家的物质身体与他的风格合二为一。(52)Peter Charles Sturman.Mi Fu:Style an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 Northern Song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6-7.苏轼艺术创造力的呈现不拘于文学艺术门类和领域,哪怕各门类的文学艺术各有自身的技巧、物质载体和表达方式,他的作品总能完整地表达其品行、学养和情感等主体精神的真实状况。当然,上述诗文与书法之间的交融共生虽也涉及到了气、意等审美范畴等方面的内容,但其出发点还主要是从诗文与书法自身规则着眼所进行的讨论,至于苏轼诗书之形而上的追求以及人文性等精神层面的会通之处,则另当别论。
三、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成因
文学与书法的互融共生,为何到宋代才达到深度融合的程度呢?仅就唐而言,亦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文化思潮、学术和艺术形式,唐文化甚至达到了“古典文化的巅峰”(53)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为何各种文艺形式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唐朝的各门文艺都朝着各自的方向深耕细作,当时的学术和文艺整体上倾向于专门化,一人很少兼顾多门学问和技艺,如杜甫专注于诗歌,有“语不惊人死不休”(54)周啸天主编:《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的志气;又如草圣张旭善草书,有“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55)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教研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91页。之论。那么,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众多,文学与书法又为何只在苏轼(以及其他少数士人)身上实现了深度融合?这与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1.文道之辩:“吾所谓文,必与道俱”
中国美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就是强调“道”作为文艺价值的来源。而“文”的原意,《说文解字》解释为:“文,错画也。象交文。”(56)万献初讲授,刘会龙撰理:《说文解字十二讲》,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页。《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57)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29页。因此,古人对于“文”的认知都是非常具象的视觉呈现而非抽象的思维。在宇宙层面,“天文”是道在现象界的呈现,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宇宙之“文”来获得对“道”的悟识。《易·系辞上》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58)陈鼓应、赵建伟注译:《周易今注今译》,第569页。刘勰《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征圣》《宗经》以作“文”的枢纽,阐释了道、圣、文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59)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5页。天地之道通过圣人的“文”彰显出来,圣人通过“文”呈现天地和人类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60)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第146页。此处之“文”,包括了文字、文学、文章,学术、文化,以及一切事物的形状、色彩、纹理、声韵、节奏等诸多含义。(61)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第147页。从天文、地文推演至人文的“自然之道”,每一种“文”都意味着“道”的一种自我呈现方式,“文以明道”成为唐宋古文家们不断重复的为文之本,作为人类审美模式的表达方式,文学艺术自然也是表达道的工具。
自宋太祖、太宗结束唐末五代混乱局面建立大宋以来,偃武修文;加以真宗、仁宗两朝休养生息,国内安定,上至帝王,下迄庶民,或留心诗文,或寄情书画,其文艺之盛,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6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邓广铭:《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文学艺术不仅受一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一时代文艺思潮的浸润。苏轼继承了中晚唐以来古文运动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文学传统,强调“有为而作”(63)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32《论语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0页。,主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6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第3319页。。苏轼眼中的“道”更具有综合性,是“多元一体”的(65)Peter K.Bol.This Culture of Ours.1992:254-299.,更能显现在诗词、散文、书法等多种文体和文艺门类中。相比较而言,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周敦颐受王安石经术文章观的影响,提出了“文以载道”的命题(66)转引自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第255页。,这种轻视文章的态度到了程颐那里甚至变成了“作文害道”的观点(67)转引自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第251页。。正如包弼德所言,理学家朱熹一路代表了一条渐趋狭窄的思想传统,以道德意义上的“道学”取代了苏轼所代表的“文”的多样性。(68)Peter K.Bol.This Culture of Ours.1992:340-341.那么在苏轼眼里,通过什么样的文艺实践形式才能达道呢?
2.修道之别:“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
苏轼与禅师交往密切。1091年,苏轼为即将离京的钱塘僧思聪作《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一文,目的是印证思聪求道的艺术造诣。他在文章的开篇首先提出了“一六”说:“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见。”(69)苏轼:《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第325页。具有统一性的“天一”与多样性的“地六”相互结合产生了水,水便成为得道的象征,“六一说”暗示了道是从多样性与统一性、知识与实践的结合中产生的想象。苏轼关于“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70)苏轼:《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第326页。的求道描述,也让人联想到《周礼》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如果把“一”理解为智慧,“六”理解为多种文艺修养的话,那么二合一的结果就是水的生成,“使聪日进不止,自闻思修以至于道”(71)苏轼:《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第326页。,而水则象征着僧人的最高目标——得道。思聪学艺求道的途径是自琴、书而诗,最后到达“法界海慧”(72)苏轼:《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第326页。,属于“慧生定”的具体例证。苏轼认为得道的方式是多样的,而在得道的意义上,所有方式的效用都是一样的,但在强调各种法门“发其巧智”(73)苏轼:《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第326页。的同时,也暗含了他对艺术手段的偏爱:第一,“诗法不相妨”(74)苏轼:《送参寥师》,见《苏文忠公全集》卷10,明成化刻本。,在唐末以来翻译佛法和讲解佛法不被重视之后,诗歌也就成了另一种得道的手段;第二,禅宗提倡在日常中悟道,那么书法自然也可以作为禅修的手段,只要它的目的在于培养禅定之心。(75)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因此,书法也是一种得道的方式;第三,在禅师思聪的禅定中,苏轼提出了“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76)苏轼:《送钱唐僧思聪归孤山叙》,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第325-326页。的观点,也就是研习多种艺术的僧人比单纯修习佛法的僧人得道更快,这显然与苏轼儒学的文道之辩相一致,而“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苏轼也由此论证了诗、书、琴尤其是诗作为求道手段的合法性,所以诗歌是最有效的得道方式。
那么为什么诗歌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还有差别呢?苏轼对文学与书法统一性和差别性的认识受到了天台宗的影响。禅修、艺术和实用技艺三种不同的悟道方式,以及文学与书法各门艺术在通向求道的同一目标时,在悟道的质量、速度和效力等方面还是有差别的。1095年苏轼在流放惠州期间所作的《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借用《金刚经》和《维摩诘经》中的两个典故阐发了佛学“以无所得故而得”(77)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2,第390页。的意旨,认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78)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2,第390页。。佛法是一个统一体,即使各种技艺之间,甚至手工匠人与如来之间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差别在于程度上的不同。就“道之大小”(79)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2,第390页。而言,大菩萨和如来之间也有天壤之别。正因为没有定法,求道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求道,因此虽“皆以无为法”,但求道的途径、方式和程度仍存在差别,不过这种差别是在本质一致基础上超越形式之后的差别。
3.差别之因:“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80)苏轼:《题笔阵图》,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第2170页。
苏轼强调文学与书法互文会通,但是并不混淆不同文体、艺体以及相互之间的界限。各种文体、艺体由于其体裁形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自有其独立的审美特征,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要根据表现现实世界和艺术家内心感悟的需要,结合各门艺术的长短优劣,选择适合表达效果的艺术形式。同时,苏轼认为各种文艺形式之间也有先后高低之别,如其所谓“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为什么在苏轼的眼里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卜寿珊认为,这是不同技艺在社会上的实用程度不同导致的。(81)卜寿珊:《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皮佳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在中国传统文艺中,诗文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82)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承载着政治教化的功能,能给作者带来更高的声望,其地位自然比书画要高。宋朝科举考试取消以书取仕科目,实行誊录制,导致士人对书法实用性和法度意识的欠缺,再加上苏轼继承了欧阳修作字“自是一乐事”(83)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30《试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75-1986页。的观念,主张“适意无异逍遥游”(84)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见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6,第236页。,将书法作为事业、文章之余事,更强调书法的非功利性和游艺功能。
苏轼关于文学与书法边界和差异性的认知,也与他的哲学观念有关。苏轼把文学与书法作为求道的艺术手段,但是这些所谓被视为得道的物质形式恰恰又是有限的,对于终极自然的“道”而言仍是一种障碍。苏轼在《墨妙亭记》中表达了这种忧思:“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85)苏轼:《墨妙亭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55页。受庄子“物物不物于物”(8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09页。观念的影响,苏轼曾在为好友王先新修建的藏画楼宝绘堂所撰的记中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87)苏轼:《宝绘堂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56页。从物质技术上讲,书法爱好者、收藏者都有“留意于物”的毛病。苏轼自己少时亦有嗜好书画收藏之病,在内心反复斗争后,才达到了“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88)苏轼:《宝绘堂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第357页。的境界。
苏轼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没有物质性的。苏轼最喜爱的诗人陶渊明曾设无弦琴,苏轼欲“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89)苏轼:《和陶东方有一士》,见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41,第2267页。。诸门艺术中,诗歌的物质性最小,更具纯粹的思维形式,可以不依赖笔墨纸张等物质性条件而以口头形式完成。书法学习则意味着消费物质性资料。书写者需要大量纸张来练习,苏轼曾开玩笑地说:“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90)苏轼:《墨宝堂记》,见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第374页。诗歌的相对无物质性意味着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具有物质性的书法其自由则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表明其在求道之路上自然比不上有高度自由的诗歌。
余 论
近代美国心理学家S.阿瑞提认为,“天才是由于在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各种文化要素产生了有意义的综合。……实际上,有意义的综合,就是创造过程本身,它是那样富于意义,并且不可预料”(91)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苏轼文学艺术感染力的来源,被阐释为他天性的表达和天才的流露(92)卜寿珊:《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皮佳佳译,第201页。,能达到苏轼这样成就的艺术家毕竟是少数。作为“全能”型文学艺术家,苏轼顺应文艺的时代要求,开创并成功实践了文学与书法艺术综合论,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所能达到的理论和创作高度。
苏轼的“诗书一体”观,对宋之后的文艺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文人群体中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文字、文学、书学等关联为一体的结构性关系中历史地解读和创作诗文书画印石园林诸门艺术。在这一流变中,变化的是随时代发展的艺术风格,不变的是植根于多种艺术中的文人精神。(93)潘静如:《诗、书、画的精神会通与审美边界》,《艺术学研究》2019年第3期。苏轼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不同于20世纪以来跟随西方艺术发展的可能道路:面对近代以来学科分化的格局,以综合、交叉、兼通的辩证思维,还原古代文的观念,回归文学与书法融合会通传统,重建丢失的大传统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