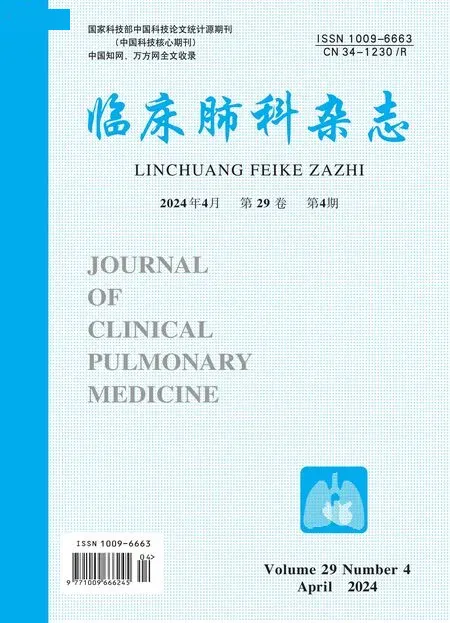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贫血的研究进展
罗苗 曹晓红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定义为一种异质性肺部疾病,其特征是由于气道异常(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和肺泡异常(肺气肿)引起的慢性呼吸道症状(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和恶化),导致持续性、进行性的气流阻塞,其会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甚至造成死亡[1]。 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3万人死于COPD[2],COPD是第三大死亡原因(按年龄标准化死亡率计算)[3]。COPD指南指出可出现肺外合并症,例如贫血、代谢性疾病、精神疾病[1],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治疗难度增加和死亡风险增加[4]。红细胞增多症与贫血均为COPD合并症[1],但由于家庭氧疗普及等原因,贫血比红细胞增多症患者更常见。目前COPD患者合并贫血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将主要在炎症-铁调素-铁转运蛋白、炎症-铁调素-EPO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这三大方面进行综述,以增强临床医生对机制的理解,从而指导治疗。
一、发生机制
1.炎症-铁调素-铁转运蛋白
COPD是一种全身性炎症性疾病,COPD合并贫血的具体机制尚未阐明,但至少与炎症相关,主要是通过炎症-铁调素-铁转运蛋白途径来影响体内铁的分布,从而引起铁利用障碍。铁调素是一种主要由肝细胞产生的25个氨基酸的肽激素,但只有肝细胞合成的铁调素才能调节全身性铁稳态。铁转运蛋白(Ferroportin,FPN)是唯一已知的细胞铁输出者,铁调素通过与FPN结合起作用,导致FPN在溶酶体内内化和降解,细胞铁输出减少。血浆铁或铁储备增加以及炎症期间刺激铁调素生成。由于FPN 在十二指肠细胞、巨噬细胞和肝细胞中高表达,铁调素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调节铁稳态:控制膳食肠道吸收、巨噬细胞回收衰老红细胞和组织铁储存中的铁。COPD最常见的贫血是慢性病性贫血,炎症细胞因子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它可以刺激铁调素的生成,抑制铁从肠道细胞进入血液、巨噬细胞释放回收铁减少及细胞内不稳定铁增多,最后使红细胞使用铁障碍。从分子层面来说,血浆铁或铁储备增加或炎症刺激可以在转录水平上调节铁调素的表达,炎症介质诱导,特别是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其主要通过JAK-STAT3信号通路触发铁调素转录,尽管炎症也可能通过TGF-β/BMP超家族配体刺激铁调素[5]。
2.炎症-铁调素-EPO
炎症不仅干扰红细胞对铁的利用,还通过炎症-铁调素-EPO途径影响红细胞在骨髓中的正常发育。红细胞在骨髓的发展过程主要如下:干细胞→红系祖细胞→原始红细胞→早幼红细胞→中幼红细胞→晚幼红细胞→网织红细胞→成熟红细胞。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在早期红细胞生成中至关重要:在与红系祖细胞的红系爆式集落形成单位(Burst forming unit-erythroid,BFU-E)的EPO受体(Erythropoietin receptor,EPOR)结合,尤其是幼红细胞集落形成单位(Colony forming unit-erythrocyte,CFU-E)时,它通过JAK2-STAT5激活红系基因的表达信号,并启动转铁蛋白受体1(Transferrin receptor 1,TFR1)增加铁摄入。铁在血红蛋白合成中起主要作用,血红蛋白合成发生在终末红细胞生成中,即从原始红细胞阶段到网织红细胞。既往多项研究表明,炎症因子会抑制肾脏产生EPO或使骨髓对EPO产生抵抗,但少有综述对其中的机制进行总结。
炎症导致铁调素水平升高,从而使循环铁水平降低。张德良等人表明,在循环铁水平低的条件下,维持Hb各组分之间平衡的调节机制一方面通过铁调节蛋白1(Iron regulatory Protein 1,IRP1)-缺氧诱导因子2α(Hypoxia-inducing factor 2α,HIF2α)轴抑制EPO的产生,另一方面通过抑制乌头酸酶来抑制红系成熟[6]。此外,Scribble是受体运输的调节因子,红系可利用循环铁低时,抑制Scribble的表达,进而抑制转铁蛋白受体1(Transferrin receptor 2,TFR2)的表达,从而减弱对EPO的敏感性[7]。TFR2是红细胞生成的调节剂,与EPO受体(EPOR)的作用保持一致。使用红细胞中TFR2特异性缺失的小鼠,红细胞对EPO的敏感性降低,表明TFR2增强成红细胞对EPO的敏感性[8]。因此,通过调节红系前体的EPO敏感性,TFR2可以作为红细胞数的控制系统,以保持红细胞生产和可用铁之间的正确平衡。Sala E.等人研究表明,COPD患者中炎症因子和EPO成负相关:AECOPD组中的EPO水平[(0.46±0.32)mU/mL]明显低于稳定COPD组[(1.05±0.23)mU/mL],这可能与全身炎症的爆发有关[9]。COPD患者的EPO水平与氧饱和度以及血红蛋白(Hemoglobin,HB)和血细胞比容(Hematocrit,HCT)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10]。Ahmed G.El Gazzar等人研究显示,COPD(Ⅱ、Ⅲ)级患者的EPO水平明显高于(Ⅰ、Ⅳ)COPD患者,缓解期高于COPD加重期[10]。这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此外,该研究还得出结论,COPD贫血患者的EPO水平明显高于非贫血COPD患者[10],这可能与EPOR对EPO敏感性下降有关。
总的来说,炎症细胞因子参与了COPD慢性贫血的发生过程,这其中包括炎症-铁调素-铁转运蛋白、炎症-铁调素-EPO这两大轴。动物实验发现,炎症细胞因子,比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可通过抑制中枢和外周食欲来影响铁的摄入[11-14],参与贫血的发生。炎性细胞因子,如IL-1,它增强了巨噬细胞摄取和破坏红细胞的能力[15],也可引起贫血的发生。α-1抗胰蛋白酶缺乏作为COPD三大发病核心之一,最新研究表明α-1抗胰蛋白酶缺乏可使铁调素水平升高[16],也参与了贫血的发生。
3.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肾素-血管紧张素(Renin angiotensin,RAS)的激活可能增强COPD患者的红细胞生成,并促进红细胞增多症的发展[17]。RAS增加红细胞质量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目前可用的证据表明,RAS的活性八肽血管紧张素Ⅱ参与了红细胞生成的调节。首先,血管紧张素Ⅱ是一种传出小动脉的选择性血管收缩剂,它会减少肾小管周毛细血管的血供,导致肾小管间质缺血,并影响缺氧诱导因子1,从而增加EPO的产生和分泌[18]。另一方面,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 Ⅱ,AT1)可能作为红细胞祖细胞的直接生长因子,通过激活其表面特定的血管紧张素Ⅰ受体(Angiotensin receptor Ⅰ,AT1R)[19]。
COPD可同时存在多种合并症,其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为55%,冠状动脉疾病为10%,充血性心力衰竭为11%,糖尿病为22%[20]。RAS阻滞剂已经作为所有这些共病的基础治疗方法,并被广泛用于COPD。如果血管紧张素Ⅱ刺激红细胞的产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ARB)失活与降低红细胞压积的作用和或贫血可能就有关[21]。
二、治疗方法
关于COPD合并贫血患者的规范化治疗,目前尚无指南指导。有研究表明,COPD合并贫血患者的血红蛋白每增加一个单位,死亡风险就会降低5%[22]。因此,本研究将针对以下方面进行阐述,这其中包括铁替代疗法、红细胞输注、铁调素拮抗剂、促红细胞生成素刺激剂 (Erythropoietin stimulator,ESA)治疗、PHD抑制剂、SGLT-2抑制剂。
铁替代疗法包括口服补铁和静脉补铁,口服补铁会因铁调素升高而抑制肠道铁的释放入血而疗效欠佳。静脉补铁避免了肠道细胞的释放限制,Martín-Ontiyuelo C.等人研究表明,静脉补铁可改善稳定期COPD缺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23]。在活动性感染患者中,炎症性贫血(AI)实际上是身体对入侵微生物的一种防御策略,以限制病原体的铁可用性,也称为“营养免疫”。对这些患者进行AI治疗,特别是补铁,不仅会随着毒力增加而促进病原体生长,还会损害宿主对病原体的免疫应答,此外还可因铁过载引起氧化应激,因此,静脉补铁会有导致COPD的发生、发展和感染不易控制的风险,不建议静脉补铁。
研究证明,输血和静脉补铁一致,虽对COPD患者均有益处,但过量的铁同样会造成不利影响。每毫升红细胞输血含1毫克铁,或每单位输血超过200毫克,有效地绕过了控制铁摄入量的调节机制,而过量的铁可能最终会导致毒性和器官损伤。因此,输血也受到了限制[5]。
研究表明,铁调素不仅可以作为诊断炎症性贫血的新型生物标志物,还可以作为新兴的治疗靶点。目前正在开发几种拮抗铁调素的策略,包括减少内源性铁调素的产生(铁调素刺激途径的拮抗剂,如骨形态发生蛋白或IL-6信号传导),中和铁调素(抗铁调素抗体或工程蛋白或基于核酸的结合剂,如抗金霉素和Spiegelmers),以及使用抗铁转运蛋白抗体或小分子(如呋喃硫胺)干扰铁调素与铁转运蛋白的结合。使用不同的铁调素拮抗剂的实验性治疗改善了几种炎症性贫血动物模型中的贫血,但针对潜在疾病过程的已建立和新型抗炎疗法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可能使人体试验具有挑战性[24]。
ESA是红细胞生成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因炎症性贫血与EPO关系的复杂性,使 ESA的应用受到了限制。首先,细胞因子不仅抑制EPO的产生,还抑制EPO介导的信号传导[25],并直接损害红系细胞增殖和分化[26]。ID还通过其对Scribble表达的影响对红系细胞中的EPO信号传导产生负面影响[27],但也在后期钝化红系分化[27]。
PHD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ed factor,HIF)的降解,来模拟HIF对缺氧的生理反应,调控靶基因的表达,如促红细胞生成素。 HIF是一种异二聚体,由α和β单元组成。这种异二聚体易位到细胞核并与缺氧反应元件的DNA序列结合。β单元始终存在(HIF-β),而α亚基有三种亚型(HIF-1α,HIF-2α和HIF-3α),其活性主要由其降解速率控制。在常氧中,HIF-α亚基被脯氨酰羟化酶结构域(Prolyl hydroxylase domain,PHD)酶家族羟基化,其中有三种亚型:PHD1,PHD2和PHD3。羟基化的HIF-α亚基被VHL介导的泛素化降解。在缺氧下,PHD的羟基化活性受到抑制,导致HIF-α积累并与HIF-β结合,导致缺氧反应基因的转录增加。此外,PHD抑制剂可通过降低铁调素和铁蛋白水平来增加血红蛋白水平。日本已经推出了五种缺氧诱导因子-脯氨酰羟化酶抑制剂(Hypoxia-inducing factor-prolyl hydroxylase inhibitor,HIF-PHI):罗沙司他(roxadustat),达普司他(daprodustat),伐度司他(vadadustat),依那度他片(enarodustat)和莫立司他(molidustat)。Roxadustat还获准在中国,欧盟,英国,智利和韩国上市。有研究表明,在透析患者中对促红细胞生成素低反应的32人中,将促红细胞生成素改为Roxadustat,并进行24周的随访。15例(占48.39%)达到血红蛋白目标水平,16例(51.61%)未达到目标水平。比较上述两组的基线情况。未达到组超敏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2和血清铁蛋白水平高于实现组,残余肾功能、血清白蛋白、铁、转铁蛋白和总铁结合力水平均低于达到组[28]。Zheng Qiyan等人研究表明,HIF-PHI 可促进铁的利用并减少静脉铁剂治疗的使用。HIF-PHIs,如罗沙司他,维持独立于炎症状态的红细胞生成反应,而ESA由于缺铁和炎症而反应迟钝[29]。罗沙司他在我国肾性贫血患者中广泛应用,而COPD合并贫血与肾性贫血有相似的发病机制,该药在COPD合并贫血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合并症药物的合理选择可能对纠正COPD合并贫血患者有价值。与ACEI/ARB类药物作用相反,有多项研究表明,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Inhibitor of 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SGLT-2i)可能调节造血和刺激RBC,具体的介导途径尚未完全明确,高度提示其可诱导EPO表达或分泌,从而增强造血过程[30]。目前涉及三种可能的信号通路:其一,氧化应激可降低造血功能,SGLT-2i可降低近端小管周围的代谢应激及激活HIF-2,进而促进EPO的生成。其二,缺氧可抑制EPO的表达和释放,SGLT-2i可减少肾小管间质组织缺氧,增加EPO的生成。其三,SGLT-2i可增加循环中的酮体,从而诱导造血[31]。在最近的结局试验中,SGLT2抑制剂在RAS阻断的基础上给予的血细胞比容升高可能有助于获得心肾保护[30]。
三、小结及展望
COPD合并贫血的机制不是十分清楚,目前对炎症-铁调素-铁转运蛋白、炎症-铁调素-EPO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进行了较多研究,COPD合并贫血发病机制的复杂性,输血、补铁及ESA的治疗效果受到限制,铁调素拮抗剂和PHD抑制剂和SGLT2i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