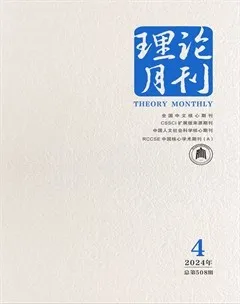地理叙事的美学意义
邹建军 王冠含
[摘 要] 美国华文作家苏炜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具有独特的地理叙事特征并体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可贵理念。其长篇小说通过构建奇异的地理空间结构,塑造奇幻人物形象,借助地理意象和景观的象征与神话修辞,展現出浪漫主义美学风格。《小鸟依人》《独自面对》等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因植根于浪漫主义美学中对自然地理的敬畏之情,进一步发展出鲜明的生态美学风格。地理叙事在构建这两种美学风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作家提供了创作方法,更为批评者提供了解读浪漫主义和生态主义作品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 苏炜;地理叙事;浪漫美学;生态美学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4.016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4-0153-08
作者简介:邹建军(1963—),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冠含(1983—),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地理叙事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重要术语,指的是“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 以地理景观、地理空间等地理因素作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 艺术传达的重要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艺术传达上产生了创造性的意义” 1。“地理”一词虽然泛指“天地之物”2,但和室内空间相比,地形、地貌、动植物等自然景观及地域风俗、文化建筑等人文景观显然更具有地理叙事特征。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重在对城市空间的描述,“狄更斯的伦敦,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的巴黎,现实主义大师们对城市描写的精细程度似乎经得起地理学家的考证”3。相对而言,古希腊的神话和小说、18世纪的启蒙文学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则构建了更多的自然地理意象和广阔的地理空间。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生态文学的兴起,其中的自然环境和地理因素以新的形式得以呈现。当代华文作家苏炜的小说在地理叙事基础上,上承浪漫文学的崇尚自然和奇妙想象,下接生态文学的绿色之思,构建出作品的浪漫与生态美学风格。
苏炜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写作中就崭露头角,也是“中国大陆背景的海外留学人中,最早开始进入‘留学生文学与后来的‘新移民文学创作的”1。其文学创作虽然数量不多,却独具个人性情和特色。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长篇小说《迷谷》《米调》等作品。关于《迷谷》,学者主要关注了其中的“现代性”2、“迷幻玄想”3、“地域文化”4等特征;关于《米调》,大家更关注其对知青精神的重构和反思5,对“人性变异”的刻画6,对信仰的追寻等7。就其小说整体而言,有学者指出其中蕴藏着“理想主义的担当意识”和“学院派温情的批判质疑色彩”,实现了“新移民文学本质性超越”8;也有的指出其小说“以人性剖析统一地理诗学和历史诗学,小说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政治寄寓”9。还有的学者从叙事特色的角度解读苏炜小说,论述了其复调叙事特征和叙事中的异域色彩10。此外还有一些访谈和对话性文献,对作者及其文学创作有多方位探讨。以上研究中,一方面侧重小说研究,对其文学创作缺乏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对其创作方法和美学特征的关系还鲜有涉及。基于其小说文本中丰富新奇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意象等突出特征,本文拟从地理叙事的角度切入,以期更深入全面地探讨地理叙事方法对其作品美学风格的影响。
一、叙事结构:奇异的地理空间
地理空间是地理叙事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小说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苏炜的小说具有以地理空间来构建小说结构的明显特征。《渡口,又一个早晨》中的山城藕菱渡,是一个类似沈从文《边城》中的边远山城,那里山高地远,相对闭塞,三条河流交汇,由于没有桥梁与外界连通,渡船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迷谷》中的海南岛巴灶山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空间,其中山溪环绕、杂草丛生,遍布橡胶林,还有鹦哥楠、鹿豆梅、鸡头木、花梨木等珍稀热带树木,飞蚂蟥及神秘的巨蟒,这些罕见的动植物和高温高湿、暴雨山洪等热带气候一起构建起小说极端奇特的地理空间;《米调》中的地理空间不仅奇特而且繁复,主要空间是西北大沙漠、戈壁滩,那里晃动着胡杨和红柳的影子,同时穿插了粤东闽西交界处的深山、西双版纳、缅甸等边缘地域空间。三部小说在地理空间上的共同点在于,这些空间都地处偏远具有边缘性特征,且在自然气候、地形地貌、动植物意象上独具特色,呈现出极端而奇异的地域之美。同时,地理空间也构建起小说的叙事结构,使其小说体现出鲜明的空间化结构。
《渡口,又一个早晨》是苏炜的首部长篇小说,1982年在《花城》连载。创作伊始,作者就很注重对小说中地理位置、地理空间的构思。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西南某个偏远的山城藕菱渡,小说开篇的引子专门介绍此地的地理位置:“这儿,倒因为汇聚山城下的西江三条支流——渡口前大河叫藕河,插入堤岸两边的河汊叫菱河和莲河——才换上了现在这么一个颇带点书卷气的名字。”11此外,小说的主人公卢子昆是留学苏联的桥梁专家,因在特殊年代受到冲击而隐姓埋名成了渡口的“船家水手”。他之所以恋着藕河,是因为惦念着年轻时因政治运动半途而废的在藕河上建桥的梦想。因此,渡口一地连接着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物和地理环境高度融合统一,成为整篇小说潜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渡口因为人员流动量大,小说主要人物大多在此出场并进入读者视野。此外,渡口这一位置还是连接城里和城外世界的衔接点,从而扩大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和审美视野。在后续创作中,作者对地理空间的构思得到进一步的表现和发展。
《迷谷》基本上是从地理空间着手而构思的,在谈到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时,作者说:“《迷谷》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做文章,截取时光之流中一滴水珠,把它作透视式的放大、观察。”1相对于《米调》中地理空间的阔大和多变而言,《迷谷》中的地理空间显得集中而极端,主要为海南巴灶山中的原始山林空间,此外还有山下农场空间和巨蟒所在的神秘空间。全书共十四章,只有第一章较为集中地涉及农场空间,这一空间也是整个小说的引子和远景,通过农场里人们的话语和行动,不言自明地暗示了特定的历史时间,可谓巧妙地将时间空间化了。第八章和末章讲述了神秘空间,其中第八章显然只是伏笔,是为末章的收尾做铺垫。其余章节则主要集中在巴灶山的原始山林空间中。由此小说的结构也比较清晰:首尾各自对应一个地理空间,而中间或者说主要小说情节则集中在巴灶山这一原始山林空间,是在这一狭小的空间内展开的。正是在原始山林空间,主人公路北平才会遇到入山伐木为生的流散仔,随之才有阿佩、阿秋等主要人物的出场,人物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展开,并在山林空间中不断深化、发展。路北平和阿佩之间情感、关系的进展就得益于荒林、山溪的天然之助,在原始混沌的环境中展露出生命原初的本真形态。
《米调》中的时间处于若隐若现或交错闪回的状态,而其中的地理空间及其转换却鲜明而突出。小说的主要地理空间位于西北的大沙漠,我们称之为主空间;文本中的空间还不时地转换到闽西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兵团、西双版纳乔芭寨、缅甸寺庙和山林等空间,可称之为次空间。主空间和次空间之间存在着隐喻对应的关系。小说在第八部分讲到沙漠中遇到大沙暴后,第九部分就开始讲述20世纪60年代末米调等北京青年结成“203”的秘密组织,并进行着纯粹革命行动。这显然是政治社会领域的另一场“大沙暴”。第十一部分先讲述了在沙漠中过夜的“浪漫”2,接着就转入米调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西双版纳乔芭寨和女友辞行时共度的浪漫之夜。主空间和次空间虽然快速切换,但因为二者存在内在的隐喻或类同,因此并不显得突兀反而有种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处的交相互映之美。小说在差异巨大的地理空间的交错转换中构建起小说主要框架,讲述主人公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变迁中对理想、信仰的苦苦追寻。
二、人性和自我的探寻:奇幻的人物
如果说从整体看,地理空间构建了小说的叙事结构,那么空间中的人物形象则是地理叙事的又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在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中,人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文学作品地理空间的营造是以人为中心的,对文学作品地理空间的分析也应以人为中心” 3。苏炜小说中的人物与地理空间是融为一体的,地理空间限定了人物的特征,也推动着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变化。上文论及小说地理环境的奇异、边缘等特征,其中的人物相应地也具有奇幻、原始等特点,从读者接受层面看,人物既要符合真实性逻辑也要具有相对的独立审美价值,但从创作层面看,人物仍然是虚构的且具有一定的功能,服务于文本在思想意蕴方面的艺术传达目的。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原始化特点,传达了文本对原初本真人性的探寻。《渡口,又一个早晨》中,牛皋就是这样的人。“这个粗悍的小伙子,身上总洋溢着一种未受世俗污染的质朴而野性的气息,就像一片还未开垦的荒地……”4 正因为这一特点,特立独行的“居里女士”才借他当“男朋友”以拒绝省城贵公子的追求。到小说《迷谷》中时,这样的人物已经从一个变成一群,巴灶山的流散仔阿扁、阿秋、阿佩等人,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都充满原始野性。在炎热的深山荒林中,流散户常常赤身裸体,让知青路北平感觉他们像“猿人”“小兽”一样1,过着原始群居般的生活。特别是阿佩的形象,混合着原始野性和母性的特质。这与他们远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深居荒山野林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也暗合了作者追尋自然本初人性的创作宗旨。《米调》中的主人公本是北京城里人,他身上的原始性主要是流浪在外,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慢慢形成的,形成原始性的过程也是他远离社会后逐步回归本真人性的过程。米调身上具有顽强的原始生命力,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下来,来回多次穿越大沙漠,最艰难的时候甚至靠吞食肉蛆以维持生命。同时,他和潘朵、黑皮结伴而行的生活方式同样具有原始本真的意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自然又相互扶持,体现出人性单纯美好的一面。可以说,对原初本真人性的探寻和向往是苏炜多部小说的共同主旨。作者曾谈到沈从文对自己的影响,当听到朋友说《迷谷》好像是‘文革小说中的《边城》”时,他觉得,“自己一个隐约的心思,好像被他点破了” 2。无论《边城》还是《渡口,又一个早晨》以及《迷谷》《米调》,其中所揭示的为时代社会所遮蔽的自然本真的美好人性和生活本身的诗性,都离不开文本中特定地理环境的支撑,否则小说中的人物就失去了存在的真实性,叙事也无法展开。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奇幻特质,体现了作者对自我的寻找和完善。对奇幻的最基本理解是“奇异而虚幻”3。对什么是奇幻,法国学者托多洛夫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奇幻以读者对一起怪诞事件的犹疑为基础。假如这个事件被作为现实来看待,也就是被视为想象或者幻觉的产物,犹疑可能就会消失;换言之,我们可以决定这一事件是否存在。”4 这一定义比较强调事件或故事的奇幻特征,在讨论人物的奇幻特征时也同样适用。在苏炜的几部小说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构建的地理空间是相互适宜、相互交融的,人物的奇幻性正适应奇异的地理空间,二者共同体现出浪漫想象的特质。首先是阿佩。她那种“一女多男”的生活模式,从传统家庭伦常看显得非常奇异,有学者指出“阿佩是作家的一种浪漫想象,阿佩对现有的家庭和爱情的定义的挑战也是在想象中进行的浪漫行为,在现实里大概不大可能发生” 5。其次是阿秋,他是流散仔中的一个古怪人物,也是男主角的同性恋对象,其身上的种种奇特之处使人物显得奇异而虚幻。小说中的主要叙事者路北平也认为:“他在巴灶山遇见的这位阿秋其实是幻觉的产物,他只是为着提醒他记挂着一点什么、正视着一点什么而存在于这个阴阳地界里的。”6这种元叙事的说明,似乎暗示读者可以把阿秋理解为路北平想象中的精神知己,或精神理想的投射对象。事实上,这两个人物象征了作者自我探寻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是肉身对女性的依恋,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不断追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只侧重对第一个维度的揭示,而《迷谷》则探寻了更为完整的自我:人不仅是肉身的更是精神的,二者的对立统一才是完整的自我。《米调》中的主人公有很强的传奇色彩,从早期追随革命的米调到后来流浪西部沙漠的“索罗卡拉”,他的冒险和流浪经历,似乎漫无目的又好像在寻找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这种上下求索的过程,正如段义孚所说:“求索——就像寻求圣杯的壮举一样——正是浪漫的核心所在。”1对人物自身而言,这种求索也是从自我迷失到自我救赎的过程,同样体现了人物对自我的寻找和完善。
三、象征与神话:地理意象和文学景观
地理意象和自然景观也是地理叙事的重要表现。“意象”这一概念源自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出自《文心雕龙》“神思”篇:“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2意象由作者之意和外物之象两部分构成,指出了“诗人是凭借着外物形象驰骋想象,外物形象又在诗人的情意之中孕育成审美意象” 3。地理意象强调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的应用,文体上也不像古代文论那样只限于诗歌批评,而扩大到小说、戏剧、散文等不同文体。文学景观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4。中国古代诗文中书写了不少著名的文学景观,如崔颢的黄鹤楼、王勃的滕王阁等,主要体现了抒情的文学功能。在小说文本中,地理意象和文学景观还具有叙事的重要功能,并通过象征和神话等修辞形态得以体现。
首先是地理意象和文学景观的象征性表达。《渡口,又一个早晨》创作的时代背景正是历史上拨乱反正后弃旧立新的过渡阶段,有太多时代原因造成的断裂和阻隔需要重新衔接连通,这就是小说中渡口和桥梁的象征意义。文本中卢子昆一再申请要修的桥梁,不仅仅指地理意义上的实物,更具有特定的时代象征内涵。正如小说第一章的标题中说“因为地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沟堑,把道路隔断了,所以,才需要渡口和桥梁”5, 表面上是说藕菱渡这个地方的河流和道路,深层则象征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桥梁和渡口的连接。小说《迷谷》中的标题“迷谷”这一意象不仅指小说的主要地理空间——巴灶山的山林谷地,还象征了自我的幽深内心、人性的复杂迷惑等多重内涵。甚至有学者指出“‘迷谷至少包含了自然之谷、山民世界、女性身体、迷茫彷徨、迷失于非理性世界等五种象征的意义”6。此外,小说的主人公路北平和村长家去世的女儿结了阴亲,成为“鬼丈夫”,他在山林中放牧牯牛,而山林深处的巨蟒又被奉为“蛇神”,凑成了一个“牛鬼蛇神”的世界。这些牛、鬼、蛇神在小说中既指形象本身,但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显然也象征了某一类人或某些群体。“在象征中,好像因为错觉引起了一种惊讶的心情:原以为事物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然后发现它也有一种(第二层)意义。”7从中可知象征的双重意义,就地理意象的象征意义而言,它一方面是小说中的叙事单位,指称具体的物象或环境;另一方面也指向叙事的深层意蕴,提升了小说的多重内涵。《米调》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自然景观是沙漠中的水源和海市蜃楼之景,作者显然以这些自然现象象征了人生中的某些可能的奇迹,特别是绝望中突然而至的生机和希望。在文本中,这些象征场景之后紧接着就是故事情节的转折和人物命运的转机。
其次是地理意象和文学景观的神话修辞。神话修辞指的是苏炜小说中对神话母题和原型的改编再造。《迷谷》中“巨蟒”是小说中反复渲染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这一“蛇意象”也是中西神话中常见的原型。《圣经》中的蛇扮演着引诱者的角色,是邪恶的象征。但在中国神话中,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的图文记载皆是人首蛇身,同时“人祖伏羲女娲又是龙图腾”8,这也体现出中国人龙蛇混用现象。因此,小说中的“蛇神”不仅具有某种图腾意味而受到流散仔敬拜,而且这一意象也和民族始祖神话相联系,使小说文本和神话文本产生互文共通,从而生发出深层隐喻意义。此外,小说山洪暴发及洪水后阿佩受孕的情节中镶嵌了“洪水(A1010)和最初的人类夫妇(A1270)”1神话母题,虽在这一母题基础上做了适当的改编和再造,但这种神话母题的运用却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时空视野,显示了小说厚重的文化张力。《米调》中对西夏古国和凶巴国等文化景觀的想象,同样具有某种神话意味,因为这些消失的史前文明,正是神话想象的重要内容,表达了作者希冀通过返回古老文化中以修复现代文明弊病的文化理想。
四、地理叙事与浪漫美学风格
地理叙事所展示的地理空间的奇异性、极端性,人物的原始奇幻与自我追寻以及地理意象和文学景观的象征性和神秘性,说明苏炜的小说和现当代文学中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并非一类。这几部小说的内部风格与现实主义相反,体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质。就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而言,学界已有共识,如“强烈的主观性、对民间文学的重视等”2。其中对浪漫主义诗歌的概括更为全面:“就诗歌观来说是想象,就世界观来说是自然,就诗体风格来说是象征与神话。”3这一特征虽然是针对诗歌艺术而言的,但对于包括小说在内浪漫主义文学同样适用。如上文所言,在小说文本层面,其内部地理空间结构、空间中的人物形象和地理意象的修辞技巧三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小说崇尚自然和自然人性以及象征、神话修辞的叙事特征,这些无不契合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质。事实上,苏炜小说被认为是“对‘文革小说以来盛行的写实主义的一个反拨”4。作者也自述其创作“是有意想让其诗化,是想主动地实验浪漫主义在写实小说中的应用”5。
从地理叙事的角度之所以能够揭示苏炜小说的浪漫美学风格,首先是因为苏炜小说中的地理空间、空间中的人物等地理因素本身就直观而形象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特征。段义孚认为,“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思考的极端性” 6。因此其《浪漫地理学》中所论述的自然环境是山、海、森林、沙漠、冰,都是极端的自然环境。而苏炜的三部长篇小说中其主要自然环境也是这样奇异而极端的地理空间:《渡口,又一个早晨》中的山城、《迷谷》中的巴灶山和热带森林及《米调》中的沙漠。这些地理空间奇异而极端的特征决定了小说并非是写实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叙事,而是超越日常生活的某种想象、理想的表达。正如诗人托马斯·休姆所言,“浪漫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是人类完美主义的信仰”7。与此相应,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具有脱离或超越群体和当时社会,勇于追求或自我探索的特征。《渡口,又一个早晨》中的卢子昆是留洋专家却隐姓埋名于边地山城,坚守着未完成的建桥梦想,可以说是一个“圣贤”形象;《迷谷》中的路北平远离他所属的农场青年群体,独自带着一箱书隐居巴灶山深处并因而遭遇山中流散仔,开始了其个人的冒险之旅,属于“个人冒险者”形象;《米调》中的主人公则混合了流浪冒险和英雄特质,还带了些圣徒的气息。这些人物“更多地受到内在情感和理想的推动,更倾向于脱离群体之常规,简言之,更加浪漫”8。地理意象的神话修辞方法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盛行时期的惯用技巧,远古神话本身充满浪漫想象色彩,远离人间现世的日常和文明弊病,因此作家常借神话来表达对自然的向往和对人类原初淳朴秉性的赞美。《迷谷》中的“蛇神”和洪水神话,不仅表达了对大自然威力的敬畏,同时洪水中动物的诞生以及阿佩的受孕也是对自然生命的最高礼赞。这些极端环境中的极端事件无不体现出作家的浪漫想象。
其次,更进一层说,地理叙事也是从“文地关系”的角度探讨地理要素与小说文本构成及其美学风格的关系。“文地关系”是“人地关系”的具体表现,“文学地理学首先和最直接的是要关注‘文地关系, 但没有‘人地关系也就没有‘文地关系。”1“人地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如何看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内容。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地理叙事或者说文学地理学和浪漫主义文学能够协同共振的关键。文学地理学理论的一大宗旨就是要恢复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密切联系。德国“自然哲学之父”谢林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是那些类同自然之作,能够传达出那些尚不具备完整意识的生命的悸动。”2这一观点把文学创作和自然界联结起来,也把人的意识和自然界的“无意识生命”联结起来。这与中国老子、庄子等先哲对自然的认识有共通之处。韦勒克对浪漫主义作家也有相似的论述:“他们全都认识到想象、象征、神话和有机自然界的涵义,并把这种涵义看作是旨在克服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分裂状态的伟大努力中的一部分。”3
由此可以概括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对待自然的共同之处:多相信万物有灵,将自然界加以神化,并与人的内部心灵世界存在某种联系和照应, 作家能感知这些神秘并将之诉诸笔端,从而成为天地自然的代言人。西方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卢梭、歌德以及荷尔德林等,以及中国的庄子、屈原、陶渊明、苏轼等的诗文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神秘自然观。苏炜的文学作品也可纳入这一文脉系统。但是,不论是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文人,还是浪漫主义流派的作家,他们对自然的态度都是自发的、直觉的、神秘的,而和浪漫主义密切相关的生态主义者对待自然则是自觉的、理性的,并“从人与自然的关联中开拓了人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 4。
五、从浪漫美学到生态美学
“虽然当下的精英群体认为浪漫主义是浅薄而幼稚的,但它对文化仍然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5事实上,浪漫主义的潜流可以说从未间断,如20世纪法国的存在主义思潮就和浪漫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6。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生态主义思想,与现实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有直接联系,同时也和浪漫主义思想存在内在联系,其联结点在于对自然的崇尚和依恋,因此也有学者称生态主义为“后现代浪漫”7。浪漫主义作家歌德、荷尔德林、梭罗等无不崇尚自然、向往自然。特别是浪漫主义发源地的德国,更具有尊重自然的传统。被誉为“生态伦理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去德国考察后,德国人对自然的生态和审美的态度,“特别是对鹿、森林的尊重态度,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8,促使其思想从早期的资源保护向生态思想转变,最终提出了人与土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只是“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平等的参与者而不是征服者。当然,这里的土地“并不仅仅是土壤,它是能量流过一个由土壤、植物以及动物所组成的环路的源泉”9。因此,这里所说的土地事实上也代表了自然界本身。与浪漫主义者自发地欣赏、感悟、敬畏自然不同,生态主义者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自觉地认识到“人类与整个自然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的生命与整个生物圈的生命相互关联。只有在人类与自然的共生中才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前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取得自身和谐和发展的前提”①。
苏炜早期的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等长篇小说虽然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但其对自然地理的崇尚与敬畏也孕育着生态美学的因子。长期定居美国生活更激发了作者对生态美的自觉体认,使他成为骨子里的“生态人”。这在作者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小鸟依人》和散文《犹子之谊——记大友巴顿》《莲在天涯》《站立的时光——关于树的笔记之一》等作品中得以集中体现。尤其是短篇小说《小鸟依人》,故事通过喂养跌落的雏鸟,家人与鸟相互的情感依恋到鸟的自行飞走又归来,直到最后全家以隆重仪式放飞小鸟这一过程,在温暖安全却如“牢笼”的室内空间和青草蓝天的开阔自然空间的对比中,体现出明确的生态观念:“人鸟相依——其实,世界得以界定、存活的自然生物链条,本来就是这样环环相扣、物物相依的。”②而且,小说通过自然地理叙事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惯性立场,反思了现代文明对“物性”的奴役和征服,认为人类心性的彻底解放首先在于“敬惜每一个生命的‘物性”③,体现出对生态美的价值追求。《犹子之谊——记大友巴顿》《莲在天涯》等散文作品中,狗、莲花等动植物同样成为人们平等的伙伴和朋友,表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亲密和谐关系,揭示了超越物种界限的博大情怀和精神境界。苏炜创作中的生态美学风格在北美华文文学中颇具代表性,北美华文作家中,从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到严歌苓、张翎等,都较为注重表现人物心理,特别是对跨文化语境中人的矛盾和悲剧性心理的表达,着重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不是很多。而苏炜的小说和散文作品通过地理叙事对自然界动植物进行平等凝视和审美书写,对人与自然之物相互依恋之情的款款讲述,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又彰显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之美,丰富并提升了华文创作所涵盖的范围及意蕴。
苏炜以地理叙事为基础体现出的美学风格及其转变在新移民文学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体现出对新移民文学常见的文化冲突和身份异化等主题的超越。这与美国等西方社会生态主义的蓬勃发展有一定联系,与中国当代文学中阿来、张炜等作家的创作相互呼应。其作品的地理叙事特征有以下美学意义:首先,地理叙事是一种基于自然、崇尚自然的叙事方法(对作家而言可能是不自觉的),通过这一创作方法,可以重新建立文学与自然地理的联结,构建作品的诗性浪漫和生态美学风格。其次,地理叙事作为文学批评方法,更适宜阐释描写自然或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浪漫主義或生态主义作品,从而推动以自然为大道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再次,从时代和社会层面看,地理叙事的意义在于促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推动社会生态文明进程。“美丽中国”呼唤绿水青山的自然环境,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地理叙事将从文学批评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力量,推动人们生态观念的更新进步。
责任编辑 余梦瑶
1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2参见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页。
3颜红菲:《地理叙事在文学作品中的变迁及其意义》,《江汉论坛》2013年第3期。
1江少川:《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
2参见孙利迎:《论〈迷谷〉的现代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
3参见胡传吉:《“怪力乱神”中的历史与超现实——论苏炜的长篇小说〈迷谷〉》,《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4参见王岫庐:《论〈迷谷〉英译本中的地域文化重构》,《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5参见罗四鸰:《英雄的消失与米调的归来——从苏炜小说〈米调〉反思当代小说的精神缺失》,《华文文学》2009年第4期。
6参见公仲:《人性的开拓 宏大的叙事——评中篇小说〈米调〉》,《华文文学》2005年第2期。
7参见戴瑶琴:《流浪者的信仰——比较〈米调〉与〈丛林下的冰河〉》,《华文文学》2006年第3期。
8参见李良:《苏炜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3期。
9参见颜水生:《地理、历史与人性——论苏炜小说的诗学与政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0参见罗长青:《复调·偶然性·异域色彩——苏炜长篇小说的叙事特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11苏炜:《渡口,又一个早晨》,《花城》1982年第2期。
1融融、陈瑞琳主编:《一代飞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2参见苏炜:《米调》,《钟山》2004年第4期。
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2页。
4苏炜:《渡口,又一个早晨》,《花城》1982年第2期。
1苏炜:《迷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2李陀、苏炜:《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他——关于〈迷谷〉和〈米调〉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3商务国际辞书编辑部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64页。
4兹维坦·托多罗夫:《奇幻文学导论》,方芳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5李陀、苏炜:《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他——关于〈迷谷〉和〈米调〉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6苏炜:《迷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1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8页。
2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20页。
3王先霈、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3页。
4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33页。
5苏炜:《渡口,又一个早晨》,《花城》1982年第2期。
6郑一楠:《宏大的包容 全新的转折——苏炜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华文文学》2007年第3期。
7 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国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7页。
8参见段宝林:《中华龙图腾浅说》,《文化学刊》2012年第3期。
1陈建宪:《神话解读》,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54页。
3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55頁。
4李陀、苏炜:《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他——关于〈迷谷〉和〈米调〉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5郑一楠:《宏大的包容 全新的转折——苏炜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华文文学》2007年第3期。
6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4页。
7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3页。
8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147页。
1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核心理论问题》,《美学与艺术评论》2019年第2期。
2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洪丽娟、孙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31页。
3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4徐恒醇:《生态美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5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5页。
6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洪丽娟、孙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60页。
7参见鲁枢元:《东方乌托邦与后现代浪漫》,《长江学术》2023年第2期。
8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70页。
9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5页。
1徐恒醇:《生态美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②融融、陈瑞琳主编:《一代飞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③融融、陈瑞琳主编:《一代飞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