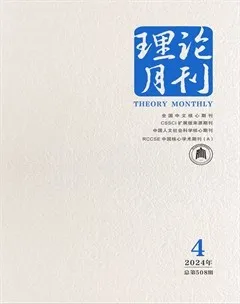重新定义“云”时代:虚拟现实的技术转场与情感逻辑
[摘 要] ChatGPT、元宇宙、虚拟现实等新的合成技术和应用场景在改变人的生活、学习方式的同时,还营造了不同于传统交互方式的“云生活”“云娱乐”“云学习”的文化形态。“云”时代的媒介技术已渗透到人的情感深处,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与技术的关系,传统认知逻辑中的主体成为技术实践过程中的一部分,被技术捕获的同时,参与并完成了与技术之载体的互动,在获得参与感的同时,又把主体的自主性交还给由主体创造的物。“云”时代的技术所营造的虚拟现实叙事正在利用沉浸逻辑和回馈机制塑造一种“情感惰性”的假象,构建了一个虚拟现实的架空模式,直击人的精神和内心困境,从而掩饰了现代性焦虑的发生,这也就构成了一个大写的时代寓言文本。
[关键词] “云”时代;虚拟现实;情感逻辑;寓言文本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4.015
[中图分类号] I06; G206; B842.6; K90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4-0146-07
基金项目: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网红打卡地的空间生产与符号建构——以秦皇岛阿那亚为例”(HB23-QN003)。
作者简介:孙立武(1991—),男,文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随着新冠疫情的远去,人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是疫情时代催生的一些特殊生活和学习方式仍然在影响着大多数人。时至今日,在任意搜索引擎键入“云毕业”,其搜索结果多达几百万条,近几年的大学生经历了特殊的学习方式、别样的课堂交互、难以忘怀的云端毕业典礼。这只是“云”端生活的一个缩影,“云会议”“云讲座”“云蹦迪”“云面试”“云拜年”等新的“云”方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体验,疫情等客观要素催生的这一系列改变,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深了人之主体对于技术的情感依赖,以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于“云”端的交流和娱乐方式,产生了“生活原本可以如此简单”“工作原来可以这么便捷”的认知。“云”时代尤其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简化了许多烦琐的程序,也催生了技术与人之间情感逻辑的变化,技术进步已经由推进生产力发展逐渐转场到对情感的“麻醉”,主体之于技术的掌控正发生着反噬,尤其是在“云”时代,主体对于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科学”“有效”“便捷”“简化”等认知的影响下,技术正在物质和情感的二元交互中制造新的矛盾。
一、资本与技术的合谋——矛盾中的“云”体验
“云”时代的衍生品是资本、技术和审美相互“博弈”的产物,技术推动型产物、资本主导型产物、审美偏向型产物等类型的划分虽然不能完全囊括“云”时代的万象,但是这些要素构成了整个“云”时代得以运转的动因。借助于技术,人们获得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便利;借助于资本,人们能够在“云”端谋生和获利;囿于审美的冲动,人们能够在“云”时代获得不同于传统的愉悦体验。事实上,“云”时代与这些动因是互为前提的,资本和技术介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技术革新带来新的符合人們需求的产物,人们的需求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引导下又会产生新的更高的要求,技术和资本便会迎合人们的需求制造新的产物。“云”时代的特性在于把这种更迭速度加快,使迭代更新的速度赶超传统的技术进步逻辑。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云”时代技术和资本的融合恰好凸显了资本的这种社会性,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性打破了时空的边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关系,虚拟现实叙事空间应运而生。“它以游戏性的叙事为核心构建起故事空间,但它的虚拟现实与现实经验完全同构同在。”2虚拟的叙事空间正在打造一个不同于以往技术逻辑的“云”时代,技术在让现实变得更简单的同时,也更容易形成对于人之情感的反噬。“云”时代的技术对于人的控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甚至无需过多的情感投入和行为显露,大数据足以捕捉到每一个体的习惯。“云”时代正在对个体形成反噬,它基于技术对于个体的捕获来吞噬个人情感的自主性,削减作为个体人的情感投入。身体的“不在场”使得个体情感存在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身体变为‘技术态身体‘无器官身体。”3单向的接受、单向度的愉悦便在这种身体缺席的场域中发生。
近些年兴起的“云课堂”让原本边缘化的慕课平台、线上课程平台在资本的助推下走进了人们的学习和生活,在把课堂商业化的同时,也改变了学习者参与学习的方式。有研究指出:“在线下学生可能胆小害羞、不善言辞,但在线上,在网络背后,又可能变得非常主动,不仅思维活跃,甚至金句不断。”4但是从授课者的角度讲,“云课堂”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单向的输出,网络虽然提供了比线下课堂更多的互动方式,但是技术的便捷并没有达成情感的共鸣。换言之,授课者再多的情感投入也只是被技术这一虚拟空间的漩涡吸食,而受众更多地搁置自己的情感,呈现为一种“闲置”状态。这种情况走向另一个极端则是网络世界完全掌控主体的情感,而且是一种对于人习惯的持续性影响。
“云”时代的技术除了参与人们的学习之外,还带来了娱乐方式的改变。网络直播充分发挥了手机直播的优势,依靠着门槛低、受众广、盈利多的特点,吸引了更多的人投身于直播行业。随着众多流水线式的网红诞生,庞大的粉丝群体也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迅速出现在网络社区之中。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下,网络直播中那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正在转变为双向的交互生产,受众相较于以往投入了更多的情感参与网络直播这一文化形式的构建。观看者化身为虚拟的人物在一个由媒介技术打造的虚拟空间里通过“打赏”“投币”“点赞”等消费机制完成互动,这些虚拟形象、动画模拟如今正在以符号化的方式从媒介互动的主体拟真走向主体“沉浸”情境的情感真实。如果说在过去,“(观看者)通过网络直播所提供的无处不在的‘屏幕,人们在‘镜面之中不停地捕捉他人的生活”5。那么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如今媒介拟真的实现更多地依赖受众主体的参与和共情而得以实现,无论是“云蹦迪”1,还是“云答题”2,“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是交互方式的变革,交互方式正从传统的触摸交互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多模态的拟人交互转变”3。这种交互转变的背后是一种资本助推消费行为发生的运行机制,无论是什么样的游戏场景,受众想要获得快感体验的前提是氪金4行为的发生,只有消费才能获得好的虚拟形象,只有投入更多的金钱才能走在参与群体的前列,这种互动性不仅增强了直播这一文化形式的参与感,同时也把媒介主体的互动行为变得游戏化。
“交互性”“沉浸感”“游戏性”这些特质如今正在掩饰资本和技术催生消费行为的本质,技术和资本正在借助媒介技术所营造的虚拟叙事空间让受众的身体和情感完全分离,身体的缺席,情感的沉浸式投入,催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情感逻辑。
二、基于沉浸、回馈两种机制的“情感惰性”形成
“云”时代的文化形式生产正在改变人们生活、学习和娱乐的方方面面,人们已经习惯于“云”的伴随。几乎没有人能够习惯于一个没有网络、没有新兴媒介的世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滋生了一种“情感惰性”。即虽然主体对于技术有着过度的依赖和顺从,但是情感并没有真正与技术融为一体,而是完全投身于技术所营造的虚拟叙事空间之中并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相对独立是因为虚拟叙事空间中的主体情感是由技术“强行掠夺”而来的,它游离于主体和媒介技术的交互机制之中,最终又将加工过的情感交还给主体,营造了一种“情感惰性”的假象。
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云”时代的媒介技术对于人的主体的逻辑关系已经由“观看”转变为“沉浸”,“所谓‘沉浸,就是人在故事中行进,而不是接受者(单纯观看者或倾听者)把自己的愿望或情感想象性地委托给故事中的人来实现”5。人们往往以批判的视角审视技术对于情感的剥离,却忽略了交互机制中的技术在完成“掠夺情感”这一阶段性任务之后,还会把融合了技术的“新情感”交还给受众,这后一阶段往往被忽视,或者被简单地与第一阶段融合。“情感”在此成为一个客体对象,“情感惰性”及其假象便在这两个阶段发生,主体的情感体验正在以“惰性”的方式维护其合法性,而技术也在以“交还”的方式掩饰其剥削性,于是两个阶段构成了一个综合矛盾体。
其实,这是一种“媒介技术决定论”向“媒介逻辑视角”的转变。“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6而当人们认识到技术对于人的主体的决定性之后,则会以批判的视野重新审视技术的发展并把“技术决定论”视作一个污名化的标签。技术与人之间并非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它是媒介技术与主体之间共生的一套逻辑体系。“媒介逻辑是媒介内容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股力量,同时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媒介逻辑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1在媒介逻辑的视角下,“云”时代的技术与人的关系也呈现为一种动态的逻辑关系。
在第一个阶段,技术将情感从身体剥离并营造一种技术和情感共生的虚拟现实场景。在“云蹦迪”的虚拟场景中,传统的观看者借由媒介技术变身为参与者,这种参与一方面是指主体情感的沉浸式投入,一方面也指个体实际操控媒介终端的实践行为。其实,在人工智能之前即人与媒介技术的融合没有这么紧密之前,人们在“云”空间中的学习、娱乐行为已经有了沉浸式的参与性,只是在媒介技术发展到将人的情感禁锢的程度之前,在看与被看的机制中,主体尽管投入了很大的情感,其肉身的实践行为还是压制了这种情感的完全浸入。比如:网络直播中的弹幕互动行为还只是一种基于粉丝文化的互动机制;网络中的礼物贡献也还是一种基于消费文化的消费行为。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虚拟现实场景是技术和人的情感共生的空间架构,情感体验在此已经凌驾于肉身的互动和消费行为。
在第二个阶段,技术将改造过的情感交还给主体,这里的“交还”是技术与主体互动机制的一部分,也是技术最为“恐怖”的一面,它营造了一种“情感惰性”的虚假景象。这里的“交还”机制又有可见和隐含两种属性,所谓可见是指技术对于情感的回馈方式具有可感知的属性,这种可感知既有视觉上的可观,又有物质奖励机制带来的情感满足。比如,“云”空间的娱乐主体往往以一个虚拟的符号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符号化的虚拟人物或名称通过氪金行为获得了不同的“出场特效”“贵族坐骑”等差异化的虚拟场景,在某些机制中还会根据消费的多少设定符号化的代表在虚拟场景中的位置,这都是一种技术将主体纳入精心布局的虚拟空间之后的持续性掌控方式。此外,传统的弹幕互动、抽奖互动都是可视化的显在的回馈方式。所谓回馈机制的隐含属性,是指以“云”为核心的娱乐和生活方式正在将祛魅的“云”现场重新赋魅,主体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云”现场乃是一种虚拟技术的营造,但还是甘愿沉浸于虚拟叙事空间。因为技术的祛魅并不能缓解现代人生活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正在孕育孤独美学的发生,个体的娱乐和交际在“云”端获得了另类的充实感,这种情感的陶醉,让原本祛魅的网络世界在情感维度上又得以赋魅。
沉浸只是技术捕获主体之情感的第一个阶段,而随着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生,“云”端除了是一个主体与技术共同构建的叙事场景外,它还是一个情感交互的博弈空间。沉浸是技术切入主体情感的一种逻辑,同时也是自我陶醉机制的构成部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技术的一个发展倾向就是用沉浸逻辑掩饰了回馈逻辑的真实存在,同时让主体在新兴的“云”端保持一种情感的相对独立,凸显了主体面对技术双重逻辑之下的主体性,营造了一种“情感惰性”的假象。
三、“云”时代的“现场主义”与现代性焦虑
“云”时代制造了一个情感内核消逝的虚拟现场,其本质在于打造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叙事空间,主体以游戏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让故事在现场得以自然地发生。何为现场?何为现场主义?现场主义是现实主义文论话语在新的媒介语境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周志强认为:“从文本呈现‘现实所追求的真实幻觉的层面来考量,就会发现,‘现实主义才是真正塑造‘现场感的文体。即‘现实主义通过隐藏叙事者或创作者的痕迹,来假装它所陈述或刻画的场景,乃是完全的真实现场的再现。所以说,‘现实主义归根到底乃是‘现场主义。”2现场主义塑造了一个建基于现实的真实幻觉场景,在媒介技术发展的今天,尤其是虚拟叙事、人工智能的时代,叙事空间中的现场感获得也更为容易。
长期以来,現实主义这一文体的主义规约性限制了人们对于现实的美好想象,把现实牢牢地绑缚于主义之上。当我们把“realism”的后缀“-lism”分离出去,得到的是一个所有人文学科都要面对的“real”,如果对其作概念史的梳理,“real”更接近一个哲学概念,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它可以是理念,可以是某种自然物质,可以是一个象征符号,还可以是一种客体存在,这些纷杂的解读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类认识世界方式的转变。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没有人忠于某一哲学概念的拷问,而是把重心完全置于个人的情感体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认识:“不必俯首于‘现实,也不必臣服于‘主义,只要拥有并忠于现实感,自然会有现实主义的创造。”1现实感掩饰了现实的发生逻辑,媒介技术的生产机制被搁置,主体的情感体验成为唯一的追求,也就是说,普通受众不会思考是什么机制让自己沉浸于一个技术打造的叙事空间之中,也不会去深思是什么样的资本推动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一个不断加速的社会中,他们只想寻求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获得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以想象的方式,以沉浸故事的方式,来缓解普遍的现代性焦虑。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动力特质之一就是“时空分离”,“时空的虚空化过程绝非一种直线式发展,它以一种辩证的形式不断推进。在时空分离过程形成的社会情境下,‘鲜活的时间(lived time)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时空切割为它们的再次重组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重组以协调不必考虑其具体位置的社会活动这一方式而展开”2。“云”时代的各种媒介技术恰好让时空分离的特质有了新的表现,因为它在分离的基础上又营造了一个新的时空叙事空间,这种分离同时隔离或过滤了主体的情感焦虑。“焦虑是本体性的,源于本体性安全体系(保护壳)本身的失灵或崩解,而这个本体性安全体系之所以失灵或崩解,则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传统惯常秩序的消失。”3传统惯常秩序的消失主要表现为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时那种自我主宰和自我控制能力的消失,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各种压力都在催生焦虑。
来自“云”时代本身的焦虑主要表现为技术对于人之理性的主宰,甚至在某一新技术出现之时,人们所表现出的被技术所替代的恐惧。比如:ChatGPT出现引发了学者的忧虑,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强调人工智能和人类在思考方式、学习语言与生成解释能力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ChatGPT使用的大語言模型,实质上是一种剽窃;齐泽克更是认为AI只能在字面上理解人类语言,把ChatGPT称为“人工智障”,但显然ChatGPT的快速发展已超出了预定假设。事实上,相较于专业领域的讨论,“云”时代之于普通大众只是一个新的叙事空间,相比思考技术到底能不能替代人来讲,更多的人选择放弃自我主宰和自我控制,甘愿坠入由技术所营造的叙事空间,选择自觉接受规训。因为在这样的空间里他们可以获得想象,获得满足。新技术在短视频、直播等场域中正在以新的情感逻辑缓解现代性焦虑,相较于以往的符号想象、审美语境、拟态环境的构建,新的媒介技术依托数字仿真技术在打造主体沉浸其中的叙事空间之外,还发挥互动性与主体形成了一种回馈逻辑。这一回馈逻辑往往沉于传统沉浸逻辑之下,但是它的游戏性、互动性暂时性地将人从现代困境中解放出来。
“任何一种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历史舞台时,都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产生冲击并进而发生观念与文化的变迁。”4短视频中的田园想象艺术化地重构和再造田园生活来缓解不断加速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快节奏疲惫;许多当下电影文本也在表现当代人的现代性焦虑的同时塑造一种回乡的愿望;一些书写小城的小说正在诉说着一些别样的现代化追求。多类型的文本都在聚焦现代性焦虑,并且以乌托邦的构想缓解这种焦虑,这是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一个精神史的命题,还是一个关于人内心的命题。王一川认为:“确认人的主体心性活动在其整个人生活动中具有优先性和主动性,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中心和先导因素。”1心性论传统是一个以人为核心要素的现实表现方式,而“云”时代作为一系列媒介技术的集合,正在构建一个虚拟现实的架空模式,直击人的精神和内心困境。它通过技术隐晦地传达其目的,又以技术掩盖了其功能性意义,但是其功能具有大的时代文本所具有的共性。
四、“云”时代作为大写的寓言文本
“云”时代所营造的基于技术的叙事空间还是一个具有悖论性的大写文本。这个大写的文本一方面依托新的媒介技术让现实世界的再现变得更加真实,一方面又用这种打造的虚拟叙事空间缓解或掩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情感焦虑。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具有保存和存在两种特性,所谓保存,就是文本通过创作主体的权威将语言保藏进书写的状态,而存在则是指文本占据了一个具体的位置。“云”时代通过先进的虚拟现实叙事逻辑把主体纳入技术的逻辑范畴,媒介技术的权威代替了传统创作主体的权威,传统的创作主体正在以参与者的身份被纳入一个超越现实的叙事空间。作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叙事空间有着独特的呈现方式。
首先,“云”时代的叙事空间呈现为真实与复现的对立,尤其是网络直播、短视频等传统的媒介景观与VR、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结合在一起,二元的再现逻辑发生了偏转。“云”时代的叙事空间对于真实的再现在此表现为一种“介入性真实”,技术策略对可触及的真实以及不可触及的真实进行编码,参与主体沉浸于被技术编码后的具体形态之中,丧失了寻求和解读真实的欲望,真实虽然被重新编码,或许表现得比现实更为真实,但是真实之于主体却是隐匿的,被搁置的。
其次,“云”时代的叙事空间凸显了作为“第三时间”的阅读时间,而这恰好是技术得以剥夺人的情感逻辑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叙事中,阅读时间——在这里可名之曰‘第三时间——则被看作是不存在的行为,人们会把‘第三时间假定为‘零时间。”2“云”时代的叙事空间正在营造一个以参与主体为核心的情感逻辑,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叙事时间都被搁置,参与主体的阅读时间成为叙事空间的主要架构。当技术遭遇时间,斯蒂格勒试图论证:“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来寻求生命。……生命一旦成为技术,它也就成为滞留的有限性。”3技术的本质并非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其与时间交互所呈现的独特时空架构。主体在技术所营造的叙事空间里,获得了某种基于技术的真实体验,但是却面临着自然时间被技术时间剥夺的被动情境,在此,参与主体的生活体验会因为文本的丰满而变得贫瘠。换言之,生活时间被文本时间掠夺之后,主体为了避免那种生命的空虚,会被挤压到阅读时间时刻去寻求情感的抚慰。
这是一个打破了时空界限的全新世界,“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培根阐述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4。这种难以把握源于技术带来的新变,当然这种难以把握也对于观察视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以“寓言”的方式介入这样一个大写的时代文本。周志强认为:“寓言论批评就是不再相信艺术作品和生活之间直接的关联,它要找到新的编码方式,找到重新编码的艺术文本当中的这些符码,同时认为,这种编码的想象方式依然被一个更加深层的历史原因所决定。”5“云”时代的技术生产作为一个大写的时代文本,应该对于虚拟叙事予以解构,重组技术、时间、主体、情感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一个新的编码体系中重新定义“云”时代的发生。
五、结语:游走于技术、情感与时间之间
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中发问:“人类必须屈从于机械的苛刻逻辑吗?或者能否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技术,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它的创造者呢?”①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困境一直困扰着人类,但是普通大众不会像哲学家或理论家那样去思考技术发展的辩证逻辑,他们只会沉浸于“云”时代的叙事空间里,享受技术带来的愉悦与快感。即便如此,个体的人也不会就此完全成为技术的俘虏,人的情感逻辑虽然在技术的改造下正在由自主性的观看逻辑转向沉浸逻辑,并且有可能在技术的沉浸逻辑和回馈机制之中形成一种“情感惰性”的假象,但是,技术在捕获人的情感让主体陶醉期间,只是暂时性地压制了理性。换言之,在一个充满现代性焦虑的社会,个体有时候甘愿隐藏自己的理性,只是在一个由技术打造的特殊空间和特殊时间里享受自己的症状。
责任编辑 余梦瑶
Redefining the “Cloud” Era: The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and Emotional Logic of Virtual Reality
Sun Liwu
[Abstract] New synthesized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such as ChatGPT, meta-universe, and virtual reality have not only changed the way of human life and learning, but also created the cultural forms of “cloud life”, “cloud entertainment” and “cloud learning”,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interaction methods. The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cloud” era is penetrating into peoples emotions and silently chan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echnology. The subject in the traditional cognitive logic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practice, participated in and completed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carrier of the technology while being captured by the technology, and handed back the subjects autonomy to the object created by the subject while obtaining a sense of participation. The virtual reality narrative created by the technology in the “cloud” era is utilizing the logic of immers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feedback to create an illusion of emotional inertia. This will help construct a virtual reality overhead model that strikes directly at the spiritual and inner dilemmas of human beings, and thus conceals the occurrence of anxieties of modernity, which constitutes the great text of an allegory of the era.
[Keywords] “cloud” era; virtual reality; emotional logic; text of an allegory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2页。
2周志强:《“小故事”的时代——元宇宙与虚拟现实叙事的沉浸逻辑》,《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2期。
3任政:《空间、身体与生存境遇》,《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9期。
4梁剑:《疫情背景下高校“云课堂”在线教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0年第6期。
5余富强、胡鹏辉:《拟真、身体与情感:消费社会中的网络直播探析》,《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7期。
1“云蹦迪”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方式,参与者通过消费获得一个虚拟的人物形象,其不同的礼物消费可以改变虚拟人物在虚拟场景中的位置、动作、服装等特质,参与者通过观看虚拟叙事空间的场景构建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
2“云答题”是一种参与性极强且具有求生欲望的新型叙事,与“云蹦迪”类似,参与者获得一个虚拟形象,所有参与者身处一个虚拟的跑道上。屏幕上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题目,参与者通过弹幕答题,答对得越多,参与者在虚拟空间中的位置就越靠前,这是一种互动性和参与性极强的虚拟现实场景构建。
3喻国明、耿晓梦:《试论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偶像的技术赋能与拟象解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4氪金,即支付费用,特指在网络游戏中的充值行为。参见栾轶玫:《饭圈失范的表象及纠偏》,《人民论坛》2020年第26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虚拟现实所营造的叙事空间具有游戏性的特质。
5周志强:《“小故事”的时代——元宇宙与虚拟现实叙事的沉浸逻辑》,《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2期。
6于光远:《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1童兵:《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周志强:《现实·事件·寓言——重新发现“现实主义”》,《文艺理论》2020年第6期。
1汪政:《现实·现实感·现实主义》,付秀莹编:《新时代与现实主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2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3王小章:《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浙江学刊》2015年第1期。
4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王一川:《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中的心性论传统》,《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2周志强:《游戏现实主义:“第三时间”与多异性时刻》,《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3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4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5周志强:《寓言论批评:寻找新的编码方式》,《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13日,第6版。
1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