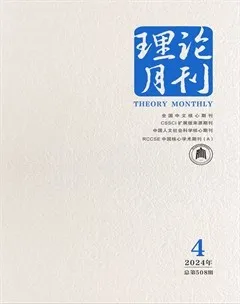“惊喜产业”抑或“赌博盒子”:网络盲盒营销的赌博风险识别

[摘 要] 明确赌博行为识别标准是盲盒产业监管的前置性议题。盲盒商品发源地美国相关司法判例与产业政策显示,即便所涉案件中消费者诉求并未获得支持,即便目前所涉卡片盲盒在美国被视为合法文化商品,却并不能得出“在美国卡片盲盒不是赌博,乃至盲盒不是赌博”的误读,而只能推断得出“卡片盲盒即便是赌博,当前在美国也并不违法”的结论。在比较法视角下借鉴域外相关法律界定,当前研判具体盲盒产品是否赌博之标准应为:一为盒内物品是否涉及转化为现实货币的可能;二为应关注其奖励相对于售价是否过高,比例过小;三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特定盲盒是否严重违背等价有偿原则并制造了交易风险。防止文化掩盖下盲盒赌博交易泛滥应基于上述三重标准进行研判,以期有利于我国盲盒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盲盒;卡片盲盒;交换卡;赌博交易;随机性奖励机制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4.012
[中图分类号] DF414; DF525;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4-011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系统重要性金融科技公司的法律规制研究”(20CFX062);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的‘情感温度”(HBSKJJ2023211)。
作者简介:刘京(1987—),男,民商法博士,湖北大学数字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一、问题提出
所谓盲盒,英文以minifigures、blind boxes或mystery boxes 表示,指一种外观包装相同、内部物品信息隐蔽,包含随机性奖励机制(random reward mechanisms,RRMs),没有固定规律,无法预测奖励出现时间的商品。如目前直播销售中流行的卡片盲盒,便是对交换卡、明星签字照片、衣物切片等文化藏品的发行,借助RRMs机制进行不确定性发售。在全球范围内,这种作为“盒内之物”的文化产品正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据Ebay公司统计,仅2021年度美国本土的交换卡交易增长量达到创纪录的142%,总成交量较前一年度增加了400多万张,其中来自中国买家的销售量增长了205%1。一方面是“盒内之物”受到国内外市场的热烈追捧,另一方面这种具有不确定性、信息不透明、非等价有偿的RRMs发售机制却不能摆脱新型赌博、变相赌博的印象。如国内近期便出现公安机关在某盲盒直播带货中,以招揽赌客进行变相赌博,涉嫌开设赌场罪为由进行抓捕的案例1。假如按照赌博的直观定义,“赌博是这样一种合同:二人达成协议,各自声称对某一未来不确定事件持相反的观点,根据事件的最终结果,一方从对方赢得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其他赌注……双方在该合同中除了会输掉或赢得赌注外,并无其他利益”2。某消费者花费5000元人民币购买一盒美国帕尼尼(Panini)公司发售的2022-23 Panini Prizm Hobby Basketball盲盒,有可能开出一些仅仅价值数百元的普通卡片,也有极小概率开出一张价值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限量版卡片。结合上述对赌博行为的定义,该笔交易的确较为符合“赌博盒子”的印象。即便其可界定为射幸行为,反而加大了嫌疑,因射幸行为并不排斥赌博,“赌博合同可能是最为特殊的射幸合同之一”3。更紧迫的是,作为同样潜藏RRMs的交易安排,原理相同的盲盒商品已经出现于诸多商业消费领域。随着网络平台经济分布式、多元化、共享性特点逐渐凸显,盲盒经济借此东风迅速风靡,引发如玩具盲盒、机票盲盒、球鞋盲盒、虚拟盲盒等商品通过平台不断推陈出新。在高关注度、高流行度、高扩散性的网络商业宣传推动下,这类流量商品也促使监管者不能将目光局限于卡片盲盒,而应立足于整个盲盒产业立场,反思盲盒产业与赌博交易二者的边界。
可喜的是,2023年6月出台的《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明确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以盲盒名义从事或者变相从事赌博活动”4,但盲盒赌博问题的讨论空间依然巨大。首当其冲便是似是而非、不言自明的赌博识别标准,即相关监管活动是否存在明确清晰的赌博认定界限。具体而言,据此条文是否单纯制作发售盲盒便绝对不是赌博?抑或赌博活动也包含盲盒形式?那么划定二者边界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尤其在盲盒商品主要发源地的美国,在盲盒商品目前具有合法性前提下,上述问题更平添几分困惑与隐蔽。对此,国内学界目前多从社会文化层面5、社会情感角度在解释论层面诠释盲盒消费的动因6,较为欠缺规范性维度的批判,尤其是与赌博交易界限的审视。而现有规范性研究又存在对美国相关案例有待商榷的解读,对美国赌博司法监管情况较为粗疏的诠释,对赌博识别标准并不周延准确的界定,也难以划定盲盒产品与赌博交易的清晰界线7。因此,怀揣对监管活动中前置性问题“盲盒是否赌博盒子”的疑惑,本文将从美国相关判例重新出发,尝试针对赌博判定标准问题作出回应。
二、何以必要:重思美国卡片盲盒司法判例的三重动因
作为卡片盲盒的发源地,早期用于收藏的卡片由当时美国烟草制造商装于香烟盒中随机赠送,顺应了部分美国人自维多利亚时代保存纪念品的嗜好。尤其当时因附有棒球球员卡片深受棒球迷好评,其逐渐成为特有的一种收藏品。于是在1890年美国之叶(American Leaf Tobacco)烟草企业径直成立托普斯(Topps)公司,专门制作发行成套体育内容的卡片以回馈卡迷需要8。当前,中国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美国作为盲盒商品发源地,其相关司法监管政策与判例值得关注。但重新思考这些判例,绝不只是涉及单一盲盒市场的监管问题。因为不同的盲盒产品“盒内之物”即便并不相同,但都基于相同的RRMs机制,面临着本质相同的赌博嫌疑。所以考察这些早期、域外的相关司法判例便具有了从盲盒商品源头处寻求监管共性的研究指向。换言之,对美国相关卡片盲盒判例进行批判性解读,并报以严谨与理性态度的发问,亦可成为研判共享RRMs商业逻辑的盲盒商品是否构成赌博交易,乃至思考我国盲盒产业监管制度构建的重要切入点,具体而言:
(一)先例可循:全球最早涉及盲盒是否赌博的司法判例
全球范围内最早有关盲盒是否涉及赌博的司法判例发生在美国的卡片盲盒领域,并作为参照或多或少影响着其他西方国家的监管政策。20世纪中期美国就已陆续爆发部分消费者以卡片盲盒营销涉嫌赌博,违反联邦《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法案)为由,起诉美国盲盒生产商的集体索赔案件1。而这些案件无一例外基于类似理由被法院陆续驳回,并由此衍生出合法商品的司法评价,以及成功地创造了对时尚文化的正当性维护。同时,上述案例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得出本文并不认同,深感忧虑的解读——“在美国,盲盒卡片等实体销售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难以符合赌博行为的认定标准”2。事实上,“当一项活动在特定语境下利大于弊,即便包含了巨大的赌博因素,也会适度容忍,并辅之以强监管政策”3。换言之,如国家福利彩票的发售,在承认存在合法赌博的前提下,某种交易安排能否被识别为赌博,并不等同于该赌博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即前者是客观行为符合性问题,后者则是利益权衡思维下的合法性评价。对美国相关司法判件的粗略考察,很有可能导致研判特定交易行为两个维度问题的逻辑混乱,并简略得出“在美国卡片盲盒不是赌博”的错误印象。甚至,该观点可被进一步加工为当下生产、销售主体所普遍赞同的“盲盒不是赌博”的意见,严重干扰监管者的判断思维。因此,有必要重返上述案例,相对谨慎地回应如下问题:在美国司法语境下,究竟“卡片盲盒不是赌博行为”抑或“即便其是赌博,也并不违法”。
(二)逻辑复制:共享 RRMs 机制的新型盲盒产品不断引发新的质疑
當前,卡片盲盒在美国具有合法性的既定事实,已客观激励了美国其他商业领域不断复制类似商业模式并推广至全球市场。但潜在的社会管理问题又随之而来,导致这些新型盲盒产品是否为赌博的学术讨论与司法诉讼不断。如在电子游戏市场,游戏开发者们模仿了老虎机的视觉和听觉,将可以线上交易的游戏装备或皮肤,利用电子盲盒(战利盒)的RRMs原理进行全球发售。研究显示,全球在战利品盒和皮肤赌博上的总支出(在电子竞技比赛中使用游戏内皮肤物品的赌博,包括从战利品盒中获得的物品),从2018年的300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500亿美元4。尽管批评者呼吁关注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性,指出“这些电子盲盒借用与赌博机制相同的策略来利用物理和心理触发机制”5,尽管比利时、荷兰政府对不符合本国赌博规范的电子盲盒已采取了完全禁止的管制措施6,但目前美国相关诉讼中依然没有出现任何支持消费者索赔的案例。其中一种强而有力、无法回避、无懈可击的类比逻辑便是来自卡片盲盒在美国的既定合法性。北美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ESRB)的辩解具有代表性,“我们不认为战利品盒是赌博……战利品盒更像是棒球卡,其中有惊喜元素,你总能得到一些东西”1。就美国盲盒监管整体现状而言,卡片盲盒相关司法判例已经成为整个盲盒产业回应赌博交易质疑的挡箭牌。而重新回到这些案例,得到合乎逻辑、客观公允的评价,将有利于我们把握盲盒商品RRMs的本质,扫清当前盲盒产业赌博问题上非左即右、全有全无的思维障碍。
(三)产业跃进:美国卡片盲盒超越单一文化产品的质变
即便是卡片盲盒产业本身,其产品特征、产业规模、产业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亟须根据新的商业道德评估与行为性质判断。根据GlobeNewsWire报告显示,仅仅全球体育交换卡单一市场在2019年的价值就为138.2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987.5亿美元,从2020年到2027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3.01%2。在美国司法的合法性背书下,当前美国发行的卡片盲盒总体上较之20世纪初案例中所涉的商品,制作技术更复杂、售价更昂贵、奖励性更高。这种产业在全球范围已形成了包含拍卖、评级、销售等方面的完整链条,完全具备收益性、风险性、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外观。如帕尼尼公司高端系列Eminence Box产品,直接在卡片中嵌入钻石、贵金属。个别情况下该盲盒可开出上百万元人民币的卡片,并经赛事影响、评级打分、商业炒作等因素影响产生巨大的价格波动。这种产品的对价与奖励比例已经明显超出了美国以往案件所涉盲盒的价格范畴与单一文化商品的理解。如在美国第一起相关案件Price v. Pinnacle Brands中,当时美国法院驳回原告消费者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援引《纽约刑法典》关于博彩行为数额的规定 ,认为“在纽约刑法第225.10条中,表面上没有任何内容会惩罚制造商或许可人向单个‘人出售一副纸牌,除非这种纸牌的售价超过500美元。在购卡人的诉状中,没有一个购卡人声称一盒卡的价格超过500美元,更不用说获得插入卡的‘机会的‘价格”3。时过境迁,从产品市场价格看,这一理由几乎没有了事实基础,因为目前大部分产品售价都远远高于此。诸如两百多年来期货交易是否赌博的曲折判断过程,对具有争议性、复杂性、非典型交易行为的界定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过程,需历经时间检验与实践摸索。即便单单对卡片盲盒是否赌博的判断,也不能拘泥于旧有结论,须结合以往相关案例中的司法判断过程,综合考量商品内外部的动态因素,方能在当下给予更准确的答案。
三、何以合法:美国赌博治理背景下卡片盲盒司法判例之解读
在美国联邦法律中并不存在对于赌博行为非常明确、清晰的界定,而有关赌博的联邦法规通常集中表现在违反该游戏行为或行为主体所在州的赌博法规范上。在联邦层面仅有的规范只是罗列典型的赌博类型,如18 U.S.C.§1955(b)(4)之规定:“‘赌博包括但不限于出售赌注、赌博、维护老虎机、轮盘赌轮或骰子桌,以及进行彩票、保险单、博利塔或数字游戏,或在其中出售机会。”4正如有学者批评,“18 U.S.C.§1955完全没有提到互联网赌博或任何现代技术的使用,法律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处理由技术创新产生的新问题”5,上述法条在政府监管赌博中不允许扩大解释,存在着较大的规范真空。事实上,目前赌博的界定、合法性判断均取决于该行为或主体所在州的法律。换言之,每个州都有其各自的定义,而联邦法规适用状况取决于各州法律有可能摇摆的自我判定。如经营网络赌场在美国三个州被认为合法而在其他州被视为非法,正是这样一个复杂、松散与开放的法律规范网络,导致某个赌博行为因所在地不同而可能发生不同评价。另外,纵观美国的赌博演化历史,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与主题:“赌博必须适应法规,法规必须适应赌博。”1之所以各州不是直接禁赌,而是通过规范管理以控制这种产业的掠夺性、破坏性,其短期收益方面的考量是明显的。2018年度美国博彩协会研究报告显示,仅2017年赌博为美国经济贡献了2610亿美元,产生480亿元的税收,提供180万个岗位2。以上,一方面在联邦层面缺乏统一的赌博认定标准,各州在立法与司法层面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各州难以拒绝赌博产业短期的经济诱惑,又受制于赌博产业集团的州议会游说,导致目前美国社会尤其对于新型的赌博活动,并不能采取迅速、统一的公共治理行动,更倾向于接纳、容忍与规范赌博产业。
与卡片盲盒有关的司法案件便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发生的。提取美国各州对于赌博不同定义的要素归纳,赌博构成一般应满足三个普通法要素:机会、奖励、对价。但上述每个要素在不同州的司法审判中都存在适用差异,如:何为奖励?虚拟物品可否成为一种奖励?各州法院存在少数规则与多数规则,二者区别在于是否具备现金价值3;再如,当机会要素掺杂行为人自身的技能,又如何确定要件符合性?各州法院存在主导地位标准 、赌博本能标准、实质性要素标准三种方式4。然而,即便是各要素存在司法理解分歧,具体到“卡片盲盒是否赌博”,至少在系列案件的原告消费者看来并非那么具有争议性。从机会要素看,开启盲盒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偶然性并不涉及技能;从奖励要素看,消费者开启盲盒产品希望获得昂贵的卡片,最终得到了价格不确定的卡片;从对价要素看,消费者通过支付现金购买。这与将硬币投入老虎机相比,唯一可能的区别在于:消费者至少不至于空手而归。但大量证据表明,只有稀有、限量或特定的卡片才具有卡迷追捧的市场价值,才是消费者持续购买的核心动力。心理学研究发现,卡片爱好者若将自己的购买动机分为“只买”和“追逐(稀有)插入卡”两类,后者在“可能病态赌博”量表得分上远高于平均水平5。
事实上,在基于赌博案由的民事索赔诉讼中,盲盒消费者无一例外地被驳回,是否意味着“在美国,卡片盲盒并非赌博”的命题成立?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原告起诉目的便是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尽可能在诉讼活动中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在美国消费者挽回“赌博损失”的诉讼路径无外乎两种选择:依据联邦《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法案)或依据所在州的消费者保护法6。在利益权衡角度下,早期案件选择前者RICO法案寻求救济,原因在于该法18 U.S.Code§1964(C)之规定,“一旦原告胜诉可获得三倍于其所遭受的损害赔偿和诉讼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1。当然,随着该系列案件在RICO法案框架下被全部驳回,自2017年以来美国电子盲盒诉讼的消费者逐渐摒弃这一路径,转向根据各州的损失赔偿法规提起诉讼。因司法主流意见拒绝承认虚拟物品的现实货币价值,至今仍无消费者胜诉案例2。而梳理1996年以来RICO法案框架下基于相同案由的卡片盲盒案例,消费者群体败诉原因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一)规范背景:RICO法案立法目的与赌博民事索赔案件类型并不适配
从立法目的看,RICO法案立法目的与赌博交易的民事索赔案件类型并不适配,导致美国司法系统难以动用该法案支持原告的民事索赔诉求。如前所述,并不存在明确定义赌博行为的联邦法律,而侧重于赌博监管的联邦法规又必须基于州法律的不同定义。这势必导致联邦相关法律只能聚焦赌博监管的某个层面。如1992年的《专业与业余体育保护法》(PASPA)主要用于规范体育博彩行为。2006年的《非法互联网赌博执法法》(UIGEA)没有定义非法赌博,只是针对赌博的金融支付系统,排除互联网运营商在线接受赌博有关金钱的行为3。换言之,即使案件所涉的卡片盲盒是賭博,在联邦层面缺乏契合的法律也是盲盒赌博索赔诉讼活动难以克服的障碍。具体而言,联邦RICO法案旨在遏制有组织的犯罪,防止犯罪组织渗透到合法的商业企业中4。而该法案对赌博交易的规制并未以独立条款予以规定,而是包含在18 U.S.Code§1962(C)“敲诈行为”(racketeering activity)条款之下。在此逻辑体系下,如Reves v. Ernst & Young案、Steele v. Hosp. Corp.of Am案中所表明的司法限制适用的态度,RICO的开放性条款的表象下恰恰是有限的司法适用范围。该法案并不是提供给每一位原告三倍赔偿的诉讼理由,“自由解释条款不等于欢迎将RICO应用于国会从未打算过的新目的”5。
(二)证明要件:RICO法案下的证立要素完全不等于普通法中赌博的构成三要素
与第一点相关,从规范要件的证成看,该法案框架下索赔成立条件并不等于普通法赌博行为成立的三要件。既然法案中赌博行为规制依附于“敲诈行为”条款下,在具体诉讼进程中原告起诉必然要符合该法案的“起诉资格”的特定要求,同时满足法案索赔的四个证立要素:“(1)行为(2)企业(3)通过一种模式(4)敲诈活动”6。在起诉资格的司法审查上,最高法院在1985年的Sedima, S.P.R.L. v. Imrex Co案中确定了一种审查原告起诉资格的先在意见,即RICO中“经济伤害”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勒索活动的谓词行为所造成的直接伤害”,即必须证明一个“专有”的伤害,而不是泛指现金或者机会的损失。这种先在的司法观点具体表现在早期盲盒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案件中,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卡迷“预期利益的损失”,未能显示对其业务或财产的“专有”损害,不符合RICO的资格要求1。此观点随即受到后继所有盲盒判例的认同。另外,即便拥有诉讼资格,原告消费者也很难证明索赔成立的四个要件。在Dumas v. Pinnacle Brands案件中,原告没有指控被告人存在任何欺诈或不诚实的行为,如向购买者虚报出卡几率,因此被认定没有欺骗。在 Allard v. Flamingo Hilton 案件中,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进行交易,获得了交易的好处,所获得的一包卡包括一个真正的获胜机会,很难认定为专有损失2。至此,RICO法案框架下原告诉讼行动的指向已经远远偏离了普通法赌博三要素的证立,消费者也面临完全不同的证明责任与更艰巨的证明任务,当然基于该法案之原告诉请亦在每个案件中被驳回。
(三)案件影响:产业联盟无法承受相关案件败诉或和解后的连锁反应
从诉讼后果来看,在针对赌博产业相对宽松的美国公共政策下,交换卡制造商与体育联盟、球员协会亦无法承受败诉或和解后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早期的案件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曾经尝试和解,如1998年原告与产业联盟的和解会议,但因联盟认为消费者Milberg Weiss的和解的要求过高而最终和解破裂3。事实上,双方和解的后果将导致当时几十亿美金的整个产业迅速崩溃,必定无疾而终。根据教授约翰·科菲(John Coffee)的说法,产业联盟拒绝和解,以免鼓励未来的诉讼4。若必定要将诉讼“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司法对于赌博产业适度容忍、相对宽松的态度则成为案件不得不考虑的潜在因素。在早期的Price v.Pinnacle Brands案中,纽约地方法院判决书反而表达了卡片盲盒即便是赌博亦可接受的观点——“追回赌博损失的法定权利并不意味着赌博交易支付的任何对价本质上是有害的”“纽约州趋势表明,接受有执照的赌博交易是一种道德上可接受的活动,在一个社区中合法和被认可的社会行为的现行标准下,这并不令人反感”“仅仅是非法的赌博交易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有害的,更重要的是活动是否公平、诚实地进行。在本案中,购卡人的指控并不能说明他们因不公平或不诚实的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5。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即便上述案件中消费者并未得到赔偿,即便目前卡片盲盒在美国被视为合法商品,但仍不能得出“在美国卡片盲盒不是赌博”的结论,只能推断出“在美国卡片盲盒即便是赌博,当下也并不违法”。如我国并不将体育福利彩票活动视为违法,区分赌博行为的符合性和合法性两个维度的重要之处在于,虽然符合性判断也会掺杂价值判断因素,但行为识别必须成为合法性判断的前置问题,即“在详细分析法律应对赌博的策略前,首先应辨识赌博”6。换言之,在行为判断标准明确的前提下,假如某个行为很难被识别为赌博,那么无需研判与赌博密切相关的合法性。相反,在一种不言自明的行为性质判断状态下,相关规制策略便会缺乏必要的正当性。因为赌博的合法性维度对应的是如何规制赌博交易的策略问题,是否考虑或如何实现社会各类利益平衡的问题。如表1所示,某种交易即便是合法的,也不能贸然断定其绝非赌博,因不同国家与地区亦存在着大量合法赌博的情形。尤其鉴于美国各州已存在诸多合法赌博产业,美国卡片盲盒即便拥有了合法性,更不能推断其必然不是赌博。相反,美国司法从未以普通法三要素为前提,正面回答卡片盲盒是否构成赌博,并以“未构成特定伤害”为由驳回消费者诉讼资格,加剧了其赌博性质的可讨论性。
四、以何为界:研判盲盒产品赌博交易的三种维度
由上文可发现,美国相关司法判例从未正面回答“卡片盲盒是否赌博”,而立足于当下千变万化的盲盒产品去回应盲盒赌博监管问题,首先须严肃质问的便是“何为赌博”,方能刺破盲盒产品品类与交易方式花式创新的表征。类似于“赌石”是否赌博的思考,一旦依赖于直观、感性、简单的赌博定义,相关非典型交易的识别便会因判断标准的模糊性而充斥分歧。然而,姑且不考虑学理定义,打击赌博特色之处在于,尽管全球管理者都对其保持警惕,但其法律描述却呈现出各有侧重的表述。这是因为,不同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行为的直观性,作为处分自身财物的赌博交易具有较大价值判断空间,也兼具隐蔽性、复杂性。如普通法三要素中对机会要素的判定,美国至少有七个州采用的是实质性要素测试,实质性的含义却没有统一定义。法官往往依靠陪审团意见方可判定,但“法官或陪审团也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提供的证据、专家意见以及案件的事实和情况,对特定游戏中对什么是实行性机会产生不同看法”1。由此,尤其鉴于我国当前较为简洁的赌博定义,判定盲盒产品及其衍生的交易行为是否为赌博的难点,关键在于标准的确证。而梳理全球有关界定,除行为人获利动机的主观因素外,以下为可供参考的最低限度客观要件。
(一)对象维度:参与者具有客观上获利的可能性
一般认为,赌博交易须指向财物,即以财物输赢作为不可或缺的要素。该要件在美国、加拿大普通法三要素中的表现为“奖励”(value)要素,在比利时《博彩法》中表达为“收益”(gain)2,在日本相关文件中表达为“财物的得失”(財物の得喪)3。目前,包括卡片盲盒在内的绝大部分盲盒内的物品明显具有财物属性,争议之处在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除现实钱财外,是否应当包含某种机会、权益或者可转让交易的虚拟物品。例如,在盲盒产业最新动向上,生产商已利用区块链加密技术与线上支付手段,向市场推广各类可交易流通的NFT(Non-Fungible Token)交换卡。对此,作为同属虚拟物品的游戏盲盒(战利盒),其是否构成赌博的域外判定观点可供参考。
美国在有关诉讼中多数司法意见主张“奖励”要素应限定于现实财物,英国赌博委员会以游戏中并不一定包括“随时可获得兑现或将奖励的游戏道具兑换成金钱或金钱价值的机会”4,亦排除了虚拟物品为赌博要素。相反,日本消费者事务局2012年依据《不当赠品类与不当标注防止法》中“任何物品、金钱或其他经济收益”之“赠品”定义,认定游戏盲盒须接受严格监管。同时,比利时政府以价值(value)可被定义为“可用性”,荷兰政府以“可转移性而具有市场价值”之标准,亦分别作出禁止发售的类似规定5。在我国,2020年《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第六条要求游戏不得宣扬赌博内容,尤其是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要求经营者应依法取得“游戏游艺设备电子标识”,以概率性方式提供实物奖励应当明示概率范围1。同时,2020年《关于规范网络游戏经营秩序,查禁利用网络游戏赌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规定,“对于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兑换为虚拟货币、游戏道具等虚拟物品,并用其作为筹码投注的,赌资数额按照购买虚拟物品所需资金数额或者实际支付资金数额认定”。从比较法视角,我国目前已关注到虚拟物品赌博的问题,倾向于将向经营者兑换现金的虚拟物品予以直接认定。问题复杂之处在于,假如并不直接或间接兑换虚拟物品,盲盒发行商只是默许了虚拟物品存在自由交易的情形,是否符合此要件。《通知》仅简略地就“游戏积分”作出规定,即“不得提供用户间赠予、转让等游戏积分转账服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剖析。
梳理当前全球范围内主要认定标准,其门槛条件由低到高分别为:比利时的“有用性”標准,荷兰的“可转移性而具有市场价值”标准,英国的“向经营者兑换”标准,美国的“现实价值”标准。取舍上述判定标准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定位、理解网络空间的意义,从而明确虚拟物品的现实价值。事实上,当现代人所感、所知、所为的全部已由智能网络深度介入,人被悬置于这一现代环境并栖居于此,与其互构而存在2。因此,虚拟物品与现实各类系统,尤其是经济系统的关联程度,可成为进一步研判的重要依据。学者Nielsen与Grabarczyk密切关注到此点,认为电子游戏的花费(cost)与奖励的价值(value)可以孤立于现实世界,即在虚拟世界之外毫无价值,也可“嵌入”(embed)现实世界经济系统中,即转化为现实世界的金钱3。他们在梳理四种不同类型虚拟物品的RRMs盲盒机制之后,认为“嵌入式—嵌入式”(embed—embed)交易应构成赌博,即“花费现实世界金钱参加—奖励回报具有现实世界的价值”4。尽管亦有学者呼吁其他两种RRMs模式仍具有现实危害,如“不以现实金钱为代价的购买”或“不提供现实金钱的奖励”5。但此处我们可提炼出一个最低限度且全球多数国家认同的识别门槛,即盒内虚拟物品可被转化为现实世界财物的可能性。目前除美国、英国外,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国家均在包含此标准的基准上,展开对盒内虚拟物品是否构成赌博获利要素的研判。
(二)方式维度:以财物奖励方式满足参与者之不确定性偏好但构成滥用
常规情景下,交易者以寻求经济活动的确定性为目的,如私法中的“等价有偿”“情势变更”“租赁合同最长期限”等规定,均旨在尽量排除交易过程中不确定性因素。但赌博交易反其道行之,刻意追逐不确定性因素,使参与者产生愉悦感、刺激感、紧张感等复杂心理反应。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中有所体现,在美国普通法要素、比利时赌博法中直接表达为“机会”(chance)要件。难点在于,到底多少不确定成分才能达到赌博程度。如此所述,目前美国司法三种不同的判断模式,均严重依赖主观价值判断,含有相当浓厚的主观色彩。比利时博彩委员会对在“机会游戏”表述中只要求“机会是一个因素”1,似乎又过于宽泛,接近于美国司法鲜有采用的“任何机会标准”(any chance test)。梳理上述判断方案,必须承认的是,假如始终立足于第三方、外部视角并以结果分析为导向,那么判断者主观價值因素之介入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交易或多或少客观包含不确定性或运气。如时下“以房养老”模式,人的寿命具有不确定性,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就越高。一种解释认为金融机构的介入,在投保人基数庞大的条件下,已有效消除其中不确定因素而不构成赌博2。但这个观点即便成立,在没有金融机构介入的“遗赠扶养协议”“律师风险代理”中,又如何消除不确定性?事实上并没有,一般亦未视为赌博。问题的理解在于,不确定性因素本身就包含着好与坏的评价判断空间,涉及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社会容忍程度与接受程度问题。如在律师风险代理中,代理人更加尽职尽责,被代理人权益因此得到更好的维护,故社会普遍接纳此种“好”的不确定性交易。
在盲盒产品不确定性判断问题上,若仅仅站在第三方与外部的价值判断立场,我们将无法缜密地给出其符合赌博的结论。尽管开启盲盒全凭运气,但运气也带来了惊喜、娱乐,也促进了盒内物品的流通与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似乎并不具有无可辩驳的可责性。然而,从行动者立场与动机维度,反思赌徒对不确定性因素乐此不疲,对运气趋之若鹜的典型行为特征,亦应成为关键线索。而由赌徒心理可明显发现,赌博者之所以痴迷于运气,在于存在前述财物奖励。更为关键的是,奖励性愈高,赌博动机、欲望、情绪愈发强烈,行为赌博特征就会愈明显,理据至少为三点:
其一,赌博虽始于娱乐,但一旦形成财物转移,“某些形态的游戏就开始从娱乐的边缘滑向异途,蜕化为赌博”3,即财物数额成为赌博与娱乐的重要边界。早在2005年相关司法解释中就已将钱财数额作为关键判断标准4。在字面解释中,“少量财物输赢”中“少量”对应的便是奖励数额。其二,感觉寻求是指个体对多变的、新异的、复杂的和强烈的感觉以及体验的寻求,并通过采取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实现这些体验的愿望5。即便是偶尔赌博,研究表明高额的奖励也将显著影响行为人风险决策,刺激行为人在风险决策中做出不利选择,是赌博成瘾性、掠夺性、刺激性不可或缺的原因。其三,赌博行为危害性之一便是造成参与人赌博障碍,而高额奖励与这种精神疾病互为因果。赌博障碍者表现之一就是近赢,更倾向于将接近赢钱而实际损失视为积极的结果6,因为“近赢会提高赌博者的赌博动机,并且会使奖赏相关的脑区激活增加”7。同时赌博也需要更高的奖励,因为赌博障碍者对奖赏的敏感性更低,其多巴胺系统功能异常,需要更大的奖励来建立和正常人相同的体验8。
由此,除对不确定性因素的中立、外部立场分析外,财物奖励的数额、比例也应成为研判特定盲盒产品是否赌博的关键标准。如彩票、老虎机、百家乐,真正的赌博往往采用高额奖励作为诱惑手段,利用以小博大来引诱交易者反复参与。此外,超越游戏层面的高额奖励亦应成为评估特定盲盒交易异化为赌博的重要参考,若由单一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财物奖励极为高昂、比例或概率又较小,便具有了引诱赌博的嫌疑。
(三)外部维度:人为制造额外的交易风险或升高固有的交易风险
此处的交易风险,指基于交易行为所导致的行为人财产状况遭受损害的可能。德国刑法通说认为,赌博交易意欲自己得利,给他人财产造成了危险,具有危害性,“是一种有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危险行动行为,而且只有这种具有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危险的行为,才具有可罚性”1。赌博交易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就是人为制造额外的、非必要的交易风险,显著提高了参与者自身财物损失的可能。其与保险交易的区别关键在于,交易者风险是分散、降低抑或制造、升高,“若原本是当事人所承担的风险,则与他人缔约分散该风险即属保险”2。早期国内有观点认为,“赌博行为有导致参赌者财产损失的危险,但赌博者本人是愿意承担这一危险的”3,故主张赌博罪不宜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之中。但此观点大大低估了个体风险的传导性与聚合性,因个人财产状况的剧烈波动,从来不只是风险自甘的私人事务。大量案例表明,因特定主体赌博行为所导致的后继违约、破产乃至违法行为,会因将无关他者卷入动荡的困境而产生风险传递现象,甚至因特定个体的特殊市场地位产生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风险。尽管赌博行为的外部风险涉及后继如何消除的对策问题,但此处并不影响将其作为符合性的必备要素。
如购买股票、期货后的涨跌是否构成赌博风险,问题在于因风险无处不在,对赌博风险要素理解亦须加以限制,防止解释泛化而导致后继监管范围过大,抑制相关交易市场的活力。但在回答之前,对赌博风险的诠释明确包含以下题中之义,即何种类型风险是国家管理者真正需要以赌博为名而警惕的,其至少包含以下三层限制:
其一,固有交易风险的排除,即“赌博是人为地制造额外的风险”4。所谓固有性,便是行为人从事常规交易活动时凭主观努力亦无法规避、无法改变、无法置身事外的客观风险,其与人为性、非必要性、异质性相反,表现为从事某种交易活动面临风险的常态性与必然性。如“赌石”交易从感官上十分接近赌博,但原料内部品相是该行业至今任何一方都无法精准预判的,单纯原料买卖的风险便具有了固有性。然而,人为附加、制造超越矿石内部价值之外的风险,如不以买卖为目的,完全以原石品质作为金钱的博弈条件,便极有可能异化为赌博交易。其二,转移、分散风险的交易行为排除。即交易行为可能引发特定个体风险状况的恶化,但在风险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特定市场总体性风险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产生风险对冲、转移的整体效应。如对期货交易的合理性解释便是,该交易安排实现了市场总体风险在立场不同主体之间的再分配,即“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将社会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风险由风险厌恶者转移至准备更充分的投机者的活动”5。其三,关联市场真实需求的交易行为须谨慎辨别。纯粹的赌博只是基于钱财投机与娱乐目的,与此处市场真实需求无关。但在某些交易安排中,赌博交易与具有真实需求的正当交易往往难以区分。一旦总体禁止了交易,亦遏制了真正的市场需求,往往需要管理者予以强制性监管而非“一刀切”取缔。
依上述分析,我们反观盲盒产品所共通的RRMs发售机制,其属于典型的人为设定、人为制造。若出现严重的货不对价,其并不属于固有风险,也未转移、分散、降低风险,反而系人为升高、创设交易风险。典型如帕尼尼公司的Instant系列卡片在官网直接销售而不是以盲盒方式,“盒内之物”完全可以用等价售卖、平台竞拍方式满足市场的客观需求。换言之,即便特定市场拥有真实的“盒内之物”需求,但其售卖未必具有须以盲盒RRMs机制为方式的必然性、固有性。因此,若特定盲盒产品严重违背等价有偿,造成购买者较大的财产损失,应被视为一种人为制造的赌博风险。上述理解也从交易风险角度进一步验证了国家市场监督局的最新规定,其明确要求盲盒商品价格不应与同质同类非盲盒销售商品价格差距过大。
五、研究结论:走出美国相关判例的藩篱
回答盲盒是不是赌博又如何监管的前提,便是首先以结构主义哲学思维置身于商品对立面,谨慎地质问“何为赌博”。一直以来,“在美国卡片盲盒不是赌博”乃至“盲盒不是赌博”的错误结论,似乎成为我们审视这一商品,探索如何监管问题的障碍。退一步而言,即便美国相关判例得出相关盲盒并非赌博的司法结论,亦不能成为阻止全球不同地域的管理者独立判断,制定符合本地公共利益之监管政策的正当理由。因为纵观域外制定法,赌博界定的多样性亦促使我们积极探索展现本国治理智慧、符合本国公共政策的认定方式。如在比利时、荷兰监管游戏盲盒活动中,尽管曾遭到美国电子游戏商的反对,但最终游戏商服从当地政府决定,在游戏中修改或删去不符合当地赌博监管规范的盲盒产品。相较之,缺乏正确的问题意识、空白的监管政策与产业公共利益的缺失,极大概率会引发特定市场的野蛮生长,呈现非合作博弈下参与主体的双输局面。政府清晰、明确的行为识别恰恰是防止文化产品掩盖下“赌博盒子”泛滥的第一步。如前所述,研判赌博行为标准的发问,可粗略转化为以下回应:
其一,盲盒“盒内之物”是否有转化为现实货币的可能。其二,盲盒必须包含RRMs机制,但其奖励钱物相对于售价是否过高,比例过小。其三,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特定盲盒是否严重违背等价有偿原则而制造了赌博风险。如无特别规定,依当前司法解释“不合理低价”的规定1,可推定损失上限为实际交易价的30%。
进一步分析,上述三条标准须同时满足,特定盲盒产品方可视为赌博。若只是符合其中某些部分虽很有可能涉及其他市场监管问题,如过度营销、消费欺诈,却唯独不能视为赌博。例如,不符合标准一的情形,消费者所得之物不具有转化为任何现实货币可能,绝非赌博。此情形类似游戏“斗地主”中盲盒“欢乐豆”并不存在任何转化为现金的可能,只能视为一种游戏。如符合标准二,不符合标准三的情形,此时消费者往往是受益者,不存在风险性又兼具奖励性,亦不应视为赌博。再如符合标准三,不符合标准二的情形,亦无须以赌博为名考察此类产品。因为此意味着该产品既无可观的奖励又无法等价有偿。其要么无人问津后退出消费市场,要么以降价方式获得市场认可。
必须承认的是,财物奖励的比例与大小问题,无法在盲盒不断更新的花式产品类型中设定一个通用上限标准,亦需管理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予以权衡。但目前市场销售的部分产品的确存在奖励过高、过小的弊端,如前述的2023 Panini Hobby Basketball盲盒产品可开出相对于其售价数十倍以上、价值十万左右的全球限量的卡片,并经评级加持达到更高价格。可供参考的建议是,监管者可适当调控盲盒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适当增加生产者市场责任,要求其公开奖励价值信息,而非仅仅披露不知价格的商品类型(配置)的比例,或经实质性审核后方可售卖,即以行政审查许可方式督促生产者控制奖励过高、比例过小的问题。当然,即便特定盲盒符合赌博性质,并不代表无法挽救,需要监管部门考察有无必要利用税费收取、公益目的限制、指定场所交易、强制披露回报率、设定消费提示义务、设定回报率与奖励上限等措施,进一步消除其涉及赌博要素。当然,作为一种新生的流量文化商品,更需要结合法学、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等学科进一步研判。
责任编辑 杨 幸
1eBay News Team:“2021 State of Trading Cards Report Spotlights Collecting Trends and Industry Predictions”,2021年2月11日,https://www.ebayinc.com/stories/news/ebays-2021-state-of-trading-cards-report-spotlights-collecting-trends-and-industry-predictions,2023年2月5日。
1《孝感警方侦破全国首起“球星卡”新型网络赌博案件》,2022年2月2日,https://news.hubeidaily.net/pc/271491.html,2023年2月5日。
2 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张文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3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
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国市监稽发〔2023〕39号)第19条,2023年6月15日,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zfjcs/art/2023/art_e2facd76a7fb4e90b03912cffb5e7d53.html,2023年8月19日。
5李琦、闫志成:《自我的迷失与消解式抵抗——网络盲盒亚文化的后现代语境解读》,《求索》2021年第2期。
6曾昕:《情感慰藉、柔性社交、价值变现:青年亞文化视域下的盲盒潮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第1期。
7馬治国、徐济宽:《数字经济背景下“盲盒”营销模式的法律治理》,《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第1期。
8黄迎新、仝泽宇:《球星卡:我国足球产业发展的“蓝海”》,《体育文化导刊》2018年第8期。
1McDonough R E,“Loot Boxes: Its a Trap!”Northern Kentucky Law Review ,vol. 62, no. 46, 2019,pp.1-23.
2马治国、徐济宽:《数字经济背景下“盲盒”营销模式的法律治理》,《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3朱建华、高袁:《论赌博行为犯罪化的法理基础》,《政法论丛》2017年第1期。
4Xiao L. Y. ,“Which Implementations of Loot Boxes Constitute Gambling? A UK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otential Harms of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vol. 1, no. 20, 2022,pp.437-454.
5Andrew V. Moshirnia,“Precious and Worthles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oot Boxes and Gambling,”Minn. JL Sci. & Tech, no. 20, 2018,pp.77-114.
6Sheldon A. Evans,“Pandoras Loot Box,”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no. 90,2022,pp.376-444.
1David Zendle, Paul Cairns,“Video Game Loot Boxes are Linked to Problem Gambling: Result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PloS one, vol. 13, no. 11, 2018, pp.1-12.
2GlobeNewsWire:“Global Sports Trading Card Market Report 2021”,2021年10月28日,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1/10/28/2322880/28124/en/Global-Sports-Trading-Card-Market-Report-2021-Market-was-Valued-at-13-82-Billion-in-2019-and-is-Projected-to-Reach-98-75-Billion-by-2027-Growing-at-a-CAGR-of-23-01.html,2023年3月18日。
3Price v. Pinnacle Brands, Inc., 138 F.3d 602 (5th Cir. 1998).
4The United States Code,18 U.S.C.§1955(b)(4).
5Ajay Harish,“The New Slot Machin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Learn to Stop Loving the Loot Box,”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no.36, 2022,pp.131-164.
1Kevin Liu,“A Global Analysis into Loot Boxes: Is It‘VirtuallyGambling?”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28, 2019,pp.763-800.
2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National Economic Impact of the U.S. Gaming Industry”,2021年6月1日,https://www.americangaming.org/resources/national-economic-impact-of-the-u-s-gaming-industry/,2023年4月23日。
3Jason Egielski, “Dont Hate the Player, Hate the Game: Video Game Loot Boxes, Gambling, and a Call f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Hofstra Law Review,no.50,2021,pp.174-212.
4Erica Okerberg,“Whats in a Game: A Test under Which We May Call a VGT a Gambling Game Is Not So Sweet: Why Courts Should Not Apply the Material Element Test to VGTS, ” Unlv Gaming Law Journal, no.5, 2014, pp.27-47.
5Elliott S A, Mason D S, “Emerging legal issues in the sports industry: are trading cards a form of gambling”, Legal Aspects Sport, no.13, 2002,pp.101-112.
6Brewer A,“The Hunt for Loot: Proposed Solutions to More Effectively Regulate Addictive Gambling Mechanics in Video Games,”JL & Poly, no.29, 2020,pp.158-172.
1United States Code, 18 U.S. Code§1964.
2McDonough R E,“Loot Boxes: Its a Trap!”Nother Kentuck Law Review, vol.62, no.46, 2019, pp.1-23.
3Castillo D J,“Unpacking the loot box: How gamings latest monetization system flirts with traditional gambling methods,”Santa Clara L. Rev., no.59, 2019, pp.166-201.
4Mudd C D, “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 LP: Swapping Trading Cards for Treble Damages - Can Individuals Really Sue Trading Card Companies under the RICO Act,” Villanov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no.10, 2003, pp.357-377.
5Mudd C D, “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 LP: Swapping Trading Cards for Treble Damages - Can Individuals Really Sue Trading Card Companies under the RICO Act,” Villanov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no.10, 2003, pp.357-377.
6Kevin Liu,“A Global Analysis into Loot Boxes: Is it‘VirtuallyGambling?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28, 2019, pp.763-800.
1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 LP, 300 F.3d 1083 (9th Cir. 2002).
2Elliott S A, Mason D S, “Emerging Legal Issues in the Sports Industry: are Trading Cards a Form of Gambling,”Legal Aspects Sport, no.13, 2002, pp.101-112.
3McGregor G, “Sports Cards Denounced as Gambling Racket: Lawsuit Targets Valuable Chase Cards,” Ottawa Citizen, 1999,p. AI.
4McGregor G, “Sports Cards Denounced as Gambling Racket: Lawsuit Targets Valuable Chase cards,” Ottawa Citizen, 1999, p. AI.
5Price v. Pinnacle Brands, Inc., 138 F.3d 602 (5th Cir. 1998).
6許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Erica Okerberg,“Whats in a Game: A Test under Which We May Call a VGT a Gambling Game Is Not So Sweet: Why Courts Should Not Apply the Material Element Test to VGTS,” Unlv Gaming Law Journal, no.5, 2014. pp.27-47.
2Belgium Gaming Act,Article 2 (1).
3日本法律目前没有关于赌博的定义,但2018年2月20日(平成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日本参议院《质询信》(内閣参質一九六第一三号)针对参议院议员真山勇一提出的关于赌博定义及认识的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参见日本参议院:《賭博及びギャンブル等の定義及び認識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2018年2月20日,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syuisyo/196/syuh/s196013.htm,2023年5月30日。
4UK Gambling Commission:“Virtual currencies, eSports and social gaming - discussion paper”,2021年10月8日,https://www.gamblingcommission.gov.uk/about-us/page/virtual-currencies-esports-and-social-gaming-discussion-paper,2023年5月15日。
5McDonough R E,“Loot Boxes: Its a Trap!” Nothern Kentuck Law Review, vol. 62. no. 46, 2019, pp.1-23.
1《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19〕129号,2019年11月21日,https://www.mct.gov.cn/preview/whhlyzcxxfw/wlrn/202012/t20201228_920281.html,2020年12月28日。
2刘京:《媒介社会下“流量”实在论:基于“数据—权利”之视角批判》,《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第7期。
3Nielsen, Rune Kristian Lundedal, and Pawel Grabarczyk, “Are Loot Boxes Gambling?: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 Video Games,” Transactions of the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no.4, 2019, pp.171—207.
4Nielsen, Rune Kristian Lundedal, and Pawel Grabarczyk, “Are Loot Boxes Gambling?: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 Video Games,”Transaltions of the Digltal Games Reseach Association, no.4, 2019, pp.171—207.
5Xiao L.Y.,“Which Implementations of Loot Boxes Constitute Gambling? A UK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otential Harms of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vol 1. no. 20, 2022, pp.437—454.
1Belgium Gambling Act ,CHAPTER I, Art. 2. 1.
2許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戈春源:《赌博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
5Zukerman M, “The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V (SSS-V): Still Reliable and Vvalid,”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43, no. 5,2007,pp.1303—1305.
6Belisle J, Dixon M R,“Near Misses in Slot Machine Gambling Developed Through Generalization of Total Wins,”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no.32, 2016, pp.689—706.
7H, W, Chase,“Gambling Severity Predicts Midbrain Response to Near-Miss Outcom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vol.30, no.18, 2010, pp.6180—6187.
8Meng Y J et al., “Reward Pathway Dysfunction in Gambling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vol.275, 2014, pp.243—251.
1章惠萍:《论我国赌博行为的刑法规制》,《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
2许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章惠萍:《论我国赌博行为的刑法规制》,《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
4Borna S, Lowry J, “Gambling and Specul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87,pp.219-224.
5冯果、余猛:《期货交易与赌博的法律关系之辨》,《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十九条规定。
1eBay News Team:“2021 State of Trading Cards Report Spotlights Collecting Trends and Industry Predictions”,2021年2月11日,https://www.ebayinc.com/stories/news/ebays-2021-state-of-trading-cards-report-spotlights-collecting-trends-and-industry-predictions,2023年2月5日。
1《孝感警方侦破全国首起“球星卡”新型网络赌博案件》,2022年2月2日,https://news.hubeidaily.net/pc/271491.html,2023年2月5日。
2 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张文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3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时代法学》2010年第2期。
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国市监稽发〔2023〕39号)第19条,2023年6月15日,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zfjcs/art/2023/art_e2facd76a7fb4e90b03912cffb5e7d53.html,2023年8月19日。
5李琦、闫志成:《自我的迷失与消解式抵抗——网络盲盒亚文化的后现代语境解读》,《求索》2021年第2期。
6曾昕:《情感慰藉、柔性社交、价值变现: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的盲盒潮玩》,《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第1期。
7马治国、徐济宽:《数字经济背景下“盲盒”营销模式的法律治理》,《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哲學社会科学版)2022第1期。
8黄迎新、仝泽宇:《球星卡:我国足球产业发展的“蓝海”》,《体育文化导刊》2018年第8期。
1McDonough R E,“Loot Boxes: Its a Trap!”Northern Kentucky Law Review ,vol. 62, no. 46, 2019,pp.1-23.
2马治国、徐济宽:《数字经济背景下“盲盒”营销模式的法律治理》,《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3朱建华、高袁:《论赌博行为犯罪化的法理基础》,《政法论丛》2017年第1期。
4Xiao L. Y. ,“Which Implementations of Loot Boxes Constitute Gambling? A UK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otential Harms of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vol. 1, no. 20, 2022,pp.437-454.
5Andrew V. Moshirnia,“Precious and Worthles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oot Boxes and Gambling,”Minn. JL Sci. & Tech, no. 20, 2018,pp.77-114.
6Sheldon A. Evans,“Pandoras Loot Box,”Th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no. 90,2022,pp.376-444.
1David Zendle, Paul Cairns,“Video Game Loot Boxes are Linked to Problem Gambling: Results of a Large-scale Survey, ”PloS one, vol. 13, no. 11, 2018, pp.1-12.
2GlobeNewsWire:“Global Sports Trading Card Market Report 2021”,2021年10月28日,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1/10/28/2322880/28124/en/Global-Sports-Trading-Card-Market-Report-2021-Market-was-Valued-at-13-82-Billion-in-2019-and-is-Projected-to-Reach-98-75-Billion-by-2027-Growing-at-a-CAGR-of-23-01.html,2023年3月18日。
3Price v. Pinnacle Brands, Inc., 138 F.3d 602 (5th Cir. 1998).
4The United States Code,18 U.S.C.§1955(b)(4).
5Ajay Harish,“The New Slot Machin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Learn to Stop Loving the Loot Box,”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no.36, 2022,pp.131-164.
1Kevin Liu,“A Global Analysis into Loot Boxes: Is It‘VirtuallyGambling?”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28, 2019,pp.763-800.
2American Gaming Association:“National Economic Impact of the U.S. Gaming Industry”,2021年6月1日,https://www.americangaming.org/resources/national-economic-impact-of-the-u-s-gaming-industry/,2023年4月23日。
3Jason Egielski, “Dont Hate the Player, Hate the Game: Video Game Loot Boxes, Gambling, and a Call f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Hofstra Law Review,no.50,2021,pp.174-212.
4Erica Okerberg,“Whats in a Game: A Test under Which We May Call a VGT a Gambling Game Is Not So Sweet: Why Courts Should Not Apply the Material Element Test to VGTS, ” Unlv Gaming Law Journal, no.5, 2014, pp.27-47.
5Elliott S A, Mason D S, “Emerging legal issues in the sports industry: are trading cards a form of gambling”, Legal Aspects Sport, no.13, 2002,pp.101-112.
6Brewer A,“The Hunt for Loot: Proposed Solutions to More Effectively Regulate Addictive Gambling Mechanics in Video Games,”JL & Poly, no.29, 2020,pp.158-172.
1United States Code, 18 U.S. Code§1964.
2McDonough R E,“Loot Boxes: Its a Trap!”Nother Kentuck Law Review, vol.62, no.46, 2019, pp.1-23.
3Castillo D J,“Unpacking the loot box: How gamings latest monetization system flirts with traditional gambling methods,”Santa Clara L. Rev., no.59, 2019, pp.166-201.
4Mudd C D, “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 LP: Swapping Trading Cards for Treble Damages - Can Individuals Really Sue Trading Card Companies under the RICO Act,” Villanov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no.10, 2003, pp.357-377.
5Mudd C D, “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 LP: Swapping Trading Cards for Treble Damages - Can Individuals Really Sue Trading Card Companies under the RICO Act,” Villanov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no.10, 2003, pp.357-377.
6Kevin Liu,“A Global Analysis into Loot Boxes: Is it‘VirtuallyGambling?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no.28, 2019, pp.763-800.
1Chaset v. Fleer/Skybox International, LP, 300 F.3d 1083 (9th Cir. 2002).
2Elliott S A, Mason D S, “Emerging Legal Issues in the Sports Industry: are Trading Cards a Form of Gambling,”Legal Aspects Sport, no.13, 2002, pp.101-112.
3McGregor G, “Sports Cards Denounced as Gambling Racket: Lawsuit Targets Valuable Chase Cards,” Ottawa Citizen, 1999,p. AI.
4McGregor G, “Sports Cards Denounced as Gambling Racket: Lawsuit Targets Valuable Chase cards,” Ottawa Citizen, 1999, p. AI.
5Price v. Pinnacle Brands, Inc., 138 F.3d 602 (5th Cir. 1998).
6許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Erica Okerberg,“Whats in a Game: A Test under Which We May Call a VGT a Gambling Game Is Not So Sweet: Why Courts Should Not Apply the Material Element Test to VGTS,” Unlv Gaming Law Journal, no.5, 2014. pp.27-47.
2Belgium Gaming Act,Article 2 (1).
3日本法律目前没有关于赌博的定义,但2018年2月20日(平成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日本参议院《质询信》(内閣参質一九六第一三号)针对参议院议员真山勇一提出的关于赌博定义及认识的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参见日本参议院:《賭博及びギャンブル等の定義及び認識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2018年2月20日,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syuisyo/196/syuh/s196013.htm,2023年5月30日。
4UK Gambling Commission:“Virtual currencies, eSports and social gaming - discussion paper”,2021年10月8日,https://www.gamblingcommission.gov.uk/about-us/page/virtual-currencies-esports-and-social-gaming-discussion-paper,2023年5月15日。
5McDonough R E,“Loot Boxes: Its a Trap!” Nothern Kentuck Law Review, vol. 62. no. 46, 2019, pp.1-23.
1《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19〕129号,2019年11月21日,https://www.mct.gov.cn/preview/whhlyzcxxfw/wlrn/202012/t20201228_920281.html,2020年12月28日。
2刘京:《媒介社会下“流量”实在论:基于“数据—权利”之视角批判》,《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第7期。
3Nielsen, Rune Kristian Lundedal, and Pawel Grabarczyk, “Are Loot Boxes Gambling?: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 Video Games,” Transactions of the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no.4, 2019, pp.171—207.
4Nielsen, Rune Kristian Lundedal, and Pawel Grabarczyk, “Are Loot Boxes Gambling?: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 Video Games,”Transaltions of the Digltal Games Reseach Association, no.4, 2019, pp.171—207.
5Xiao L.Y.,“Which Implementations of Loot Boxes Constitute Gambling? A UK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otential Harms of Random Rewar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vol 1. no. 20, 2022, pp.437—454.
1Belgium Gambling Act ,CHAPTER I, Art. 2. 1.
2許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戈春源:《赌博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3号)》。
5Zukerman M, “The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V (SSS-V): Still Reliable and Vvalid,”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43, no. 5,2007,pp.1303—1305.
6Belisle J, Dixon M R,“Near Misses in Slot Machine Gambling Developed Through Generalization of Total Wins,”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no.32, 2016, pp.689—706.
7H, W, Chase,“Gambling Severity Predicts Midbrain Response to Near-Miss Outcome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vol.30, no.18, 2010, pp.6180—6187.
8Meng Y J et al., “Reward Pathway Dysfunction in Gambling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of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ies,”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vol.275, 2014, pp.243—251.
1章惠萍:《论我国赌博行为的刑法规制》,《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
2许德风:《赌博的法律规制》,《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3章惠萍:《论我国赌博行为的刑法规制》,《法学评论》2006年第3期。
4Borna S, Lowry J, “Gambling and Specul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87,pp.219-224.
5冯果、余猛:《期货交易与赌博的法律关系之辨》,《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十九条规定。